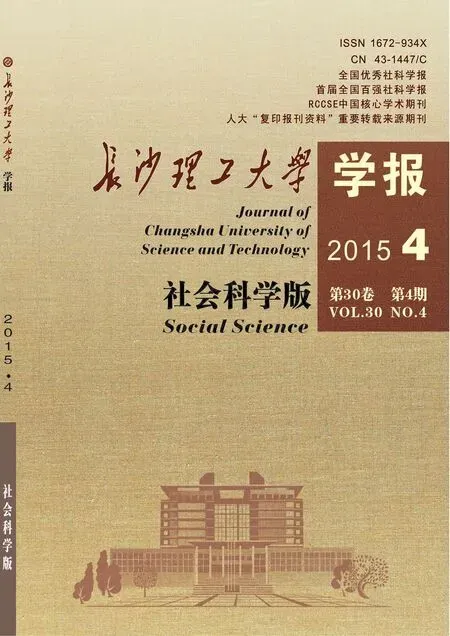论张枣诗歌的“内在超越”
2015-02-21赵飞
赵 飞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论张枣诗歌的“内在超越”
赵 飞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依托具体文本,文章从文化思想、存在意识等方面对张枣的古典诗学渊源进行探溯。由“天人合一”思想集中体现的儒家文化意识,让张枣相信诗人应该在诗歌中重建人与世界、自我的和谐关系。他的诗歌内含对现世生命的体谅,对生命领略麦芒似的浓缩,并注重把世界糅合进心境中取其精粹,在诗境中提升人境,以“内在超越”追求诗与生命的动态和谐,在诗歌中赢得“溢满尘世的美满”。
张枣;天人合一;儒家;“内在超越”
诗人张枣是以“内在超越”,即吸收儒家的“内圣”思想,如明儒王阳明那样一种“动态的理想主义”来守护他的诗歌理想,在“日常之神的磁场”中来感应诗与世界万物的同一感,包容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光是彼世的那个超验世界,也是此世的活生生的周遭世界。这里,就有现代基督精神与儒家思想的对话与交流。神学家汉斯·昆在论述荷尔德林时曾说,“对于现代宗教,某种决定性的东西产生了”:
上帝、神性——或者如人们通常所称的终极的最真实的现实——不再从素朴的人类学上,看作是一个在物理学天空中居于我们之上的神,同时也不再从启蒙主义和自然神论上,看作是一个外在于世界,即处于形而上学彼岸的神。恰切的方式是,思考世界中的上帝和上帝中的世界,亦即有限中的无限,内在中的超越,相对中的绝对。因此,上帝、神性作为包容万物统治万物的现实,处于事物之中,处于人之中,处于整个千差万别的感受中[1]。
这段话就像在呼应儒家思想,儒家的“天命观”、有机宇宙论、对“仁”作为天道贯注人身又内在于个体心性的不懈追求与道德实践,使其具备了一种“此世超越主义”的宗教性:“儒家思想有一超越的面向。人道源于天道的观念,暗示着儒家的现世观具有深远的宗教性。”[2](P15)
张枣的组诗《云》作为一首“天人合一”的颂诗在他的诗学思想与作品中拥有重要意义。这首诗的明朗与甜蜜呼应的正是张枣所向往的诗学之境:“人类诗歌的终极应该是喜而非悲,对神性完美的向往追求。人在诗歌中的生存应该是和谐。”自然,这种和谐不会来得那么轻易,它必然是人与世界、他者、自我痛苦纠缠与对话的产物,是一种历经磨砺而抵达的圆融——通常情况下仍然只是对圆融的一以贯之的心愿、追求圆融的过程,正如儒家的君子须漫长的一生来修为、实践对仁的追求,成圣更是永无止境——否则还是一击就破碎。如同卡夫卡的启示——“私人的信仰”必与其“私人的受苦”密切相连——若要理解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诗学问题、宗教问题,必须事先了解提出这一问题的人私人的受苦[3]。也即,并没有一种抽象的、想象的、与世界事物脱离关系的神性,此世即神性的一部分,乃神性必然拂照的世界。人作为有灵之长,必能感应“日常之神的磁场”,“能近取譬”,触发内在心性体验贯通天道,“为仁由己”。在此,我们就通过张枣的《而立之年》来探讨他的日常神性诗学以及他的内在超越之道。诗题“而立之年”自然出自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是孔子对自我精神修养发展过程的综述,引领这一过程导向的是超道德的天命。“志于学”乃“志于道”,因“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这种天命观,也是君子修道的根据与源泉。《而立之年》作于1994年,张枣32岁,但这首诗整体上波动的情绪节奏暗示着张枣并不觉得自己已立起来。一些困惑充斥着他的内心,生活中的不安、不满在诗的开篇即完全暴露出来:
一边哭泣一边干着眼下的活儿
自由,燕子一般,离开了铁锤
我的十根手指纳闷地伸向土地的尽头
聆听。是什么声音呀,找着,找着
一种旋律,一块可以藏身伏虎的大圆石
一个迹象,一柄快剑,让我学习忍受自己
这里呈现了两种状态:日常存在与对神秘事物的渴求。哭泣地干着眼下的活儿,自由在日常事物中远离,“我”纳闷地向土地的尽头聆听一种声音。个体的内心对现实处境尚处于不自由的逃避状态,寻求“一块可以藏身伏虎的大圆石”。张枣属虎,此处应有自况味道。而大圆石仍是外物,真正的融洽并未在内心产生,因而不得不“学习忍受自己”。来自土地尽头的声音与旋律乃神秘的诗意、宇宙的口令。然这必须用作为宇宙内在反响之一部分的生命力去听,用一种怡然、超然的心境,才能聆听作为“我”之内部声音的“天籁”。鲁迅有言:“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4]张枣的友人钟鸣说过,张枣“是那种仅为诗而存在的人,或者说,视诗为人生惟一意义者。”[5]可是在而立之年,他对于自己的诗歌之路也必然惶惑,为写作忧心忡忡:“我今年的写作数量锐减,不知何故,莫不是江郎才尽了吧。”[6]这或是每一个为写作痴迷的人都有的焦虑,而张枣是把这种写作的困难和危机感与生活的困难等同,在诗歌中持续不断地对此做出迫问,以此境喻存在的困难并作为创作本身富于诗意的动机。于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如何突破写作危机又成为张枣的闪光诗意:
雨意正浓,前人手捧一把山茱萸在峰顶走动/他向我演绎一条花蛇,一技之长,皮可不存/关键有脱落后的盈腴,鸣响沧海桑田的可能/歌者必忧;槐树下,西风和晚餐边一台凋败的水泵/在那里,刺绣出深情的母龙的身体
我们要说,上面这节引诗是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中国古典诗歌乃一种现世诗歌,多写日常际遇,在日常际遇中又渗透着人间温情与细腻情怀,其美感在于于尘俗世界中感应万物,于心物交融中体悟宇宙永恒。但极少漠视世界,并将高远的审美落实为富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譬如在重阳节这样一个民俗节日,古典诗人对于吟咏手捧茱萸登高、仰观俯视、游目骋怀格外青睐,生命的绸缪往复就在这长久的习俗与天地间:“万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风日几重阳”(李东阳《九日渡江》),宋僧道灿亦有“天地一东篱,万古一重九”的诗句。就在“江水”“东篱”“重九”这现世的事物中,诗人敏悟幽深浩渺的无限宇宙。
而诗艺正如“演绎一条花蛇”,它挑剔技艺的纯熟,剥落一切粗芜表皮,显露世界的盈腴晶莹,又必容留宇宙大化、社会历史变迁的沧桑。“歌者必忧”的信条再次流露张枣对古典言志诗学的认可。最后一句,在西风、晚餐和凋败的水泵这些日常现象的事物中,“刺绣出深情的母龙的身体”,意味着他“试图从汉语古典精神中演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的诗歌方法”[7]。或者,写诗本如刺绣,对现实纷乱事物的挑选犹如从杂乱的线团中配色,绵密的针脚最后给人出其不意的惊喜。龙作为传说中的图腾之物,凝聚着中国人的神性崇拜。因而,这里的微妙处又在于,从槐树下这一切身的周围事物来寄寓对神性之物的想象,诗歌乃帮助我们发现这一“日常之神的磁场”。张枣一直想在诗歌中建构日常世俗的神性。因为,假如生存是不可脱离的,人对幸福的追求是无可遏止的,那么我们就一定需要某些途径来支撑并安顿我们在世俗生活中对精神、灵魂、神圣、超验这些隐秘而无穷之境的向往,他坚信,这样一个安顿处在诗歌中。奥尔巴赫在论述旧约时说:“上帝的伟大作用在这里深深影响着日常生活,从而崇高与日常生活不仅在实际上紧密相连,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分开。”[8]基督精神中世俗与神性的趋和在西方文学中构成了一对恒久的张力。中世纪基督教对肉体的束缚与强调反而显露并加强了肉欲概念,使世俗的肉体在罪恶中寻求灵魂的皈依,诺瓦利斯甚至断言:“基督的宗教是本真的性欲的宗教。罪是对神爱的巨大刺激。”[9]而如果说,有罪的是人的处境,不是罪恶本身,那么,这处境就是我们必须活在不完满的尘世,而最终于这处境本身体会神性,哪怕深陷恶之中。正是这恶,这使人饱经沧桑的处境,才会令人最终以朴素、仁厚之心接纳、关注日常事物中的崇高与神性吧,于是我们听到了张枣那句发自肺腑的感叹:
要走多少路,人才能看见桌上的一只
鳄梨啊?周围是
一杯红酒,一颗止痛片,口琴,落扣,英雄牌
金笔,它们都偎着我朴素的中年取暖
这些诗句本身是朴素而温暖的,它蕴含的是生命的智慧。一些精心挑选的日常物品,投射着深厚的情怀。而“偎着”一词,又让我们看到中年张枣对日常生活的拥抱。这种拥抱焕发着实在的神奇力量,它包含着对待生活的谦卑、成熟和炽热的信念,以及由之而来并不凌空蹈虚的超越境界。这或许是张枣最从容的四行诗,面对漫长的人生旅途,面对生活中的空白,凭借内心的力量真正地去学习容忍直至拥抱:
我身上的逝者谈到下一次爱情时
试探地将两把亮匙贴卧在一起,头靠紧头
是什么声音呢,哑默地躲在
日常之神的磁场里?
可以看到,在“逝者”和“下一次爱情”之间,就是此刻的空白。此时没有爱情,但已学习“试探地将两把亮匙贴卧在一起,头靠紧头”。爱情是最具人间温情的事物,是生命之源,同时又伴随着凡俗仪式、生活琐碎、复杂的体验。现代人的爱情甚至需要凭借哲学思维来理解,如穆旦著名的《诗八章》所表述的:
相同和相同溶为怠倦,
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
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
我制造自己在那上面旅行。
他存在,听从我底指使,
他保护,而把我留在孤独里,
他底痛苦是不断的寻求
你底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
——穆旦《诗八章·六》
爱情的复杂、深刻、变动不居在穆旦的揭示下几乎给人绝望的感觉,这或许根源于个体本质上的孤独,克尔凯郭尔式的“生存性绝望”,并最终导向飞跃式的终极断裂及至信仰。但清晰洞察如此,穆旦也仍然写下如下诗句:“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这种恐惧与对温暖的渴求,也是张枣走过多少路后对“一杯红酒”的渴望。“我身上的逝者”对两把亮匙的贴卧意味着让下一次爱情好好相处的期待。两把亮匙乃相近的事物,易靠近易亲切,又易“溶为怠倦”,其结合或许不会如钥匙与锁那样有实在的吻合,此处仍以精神的交融为先,但“头靠紧头”的亲密却带来真实的身体感觉,这是血肉存在的感官爱情,而非抽象的形而上之爱。但张枣也并不确定,“试探地”这一限定性副词微妙地流露出他的小心翼翼,毕竟只是而立之年,并非“不惑”。然而他又探听并追寻那“哑默地躲在日常之神的磁场里”的声音了,或许仍难以辨识,但那内在的喜悦也微妙地流露出来了。这一次,“燕子自由地离开铁锤”,比较全诗第二行“自由,燕子一般,离开了铁锤”,凭借主语与状语的互换制造了完全相反的效果:“自由”离开后只剩沉闷、空乏,“燕子自由地离开”却是欢快、空灵,于是我们将读到的就是下面这段充满窃喜直至狂喜、语言旋转如舞蹈的诗:
外面正越缩越小,直到雷电中最末一个邮递员
呐喊着我的名字奔来,再也不能转身出去
玻璃窗上的裂缝
铺开一条幽深的地铁,我乘着它驶向神迹,或
中途换车,上升到城市空虚的中心,狂欢节
正热闹开来:我呀我呀连同糟糕的我呀
抛撒,倾斜,蹦跳,非花非雾。
“外面”在张枣那里有一种神秘的形而上感,尤其在中后期其用法多接近哲学维度,如《空白练习曲》中有“我呀我呀,总站在某个外面”“少于,少于外面那深邈的嬉戏”;《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中有“等你/再回到外面,英雄早隐身”“你喊,外面啊外面,总在别处!/甚至死也只是衔接了这场漂泊”;在《纽约夜眺》中有“露天消失/零星的外面抛赏给自杀者”;《钻墙者和极端的倾听之歌》中有“苹果林就在外面,外面的里面,/苹果林确实在那儿,/源自空白,附丽于空白,/信赖它……”等等。由此可见,“外面”在张枣那里乃与心相合,“他的心智对‘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宇宙模型怀着最迷狂的激情”[10],几有“万物皆备于我”的诚与乐。在孟子,最高范畴乃天,是天将万物备于我身,故有君子反躬自问,恕而求仁,这一内在的主体意识即尽心知性,进而知天、与天合一,因而并没有“外面”:“外面正越缩越小,直到雷电中最末一个邮递员/呐喊着我的名字奔来,再也不能转身出去”。可以认为“雷”呼应了前文“母龙的身体”,古人与民间即以天空中的雷电为龙,带神的生命格。“邮递员”隐喻诗人,那传递宇宙口令的使者,被雷电中,“呐喊着我的名字奔来,再也不能转身出去”。“我”吸纳宇宙山川,天地自在我怀,这境界,正如孟郊所唱:“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以“天地为庐”,正可谓“玻璃窗上的裂缝/铺开一条幽深的地铁,我乘着它驶向神迹,或/中途换车,上升到城市空虚的中心”。世界有其支离破碎的“裂缝”与“空虚”,然而“我”也并不能逃离,正如梅洛·庞蒂指出的:“我能逃离存在,但只能逃到存在。”[11]不在自身之外,也就是不在世界之外去寻求意义,“我”总能于幽深处瞥见一条出路,“驶向神迹”。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道”与“神迹”,皆由生命本身来鸣响其节奏,它们具象于生活,而为诗人“我”以象罔之艺所寻获。象罔,境象与虚幻的融汇,变灭与永恒的形相,闪耀着宇宙生命的真理、道、神性。这样的艺境将给人带来酒神式的狂热的迷醉感,因而接下来的诗句中攫住了一种扭动的狂喜,一种“非花非雾”的艺术迷狂,有趣的是,狄奥尼索斯同样是人神结合之子。然而,张枣深知,现实中的矛盾始终存在,所有对“我所当是”的信念都只能蕴藏在“我之所是”的结构中。犹如儒家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呼唤每个人都必成圣,然而在现实存在中,纵使圣人孔子也强压着脱离人间世事的诱惑,做着“知其不可而为之”之事,也承认君子学道修行的永无止境[2](P106-115):“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于是,在《而立之年》的最后,我们又看到这一根深蒂固的矛盾在诗人内心浮现:
高脚杯突然
摔碎,它里面的那匹骏马戛止
如一绺高贵香水
于黑暗中循循诱动
我祷告的笔正等着我志在四方的真实儿女,而
一种对公社秧苗的
不详预感
一种谈心,无法践约的
在我之外,如一个滑旱冰的
小阿飞
委蛇而来。
酒神的器皿“高脚杯突然摔碎”,烈酒如奔腾的骏马戛止,如高贵香水于黑暗中循循诱动。这是又一次的受阻。但这一次,是对矛盾的正视,抱有思虑过日常存在之苦与甜的释然。或许正是这苦与甜,喂养着诗人“祷告的笔”,这支笔“等着我志在四方的真实儿女”,这是真实的世界,这是真实的儿女,“活着就是去大闹一场”,志在四方。有趣的是,张枣接下来用了一个看似世俗意味极为浓厚的短语——“公社秧苗”——来指代人间世。公社曾经作为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政权与生产组织,秧苗又携带着一种喜洋洋的合作社风情,可谓别具一番中国特色的汉语性。然而在中国古代,公社又是官家祭祀天地鬼神的处所:“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因而仍有其神圣处,仍在“日常之神的磁场里”。在张枣精心挑选词语时,他似乎总欲溯其源头,进而让一个古老的词语作为新词出现,重新焕发魔力。于是,纵然仍有“不详预感”,有无法践约的在我之外的谈心,但这是否意味着,诗人需要将自己置身于现实存在之长久的危险之中,在日常与超验的紧张互动乃至冲突中激发诗之激情,毕竟,“最大的贫乏是不能存于客观世界之中”,而丰富、波动起伏正为诗构造难以平息的张力感。但在经过写作的调整之后,诗人必能收获暂时的解脱,那一首诗的安慰,那艺术超越时间的自由与满足。于是,我们看到,无法践约的可能性就在戏谑、轻松的语调中出场了:“如一个滑旱冰的/小阿飞/委蛇而来。”没有讥讽,更不拒绝,只有亲切、相迎。这是诗的可能性,正是诗的存在使尘世可能与不可能的都化为幸福,这种幸福,就在《狷狂的一杯水》中:
薄荷先生闭着眼,盘腿坐在角落。
雪飘下,一首诗已落成,
桌上的一杯水欲言又止。
他怕见这杯水过于四平八稳,
正如他怕见猥亵。
他爱满满的一杯——那正要
内溢四下,却又,外面般
欲言又止,忍在杯口的水,忍着,
如一个异想,大而无外,
忍住它高明而无形的翅膀。
因此,薄荷先生决不会自外于自己,那
漫天大雪的自己,或自外于
被这蓝色角落轻轻牵扯的
来世,它伺者般端着我们
如杯子,那里面,水,总倾向于
多,总惶惑于少,而
这个少,这个少,这才是
我们唯一的溢满尘世的美满。
这是一首富有魔力的诗。标题“狷狂的一杯水”引人无限遐想,仿佛这是一杯魔水,一杯正在狂热地扭着腰肢的水,它自由潇洒,又玲珑通透,因而可与人物人格相关联,这使其成为一首诗人品藻之作,它同样构成张枣对古典写意在现代诗写中如何可能的一个面向,这一次,他的对象是魏晋名士般的诗者精神与人格。狷狂,狷介狂放也,清洁自好而狂以进取,“狂者志存古人,一切声利纷华之染,无所累其衷,真有凤皇翔依千仞气象。”[12]这是张枣喜欢的王阳明对狂者的肯定,溯及孔子及儒家对人格与气象的推重。不累其心,乃怀本真之心、赤子之心,现真性情、真血性的“仁”。譬如孔子痛恶虚伪:“巧言令色,鲜矣仁!”“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在他看来,徒有其表之礼法乃“乡原,德之贼也”,是为“小人儒”。故而他极力赞美狷狂(“……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而摈斥乡原,对生活怀着超然蔼然的“依于仁、游于艺”之性情与情怀,在“乐山乐水”中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狷狂的一杯水初看可隐喻诗人主体志愿的自然形态,一种现代狷狂之士。张枣曾说:“我不相信诗来自现实的说法,我相信一首诗的真正源头是创造那首诗的诗人本身,诗来自诗人。”[13]诗与诗人之不可分,正如舞与舞者之不可分。真正的诗人本身亦是一首经得起品藻的诗。张枣的薄荷先生即神情超迈、名姓清凉:“薄荷先生闭着眼,盘腿坐在角落。”这里透露出“枯坐”中的心游万仞,亦有“自诚明,谓之性”即本体即工夫的合一:闭眼静坐,则“精神命脉全体内用”,安于其所思,中心磊落,不为媚世。“诚者,天之道”,天人感应而“雪飘下,一首诗已落成,”——这种神秘感应在那首著名的《镜中》早露端倪:“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后期,又在充满个人寂寥和芳香的无限《边缘》中显现:“他时不时望着天,食指向上,/练着细瘦而谵狂的书法:‘回来’!/果真,那些走了样的都又返回了原样:新区的窗满是晚风,月亮酿着一大桶金啤酒;”——这一句呼应了《一首雪的挽歌》中的神秘:雪作为上帝的言辞飘下,降而为诗人之词。诗人作为尘世与神性之桥梁,对这一使命的担负必有与天同德的率性、光明内心而旨高韵远,故有“桌上的一杯水欲言又止。”这杯水既为一首诗,也是诗者之心。诗者不粘滞于物的活泼性灵既皎皎脱俗,又与世界事物发生高迈的精神关联,和其尘同其光,在现量的生活里追求无量的生命意味。“四平八稳”与“猥亵”为狷狂者所害怕。“满满的一杯”正为满心天地——行文至此,可以感觉,张枣极大地宣扬了一种心学诗学。这一方面是他对中国传统思想做现代诗学转化的积极努力,另一方面,史蒂文斯对心智的推崇也对他影响甚深:“心智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东西。”[14]在史蒂文斯那里,“世界作为冥想”意味着“心与思不停地合跳”,其多数作品,如《内心情人的最高独白》《世界作为冥想》《胡恩宫殿里的茶话》《宁静平凡的一生》(这些诗均为张枣所译)赞颂的几乎都是诗人的慧心及其高妙的想象力。把《宁静平凡的一生》与《狷狂的一杯水》对读会发现,经由张枣译出的史蒂文斯已切实成为张枣身上的史蒂文斯:
他坐着冥想,他的位置,不在
他虚构的事物中,那般脆弱,
那般暗淡,如被阴影笼罩的空茫,
就像是在一个雪花纷飞的世界,
他起居在其中,俯首听命于
寒冷骑士挥洒的意念。
不,他就在这,就在此时此刻,
因地制宜。就在他家的他的房里,
坐在他的椅子上,思绪琢磨着最高的宁静。
最老最暖的心,任凭
寒夜骑士挥洒的意念切割——
夜深又寂寥,在蛐蛐的合唱的上方。
听它们喋喋不休,听各自独领风骚。
高妙的形态里是没有愤怒的。
而眼前之烛却炮制出熊熊烈焰。
——史蒂文斯:《宁静平凡的一生》
这同样是一个雪花纷飞的世界,寒冷骑士“坐在他的椅子上,思绪琢磨着最高的宁静”,为意念所切割。张枣的薄荷先生就像史蒂文斯诗中的寒冷骑士,同样“忍着,/如一个异想大而无外,/忍住它高明而无形的翅膀。”对意念世界自由而无形的沉湎充盈着这两首诗。一种奇妙的平衡感在于,诗哲同源间,诗人唯心主义思想中看似如此虚无的思绪收获的并非面目狰狞相,反而是温暖迷人的心境与诗境之交融:“我的心境下着金色的香油之雨”(史蒂文斯《胡恩宫殿里的茶话》)。《狷狂的一杯水》也在对心灵神性的持守中抵御了对“尘世”的落荒而逃,它甚至引出对重复的来世——“被这蓝色角落轻轻牵扯的/来世”——之向往:“它伺者般端着我们/如杯子”。最后两节满溢着源自内心力量对世界的赞颂:“这个少,这个少,这才是/我们唯一的溢满尘世的美满。”呼应史蒂文斯的信念:不完美是我们的天堂。这个少的美满、这个不完美的天堂,它出自“永无休止的心灵”与“高妙的形态”,诗与心,在诗者那里互为对方安顿秩序,或二者本就是宁静平凡的一生中唯一的美满。
[注释]
①借用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提出的“内在超越”概念。在1953 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唐君毅指出:“在中国思想中, ……天一方不失其超越性,在人与万物之上; 一方亦内在人与万物之中。”牟宗三在两年后发表的《人文主义与宗教》一文中,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儒家所肯定之人伦(伦常), 虽是定然的,不是一主义或理论,然徒此现实生活中之人伦并不足以成宗教。必其不舍离人伦而经由人伦以印证并肯定一真美善之‘神性之实’或‘价值之源’, 即一普遍的道德实体, 而后可以成为宗教。此普遍的道德实体,吾人不说为‘出世间法’,而只说为超越实体。然亦超越亦内在,并不隔离。”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亦说:“天道既超越又内在,此时可谓兼具宗教与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不过,在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内在超越不只被用来描述儒家,更广泛地用于概括儒释道三家(汤一介:《儒释道与内在超越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参见郑家栋在《“超越”与“内在超越”》一文对“内在超越”概念的提出与缘起之梳理,《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②尽管基督教在中国也多有人信奉,儒学也被国外一些思想家称为儒教,鉴于本文乃是探讨现代汉诗与文化的关系以及诗人的诗学信念等问题,并非宗教论文,因而在此仍谨慎地使用基督精神与儒家思想这两个词来表达宗教精神对诗人的影响。
[1][德]汉斯·昆,瓦尔特·延斯.诗与宗教[M].李永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5:122.
[2][美]杜维明.儒教[M].陈静,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229.
[4]鲁迅.导师[J].莽原,1925(4).
[5]钟鸣.镜中故人张枣君[N].南方周末,2010-03-12.
[6]引自陈东东.亲爱的张枣[A]//宋琳,柏桦,编.亲爱的张枣[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70.
[7]张枣.销魂[A]//张枣.张枣随笔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8.
[8]Erich Auerbach.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22-23.
[9][德]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M].林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36.
[10]宋琳.精灵的名字——论张枣[A]//宋琳,柏桦,编.亲爱的张枣[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170.
[11]转引自[美]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思维[M].姜志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23.
[12][明]王守仁.刻文录叙说[A]//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307.
[13]张枣.略谈“诗关别材”[J].作家,2001(2):78-79.
[14][美]华莱士·史蒂文斯.最高虚构笔记 史蒂文斯诗文集[M].陈东飚,张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53.
On the "Inner Transcendence"of Zhang Zao's Poetry
ZHAOFei
(ResearchSchoolforLiteratureScience,HunanAcademyofSocialSciences,Changsha,Hunan410003,China)
Based on a specific text,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source of Zhang Zao's classical poetics in terms of cultural ideas and awareness of existence. It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Confucian culture,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ity" that leads Zhang Zao to believe that poets should rebuild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self and the world. His poems show his deep consideration of secular life, concentrated enrichment of life like the awn of wheat, while absorbing the essence of the world into the state of mind so as to elevate the human realm, pursue the dynamic harmony between poetry and life with "inner transcendence", and win the cup of "perfect bliss overflowing the world."
Zhang Zao;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ity; Confucianism; "inner transcendence"
2015-06-01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4CZW048)阶段成果
赵 飞(1983—),女,湖南蓝山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现代汉诗及诗歌理论研究。
I207.25
A
1672-934X(2015)04-0096-07
10.16573/j.cnki.1672-934x.2015.0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