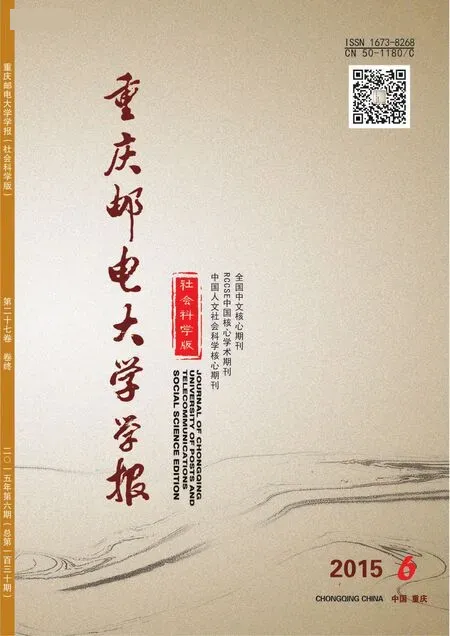越战小说中的记忆伦理*
2015-02-21梅丽
梅 丽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学院英语教学部,上海200083)
自古以来,文学作品中就有许多关于战争的描述,发动和参与战争的人都希望自己的英雄伟业通过文学作品而被千古传颂。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曾多次表示他非常羡慕阿基里斯(Archilles),因为后者的战斗功绩都被荷马(Homer)悉数记入了史诗当中,被后人代代传颂。然而,在当代文学语境下,文学作品描写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让个人英雄伟业得以彪炳史册,而是为了探讨战争本身的性质和战争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同时,战争如何被书写,创伤如何被再现,则成为当代战争创伤叙事中的核心议题。
在美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对战争创伤描写最多、争议也最多的是越南战争(1960-1975)(以下简称“越战”)。不管是当时在战争中罹难的越南人,还是受伤的美国士兵;不管是战后移民到美国的越南后裔,还是重新审视越战的美国公众,都受到了战争的创伤和冲击。在越南人、美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的眼中,这场战争有着不同的意义,仅从对它的称呼来看,就能折射出不同人群的立场倾向:这场战争在美国人那里被叫做越南战争,在越南人那里被叫做美国战争,在历史学家那里则经常被叫做“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the Second Indochina War)。
越战早已结束,但对于这场战争的记忆和争论远未停息,因为每一场战争都要打两次,第一次是在战场上,第二次是在记忆里。卷帙浩繁的越战文学,就是人们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回忆和反思的明证。在约翰·纽曼(John Newman)1996 年主编的《越战文学注释书目》中,仅收入的小说就有600 多部。作家们通过回忆越战经历,展现越战对人类造成的创伤,揭露意识形态作为战争的制造机器对人们的操控和毒害。然而,在越南作家和美国作家的笔下,对这场战争的回忆和描述有着很大的相悖性和对立性。面对如此差异,判断这些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分析作家创作的心理和过程是否符合记忆伦理。所谓记忆伦理(ethics of memory),简而言之,就是追问什么样的记忆是符合道德伦理要求的。记忆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谁在记忆”、“记忆什么”、“如何记忆”以及“如何表述记忆”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关乎记忆被合法化表达的实质。本文探讨越战小说中所涉及的记忆的正义性,正是对记忆表述的合法化实质所做的个案研究,也是构建(以越战小说为代表的)记忆伦理的一种尝试。
一、流动的记忆与身份
记忆是个人理解和界定自我身份的必要途径和手段。早在17 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就在《人类理解力》中对记忆与人的身份之间的必然联系进行了阐述:“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都能复述一个过去行动,复述时的意识和最初经历相同,并与现在行动时的意识相同,这样就可以确定这是同一个自我。”[1]对于洛克而言,在一个不受干扰的序列之中,链接过去和现在的记忆就是单一意识的状况,而单一意识使人始终和自己保持一致,不管是在时间的流逝中,还是在时间的流逝所必然带来的肉体的不断变化中。然而,洛克将记忆描述为个人身份的构成时,还带着一个限定条件——它只能适用于理想状态下的理性的人。但是,由于记忆缺乏有效的外部标准,因此它具有无限可变性,那么个人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我们或者其他人通过相互讲述关于自己和他人的故事。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迪克(Philip K.Dick)在《我们能够为你批发记忆》(We Can Remember It for You Wholesale)中塑造的奎尔(Douglas Quail)这一形象,就生动再现了记忆是如何成为个人身份的试金石的过程。奎尔对自己的身份越来越迷茫,因为星际集权统治政权的特务为了掩盖其见不得人的勾当,总是想方设法扰乱他的记忆,不仅将一些毫不相干的内容输入他的大脑,还删除一部分记忆,而所删除的也包括已经被他们胡乱篡改的内容。这样一来,奎尔既无法复原自己原初的记忆,也无法对过去做出任何可靠的判断。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只要将意识和时间联系起来,前者的混乱就会引起后者的颠覆,对个人身份造成深度干扰和影响。当这种情况延伸到集体记忆和集体身份中时,记忆与身份的关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记忆或遗忘的社会环境。法国哲学家莫里斯·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提出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并指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中获得他们的记忆……也正是在社会中,人们回忆、辨认出他们自身的记忆,并将其个性化……而我所在的那个群体在任何时候都会给我重新塑造记忆的方法。”[2]如果认真思考霍布瓦克的解释,就会发现我们和可怜的奎尔一样,虽然不存在集权政权的压制,却同样置身于危险之中。并不需要什么特务来扭曲我们的记忆,因为这样的扭曲在具有相同作用的社会环境下完全就是多余的。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Aleida / Jan Assmann)提出文化记忆的理论,指出人的记忆具有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历史性、目的性和发展性,只在利益语境中发挥作用。处于某种社会之中的任何一个群体,都处于某种利益语境之中,都有一种相对应的记录着其时间发展轨迹的记忆,而对任何一种时间发展轨迹的记录,都离不开对过去秩序的主动建构,从而强化或者揭示现有的某种特定身份。从上述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个人身份在时间的流动中必定受到集体和社会的影响,呈现出目的性和利己性,这一现象在越战记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越战的回忆必然是一个关于暴力和创伤的话题。受害者对战争的记忆是在对战争的反思中寻求同情、缓解余痛,因此,受害者强化创伤和施暴者的罪行不仅符合伦理正义,也是在想象中得到补偿。而施暴者往往试图淡化或遗忘原罪,记忆更多地向原罪的外围延伸,消解或者覆盖罪恶,也强调与受害者一样遭受到了创伤。如果将施暴与受害双方的记忆并置,二者的记忆内容将形成一个大于历史事实的假设性的事实,其核心会围绕罪恶和利益来展开人性的剖析。
二、两种记忆下的越战小说
越战对于越南和美国两国人民来说,都是他们记忆中无法抹去的重要一笔,更是令双方对自我身份进行反思的触媒。这场战争在动荡迷离的国际背景之下爆发,在美国国内高涨的反战之声中结束,战争的发起、过程和结束充满了矛盾和争议,而战后的人们理解和再现这场战争的方式,更是折射出了两个国家所具有的不同社会环境对身份认识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越战是发生在“那边”的事,近乎遥不可及。与他们关系更密切的是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战争,比如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尽管它们发生在数百年前,但依然吸引着美国当代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不断对其翻新讨论,进而成为普通大众关注的主题。在美国人的记忆中,越战士兵都是男性,杀戮与死亡只与男性有关。尽管这场战争牵涉到了少数美国平民和妇女,但他们与战争拉上关系的原因,大多是因为他们作为工作人员为战争提供后勤服务,或者亲人死于战场需要进行善后。但对越南人来说,战争无处不在。战争摧毁了他们的家园,他们无家可归,只能寄身类似于集中营的所谓战略安置处,或者沦为难民,或者逃往国外。战后尽管有很多越南老兵及后裔在美国定居,但这场战争阴魂不散,继续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曾经参加过越战的老兵们穿着军装,在各种公共场合聚众游行。当年的南越士兵们高唱着南越国歌,挥舞着南越国旗,并时时防范共产主义的入侵,对任何具有颠覆嫌疑的行为都诉诸暴力压制。在美国生活的越南人的内部矛盾和争执不断,越南匪帮袭击越南家庭的情况屡见不鲜,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的暴力事件在越南难民居住区频频发生。这些令人不安的暴力实施者,很多都是直接或间接遭受到越战影响的人,对他们来说,越战结束后在美国作为战争难民继续生存下去,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对战争免疫,事实上,他们仍然是战斗着的老兵。
对于美国本土作家和生活在美国的越南裔作家来说,他们对这场战争的回忆与再现,注定有巨大的差异。于美国作家而言,对越战表示赞同、为美国进行辩护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两类小说中。第一类是从殖民者的视角去描写越南人,如罗宾·莫尔(Robin Moore)的《绿色贝雷帽》(The Green Berets),突出表现美军为了越南的民主和自由做出的种种牺牲,漠视越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强化他们的落后、懒惰和散漫,通篇充斥着对越南人的偏见和误解。作者所具有的话语优先权使越南人成为一个沉默和缺席的主体,并且作者以其书写的话语权影响读者,把遥远的越南构筑成为一个与现实相异的国家,这个被想象出来的越南社群也在一段时期内误导了美国国内民众对越战的态度。第二类小说则是揭示越战给美国带来的伤害,强调美国作为受害者的一面。例如科伦·麦凯恩(Colum Mcann)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Let The Great World Spin)就刻画了五位饱受越战创伤折磨的阵亡士兵的母亲,讲述她们如何对抗越战创伤的经历。
虽然美国作家们的作品霸占着话语权和文学市场,但越裔作家的声音并没有被淹没,他们在小说中控诉美国战争罪行,表现越南和越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大多数越南裔作家的态度都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立场,如果有立场不够坚定的,在作品中对美国士兵表现出同情,或者指出越南人本身问题的,就会引来众多的口诛笔伐。例如越南作家李莱(Le Ly Hayslip)于1989 年出版的小说《当天堂与地球交换位置》(When Heaven and Earth Changed Place),既揭露了美国士兵伤天害理的行径,也揭示了越南人在战争中违背人伦的种种表现。同时,她认为美国人没有必要长久以来处于负罪的重压之下,因此她对美国人表达出原谅的态度。此书出版后销售火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像她这样表现出对美国人的同情和原谅之意的越裔作家实在是少之又少,而美国读者则把她的态度当作代表越南人的一种主流态度而大加赞赏。她的作品因此备受争议,不少越南人认为她这种妥协的态度是不切实际和不负责任的,因为美国人当年为越南带来战争的那些因素还没有完全消除,过早妥协只能助长美国政府的嚣张和垄断,为以后埋下更大的政治隐患。
三、通向正义的记忆伦理
在越战文学中,不管是美国作家还是越裔作家,大多都以自我为出发点,展现自我的感受和价值判断,导致了对事实的误读、对情感的伤害和对正义的偏离。法国著名哲学家、解释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记忆、历史、遗忘》(Memory,History,Forgetting)一书中指出:“指向自我的记忆是片面和错误的,真正符合伦理的记忆应该是指向他者,即从他者的视角去进行回忆。”[3]他认为只有这样做,弱势群体的记忆才不会被强权者歪曲和抹杀。
他的看法固然跨出了自我的局限,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对于有着明显强弱差异的双方而言,或者存在着明显的霸权和弱势的双方而言,利科的记忆法无疑是适用的。但如果事件中双方的立场正义性并不明晰,且双方都为自己的立场据理力争的话,他的观点就有些力不从心。此外,他的观点还存在着令人质疑之处:如果某些记忆被认定是符合道德的,那么与之相冲突的记忆就一定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吗?
利科倡导的记忆机制鼓励遗忘自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解构的性质,颇有德里达理论的遗风,即在对他者的指向中实现对自我的建构,但德里达式的自我解构倾向于抽象的他者而不是具体的他者。再者,从实际角度来考量,任何记忆主体都无法完全做到忘记自我的立场,而纯粹从对方角度进行回忆。
具体到越南战争,两国民众都对在越战中伤亡的本国将士进行广泛的悼念活动,尽管人们对越战悼念活动的目的有不同的理解,但不管是美国人民还是越南人民都赞同的一点是,他们都有必要对越南战争进行悼念,这是一种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如果自己都不回忆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悼念伤亡的同胞,那么还会有谁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越南人深信“独立和自由最宝贵”,把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奉为英雄烈士。尽管越南在许多人眼里还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但不影响越南政府和大众将这场战争理解和定位为争取独立而必须进行的战争。美国人对越战的态度没有越南人那么纯粹和绝对,他们至今认为这场战争具有很大的争议性,一旦陷入到新的战争,都会以越战为鉴,总结战争的教训。但美国人对越战阵亡士兵的悼念是严肃而虔诚的:耸立在华盛顿特区的越战老兵纪念碑己经成为普通美国人寄托哀思之处。这一纪念碑由黑色花岗岩砌成,长450 英尺,碑体呈V 字型,140 块花岗岩墙板上镌刻着58 000 名阵亡的美国军人的名字。每天都会有人在那些名字前面留下供品,包括照片、军功勋章、啤酒等。而在华盛顿特区其他任何历史纪念馆,都很难看到有人写下留言或摆上供品,由此可见越战在美国人心中留下的深深痕迹。
虽然关于自我的回忆会占据记忆的主要部分,但过度沉溺其中则容易被政治利用和操纵,陷入自我中心和民族主义的泥淖。阿维夏伊·马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曾撰文指出,这种从自我出发的记忆几乎不会涉及到事件中的对立方或者中立方,虽然这种记忆模式将自己与家庭、朋友、同胞建立起深厚的联系,但也疏远了自己与陌生人、他者和共同生活的社区这种抽象世界的关系[4]。
由此可见,摈弃自我而从他者出发的记忆,不符合人性本质的记忆机制,而且有犯世界大同主义的极端之嫌;而专注于自我的记忆,则有宣扬民族主义之忌,不符合道德理想。一种实践上可行而且伦理上值得倡导的记忆,则是从他者的角度,回忆自己的历史。这是一种双重记忆机制,是在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之间的斡旋,是有根和无根之间、遥远与亲近之间、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的对话。这不是一种空洞抽象的理论,而是一种具体的思维方式和道德立场。无论是人们的日常言论还是艺术作品中,这种思想都有表现,见证了人们朝着正义的记忆不断迈进。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美国摄影师费利普(Philip Jones Griffiths)在拜谒越南老兵纪念碑时,就从越南人的角度对这个纪念碑的设计进行了反思。他指出,这块纪念碑的长度是450 英尺,写下了58 000 名在越战中伤亡的美国士兵的名字;如果在越南修建一个类似的纪念碑,写下所有一百多万在越战中伤亡的越南将士的名字,那么纪念碑的长度需要达到9英里。这样的对比,会让所有站在美国老兵纪念碑前的美国人在悲痛之余,产生更多的思索。
而在各种以不同艺术媒介为表达手段反映战争的作品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制作成本越高的作品,采用双重记忆机制的几率越小。以电影为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约翰·韦恩(John Wayne)主演的战争系列片风靡全国,他在片中塑造的美国英雄形象表现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地位和崇高的道德地位。1960 年,当一群海军陆战队士兵被问及为何入伍时,“约一半的人都表示是因为看了约翰·韦恩的电影”[5]。而众多表现越战的美国电影——从《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到《兰博》(Rambo)——都讲述了表现美国民族优越感的故事。这些电影不仅把战争置于保卫国家安全、提供无私援助的语境之下,还将战争与士兵个人的理想和人生价值紧密联系,使战争成为男人重要的成长仪式。与此同时,电影对越南士兵和越南人进行了抽象化和妖魔化的描述,以自我为中心的记忆机制被展现到了极致。考虑到掌握着经济资本的人群与他们所代表的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这一现象也不足为奇。相较之下,文学作品由于与资本之间的关联度弱,因此在小说(以及诗歌等)中出现对越战的道德反思和记忆伦理探讨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四、双重记忆机制的文学再现
一个令人不争的事实是,在众多表现越战的美国文学作品中,只有少数美国作家在作品中正面展现越南人,或者从越南人的视角去思考战争本身。例如罗伯特·奥尔森·巴特勒(Robert Olsen Butler)从居住在印第安那州的越南难民的视角出发,创作了多部短篇小说,收集在《从奇怪山里来的好气味》(A Good Scent from a Strange Mountain)中,并获得了普利策奖。拉里· 海涅曼(Larry Heinemann)的《黑山:回到越南》(Black Virgin Mountain:A Return to Vietnam),描写他回到昔日的越战战场后,不仅与当年视为仇敌的北越士兵握手言和,还将北越加入越战看作一项英雄伟业。尽管对越南的理解和尊重迟来了几十年,但他内心最终获得了平静和升华。《肉搏战》(Close Quarters)一书,更是一部发人深省之作,他没有加入一句评论,自始至终站在一个白人士兵的立场,表现他如何被残忍的战争所异化,揭示他的人性如何在对越南人的施暴过程被泯灭。作者采用自我的角度(代表美国人的角度)进行回忆,并刻意忽略他者的策略,让自我一方的邪恶和丑陋被展现到极致,从而让读者对白人士兵产生深深的厌恶和仇恨,造成一种惊悚而震撼的阅读效果。这样的记忆策略,是对双重记忆机制的反讽性使用,使作者的道德立场显得明晰而强烈。
在越南作家的越战文学作品中,也有这种对双重记忆的反讽性使用的例子。保宁(Bao Ninh)的小说《战争的悲伤》(The Sorrow of War)排斥了其他视角,纯粹从一个受到精神困扰的北越士兵的角度出发,描写他在越战期间的经历。他的女友因美国士兵的强奸而遭到他无情的抛弃,他的残忍和偏执让女友在遭受美国士兵对她身体的侵犯后,又背负上男友在精神上对她带来的创伤。小说的(越南)读者在同情其女友的悲惨经历的同时,都不难体会到作者对越南人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观念的谴责和反思。由自己爱人、同胞带来的创伤,比起敌人造成的创伤,更加难以愈合。
对于加入美国籍的越南难民来说,如何看待越战历史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许多南越人为了躲避南越共产化的危险而偷渡来到美国。这些难民来到美国以后,会不断地讲述自己如何在国内遭到迫害,但深藏在他们内心的却是一种排他性的、亲民族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并不因为美国为他们提供了庇护而有所改变。他们在加里福尼亚的加登格罗夫建立了越战纪念碑,悼念越南的民族英雄,表达自己作为越南人的民族情结。美籍越南作家兼艺术家黎氏艳岁(Le Thi Diem Thuy)在1970 年代初期跟随父亲乘坐小木船从南越逃离,在海上被美国海军发现,安置在新加坡的难民营里,后来在加里福尼亚定居。她在《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The Gangster We Are All Looking For)等作品中表达了对美籍越南人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反思,采用双重记忆手段,通过将越南人的记忆和美国人的记忆相交织的形式,不仅表现了越南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也展现了美国人眼里的越南难民形象,还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有时候被忽略的少数群体的记忆是值得人们去关注和鼓励的,但是他们的记忆也需要加以审视,因为他们通过遗忘或者排斥,将那些不符合他们所提倡的难民民族主义的事件和人物,清理出了他们的记忆范围。
五、作为对抗手段的双重记忆机制
由于记忆本身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和利己性,记忆机制所导致的问题也往往为人所诟病,其中最常见的有记忆的遗忘、记忆的集体化、记忆的商业化以及记忆的过剩。而双重记忆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抗记忆机制中的上述潜在局限。
1.记忆的遗忘。诚然,正如尼采所说,遗忘是属于所有行为的本质特征。一个生命体没有记忆依然能够存活下去,但“要让一个生命体没有任何遗忘地存活下去,则是完全不可能的”[6]。记忆会使人疲劳,对行动造成阻碍,因此它具有损害性。尼采对遗忘的呼吁经常被人们用来证明遗忘的必要性。但是,尼采所忽略的是记忆本身的积极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一桩具体的事件,没有任何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人们的遗忘是必须的和合理的。哪怕是那些试图为纳粹的屠杀行为开脱的政客,也只是模糊地辩解说人们不应该永远背负历史的负担,而不会明确指出人们到底应该遗忘什么。因此,倡导双重记忆机制,既不会将记忆的责任仅仅归结到其中一方,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遗忘。
2.记忆的集体化。双重记忆机制反对的是从单一立场出发的片面记忆,强调记忆的全面性。但这种全面性,跟通常所说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有着不同的意义。集体记忆暗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较大群体都认可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力量操纵的结果。同时,集体记忆只有在它能够保证包括了记忆所涉及的所有群体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不管这些群体是大还是小。而事实上,囊括一切的集体记忆既不可能存在,也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遗忘必定是存在的。而双重记忆伦理建立的基本前提,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都在自己的一部分历史被遗忘的同时,从自我的记忆中对历史进行筛选性地构建。也正是如此,对立双方的记忆才有必要同时呈现。双重记忆机制克服了集体记忆的空洞和政治操纵性,使得记忆的内容更独立、丰富和全面。
3.记忆的商业化。消费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将所有的存在之物都转化为潜在的消费品,哪怕它是历史、是记忆、是伤痛。“记忆工业”这个术语应运而生,即将记忆商业化,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制造与记忆相关的旅游纪念物、历史事件纪念品,或者再现历史场景等。对于记忆工业来说,最关键的因素是感伤和民族主义。越是能触动人们这两根神经的,就越是卖得多,越能赚钱。因此,记忆工业品的制造者们会根据他们所处的场所和潜在消费群,选择制造最能赢得大众兴趣的物品。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让展现美国优越感的越战故事和越战纪念品在全球广泛地传播,在这样一场没有硝烟的不平等竞赛中,越南的声音几乎被淹没殆尽。双重记忆伦理无疑是记忆工业的一面明镜,让其片面性和功利性暴露无遗。
4.记忆的过剩。历史学家乔安娜·伯克(Joanna Bourke)指出,西方社会普遍存在记忆过剩或者记忆狂欢化的现象,记忆这个词已经“被滥用到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7]。其实,记忆的过剩并不是由于人们对历史已经了解得很充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对过去的了解还不够全面、充分,才需要用更多的记忆去掩饰缺失的那部分历史,去证明存疑的那些历史。仅仅从自我的角度去了解历史,或者仅仅从他者的角度去探索历史,都会留下更多缺失和争议。在双重记忆伦理引导下的历史记忆,不但不会增加记忆过剩的程度,反而会提高还原历史的真实程度,使得人们的历史记忆不再充斥着那么多需要去质疑和纠正的偏见与错误。
六、结 语
本文以越战文学作品为例,论证了双重记忆机制是一种克服记忆缺陷、通向正义的记忆伦理。它不仅可以在哲学和伦理层面回答关于越战记忆的质询,同时也能够实现小说美学的更高要求。一个作家能从双重记忆的机制出发进行创作,其作品在美学方面往往也具有更大的魅力。作品中的人物更具有福斯特所称的“圆形人物”的丰满和生动,人物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复杂和深刻。因此,在越战文学中倡导自我与他者的记忆邀约,无疑是我们重构作为记忆主体精神的一条通道和修复历史所遭遇的扭曲和伤害的有效途径,也是记忆作为文学发展黏合剂的实证,是文学觅得新质、重建秩序的推进力量。
[1]LOCKE J.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89)[M].London:Dent,1976:163.
[2]HALBWACHS M.On Collective Memor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38.
[3]RICOEUR P. Memory,History,Forgetting[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89.
[4]MARGALIT A.The Ethics of Memory[M]. Cambri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8.
[5]NOVELLI M .Holllywood and Vietnam,images of Vietnam in American film[M]// KLEIN M. The Vietnam Era: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in the US and Vietnam.London:Pluto,1990:107-124.
[6]KEARNEY R. Narrative and the Ethics of Rememberance[M]//KEARNEY R,DOOLEY M. Questioning Ethics: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hilosophy. London:Routledge,1999:26-27.
[7]CONFINO A.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History:Problems of Method[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5,102(5):1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