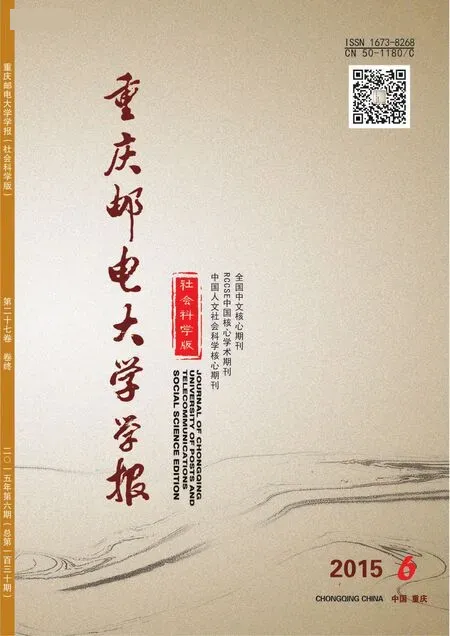文学中的时间*
2015-02-21孙丙堂
孙丙堂,袁 蓉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300222)
作为以文字为媒介、线性展开的艺术,文学生就和时间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伊丽莎白·鲍温认为“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1]。E.M.福斯特也在其《小说面面观》中称:“在小说中对时间的忠诚尤其重要,没有哪部小说是不谈时间的。”[2]确实,一部不涉及时间的小说是无法想象的,尤其是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人们对时间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时间问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突出。从古希腊时期的循环时间观、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牛顿的绝对时间、爱因斯坦相对时空观到伯格森的“绵延”说,时间观念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从客观到主观、从外在测量到内在感受的发展历程。文学的发展亦随着时间观念的发展而日趋成熟和深沉。巴赫金说:“小说这种体裁,从开始形成到发展,都建立在对时间的一种新的感受上。”[3]543马大康也称:“文学与时间密切相关,可以说,时间意识变化往往会促成文学形态,及文学整体的变革。”[4]因此,文学形式的发展,往往与小说作者处理时间的手段有很大关系。从最初的史诗、传奇到小说形式的出现和发展,再到后来的新小说,作者对待时间的方式有天壤之别。本文拟对时间的本质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探讨,随后转入文学世界内部,对叙事文学作品的时间进行具体论述,旨在阐述小说,尤其是现代主义小说处理时间的独特性。
一、两种时间
历史上对时间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时间的科学研究,这类研究首先把时间看成是现成的东西,再研究时间与世界上其他现成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时间的哲学研究,而这类研究才是对时间本身的思考,是对其本体论意义进行探究。显而易见,时间的哲学研究才是人类乃至本文关注的重心。人类根据其对时间的体验,得出了两种时间经验,即标度时间经验和时间之流经验。前者是人类使用沙漏、钟表等对时间进行标度,后者则是人们内在地对时间流逝的体会。
(一)标度时间
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研究客观时间,他将时间定义成“运动的数”[5]69。也就是说,他把时间看作某种实体、存在物,人们可以通过运动和运动持续量的尺度来测量时间,从而把握时间。人类也确实发明了不少工具来标度时间。例如,人类最早使用日晷通过日影来测量时间的长度;针对乌云遮盖的日子,人们又发明了漏壶作为计时器;为了克服冬季水会结成冰的缺陷,沙漏又开始发挥作用。可以说,在机械钟出现以前,人类对时间的把握是建立在日升月落、斗转星移、春去秋来的自然规律之上的,体现了一种循环、永恒持续的时间观念,而机械钟的出现则大大颠覆了人类对待时间的方式。工业时代机械时钟的发明使时间作为一个独立的体制从生活经验中脱离出来,从而建立自己的权威,实施对人类的暴政。人们生活中的一切行为,吃饭、上班、睡觉乃至娱乐活动,都在标度时间的严格制约之下。“时间就是金钱”,守时成为一种美德。人们原本是为了把握时间,却无形中成为时间的奴隶。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标度时间几乎成为物理学中唯一合法的时间概念。然而,标度时间本质上是某种空间化了的东西,它建立在人类迫切想要了解时间、把握时间的基础之上,我们测量到的只是物体的运动,并非时间本身,因此,标度时间并没有切中时间的本质。
(二)时间之流
最早研究主观时间的学者是奥古斯丁,他开创了通过内省之路研究时间之流的思路。关于时间本质的思考,奥古斯丁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时间究竟是什么?谁能轻易概括地说明它?谁对此有明确的概念,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可在谈话之中,有什么比时间更常见、更熟悉呢?我们谈到时间,当然了解,听别人谈到时间,我们也领会。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6]的确,时间作为一种无色无味无形、不具实体的概念,着实应了那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老话。“在时间观念史上,奥古斯丁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首次奠定了单向线性时间观的基础。”[5]193不同于希腊人的循环时间观,即把时间理解成一个圆圈,周而复始。基督教推崇线性时间观,认为时间是有方向的线性时间,它由上帝创造,但上帝又处于时间之外。循环时间观的本质是追求永恒和不朽,因此是取消时间的;而线性时间观认为存在一种统一的、普适的时间,它作为测量时间的标准,并不是外在于我们心灵的真实的东西,而是内在于我们心中的一种抽象概念。这种时间以一种均匀的速度流逝,具有不可逆性。伯格森认为,真正的时间是绵延,是一股连续不断的流[5]187。他把标度时间称作空间化的时间,认为它取消了真正的时间,只有挣脱钟表时间的束缚,时间才能活过来。而胡塞尔则认为,真正的时间只有一种,所谓两种时间只是看待时间的两种不同方式,客观的方式和主观的方式,外在的方式和内在的方式[5]196。
无论是测量时间还是时间之流,都是以人类的生活经验和感知为基础的。人一旦消失,时间也就失去了意义。
二、文学中的时间
时间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意识的发展和变革会促进文学的发展和变革。《巴赫金全集》中的《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针对长篇小说的历史发展类型做了介绍,认为早期的“考验小说”和“漫游小说”中的时间概念非常模糊。以《荷马史诗》为例,主人公奥德修斯在经历了多年的漂泊之后回到故乡,人物却依然年轻如初,仿佛处在时间流逝之外,而常用的时间用语也只是“那一瞬间”、“下一瞬间”、“提前一小时”、“到了第二天”等。这或许和古希腊人不注重历史的循环时间观念有关,时间当时还没有和人类的生存活动构成历史时空,因而那个时代的人普遍缺乏一种历史时间观念。“传记小说”催生了时间的历史性。他认为传记时间是非常真实的,“每一件事都框定在这一人生过程的整体之中”[3]225,人与人的活动和人的成长是传记小说的核心,时间开始成长为历史时间。马大康提道:“如果说,时间的历史化将时间与社会生活、社会历史相结合,那么,时间的‘虚化’却把时间从时空关联中分离开来,于是,也就与社会生活、社会历史相分离。”[4]正是完全相反的两极使时间成为可控、可表述、可重组的对象,而叙事时间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场的。换而言之,在文学中,时间既是表述对象又是实现文学的手段。然而,哲思上的时间和文学中的时间是否完全一致,它们之间又有何种联系,时间在文学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下面将对这些疑问一一展开论述。
(一)本质时间与文学时间
显然,本质时间与文学时间绝非一致,但又关系密切。首先,文学是一个完全由文字媒介构建起来的虚构世界,其时间框架也是由文字组成的,文字本身不会自动展示时间,而是通过作者的编排和读者的阅读逐渐呈现出来的。因此文学中的时间实际上是作者对本质时间的一种美学把握,哲思时间则是一种先验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二者是有区别的。杜夫海纳曾说:“无论如何……小说家为表现一个活生生的时间所用的手法都是白废心血。”[7]因此,鉴于文字这种表现媒介的线性展开特征,文学中的时间基本不能忠实表现本质上的时间,它只能在符合自身美学规律的前提下,创造自己独有的世界和时间。
其次,虽然文学世界有其独有的时间,但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它不可能完全脱离客观时间而存在,必须以客观时间为再现对象。尽管文学中的世界是人为虚构的,但仍然以现实生活为参照,以反映现实为己任。它对时间的处理亦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中的时间完全处于现实时间的压制下,否则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创造艺术就会变得了无生气。一方面,作者总是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对时间进行加工编排,从而使文学时间充满魅力,甚至比现实时间更加扑朔迷离;另一方面,由于时间是先验性地存在,人们只能内在地感受它。也就是说,时间自己不会体现自己,只能通过物质世界的变化来获得直观性的体现。
(二)文学中的时间
四大文学形式之一的小说特别注重叙事,而叙事意味着要讲故事,讲故事则少不了对时间的处理。而这种时间处理绝不仅仅是严格地按照故事发展的前后顺序安排而不带丝毫的艺术处理和把握,否则,我们只能将其称作“历史事件”而非文学。即使是古希腊时期的史诗,诗人亦非从头至尾讲述故事,而是“从中间开始”[8]。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一书中区分了叙事一词的三层意思:一层是叙事内容,即故事;一层是叙事话语,即叙事;一层是叙事行为,即叙述。随后他又区分了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对文学中时间的研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作者如何处理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二者关系的研究。根据热奈特的定义,故事时间即故事自身发生的自然时序,叙事时间则是被讲述故事最终呈现在文本中的时间,故又称作“文本时间”。故事时间是隐性的,它不直接呈现在文本当中,通常被作者切割、打乱甚至模糊化。而作者打乱故事时间的目的就在于获得艺术审美。读者根据作者提供的时间线索,将故事在脑海中按顺序重新编排,以获得故事时间。
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二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在顺序、时距和频率三方面。法国叙事学家兹维坦·托多罗夫曾经说过,文学中的时间基本上体现了一种时间倒错,也就是说,作者并不是按照故事发生的顺序在讲故事。当作者需要回顾某件事或某个人物时,就会停下叙事步伐,转而插入一段故事或描述,这就是所谓的插叙。倒叙和预叙亦是如此。使用这些手法往往可以使小说愈加生动或是充满悬念。
关于时距,人们相信,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只有时间的价值才有意义。作者往往根据时间价值大小来控制文学时间的长短,而文学时间长短的衡量尺度就在于作者愿意花费多少笔墨去描写。例如,作者有时候会用几十页的篇幅来描写一瞬间的事,却用三两句话带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岁月。
频率即重复,热奈特把它分成了四类,即讲述一次发生了一次的事情、讲述n 次发生了n 次的事情、讲述一次发生了n 次的事情、讲述n 次发生了一次的事情。以《喧哗与骚动》为例,福克纳通过四个不同的视角,在把一个故事讲了四遍之后,仍旧不满意,直到自己在17 年后又把这个故事讲了一遍才肯罢休。
保尔·利科曾经评论道:“陈述语句与被讲述事物的关系可以看成类似于索绪尔语言学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9]由此可以看出,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二者就像一张纸的两面,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共同构筑了小说中的时间。
三、空间性走向
托多罗夫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10]的确,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往往会同时发生,而针对这种现象,作者不得不在文本中对事件同时进行叙述,这种表现手法往往在中国文学中称作“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要达到这种同时性,作者必须不停地打断叙事流,在两条甚至多条叙事线路中来回进行。在电影中也不乏这种表现手法,如蒙太奇。而电影作为一种更为直观的图像艺术,显然在表现真实性方面比文学更具优势。
弗吉尼亚·伍尔芙认为,现实主义热衷于描绘外在生活细节的写作手法并不是忠于真实。因为在她看来,真实就是飘忽的瞬间印象和往昔回忆,是存在于人的主观头脑中的活动。这种活动不受客观时间顺序即“时钟时间”的支配,而是听命于心理时间即“内心时间”。由这种内心时间支配的小说写作往往时序混乱,多以人的意识为主体,而不注重讲故事。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把这种类型的小说称作空间形式小说。所谓空间形式就是作者“抛弃了时间的序列性和事件的因果性,代之以空间的并置性和时间的‘偶合律’”[11],也就是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时间顺序叙述手法,转而追求一种空间化的效果。而实现空间化的主要手段是“并置”,如多条叙事线路的并置、多个主题的并置等。当然,这里所谓的空间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而是一种隐喻意义上的空间。因为构成空间形式的要件正是时间,或者说时间序列。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实际上仍是处理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而作者之所以选择走向空间性,是为了达到表现生活复杂性和本质的目的。他们相信,这种立体的、多层次的透视方法能够做到忠于生活、深入人类本质。
四、结 语
自莱辛首次在《拉奥孔》一书中区分了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以来,文学就被确定为一种时间艺术,时间成为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2]。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不仅致力于时间表现手法的创新,还尝试把时间作为小说的主题,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家。他们根据自己对时间的理解,力求探索时间的本质,以便更好地揭示人的本质属性。米兰·昆德拉曾说,存在就是人类未来的一切可能性[13]。小说家最关心人类的存在问题,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为我们展现了人类未来的无数个可能性,而时间正是他们采用的手段。可见,对文学中的时间乃至时间本身的研究,将会是人类存在问题的永恒课题。
[1]吕同六. 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上[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602.
[2]爱·摩·福斯特. 小说面面观[M]. 苏炳文,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5.
[3]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马大康.拯救时间:叙事时间的出场[J].文艺理论研究,2009(3):128.
[5]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奥古斯丁.忏悔录[M]. 周士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42.
[7]马大康.论文学时间的独特性[J]. 文艺理论研究,1999(5):22.
[8]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M]. 王文融,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4.
[9]保尔·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第二卷[M].王文融,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43.
[10]高春民.论叙事文学中的时间意识类型[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1):51.
[11]龙迪勇. 空间叙事学[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
[12]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秦林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
[13]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