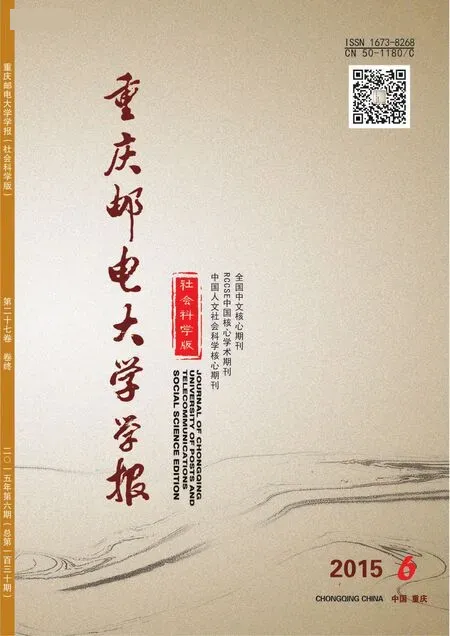《庭院中的女人》的女性群像——兼论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及其局限性*
2015-02-21张媛
张 媛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212003)
《庭院中的女人》(又名《群芳亭》)在赛珍珠的作品中有着特殊地位,《星期六文学评论》认为:“《庭院中的女人》是赛珍珠最为专注的一部作品。”[1]封底中国学界对该篇小说曾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比如女性意识①关于女性意识的评价,是目前中国学界的主流看法,比如陈敬(《死亡或超越——〈觉醒〉与〈群芳亭〉女性意识之探析》,《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 年第6 期)、岳瑜(《走出庭院的女人——论赛珍珠〈群芳亭〉中吴太太的女性意识》,《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2 期)、李冰及冯茜(《再生或毁灭——〈群芳亭〉和〈雷雨〉女性意识之探析》,《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 年第1 期)、丁琳(《从〈群芳亭〉看赛珍珠的女性观》,《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0 年第1 期)等。、宗教观②关于宗教观的评价,有陈超(《中西宗教观的共融——赛珍珠作品〈群芳亭〉中的宗教观》,《长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2 期)、许砚梅及宋艳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小说〈群芳亭〉透视赛珍珠的宗教观》,《电影评介》2007 年第14 期)。、后殖民视角[2]、中西方文化观[3]、生态女性主义[4]、浪漫主义[5]等等,不一而足。虽然这些解读言之成理,但要么从概念出发,要么停留在浮光掠影的简单引证上,缺乏纵横深入的比较与研究。笔者认为,在分析《庭院中的女人》时,应该在文本细读基础上,联系作家的整体创作情况及发展态势进行评价。1946 年,《庭院中的女人》成文面世③《庭院中的女人》的成书时间,绝大多数论者认为是1946 年,比如《庭院中的女人》的译者黄昱宁(赛珍珠:《庭院中的女人》,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就持这种看法;但镇江市赛珍珠纪念馆的展览资料标为1956 年,与《帝王女人:中国最后一位皇后的故事》同年发表。笔者认为,黄昱宁的看法比较可靠,镇江市赛珍珠纪念馆的展览资料可能有误。,十年后赛珍珠还发表了另外一部小说《帝王女人:中国最后一位皇后的故事》(以下简称《帝王女人》),将两部同样描写中国上流社会女性的小说进行对比研究,这对于把握赛珍珠小说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而把握赛珍珠的女性意识,无疑都是有意义的。
一、《庭院中的女人》的女性人物群像
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庭院中的女人》是一部类似《红楼梦》《镜花缘》的小说,是一部主要描写女性活动场所及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品。
吴家女人活动的庭院,简直就像一个微型“大观园”。在这个小小的庭院里,活跃着大大小小身份有别、性格各异的女性人物:这里有吴老爷的母亲、吴太太的婆母——类似于贾府里的老祖宗贾母,这里有吴太太秉性各异、背景不同、命运有别的三个儿媳妇。
大儿媳萌萌是典型的传统家庭妇女。萌萌是吴太太大儿子良漠的妻子,也是其好友康太太的女儿,家境殷实,“实在是糖水里泡惯了的”[1]64;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什么主见,更谈不上“自我”之类的现代意识——“她压根儿也不想要什么自我”[1]64,却“一向过得开开心心”[1]25,传宗接代是她的基本职责和使命:“替他(良漠)生一大堆孩子是她唯一的期盼。她是帮他延续生命的工具。”[1]64“儿子一个接一个地生,良漠也对她很满意。他们俩爱得恰到好处,一起创造了新的一代。”[1]266这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女性,根据美国职业心理学家约翰·亨利·霍兰德(John Henry Holland)创立的人格类型理论,应该是归属于“传统型”人格性向之列的女性[6],是吴太太在大家庭中最欣赏也最易管理的一类人。
二儿媳若兰是新派的现代上海姑娘。若兰是吴太太二儿子泽漠的妻子,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开明的新思想,相信男女平等。可在吴太太眼里,“这姑娘似乎以粗鲁唐突为乐”[1]61。由于她比泽漠大,“又私定终身”,没有让吴太太张罗婚姻大事,造成吴太太“永远都不会原谅”她的心结[1]63。她对吴太太为吴老爷张罗纳妾的事情相当鄙夷,当面批评吴太太的落伍:“讨姨娘那一套,早就不时兴啦。”[1]64并拿起法律武器捍卫女性的尊严:“如今男人纳妾可是犯法的。”[1]64“我们都使出浑身解数,要废除纳妾制度呢。”[1]65她甚至谴责婆婆为公公纳妾是犯罪:“婆婆居然做了这么陈旧,这么——这么罪恶的事情——,回到这种既陈腐又残忍的生活,真的是一种罪恶呀!”[1]65在若兰的身上,闪耀着新时代女性的光辉,可以依稀看到“五四”后女性从庭院走向社会、参与社会变革的影子:“昨儿在市政厅参加‘国家复兴委员会’开会……给别人选上当了主任。”[1]124她懂“宪法啦国家复兴啦不平等条约什么的”[1]218。因此,若兰对于回归庭院显得格格不入:“她对生活曾有过的梦想已然消逝。住在这宅子里,她就如同困进了囚牢。”[1]72
三儿媳琳仪是大儿媳萌萌的妹妹,却是受若兰影响与旧家庭格格不入的女性。琳仪是吴太太三儿子丰漠的妻子,与萌萌不同,接受过新式教育,曾到上海念书。这招致了吴太太的指责,她在不同场合对于琳仪接受新式教育多有微词,比如当着萌萌的面说:“你娘真是不该让琳仪到上海去念那一年的书。”[1]121“我希望让这个家来塑造他们,而不是什么洋人的学校。”[1]121当着康太太的面说:“你真不该让她去上什么洋学堂。”[1]146正因为琳仪接受过新式教育,她也就同若兰一样“讨厌这样的大家庭”[1]216;也正因为琳仪接受过新式教育,她有别于萌萌的顺从,“动不动就犯倔、使性子”[1]183。这种种骄横而自私的举止当然招致了吴太太的厌恶。
更为奇特的是,除了三个儿媳外,庭院里还生活着姨太太秋明、茉莉——这些纳妾制度的受害者,她们或不自觉、或自觉地承受着腐朽、违背时代潮流的罪恶制度的摧残、腐蚀。
二太太秋明是吴太太主动招揽到身边的弃儿。为了40 岁后不再生孩子的一己私利,吴太太煞费苦心地为吴老爷选择小妾:“那年轻女子该是什么样的呢?……毫无疑问,她得跟自己截然不同。她一定得年轻,可又不能比儿媳妇小……她的书不能念得太多……她断断不能是那种摩登女子……她当然得有一副俏模样,可也不能漂亮到让宅子里的小伙子或者吴老爷自己摸不着北。看上去顺眼、秀气也就够了。”[1]51至于这女子的身份和出处,吴太太反复地左右权衡:“她要去找一个既不是太有钱也不是太没钱的姑娘……她能来自远方就更好了。”[1]74“模样要俊的……无论对谁都存着友爱之心……不管是怎么样的男人都不会让她陷得太深……娘家要离得远远的。”[1]80她用这样的标准按图索骥,同唯利是图的媒婆刘妈像买“大米鸡蛋卷心菜没什么两样”地论价,“就跟做一宗买卖下订单似的”[1]52。秋明沦为物而失去了人的地位与尊严。她在吴家虽然衣食无忧,但并“不快乐,她不想属于上一辈人”[1]294的吴老爷,内心希望同自己般配的同龄人丰漠相爱,她的上吊自杀是对这种罪恶制度的抗议。
三太太茉莉是吴老爷从烟花巷里寻来的女人。茉莉是吴太太“最讨厌的女人,粗壮俗气、粗鲁淫荡”[1]326,吴老爷却真心喜爱这个女人,为这个粗俗女人陶醉而不能自拔。茉莉有别于秋明,烟花场所出身的她对做妾这种有辱女性尊严的生活安之如饴。
除了这些正式家庭成员以外,吴府里的庭院就如同大观园一样活动着一群丫鬟仆役。如吴太太贴身侍女莺儿,萌萌大儿子的奶妈莲儿,萌萌二儿子的小奶娘等。另外庭院外的女人也时常出人吴家,比如既是老姐妹也是亲家的康太太,英国出生的不讨人喜欢、可怜兮兮的夏修女,等等。
《庭院中的女人》人物虽然众多,但吴太太无疑是作品的最主要人物,其他女性人物都是为陪衬吴太太而设置的,因此吴太太是吴家庭院中当仁不让的女主人、女强人。她不但漂亮能干而且贤惠自持,“治家理财堪比王熙凤,博古通今不让薛宝钗”[1]3。尽管如此,吴太太却使整个庭院的人都感觉不幸福,正如安德烈一针见血指出的:“你有三桩罪过:你瞧不起你的丈夫,也没有把一个理应跟你情同姐妹的女人放在眼里,你还自以为卓而不群,别的女人都没法跟你匹敌。这些罪过搅得你全家都不安宁。你的儿子惴惴不安,他们的妻子郁郁寡欢,他们不晓得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不管你的计划如何了得,反正没有人觉得幸福。”[1]297
总的来看,《庭院中的女人》的女性人物群像,有别于赛珍珠早期作品《大地》《母亲》中的女性形象。早期作品里的女主人公大都是下层社会女性,比如阿兰、母亲,他们都是勤劳朴实的农妇,赛珍珠描写了她们的坚韧、质朴、生命力;而晚期作品《庭院里的女人》《帝王女人》的女主人公则是上层社会妇女,比如慈禧、吴太太,他们或者统治一个国家或者统管一个家庭,赛珍珠表现了她们的精明、强势。赛珍珠借助不同素材,为中国女性唱出了意蕴悠长的不同赞歌,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她独特的女性意识。
二、吴太太与慈禧形象之比较
要对赛珍珠创作生涯后期的女性意识做出准确、完整的评判,有必要将赛珍珠创作的《庭院中的女人》《帝王女人》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吴太太与慈禧展开对比分析,在比较中把握吴太太的性格特点及其发展逻辑。
在赛珍珠创作的众多女性文学形象中,吴太太与慈禧犹如一枝并蒂莲,具有本质上的相似之处。其相同与神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她们都是富于主见、特立独行的女强人。慈禧的强悍世人皆知,是主宰晚清政局近半个世纪的女强人,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无冕女王”,笔者对此有专门的论述,不再赘述。而吴太太尽管外表温婉,涉足的领域也只是小小的庭院,但同样是庭院里的女强人。吴太太的强悍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圆满周全的算计:“她既不冷淡,亦非热烈。她始终温润可人。她小心翼翼地把事情做得减一分则缺,增一分则满、则溢。凡事都能处理得圆满周全且适可而止,这样的本领她生来就有。”[1]41甚至连婚姻也充满算计和计划:“婚姻就跟张罗吃、喝、住这类事差不多,会得有一番安排计划才行。”[1]240“她一直在煞费苦心地从蛛丝马迹里揣摩”丈夫想要什么[1]109,最了解其为人处世的吴老爷的评价是:“你真能算计。”[1]178吴老爷一针见血道出了吴太太温婉外表下的深沉心机。二是善于把握时机:“当年她还没出阁的时候,春日里喜欢到家里的田地上帮着抽丝。蚕宝宝结好茧子后,必须瞅准时机把茧子投进一桶热水里,要不它们就会变成飞蛾把茧子咬破了。她总是有本事抓住那一刻。”[1]99对于庭院里的事情,她总是因势利导、善于抓住时机,在表面不动声色中控制事态发展,使事情总能朝着她预定的目标进展[1]150。三是事必躬亲:“吴太太每个月得查两回宅子里的开支,看一遍土地上的账目,什么水稻、小麦、鸡蛋、菜蔬、柴草的产量,她都一清二楚。”[1]59事无巨细,吴太太都掌控得牢牢的。四是大权独揽:她曾向夏修女夸口,“这个家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得先让我知道,得到我的同意才行”[1]150,“在我们家里,老老少少,包括佣人在内,他们的一日三餐都是我安排的”[1]240。这些反映出吴太太极强的权利欲和控制欲。总之,正是因为林林总总的手腕,造成“二十二年来,吴太太大权在握”[1]5,“没有人敢不听”她的[1]262。
第二,她们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她们都只爱自己,对于违背他们意志的人或事则冷酷无情。慈禧的一切行动都是以她自己的利益、喜好为准,即使是亲生儿子,违反了她的意志都毫不留情。在同治皇帝忤逆她时质问道:“那你就要这么做?”得到肯定回答后,更是非常霸道地颐指气使:“我是你额娘,我不允许你做。”[7]243吴太太同样如此,表面上淡然如水,对任何人都周全体贴,实际上她只爱自己,吴太太曾对莺儿透露:“我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情。”[1]128她也曾经自我反省,最终诚实地认同了安德烈教士的评判:“想到的总是她自己,而且也只有她自己。”[1]304实际上吴太太骨子里不爱任何人。她不爱自己的儿子儿媳,因为不满意泽漠与若兰的婚姻就报复他们,安排最不中看的院子给他们居住[1]123。她也不爱自己的丈夫吴老爷:“她突然察觉到了真相,她不爱他,从来就不爱他。”[1]206-207当秋明告诉吴太太自己怀上孩子的时候,吴太太话音里带着尖刻,“怨气就像一条细细的青蛇,纠结在她的心里”[1]196,并厉声对秋明说:“你得记住你是谁……立马回到你自个儿的院子里去,买你来就是为了这个”[1]198。在她温文尔雅的外表之下,实际上隐藏着一颗极端利己主义的、冷酷的心。
第三,她们对自由、知识都心怀渴望,有能力并敢于标新立异以赢取独立的女性价值。慈禧对于知识有着天生的热爱和追求,“她决心要了解一切,越是她所欠缺的,她就越想知道。这不仅是她对知识的真正渴求和对宇宙的好奇心,而且也使她或许可以知道得比与其谈话的任何人都多”[7]182。慈禧热爱自由并享受自由,“她和她与之嬉戏的那些东西一样自由”[7]93。慈禧寻求的是绝对的自由。为了享有绝对自由的话语权,她追求最高权力,通权达变地几度“垂帘听政”,把满清皇朝的绝对统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吴太太同样对自由、知识充满渴望,小说的契机由她40岁生日时所做的一个决定开始。吴太太把自己的人生分为两部分,将40 岁生日作为分水岭。在这个转折时刻,她最渴望得到的就是自由——身心两方面的自由。为了得到自由,吴太太不惜主动为丈夫纳妾:“今儿个我拿定主意了,我要为孩子他爹纳一方妾。”[1]13为此她主动张罗、寻找顶替自己的对象,自己则退而独居别院,与书本为伴、清静度日。而对于知识的渴望与追求,则是通过与她的两位人生导师——吴老太爷和安德烈教士交流、探讨实现的。吴太太始终自觉自愿地遵守习俗,在不破坏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前提下追求自由。
第四,她们名如其人,都是秀美婉约、聪慧脱俗的女子。吴太太闺名“爱莲”,而慈禧选秀入宫前名唤“兰花”,入宫后被册封为“兰贵人”。两位女子都是秀外慧中、名如其人。吴太太给人的印象正如“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8]的莲花,而豆蔻年华的慈禧确是兰心慧质的曼妙女子。并且两人均身康体健,吴太太生育了3 个儿子,慈禧为身体孱弱的咸丰帝诞下了唯一的皇子同治。她们为帝国皇位的传承、家庭的传宗接代做出了贡献,因而奠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第五,她们的命运异曲同工。她们都是事业上的成功者,但在个人感情生活上却有所欠缺,她们所爱的人都在可望而不可及的不远处。慈禧之于荣禄的爱,吴太太之于安德烈的爱,都超越了世俗的肉欲之爱,更多的是精神之恋。囿于条件限制,她们在心爱的人活着时不能与之达到真正的灵肉融合,只能在其死后追忆、缅怀。
虽然吴太太与慈禧有以上诸多相似之处,但她们之间的相异之处也是明显的。
首先,她们的身份地位不同、职责有异。撇开种族(满、汉)、地域(京都皇城、江南水乡)、历史真实性(历史性小说人物、虚构性小说人物)等方面的差异,两人的身份地位是悬殊的,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其格局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一为治国,一为齐家。慈禧贵为一国之君,胸怀家国天下。在满清末年风雨飘摇、国力不济的困顿政局下,内有太平天国、义和团滋扰之内忧,外有帝国主义国家虎视眈眈之外患,慈禧运筹帷幄、刚柔并济地施展铁腕勉力支撑,维持着摇摇欲坠的帝国,延续了满清皇朝的统治。而吴太太只是一个大家族的实际掌控者及当家人,打理好阖府上下的内外事宜已经彰显了她的聪慧和能力。吴太太的职责就是把庭院里的事情打理得“井然有序”[1]153,在战乱时期,让自己的儿子都呆在家里[1]158,任何时候考虑的都是宅子的颜面[1]197。
其次,她们的行事方式迥异。两位女性身上都表现出女性的张扬个性,在各自的生存语境中显得“阴盛阳衰”,但程度有所不同。慈禧行事果敢,多次在政局动荡的危急关头当机立断、力挽狂澜,以“不让须眉”的坚韧顽强实现“为儿子撑起一个帝国”[7]73的雄心抱负,精明干练地用男性化方式颠覆了五千年封建帝制的男性世袭传统,成功实行了对一个皇朝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独裁统治。吴太太自始至终以一个温柔贤淑的贵妇人形象出现,任何“出格”的思想都隐藏、淹没在她优雅淡然的举止中,始终以礼待人:“我从来都不会强人所难。”[1]119“她 发 号 施 令 的 时 候 常 常 轻 描 淡写。”[1]120即使要改变他人,总是让“事态往她自己筹划好的方向”发展,她掌握“在家里威望高的秘诀:从来不会让人觉得她一言九鼎”[1]159。虽然吴太太待人接物也恩威并施,但带有女性的阴柔;慈禧则个性刚强,带有男性的阳刚和霸道。
最后,她们的情感世界大相径庭。慈禧情感丰富,欲望强烈,对荣禄怀着矢志不渝的爱,并且敢爱敢恨、爱憎分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要让我不痛快,我就要让他更不痛快”。吴太太始终温婉如菊,带着女性固有的温和厚道,认为“富人对贫者,高官对平民”应该客客气气才对,“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挤兑人,吴太太见了都忍受不了。自从她成了吴宅里的女主人后,再没有哪个下人挨过打,哪个小厮给羞辱过”[1]141。吴太太的感情不如慈禧强烈,如温吞水一般波澜不惊,总是以理节情,责任永远大于情感、超过情感。她对智力水平不及自己的吴老爷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爱,只有所谓责任,虽然她也知道“爱情与责任无关”[1]286,却维持这种有名无实的婚姻;即使后来爱上了安德烈,也仅仅是一种柏拉图似的精神恋爱。在男权专制与封建夫权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等级制中,作为女性的吴太太只是也只能是一种“他者”身份的存在。康太太曾直言:“爱莲,也许你福气好,因为你不喜欢你的男人。”[1]183若兰也曾质疑过:“你从来没爱过什么人吗?”[1]271吴太太自己也曾反躬自省:“我从来没能爱过一个人。”[1]299赛珍珠从自己对爱情的理解出发,指出了吴太太一贯淡然的最根本原因——缺乏爱的能力以及没有遇到值得倾心相爱的人。
综上所述,虽然吴太太与慈禧存在不少相异之处,但从赛珍珠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晚年的赛珍珠对她们无疑都是欣赏的,某种程度上说,她们是晚年赛珍珠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从中可以窥见晚年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及其局限性。
三、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及其局限性
要对晚年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及其局限性进行评判,有必要联系赛珍珠的经历及其作品展开分析,在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及其发展流变中把握《庭院中的女人》折射出的赛珍珠女性观及其局限。
(一)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及其发展
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文学写作是充分个人化的精神价值创造活动[8],从某种程度而言,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或多或少反映其情感、观念、价值取向;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能完全与作家的情感、观念、价值取向画等号。因此,对于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及其发展,我们既要从作家的经历中寻找答案,也要对其作品展开分析。
首先,从赛珍珠的个人经历分析,赛珍珠的女性意识与中国文化、中国女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1934 年回到美国前,赛珍珠一直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城镇(镇江、宿州、南京),与淳朴、善良、勤劳的中国农村妇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她早期代表作《大地三部曲》《母亲》中的女性人物都是下层劳动妇女。1934 年返美后,赛珍珠与中国大地上的下层劳动妇女失去了实际的、具体的联系,从而适时调试自己的审美焦点,将笔触更多地转向中国上层妇女阶层。
其次,从赛珍珠作品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分析,在纵向的历时性和横向的共时性两个维度中,可以宏观地探究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及其发展变化。
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考察,可以看到赛珍珠女性意识的演进过程。赛珍珠的女性观从其作品中女主人公形象的发展变化就能窥见一斑。她的早期作品主要以中国下层劳动妇女为主人公。以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为例,在1931 年出版的早期代表作《大地三部曲》中,作家以饱含同情心的笔触描写了下层劳动妇女阿兰的勤劳、朴实、坚韧,突出了她对家庭的无私奉献,特别是在她离世的时候,家里人才发现她的重要性和价值:“她让人人过得舒舒服服”,她“在这个家庭里是多么重要啊”[9]。另一部写于1934 年的力作《母亲》,其中的母亲没有具体的姓名而采用共名——母亲,本身就隐含着赛珍珠对自己的母亲凯丽(Kelly)及普天之下所有母亲的爱戴之情。母亲对子女无私的母爱、对延续生命的挚爱、对众生的泛爱、对平凡生活的热爱根植于“中国农村妇女的思想、内心和精神之中,揭示了生命永恒的价值”[10]。创作于赛珍珠晚年的《庭院中的女人》《帝王女人》与《大地三部曲》《母亲》相较,赛珍珠的关注视角有了明显背离和变化——从下层女性人物转向上层女性人物。赛珍珠通过慈禧、吴太太等形象的塑造,从对立统一的角度解读了中国上层女性的女性自我。这种女性自我虽然受到男性意识形态的压制,但由于女性主体始终保持内在的“精神独立”与“自我决定”,人物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女性形象,在赛珍珠主观创作意图的指引下,成为了具有一定女权思想的人物代表[11]。
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考察,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晚年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及其局限性。《庭院中的女人》《帝王女人》是晚年赛珍珠的女性意识之集大成者,特别是《庭院中的女人》更多地融入了赛珍珠的生命体验、女性意识及其价值观念。《纽约客》在评论《庭院中的女人》时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是作者(赛珍珠)通过中国人关注自身的第一部小说。”[1]封底外国同行的评论对于我们解读赛珍珠的女性意识,特别是解读赛珍珠晚期的女性意识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庭院中的女人》对我们全面认识、把握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及其局限性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和作用。
(二)《庭院中的女人》折射的赛珍珠女性观及其局限
《庭院中的女人》里的吴太太与《帝王女人》中的慈禧相较,吴太太是赛珍珠更为钟爱的女性人物,的确是赛珍珠“通过中国人关注自身的第一部小说”。在吴太太这个人物身上,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代入自己,即塑造出与自己具备同样性格特征和意志品质的身处另一时空中的“自我”,表述其身份定位与自身内在的思考和认同[12]。赛珍珠借助吴太太的思想、言行,对于男性与女性、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有关女性定位、历史、生存、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思考,较为全面地折射出赛珍珠的女性观及其局限。
第一,借助吴太太形象,赛珍珠对于男性与女性的差异进行了认真思考,对女性进行了形象而理性的定位。根据建构主义理论,任何自我身份的确立,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完成的[13]。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就是在对两性关系的思考、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定位中确立的。比如她将男性定位为“种子”,将女性定位为“大地”,这几乎成了赛珍珠所有作品的文学原型意象或者母题[14]。早期作品《大地》如此,《母亲》亦如此。而在《庭院中的女人》里,赛珍珠借助吴太太进一步探本求源,一方面强调男性的“种子”作用:“上天唯以生命之繁衍为本,将种子赐予男性,将土壤归于女人。土壤不可谓不广袤,然而设若没有了种子,土壤又有何用?”[1]49另一方面又强调女性的“大地”功能:“种子在男人这里,可唯独女人才能让这种子在另一条酷肖她的生命里开花结果。”[1]87这种形象的比喻,有别于传统两性关系的旧有模式——“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15]。赛珍珠的这种生态女性主义观[16],既有别于东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更有别于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两性对立[17],使她的女性观形象而理性,带着中国东方传统的中庸、和谐色彩,具有顺应自然、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
第二,借助吴太太形象,赛珍珠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思考、徘徊、挣扎,吴太太形象呈现的矛盾折射出赛珍珠女性观的矛盾和局限。赛珍珠理想中的女性人物吴太太,其精神导师一是睿智的公公吴老太爷,其思想带有东方的、传统的色彩,具有中庸、平和、理性、保守的中国文化特色;一是安德烈神父,其思想与西方、现代有缘,具有科学、文明、开放、博爱的现代西方文化特色。
在《庭院中的女人》前半部分,借助吴太太的回忆,赛珍珠再现了一个睿智的东方哲人吴老太爷的形象。吴老太爷的女性观无疑是东方的、传统的,如“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只是生育机器、传宗接代的工具”,等等。这在吴太太的回忆中屡次出现:“女人家若是脑筋比身体好使,可不是一件好事。”[1]87“女人身体确实要比头脑重要。唯独女人才能创造生命。若是没有女人,则人种必然灭亡。”[1]87“天底下没有哪个男人受得了跟他同住一间屋、睡一张床的女人比他聪明的。”[1]87“女子无才,才会受男人的宠爱。”[1]90其对女性智慧的轻视与恐惧在这些袒露心迹的话语中表露无遗。这种东方式的将女人看作器物而不是平等的人的观念,显然与赛珍珠的西方文化背景格格不入。
在《庭院中的女人》后半部分,相对于吴老太爷的真实和“接地气”,安德烈神父的形象犹如海市蜃楼、镜花水月,显得虚无缥缈。安德烈遇害后吴太太的许多高尚、无私之举,或多或少有脱离实际、故弄玄虚之嫌。比如,为了成就与安德烈的灵魂之爱,吴太太如同西方有钱有闲的贵妇人般投身到各种慈善事业中。她不仅收留了安德烈生前照料的孤儿,支持丰漠到农村办学,还秋明以自由,理解了若兰,以宽容之心接纳茉莉,为年过40 的康太太接生……她的灵魂整个儿提升,攀到了俯视庭院合家老小乃至整个世界芸芸众生的高度。
吴太太前后判若两人,其转变在思想内容、艺术表现上均缺乏说服力,这其实反映了赛珍珠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困惑、矛盾和局限。
首先是赛珍珠思想上的矛盾与局限,使其在塑造理想化女性吴太太时捉襟见肘、笔力不济。赛珍珠一直在东西方两个世界中游走[18],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徘徊,是“一个生活在两个世界同时被两个世界放逐的文化边缘人”[19]。赛珍珠从1892 年到1934 年,40余年长期生活在中国,接触了大量中国女性,在东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耳濡目染;另一方面,赛珍珠出身于传教士家庭,父亲赛兆祥是一位执著的美国传教士,其西方文明、现代文化因子无疑也对赛珍珠产生了深刻影响,造成其后赛珍珠在创作中国小说时“心里有个西方小说的参考系”[20]。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成长背景,赛珍珠接受东西方不同文化熏陶的历程使她的文化立场和女性观自然兼具保守与开放两重文化色彩[21]。这两种文化在世界观、价值取向上的冲突以及从中激发出来的思想活力,在中国思维、东方意识和美国思想、西方观念之间穿梭往返的紧张感、挑战感与努力使之融合所带来的疏离感,成为赛珍珠庞杂而矛盾的思想体系的源头。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及其局限,都源于这种思想上深刻的矛盾,她的女性意识只能是那个时代和她本人兼具东西方文化身份的个人经历的产物,逐渐在后知后觉中蜕变成了东西方文化的大杂烩:既有对中国封建父权制社会愚昧落后现状的批判意识,又没有彻底认清父权制、夫权制下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摧残与愚弄;既有根植于西方哲学和宗教信仰的前见,又没有摆脱以男性眼光为参照标准描述、评价和教导女性的陋见;既有摆脱不掉的男性认同观念,又鼓励女性挣脱女性身份的束缚走上社会以获取社会地位。这种种思想深处的内在矛盾占据了主导地位,东西方两类女性观念、两种女性意识的分歧和冲撞导致了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矛盾和不真实。她甚至称呼慈禧为“我的老佛爷”[22],赛珍珠女性意识存在的这种固有缺陷,使其在《庭院中的女人》后半部分塑造理想化女性时,显得力不从心:吴太太从绝对的利己到利他,从东方女性的独善其身到西方女性的兼济天下,从对男性权威的屈服及由此产生的自我压抑、自我怀疑到最终的突然自我觉醒、自我实现,从确立自我价值观、真正重建自我身份到兼容并包走上向善之道收获完整的女性自我,其间的质变缺乏必要的逻辑基础,其转变也显得仓促突兀。正如译者黄昱宁所说:“一个真实的赛珍珠在书页间辗转反侧,上下求索,她的作品树起一个诡异的双面镜,让我们照见既熟悉又陌生的自己,转过来,又瞻望到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相互交融的可能性。”[1]译者序12
其次是赛珍珠艺术表现手法上的舍本逐末,导致作品虎头蛇尾。赛珍珠擅长讲故事,意识流手法以及心理描写非她所长,因此小说前半部分的现实主义描写自然而真实,后半部分的心理刻画则超出了她能够驾驭的范围。《赛珍珠传》的作者彼德·康如是说:“在一个吊人胃口的开头后,小说落入了一团玄妙的迷雾中。”[23]彼德·康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分析确实击中了要害。
综上所述,《庭院中的女人》是晚年赛珍珠在思想、艺术上有得有失的一部小说,是赛珍珠“通过中国人关注自身的第一部小说”。赛珍珠身处的时代仍旧是女性陷于由性别和政治决定的双重边缘化困境的时代,赛珍珠通过对《庭院中的女人》的女性人物群像的塑造和对女性境遇的刻画,在一群女性人物中众星捧月般突出了理想人物吴太太的形象。吴太太对于自由的向往,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责任、理性的歌颂,对于男性视域中女性地位的重新思考和定位,对于女性自我完整性的追求,这一切都折射出赛珍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形象与蕴含其中的女性观及其矛盾、局限。从这个角度看,《庭院中的女人》及其主人公吴太太在赛珍珠小说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1]赛珍珠.庭院中的女人[M]. 黄昱宁,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2]黄争艳.从后殖民视角看《庭院中的女人》[J].怀化学院学报,2009(1):84-86.
[3]谢晶晶.从《庭院中的女人》看赛珍珠的中西方文化观[J].电影文学,2014(8):64-65.
[4]那茗,苏芳,邢雅范.《庭院中的女人》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37-38.
[5]苏芳.《庭院中的女人》的浪漫主义解读[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199-200.
[6]李文霞,韩卫平. 人职匹配理论之“人格类型论”述评[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87-89.
[7]赛珍珠.帝王女人:中国最后一位皇后的故事[M].王逢振,王予霞,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8]刘再复.文学的基本要素——“文学常识二十二讲”之二[J].东吴学术,2014(6):49-61.
[9]赛珍珠.大地三部曲[M]. 王逢振,韩邦凯,沈培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52.
[10]赛珍珠.母亲[M].万绮年,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封底.
[11]张和龙.后现代语境中的自我——约翰·福尔斯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16.
[12]朱翠翠.认同与嬗变——王蒙小说人物的身份解读[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4:5-6.
[13]胡学雷.身份建构与利益转变——明治维新后日本身份变化的建构主义分析[J]. 东北亚论坛,2002(2):62-65.
[14]徐清.赛珍珠《龙子》中的乡土中国[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78-85.
[1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
[16]王丽霞.中国传统女性的挽歌— —生态女性主义与赛珍珠的《大地》[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74-79.
[17]西蒙·德·波伏娃. 第二性[M]. 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7.
[18]PENDARVIS E,CLAIR C. 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赛珍珠传[M]. 方柏林,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37.
[19]朱湘莲.赛珍珠的中国情结——兼析《大地》和《龙子》[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09:1.
[20]姚君伟.论社会活动家赛珍珠的对话意识与实践活动[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4.
[21]张春蕾.赛珍珠《群芳亭》与沈复《浮生六记》的比较[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4):130-135.
[22]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7.
[23]彼德·康.赛珍珠传[M]. 刘海平,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