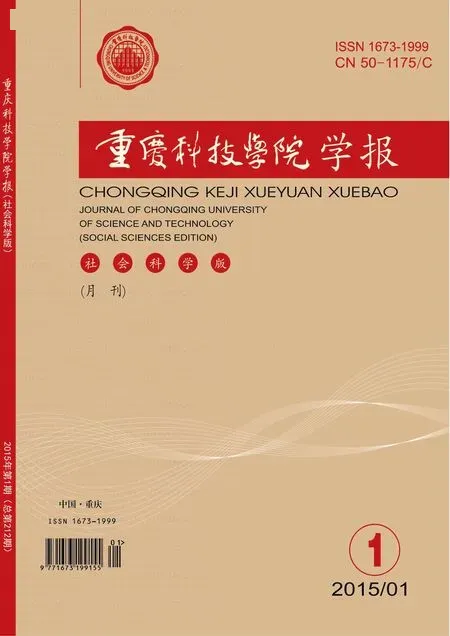浅谈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债权合同的效力
2015-02-21王建
王 建
浅谈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债权合同的效力
王 建
围绕不动产买卖合同效力是否与善意取得有关联的问题,介绍并分析了学界存在的不同观点。认为有必要明确界定物权法和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等概念,主张将不动产无权处分合同拟制为有权处分合同,将合同有效作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前提之一。
物权法;善意取得;债权合同;不动产转让
不动产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人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他人不动产转让给第三人,若第三人在交易时处于善意即可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原所有权人不得追夺。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的三个条件,即(1)受让人受让时是善意的;(2)转让价格合理;(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但是,它没有对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关于不动产债权合同效力问题,学界存在争议。
一、观点评析
关于合同效力是否直接影响善意取得的效果的问题,学者们的认识不尽相同。
(一)无关联说
部分学者认为,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发生与债权合同无必然联系。比如王利明先生认为:“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如果受让人是善意的、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原则上不应当再考虑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而直接依据善意取得规则使受让人取得所有权。”因为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与《合同法》第51条中规定的“无权处分”是两个并不完全一致的概念,善意取得中的无权处分,是指在登记错误或其他无处分权的情况下,登记权利人处分该不动产的行为[1]。也就是说,物权法善意取得中的“无权处分”的规定与合同法中关于“无权处分”的一般规定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在不符合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时候,才适用《合同法》第51条。
然而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必然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根据法制统一的精神,“无权处分”之内涵应在整个民法体系保持一致。如果这个概念在两部法律中的内涵不一致,则难免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将“无权处分”限定于“登记错误或其他无处分权的情况”,范围太过狭窄。
其次,不动产交易合同的效力认定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实施具有重要影响。善意取得制度是对交易(权利移转)安全予以保护的制度。如果行为人缺乏相应行为能力,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致使合同绝对无效,那么该转让行为还会仍然发生善意取得效果吗?如果善意取得成立与合同效力无关,当合同无效,无处分权人不完全履行时,受让人依据什么主张权利?若合同无效,受让人不支付对价或存在其他违约行为,无处分权人又依据什么主张权利?可见,合同是否有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再次,我国在物权变动模式上选择的是债权形式主义,并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在这种物权变动模式下,不动产物权转移的基本公式可以表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有效的债权合同+登记。若善意取得制度不考虑债权合同的效力,那么所有权变动之依据何在?当然,此处论证是建立在善意取得属于继受取得的基础之上的。从立法主旨来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不动产交易安全,其立法价值在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只有在无权处分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存在处分财产的法律行为时,才会发生善意取得的效力。在善意取得的场合,“第三人和无权处分人之间的交易行为依然也只能是法律行为,而非事实行为”[2]。限于本文主旨,这里不再讨论善意取得是属于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的问题。
(二)有关联说
对不动产交易合同效力进行界定,并将之作为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予以规定,这是目前学界许多学者的主张。但具体到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又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有效力待定说和有效说。
1.效力待定说
主张效力待定的学者认为,关于不动产交易合同的效力问题,现行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只能依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持法律适用上的一致性,也与法制统一的精神相符。《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由此可知,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为待定:真正权利人予以追认的,合同有效;权利人不予追认的,合同无效。依此观点,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前提必然是合同无效的事实。因为依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规则,其物权变动的基本公式为:不动产物权变动=有效的债权合同+登记。在真正权利人追认的情况下,债权合同为有效,办理完不动产变更登记后自然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一般效力,善意取得无适用余地。只有在真正权利人不予追认的情况下,合同无效,受让人(善意第三人)无法通过一般物权变动模式取得不动产物权,于是通过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按照效力待定说,则必然会产生下面的问题:
首先,将无效合同作为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与一般物权变动模式不符。因为在一般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变动必然以有效债权合同为前提。而如果将善意取得制度独立于一般物权变动模式,那么其合理性又何在?当然,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以另一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即善意取得是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笔者认为,善意取得是建立在法律行为之上,宜属继受取得,不动产善意取得依然要遵循一般物权变动规则。
其次,若将《合同法》第51条适用于善意取得情形,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很难得到有效保护。因为在真正权利人不予追认的情况下,受让人(善意第三人)只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善意取得制度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如必须完成登记过户,这样就给出卖人恶意毁约提供了机会。一些出卖人在买卖合同订立后,拒绝办理过户手续,或者在买卖合同订立后,过户手续完成前,以未经夫妻另一方同意为由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以此达到不履行合同的目的[3]。
2.有效说
文献[4]主张在《物权法》中把善意取得合同明确为有效,摒弃《合同法》中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之规定。娄爱华先生认为,应将“转让合同除无权处分外并无其他瑕疵”解释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之一,在构成善意取得之后,因公示公信原则的拟制效力,转让合同发生从无权转让到有权转让的转变[5]。
有效说的主流观点包括下面几点:
首先,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债权合同以无权处分为前提,但不按《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作效力待定处置,而是直接定性为有效合同。当然,这种合同必然要符合除无权处分外的其他一般要件,即“转让合同除无权处分外并无其他瑕疵”。具体而言,不动产转让合同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能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导致合同被撤销的危险的行为。
其次,有效说是建立在承认善意取得属于继受取得的基础上。继受取得是指通过某种法律行为从原所有人那里取得对某项财产的所有权。在不承认物权行为及物权行为无因性的前提下,债权合同只能是不动产物权变动唯一的“原因行为”。因此,只有合同有效才能保证物权变动的发生。将善意取得中的债权合同定性为有效,对于保证物权变动逻辑的连贯性是有益的。
再次,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物权变动模式的关系上,“有效说”学者普遍认为二者属于“流”与“源”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源”就有什么样的“流”。在不同的物权变动规则下,善意取得适用的结果可能会不同。如在意思主义的规则下,不要求物权变动的公式条件,那么不动产善意取得必然也不以登记为条件。
二、合同有效应为不动产善意取得之前提
在不动产善意取得中认定不动产交易合同效力问题,单就形式逻辑推理和着眼于法律体系的统一而言,有效说无疑是更具优势的。基于此种观点和立场,现在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明确界定相关的理论概念。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作为物权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物权法中的其他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一个法律“生态系统”内的相关概念应当一一对应,共同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目前,我国在物权变动模式上选择的是债权形式主义,不动产物权变动=有效的债权合同+登记,因此,必然要求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遵循合同有效的规定。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独立于一般物权变动规则之外的观点,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但是,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其内部构成诸要素之间必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彼此可以相互推出的。在可以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纳入一般物权变动规则的运行轨道之中时,将其独立出来就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有些学者认为,如果将善意取得中的债权合同规定为有效,进而纳入一般物权变动规则的运行轨道,那么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意义何在?笔者认为,将债权合同规定为有效,其法律适用上的意义主要是在无权处分人和受让人之间形成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善意取得制度在法律适用上的意义是保护善意第三人,使其所得物权不受真正权利人之追夺。在债权形式主义下,合同有效并不必然导致物权变动的发生,还要符合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和“合理价款”要件。
第二,可以将不动产无权处分合同拟制为有权处分合同。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债权合同,不应该由法律强制规定其有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包括: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有效;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禁止性规定。“如果说无权处分行为会对合同效力产生一定影响的话,它也只能与签约过程的自由与意思表示真实相关”[4]。依合同相对性原理,完全可以将不动产无权处分合同拟制为有权处分合同。合同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一般合同生效的要件,与“无权处分”无必然联系。因此,“转让合同除无权处分外并无其他瑕疵”的观点也值得商榷。根据这种观点,不动产转让合同不能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能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导致合同被撤销的危险行为。前面几种导致合同绝对无效的情形,不必说,自然无法导致善意取得的发生。但是,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善意取得是否绝对不能发生呢?笔者认为不能绝对化。“从契约本旨言,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契约即为成立”。我国《合同法》也仅是将此类合同定性为可撤销合同,合同最终生效与否并不取决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是当事人之间的选择。当事人若未行使合同撤销权,那么合同有效,善意取得在齐备其他构成要件后自然生效;若当事人行使合同撤销权,那么合同无效,善意取得不发生。
例如:张三为无权处分人,李四为受让人,张三与李四订立不动产买卖合同。
设张三在订立合同中存在欺诈,李四基于错误认识与张三订立买卖合同。这种情况下,张三为欺诈人,李四为合同撤销权人。若李四不行使合同撤销权,合同生效,李四齐备其他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时候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若李四行使合同撤销权,合同无效,善意取得不发生。此时李四可以对张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或侵权请求权,请求返还原物或恢复原状。选择权在李四(善意第三人)手中,他既可以依据善意取得保护其权利,又可以行使合同撤销权。
设李四(受让人)在订立合同中存在欺诈。张三基于错误认识与李四订立买卖合同。这种情况下,若张三不行使合同撤销权,合同生效,李四齐备其他善意取得构成要件,则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若张三行使合同撤销权,合同无效,善意取得不发生。李四进行欺诈就必然要承担合同被撤销不利法律后果的危险。这与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宗旨也相符,因而是合理的。
综上,合同有效为不动产善意取得之前提,它作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而存在。
[1]王利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研究[J].政治与法律,2008(10).
[2]崔建远.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J].中国法律评论:第1卷. 2007:67.
[3]刘贵祥.论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的冲突和协调[J].法学家,2011(5).
[4]彭诚信,李建华.善意取得合同效力的立法解析与逻辑证成[J].中国法学,2009(4).
[5]娄爱华.论善意取得制度中的转让合同效力问题[J].法律科学,2011(1).
(编辑:米盛)
D923.2
A
1673-1999(2015)01-0025-03
王建(1990-),男,烟台大学(山东烟台264005)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
2014-10-12
猜你喜欢
——从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申3020号判决切入
——以受让人权益保护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