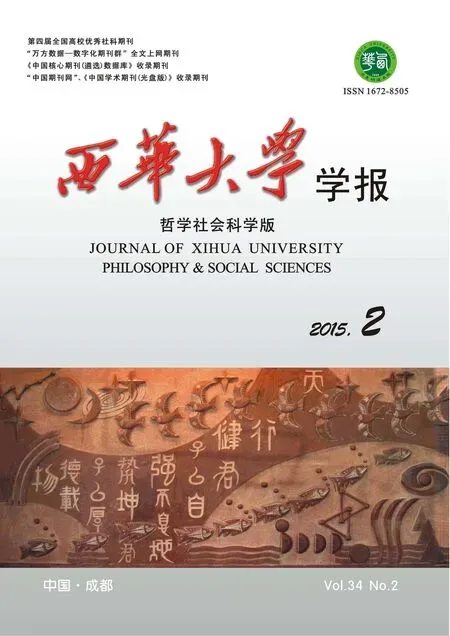历史典籍英译的“深度描写”研究
——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
2015-02-20李小霞
李小霞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湖南长沙 410012)
·翻译理论与实践·
历史典籍英译的“深度描写”研究
——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
李小霞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湖南长沙 410012)
“深度描写”是人类学中普遍使用的强调细节描写和阐释的研究方法,而“深度翻译”是“深度描写”在翻译中的直接体现。本文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对作为“深度描写”的翻译研究涵盖的四个层次:翻译事件本身、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决策和社会文化语境、对本研究的反思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深度描写”的翻译方法对中国历史典籍的外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深度描写;深度翻译;倪豪士;《史记》
20世纪以来,翻译研究经历了数次转向,依次为“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1]、“译者转向”[2]、“实证论转向”[3]、“全球化转向”[4]、“社会心理学转向”[5]等。其中,“文化转向”和“社会心理学转向”都是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翻译。文化人类学探讨人类文化的变异性,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具体民族及其文化进行全面和详尽的描述与阐释。翻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跨文化活动,译者力图呈现或阐释异质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人类学和翻译研究有共通之处,换言之,翻译研究可以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一、深度描写与深度翻译
“深度描写”分属于文化人类学,是阐释人类学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最早由英国分析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提出,后来美国当代著名阐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指出“深度描写”是对文化现象或符号意义进行深入的描绘与阐释。“所谓文化就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是可以被人理解的。阐释学是对理解的理解,是力图理解我们是如何理解他人的理解,因此,对文化的分析是一种探求意义的阐释科学。”[6]由于有着相同的研究对象即他文化或异质文化,阐释人类学为当代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研究人员不必再苦苦纠结于某些传统的争论,例如,谁的译文更忠实、更准确、更高雅,谁的方法更巧妙等。换个角度理解翻译行为,翻译就是译者力图用另一种语言来阐释并再现源文化,“既然是阐释,就没有完全所谓的精准、忠实的翻译,有的只是对源文意义的不同深度的挖掘与阐释”[7]。
“深度翻译”,亦称“深度语境化”,是“深度描写”在翻译行为中的直接体现。“深度翻译”的概念是著名人类文化学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在其名作《深译》中提出的。阿皮亚将其解释为“一种通过在译文中添加注释及注解等方法将文本置于源语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使得源语文化的特征尽可能多地保留,从而促进目的语文化对异质文化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尊重”[8]。为了更好地再现原文,就必须把原文放到它原来的语境中去解读,从而尽可能多地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质。
二、倪豪士英译《史记》的深度研究
台湾社会学家邹川雄[9]认为对生活世界的深描诠释包含四个层次:首先是关于行动本身的事实记录;其次是超越表象的深度描述,力图在此基础上对行动进行逼真的描述;再次是深度阐释,关注行动者身处的社会大环境,目的在于理解行动的主观意义,以及这个主观意义在社会中的客观意义;最后是反思的深描诠释,通过反省研究者自身所处位置和被研究行动之间的关联,构建这一行动在当下的意义和解释。根据这一理解,作为“深度描写”的翻译研究也应涵盖四个层次:考察翻译事件要把与翻译事件相关的事实陈述清楚;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了解译者作为翻译行动者的个体生活世界,根据译者的独特经历和经验,追问其翻译动机和决策;同时翻译也要考虑到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把这一翻译行为放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脉络中进一步阐释;最后研究者需对自身所处位置进行反思[10]。作者试图以这四个层次为基础对倪豪士等人翻译的《史记》进行层层深入的挖掘与阐释。
1.倪豪士译《史记》概述
鉴于到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史记》全译本,倪豪士认为,为了不误导西方读者,有必要启动《史记》英文翻译的全译工程,于是在台湾文建会的资助下着手此事。后来又陆续得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委员会、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和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等机构的资助。1994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倪豪士主编,郑再发、吕宗力、倪豪士、罗伯特·雷诺兹等翻译的英文版《史记》第1卷《史记·汉以前的本纪》和第7卷《史记·汉以前的列传》。第1卷主要译介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第7卷主要译介了汉代以前的列传1至28。2002年该社又出版了由倪豪士主编,Weiguo Cao、Scott W. Galer、William H. Nienhauser和David W. Pankenier翻译的《史记》第2卷《史记·汉本纪》。第2卷译介的内容有《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2006年出版了第5卷(上册)《史记·汉以前的世家》,主要译介汉代以前的世家等内容。2008年,Nienhauser、Meghan Cai等译的《史记》第8卷《汉朝时期的列传》(上)译书出版。目前《汉以前的世家》(下)、《汉代世家》和《汉代的列传》正在进行中。预计全部英译本将达到11或12卷。倪豪士等人的翻译是以查兰斯的法文译本和中华书局1959年版和1982年版为参考的,同时也参考了监本和百衲本《史记》以及日本泷川资言、中国台湾王叔岷等人的评述或译文。倪豪士译《史记》一经问世便赢得了西方学者的纷纷赞誉。葛朗特·哈代在对比华兹生的《史记》译本后评价倪豪士领衔英译的《史记》说:“从文学视角来看,华兹生生动的译本作为愉悦和悠闲阅读至今仍无人超越……但华兹生按照年代编排他的翻译时,他歪曲了司马迁的原始构想,读者将不能察觉司马迁结构的意义。与之相对照,倪豪士保留了《史记》的原文形式,允许读者尽可能猜想司马迁编撰的决心……倪豪士的译注在朝着尽可能使英语读者理解司马迁所要求读者具有的这种留意、批判解释的漫长道路前行。我对华兹生的翻译保有一种亲密感,我仍旧欣赏。但是我认为倪豪士的译著将更为值得仔细反复阅读。如果他和他的团队能够一直坚持到终点,他的翻译将是一个世纪以来或更长时间里最终的英译本”[11]。
2.倪豪士译《史记》的翻译动机
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文化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等方面[12]。《史记》全译工程的发起人倪豪士是美国著名汉学家,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同时致力于杜诗、唐传奇、《搜神记》、《史记》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早在20世纪70年代,倪豪士就开始从事《史记》研究,上世纪80年代还做过“百年来的《史记》研究”学术报告。可见,以倪豪士为首的翻译团队在此领域具备丰厚的学术基础,对所译题材相当熟悉。他们对自己的翻译目的、翻译选材、读者定位和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十分明确。
经过对《史记》的多年研究,倪豪士意识到《史记》应该被完整地译成英文,那种只关注故事性和行文流畅性的译本极有可能会误导西方读者,使得西方读者无法领会司马迁的写作意图以及它的历史内涵。因此,倪豪士等人英译《史记》的目标是译出一种忠实的、具有详细注解、尽可能具有文学性和流畅性且前后连贯的译本[13]。倪豪士译本面向专家和普通读者。他们对翻译过程进行精心策划,先由翻译团队的成员译出初稿,然后由其他成员写出书面评论,最终由团队反复讨论并邀请中外专家进行进一步指导。这样做既保证了译文质量,也符合翻译必须集思广益的思想。与已有的译本不同,在翻译选材和译本的结构方面,倪豪士译本保留了《史记》原有的本纪、世家、列传体例结构,译本的结构依次为对中外专家的致谢、序言、使用说明、纪年说明、度量衡对照表、缩写表、译文等;此外,每页下面附有详尽的歧义考证、相关章节成书说明、互文考证、文化背景知识注释等附加信息;每章译文后面还有译者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说明、该卷已有的译本书目和该卷的中外研究成果等;每卷后面附有全书的参考文献目录。倪豪士译《史记》重在凸显其文化价值,所附加的信息在于帮助西方读者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换言之,译者通过重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语境,帮助西方读者感受中国古代三千多年的辉煌史、荡气回肠的王侯将相故事,同时更深刻地理解《史记》带给人类的教诲,彰显《史记》对现代文化的指导意义。
3.倪豪士译《史记》与后殖民文化语境
20世纪30年代开始,民族解放运动席卷全球,越来越多的殖民地摆脱宗主国的统治,建立起了独立的民族国家。随着宗主国殖民统治的瓦解,后殖民理论应运而生。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权利话语关系,以及有关种族、身份认同、文化霸权、民族认同、性别文化等方面的内容”[14]。后殖民翻译研究关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活动,隐藏在译作背后的权力运作,考察权力与话语的不平等关系”[13]。可见,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研究摆脱了传统的文本内部研究局限,将研究视角更多地转向翻译的外部因素。“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流的前提是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让目的语读者能够领略异域文化特色”[15]。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提倡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就批评了以英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为核心的翻译策略,即“归化”策略。“归化”策略遵循目的语文化的文化规范,通过采用地道、通顺、流畅的英文对原文进行改写,有时甚至是无节制的改写与操控,结果是重塑殖民地状态下的话语不平等关系。因此,韦努蒂主张采用抵抗式翻译策略和“存异”的翻译方法,尽可能多地保留他者文化的异质性,使目的语读者更好地认识、理解和尊重异质文化,从而消解以英美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文化范式,实现各种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
具体到倪豪士等人《史记》翻译的后殖民语境,有必要回顾二战后中美关系的变化。二战后,美国实行反共政策,中美关系落入低谷,且美国凭借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输给第三世界的国家,同时“在文化领域里攫取第三世界的宝贵资源,力图构建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权力话语和全球性关系”[16]。在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翻译的主流方式为“归化”翻译。华滋生译本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诞生的。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在美国学习中国历史的人逐渐增多,美国汉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关注。同时,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促使美国的汉学研究转向中国知识界关注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达到顶峰,并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语境。翻译无疑为这种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成为了解异质文化的必然渠道。可见,倪豪士等人的《史记》翻译在相对宽松的文化语境中产生。另外,他们的翻译团队吸收了一些华人,借鉴了中外最新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外专家的指点和相关部门的资助。这使得倪豪士的译本具备还原司马迁原作的可能性,而不是仅仅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将《史记》内容按照西方人的写作和阅读习惯进行改写。倪豪士译本的体例结构、注释、纪年说明、度量衡对照表、每章说明等副文本无不体现译者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认同和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尊重。
在翻译策略上,倪豪士英译《史记》以尽可能尊重异质文化的“异化”策略为主,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字、对文化专有项的处理和译文风格三个方面。首先在语言文字方面,倪豪士英译《史记》中随处可见英语中掺杂汉字的表达形式,以《高祖本纪》为例:
例1: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17]
译文:Kao-tsu高祖(The Exalted Ancestor, ca. 248-196 B.C.; r. 206-196), a native of Chung-yang 中阳 Hamlet in Feng 丰Township in P’ei, had the cognomen Liu 刘and the agnomen Chi 季. His father was called T’ai-kung 太公(The Grandly Honored One or “Grandfather”)and his mother was called Liu Ao刘媪(Mother Liu). Previously, Mother Liu once rested on the banks of a great marsh when she dreamed she had an encounter with a spirit. At this time there was lightning, thunder and it grew dark; T’ai-kung went to look for her and saw a kraken atop her. Not long afterward she was with child and then gave birth to Kao-tsu[18]1.
以上是《史记·高祖本纪》开篇介绍汉高祖刘邦生平的文字。短短七行英文夹杂了七处汉字。乍一看似乎有点杂乱的感觉,可是仔细揣摩一下,原来是译者有意打破传统的英语语言规则,努力再现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异域风采。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和基础,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魅力。倪豪士译《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文化价值和史学价值,让西方读者准确而又真实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英文中间夹杂汉字的处理方法充分体现了译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与尊重。这种处理方法与后殖民文化语境下异质文化的地位在目的语文化中得到提升相呼应。又如,对于文化词“字”、“姓”,倪豪士选用了古罗马时代的姓名用语,“agnomen”和“nomen”。关于这一点,倪豪士指出先秦时期四种基本的姓名类型——姓、氏、名、字——在现代英语中都没有完全对等的表达,而古罗马人们有三个名字,相当于基督教的教名praenomen,族系的姓nomen,表示家族的名字cognomen,有时另外加一个名字agnomen。倪豪士采用古罗马时期的名字表达方式译介中国先秦时期的名字显得正式、味道古朴,让人联想到古老的文化,这一点与司马迁严肃的宫廷式的文体风格不谋而合。
其次,在文化专有项的处理上,译者采用最多的方法就是对原文本进行考证和注释,以扫清读者的阅读障碍,帮助不熟悉异质文化的读者正确理解《史记》和司马迁的写作意图。
例2: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史记·高祖本纪》)[17]
译文:When Kao-tsu had struck at [Ch’ing] Pu, he had been hit by an errant arrow and along the road (back) he fell ill. His illness got worse, and …. Fate lies with Heaven-even P’ienCh’üeh 扁鹊 could not help!”[18]
汉高祖攻打黔布时,被飞箭射中,路上病情加重,吕后请良医医治,高祖认为人命天注定,即使是扁鹊又有何益。汉高祖提及的扁鹊,是中国古代著名人学家,在中国人尽皆知,可是对西方读者而言,他们完全不知扁鹊为何人。所以,倪豪士在译文的下面添加了注释“A legendary Chinese healer of antiquity, see his biography in Shih chi Chapter 105”。类似的注释在译文中随处可见,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再次,在文体风格方面,“《史记》中极少用骈丽句法,文句很有韵致生气。作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舒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19]。译者在翻译时,时时注意靠近司马迁的写作风格。例如:
例3: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列传》[17]
译文:His style is concise’ his language subtle’ his aspirations pure’ his action honest. His topics are small but his intentions grandiose’ the things he brings forth are near at hand’ but their significance is far reaching.[18]297
上例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常用的排比手法,排比句的使用往往透露了作者的情感及观念,想要忠实地传递作者的意图实属不易。原排比句整齐、简洁利落、富有节奏感。译文结构忠实于原文,句式整齐、用词精确细腻、层次分明,是一种完全忠实于原文的翻译。
三、对本研究的反思
《史记》成书久远,内含丰富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想要西方读者准确全面地理解《史记》,译者必须具备敏锐的文化意识和阐释意识。很多文化信息是依托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存在的,所以要想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译者需要通过“深度翻译”策略来挖掘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原作者的写作意图。倪豪士在翻译《史记》时采用的正是这种“深度翻译”法,通过大量的副文本信息,成功地将原文本中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西方读者。
倪豪士所译《史记》体现了重要的社会意义。就其本质而言,《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最终目的重在述往事、思来者,是想通过中国历史上的风流人物,给后人某种历史教训,提高人类文化修养,而不单单为了凸显其文学价值。倪豪士等人对《史记》翻译的处理方法,处处都在向着这一目标努力。详尽的歧义考证、地点考证、相关章节的成书说明、互文考证说明、文化背景知识注释以及资料依据等等都是为了还原一个尽可能真实的历史文化语境,让读者通过书中人物去体味、感知中国古代历史的辉煌,去吸取历史教训,呼吁人们以史为鉴。
当然,本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没有对副文本进行详细的研究。但是,通过本研究不难看出,“深度描写”的研究方法对《史记》乃至整个二十四史的翻译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谢天振.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5).
[2] Robinson D..TheTranslators’Turn[M].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Hatim B..TeachingandResearchingTranslation[M].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3] Gentzler E..TranslationandPower[M].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4] Snell-Hornby M..TheTurnsofTranslationStudies:NewParadigmsorShiftingViewpoint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06.
[5] Gentzler E..TranslationandIdentityintheAmericas:NewDirectionsinTranslationTheory[M]. London : Routledge, 2008.
[6] Geertz Clifford.InterpretationofCulturesSelectedEssays[M]. New York: Basic Books,1973.
[7] 龙吉星.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人类学方法初探[J]. 中国翻译,2013(5).
[8] Appiah Kwame Anthony. Thick Translation [C]// Lawrence Venuti.TheTranslationStudies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0.
[9] 邹川雄. 生活世界与默会知识: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C]// 齐力,林本炫. 质性研究方法. 嘉义:南华大学出版社,2003.
[10] 王岫庐. 试论“深描”法对翻译研究的启发[J]. 中国翻译,2013(5).
[11] 吴原元. 略述《史记》在美国的两次译介及其影响[J]. 兰州学刊,2011(1).
[12] 熊建闽.庞德文学翻译主体性探析——以《神州集》为例[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13] William W. H. Jr..TheGrandScribe’sRecordsVolume1[M]. Tsai-fa Cheng, et. al., trans.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15] 严晓江.文化翻译观下的《楚辞》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孙大雨《屈原诗选英译》为例[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16] 祝朝伟. 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2).
[17] 司马迁. 史记[M]. 中华书局,1999.
[18] William W. H. Jr..TheGrandScribe’sRecordsVolume2[M]. Weiguo Cao, et. al., trans.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 郑爽, 范祥涛. 从视域融合看译者的主体性阐释——以倪豪士的《史记》英译本为例[J]. 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14(1).
[责任编辑 肖 晗]
Transl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ck Descrip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LI Xiao-xia
(SwanCollege,CentralSouthUniversityofForestryandTechnoloty,Changsha,Hunan, 410012,China)
“Thick description” which emphasizes detailed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s widely used in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ur levels of translation study on the basis ofTheGrandScribe’sRecordstranslated by William H. Nienhaus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ck description: the translation itself, the translator’s inten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the cultural context and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thick description; thick translation; Nienhauser;TheGrandScribe’sRecords
2014-09-21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典籍英译实践:过程与方法”(项目编号:11YBA324)。
李小霞(1981—),女,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H315.9
A
1672-8505(2015)02-004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