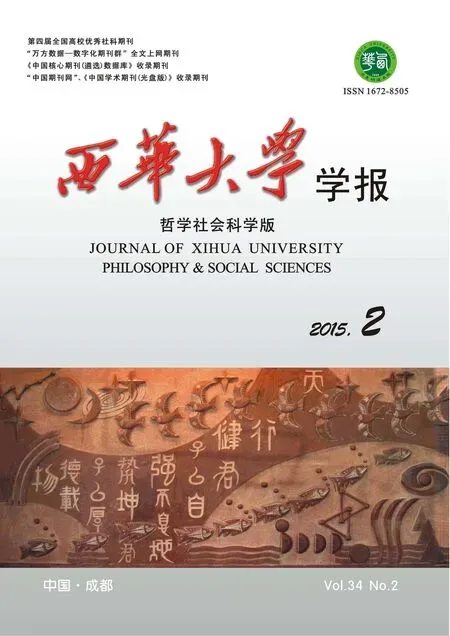“诗可以群”与律诗定型
2015-02-20岳德虎
岳德虎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部 广西柳州 545006)
关于律诗定型,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者都基本认定在初唐的后期,通过初唐诸学士的共同努力而完成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陈铁民先生的《论律诗定型于初唐诸学士》、贾晋华先生的《唐代诗人集会及诗人群研究》、杜晓勤先生的《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日本学者高木正一的《景龙の宫廷诗坛と七言律诗の形成》、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的《初唐诗》等等,在对这一时期学士个人及学士群体的诗歌声律进行了详细考察和求证的基础上,结合声律理论的发展,从而得出在初唐唱和的过程中最终实现了律诗定型。但这些论证注意到的只是定型的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定型原因却涉及甚少,特别是对于最重要的原因——“诗可以群”很少有人提及。而“诗可以群”作为孔门诗教“兴、观、群、怨”之一,与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不但存在于律诗定型发展的每一过程中,而且贯穿于律诗定型的始终,对于律诗的定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拟从“诗可以群”与诗歌的历史渊源入手,探讨在“群”的作用下,律诗的产生、发展和定型原因,如何在“群居相切磋”中一步步走向定型。
一、“群”与上层诗歌
“群”,《说文解字》释为:“群,辈也;从羊,君声。”可见,“群”最初与传统的血缘宗法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宗族内部保持团结的基本形式,在宗族成员之间通过“群”交流思想、融合感情、协调群体,具有培养宗族思想意识的统一和维护宗法伦理道德的实施等功能。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群”逐渐又被称为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团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周易·系辞上》),因而段玉裁注为“朋也,类也”。“诗可以群”作为孔门诗教的四大功能之一,也是以此为出发点,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论语注疏》释为“群居相切磋”(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即诗歌是在群居相切磋中发展起来的。
依据孔子“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结合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史实,“群”分为民间下层和宫廷上层两种形式。而随着诗歌创作的文人化,主导诗歌发展的宫廷上层的“群”,主要表现功成和外交,多以宴饮为创作舞台,突出诗歌应用功能,这在《诗经》中就多有体现,如“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诗经·小雅·鹿鸣》)。朱熹《诗集传》云:“本为燕(宴)群臣嘉宾而作,其后乃推而用之乡人也。”臣子通过赋诗来言志、沟通与帝王和其他大臣的感情,故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通过“群”的沟通、交流,以增进关系,拉近友谊,同时提高了诗艺。
春秋战国时期,最能凸显这一功能的当属“观七子之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赵武)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印段、公孙段)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音况),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基于此,杨树达在《论语注疏》中谓“春秋时朝聘宴享动必赋诗,所谓可以群也”。而“春秋之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汉书·艺文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离“群”。
两汉朝时期,“诗可以群”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縠之高喻”(《文心雕龙·时序》)。君臣宴会赋诗,以“崇儒”为基准,以赋诗为形式,以君臣同乐展现国泰民安、盛世升平的光辉业绩,从而显示儒家诗教因“群”得以传承。即席赋诗,群臣附和皇帝,以“颂美”为旨归,不但可以拉近君臣的感情,密切他们的关系,对诗歌的发展也能起到推动作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种上层“诗可以群”的发展更为迅速,因为形成了以皇室为主导的文学集团,也是中古文学集团的最主要形式,但此时的宫廷赋诗显现的是统治集团内部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在一片祥和中着重于沟通君臣、臣僚之间的感情[1],政治色彩并不浓厚,强调的是“群”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南史·文学传序》也提到“(梁)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这种带有竞赛性质的君臣赋诗,即“群居相切磋”,在扩大“诗可以群”的规模的同时,也能够促进诗艺的提高。
在公宴赋诗展其情的过程中,在前代声韵发展的基础上,永明时期出现的竟陵文学集团创制了具有律诗定型先声的“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作为“我国诗歌有较为自由的古体走向较为严格的近体的开始,它把晋宋以来诗歌的对仗与当时对声律的研究结合起来,让诗歌具有一种新的风采”[2],“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宋书·谢灵运传论》)。可见,竟陵文学集团不但继承了先前文学集团的文学创作的集体范式,切实发挥“诗可以群”的社会功能,更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诗歌声律主张,推动了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全新发展,从而为律诗定型开了先河。
二、“诗可以群”与初唐唱和
任何文学体裁的最终形成不仅要继承先前的传统,还需要进一步发挥创造性,不断地革新和积累,通过在大量的实践创作中来提高和完善,律诗定型也不例外。尽管六朝以皇室为主导的集体游宴活动非常丰富,也有大量的文学集团,但其诗歌的主要创作还体现在个人的才艺方面,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颜谢”等等,对于游宴赋诗并不热衷,声律还只局限于少数文学集团的内部讨论,处于原始阶段,发展较为缓慢。而初唐则不同,初唐的几代皇帝对于新体诗极为推崇,进而影响了各个学士集团,从十八学士到景龙学士,作为文学侍从,这些学士集团在志得意满之时,出于“事君”的需要,对声律的追求不断从自发靠拢走向自觉的群体融合,“文人群体亦开始自觉地按照统治者的要求打造自我,将诗歌创作置于儒家文化规范之下,以期实现个体价值”[3]。从各种资料统计,贞观朝唱和39次,赋柏梁体1次,唱和诗(含应诏和应令)共计约93首;高宗朝应制奉和共计37次,赋柏梁体1次,唱和诗约105首;武则天时期,共计唱和51次,唱和诗约91首;景龙时期共计应制奉和74次,赋柏梁体4次,唱和诗作达343首,盛况空前。不难看出,从太宗到中宗,上层诗歌的唱和随着诗人群体的扩大而日渐繁盛,至中宗达到顶峰,不但包括皇室的应制、应诏和应令,其他士人文会也此起彼伏,大规模的有安德山池宴集、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体等,“群居相切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律诗的定型也就有了坚实的根基。
邓绎《藻川堂谭艺·唐虞篇》认为:“一代文辞之极盛,必待其时君之鼓舞与国运之昌皇,然后炳蔚当时,垂光万世。”此二端在初唐得以最为切实的体现:
1.君之鼓舞
“有唐吟业之盛,导源有自。文皇英姿间出,表丽缛于先程……是用古体再变,律调一新;朝野景从,谣习浸广。重以德、宣诸主,天藻并工,赓歌时继。上好下甚,风偃化移,固宜于喁遍于群伦,爽籁袭于异代矣”(《唐音癸签》卷二十七)。从历史记载来看,唐太宗早在武德四年就招纳十八学士,武德九年九月即设弘文馆,开始闫文修武,“以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倡导诗歌活动,开启初唐君臣唱和的序幕。高宗“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旧唐书·文苑上》),特别是此时类书的大量编纂,在“武后之雄才大略,诗文宜无所不能”的侵染下[4],进一步推动了唱和的范围与规模,“唐兴文雅之盛,尤在则天以来。内有上官之流,染翰流丽,天下闻风。而苏、李、沈、宋接声并骛,文士之多,于此为盛”[5]。中宗于神龙二年(706年)设修文馆,景龙二年(708年)“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选公卿以下善为文者李峤等为之。……于是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儒学中谠之士莫得进矣”(《资治通鉴》卷二零九)。因此,高棅《唐诗品汇·五言律诗叙目》云“律体之兴……唐初工之者众,王杨卢骆四君子以俪句相尚,美丽相矜,……陈、杜、沈、宋、苏颋、李峤、二张(张说、张九龄)之流相与继述,而此体始盛,亦时君之好尚矣”。“君之好尚”不但扩大了“群”的范围,也确立了“群”的审美追求,从而为诗律的发展提供了最高层面(皇帝)的权力支持。
2.国运之昌皇
国运之昌皇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才兴,而初唐沿用了前隋的科举人才选拔制度,大力擢升文词之士。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开始设科取士,太宗则打破传统的氏族观念,选材“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列传第十五》)。高宗进一步大开进士之门并首创“殿试”,而进士犹主文词,显庆三年(659年),“春二月乙亥,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惟郭待封、张九龄五人居上第,令待诏弘文馆,随仗供奉”(《旧唐书:本纪第四·高宗上》),通过公开的方式遴选治国良才。武后更是重科举而轻门第,尤重进士科,“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大唐新语》)。至“中宗景龙之际,……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这就使得大批寒族庶士得以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社会,从根本上打破了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的“门荫”方式,下层知识分子就有机会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治世理想。而通过科举(同门或同年)得以晋升的士人出于“事君”的考量而自然形成了“群”,“凡进士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唐六典》卷四),这就确立了“诗可以群”在诗歌审美倾向和范式等方面的趋同,从而为声律的完善提供了规模和质量上的保障。
“君之鼓舞与国运之昌皇”促进了人才的勃兴和文词的发达,特别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实施,不但扩大了诗人的群体规模,更为诗人群指明了赋诗的审美情趣和遵从规则,促使“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祖习既深,奔竞为务。……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旧唐书·杨绾传》卷一一九),这种重诗艺高下而不重经史的诗人群体,其审美趋同因“君之鼓舞”逐渐演变成诗坛的主流倾向。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便成为读书人仕进的不二法门,统治者为控制思想也大力提倡诗教,并通过亲自参与和组织诗歌创作来体现对诗教的重视,借以宣扬皇权统治的最高权威性,臣僚则可以通过应制唱和来表达对皇帝的认同和尊崇,并因此而得以晋升,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从而形成一种上下团结和谐的关系,“诗可以群”就是这种关系的直接体现,从这个角度说,“诗可以群”的目的就是政治。“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为提升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些诗人“寻芳逐胜,结友定交,竞车服之华鲜,骋杯盘之意气,沽激价誉,比周行藏”(《唐摭言》卷三),就自然会进行针对更有利于政治前途的选择,追求适合“群”的审美趋同也就成为仕途晋升的最主要选择,“群居相切磋”就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这就为律诗定型提供了完备的前提和基础。
三、“诗可以群”与律诗定型
《梁书·文学·庾肩吾传》云:“初,太宗(萧纲)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大同)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而魏征认为“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隋书·文学传序》)。据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的统计:在齐永明至梁中前期新体诗120首,包括代表人物王融、谢朓、沈约等的新体诗无一是粘式律(对律诗定型具有关键意义),而粘对律、对式律分别为65%和35%;至梁大同时期,庾肩吾、萧绎的粘式律达到13.64%和15.62%;至梁末期,诗人群的粘式律达到总计9.05%;至陈末达到16.67%;隋末只有 14.81% 。[6]86-93虽然隋朝的粘式律略有下降,但总体上还是呈上升趋势。
初唐时期,由于皇帝的推崇,“群”的社会功能促进了诗律的迅速发展。唐太宗“首开吟源,宸藻概主丰丽,观集中有诗《学庾信体》,宗响微旨可窥”(《唐音癸签》卷五),“上有所好,下必甚之”,通过对庾信新体声律、偶对技巧的模仿和学习,对唱和诗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推动了贞观时期新体诗声律的水平有了新的发展。先看虞世南《赋得临池竹应制》的声律(以平水韵为标准,⊙表示可平可仄,下同):
葱翠梢云质,垂彩映清池。波泛含风影,流摇防露枝。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
龙鳞漾嶰谷,凤翅拂涟漪。欲识凌冬性,唯有岁寒知。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
此诗作于太宗637年,在“粘”的方面非常谨严,完全符合“粘”的要求,中二联也对仗工稳,在“粘式律”和“对式律”都比隋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在平仄方面却有明显不足,在平仄方面有5处不合,分别是“翠”应平(拗)、“云”应仄、“漾”应平(拗)、“有”应平(拗)、“寒”应仄,其中的三处“拗”还没有“救”的迹象,作为江左诗人杰出代表的虞世南,也是当时诗坛的领袖人物,其唱和诗歌的声律在此时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武德、贞观间,太宗及虞世南、魏征诸公五言,声尽入律……,即梁、陈旧习也”(许学夷《诗源变体》),而从上述分析来看,在“庾信体”的“典则”与“新巧”方面则取得了进步,可以认为,贞观诗人继承了梁、陈的声律创作模式,经过“群居相切磋”,斟酌声律,并使其成为唱和审美追求的一种主流倾向,这对于律诗的定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经过贞观诗坛的声律发展,至高宗时期逐渐形成整个“文场”的趋同,“龙朔初岁,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假对以称其美”(杨炯《<王勃集>序》),这种对诗歌审美形式的追求也提升了其理论的发展。此时元競《诗脑髓》、上官仪《笔札华良》和崔融《新定诗格》无一不把声律作为主要的内容来加以申明,“(元)兢、(崔)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文镜秘府论》西卷),从理论上确立了律诗的声调格式,“上官仪诗律学对初唐五言律体形成最为深远的影响,却在于它直接导致了元兢声律学尤其是调声术的产生。……新体诗‘二二一’音步的发现最迟应在高宗朝中前期,而且很可能是元兢发现的”[6]42,“元兢虽然提倡律体式的调声,但是这之外的调声形式并没有彻底疏远,比起第一字来更重视第二字,这已接近近体诗的规则,把平声和上去入三声对应起来,也前进了一步”[7]。试看陈嘉言《晦日宴高氏林亭》:
公子申敬爱,携朋玩物华。人是平阳客,地即石崇家。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
水文生旧浦,风色满新花。日暮连归骑,长川照晚霞。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
此诗作于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其平仄有6处不合,分别是“子”应平(拗)、“朋”应仄、“物”应平(拗)、“地”应平(拗)、“即”应平(拗)、“崇”应仄。但出现了通过“拗救”来弥补格律的不足,“子”拗“朋”救、“即”拗“崇”救。虽然“靡缛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诗薮·内编》卷四),但新体诗的格律规范无疑有了巨大进步。作为晦日置酒林亭的普通参与者,其新体诗合律如此之高,足以说明在“群居相切磋”的过程中,声律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取得了巨大突破。
武则天“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风”(沈既济《词科论》)。下层文士通过科举得以晋升,便自发地向上层靠拢,以期获得上层的认可与优待,唱和场所就成为“群居相切磋”的主要阵地。而在武则天授意下编纂的《芳林要览》,其序指出“近代词人,……文乖丽则,听无宫羽。……谢病于新声,藏拙于古体,……声节不亮,……弃徵捐商”,提倡创作新体诗和讲究声律谐和的用意更加明显,对于当时的科举入士者来说影响巨大,“众辙同遵者摈落,群心不际者探拟”(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可以看出,正是通过“群”的切磋,使声律不断得以强化,如宋之问的《幸少林寺应制》:
绀宇横天室,回銮指帝休。曙阴迎日尽,春气抱岩流。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
空乐繁行漏,香烟薄彩斿。玉膏从此泛,仙驭接浮丘。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
此诗作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从格律来看,虽然在平仄方面有15个不符,但除“乐”字外,其余“宇”与“天”、“銮”与“帝”、“阴”与“日”、“气”与“岩”、“烟”与“彩”、“膏”与“此”、“驭”与“浮”基本符合“拗救”的要求,全四联韵度和谐,中二联对仗工稳,因而《新唐书·杜甫传赞》认为“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研”。所以胡震亨认为“学五言律,……先取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苏(味道)、李(峤)诸集,朝夕临摹,则风骨高华,句法宏赡,音节雄亮,比偶精严”(《唐音癸签》卷三)。可见,通过“诗可以群”,实现了五律基本定型;同时为七律的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沈、宋等“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深刻影响着下层文士的科举晋身,自发追随主流审美趋向便成了自觉,“至中宗神龙前后,沈佺期和宋之问先后知贡举,总结了声病对偶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正式将这一诗体约句准篇,制定格式,命名为律诗,以科场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进士试诗的体式,并借行政命令的力量迅速传布远近,为广大文士所共同遵循”[8]494-495,试看张说《侍宴隆庆池应制》,其诗云:
灵池月满直城限,裁帐天临御路开。东沼初阳疑吐出,南山晓翠若浮来。
⊙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
鱼龙百戏纷容与,兔鹅双舟较溯洞。愿似金堤青草馥,长承瑶水白云杯。
⊙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
此诗作于景龙四年(710年),同题现存11首,正是唱和应制最为繁荣的时代,张说作为下层晋升的士子,垂拱四年(688年)因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而跻身宫廷,先后入珠英学士、景龙学士,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从声律上看,此诗句法严整,研炼精切;平起平收,格律合度,韵调谐和,虽有三处小“拗”(第5字“直”应平、第37字“鹅”应仄、第42字“洞”应平),但完全符合“谐”的要求;四联全部偶对精工,皆符合“俪”的法则;全诗光彩四溢,色彩斑斓[9]。因而被明代格调论的弘扬者——谢榛评为“近体第一”,“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诗家直说》卷一),其已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标准化七律。唐代顾陶《唐诗类选序》认为:“爰有律体,祖尚轻巧,以切语对为工,以绝声病为能,则有沈、宋、燕公……皆妙于新韵,播名当时。”“妙于新韵”正是律诗定型的最好注脚。
总体上看,初唐时期,由于“君之鼓舞”,诗律得到了更为快速的发展,武德贞观时期五言新体诗的粘式律总计 34.51%、高宗朝 46.27%、武后朝86.56%,其中的珠英学士更是高达93.12%。而从贾晋华的统计来看,《景龙文馆记》现存诗369首,完全合律的283首,占76.69%;而《珠英学士集》现存诗276首,但完全合律的只有23篇,占8.3%。从701年《珠英学士集》的编撰到《景龙文馆记》的完成,数年间,景龙学士的合律程度提高了5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不合律的诗歌大多来自于非学士的公卿大臣之手[8]66,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离群”。这进一步阐明了“诗可以群”在诗律形成方面的重要意义,与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的论述基本一致。这也足以说明:是“诗可以群”最终促进了律诗的定型。
结语
“诗可以群”推动着诗律的发展和进程,并贯穿于诗律形成的始终,在“事君”的影响下,从竟陵文学集团到初唐的景龙学士群体,其在诗律方面的表现无一不是“群居相切磋”的结果,特别是初唐时期的唱和“群诗”,具备了“群”之“和”且有“切磋”之义,与汉魏六朝的君臣赋诗有了很大的不同,不仅由于实行科举而促使诗人群体的范围和规模得以扩大,更由于对传统儒家诗教的推崇而出现“递相党羽,用致虚声”,此时的宫廷宴会、府邸游赏及同僚欢庆等系列活动,突破了魏晋以来贵族游宴及诗歌集群活动单纯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在展示新进士子壮志得酬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个人审美趣味与群体审美倾向的趋同,进而在诗歌艺术的追求方面保持群体的一致,这“与文学侍从为上而作的游宴诗自是不同,也胜于前述金谷‘以叙中怀’、兰亭‘世殊事异,所以兴怀’的自诉,具有一种向上的进取精神,对推动诗歌的集体创作是有益的”[12]。从本质上说,初唐的宫廷和贵族宴飨悠游活动与历史一脉相承,是“群”之“宴享”之本意,是社会上层“群”而“诗”的继承和发展。而在下层文士可以借科举得以晋身宫廷的社会背景下,群体性品格的形成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文人学士自发地从个体差异走向“群”之所向,这种审美观照下的诗艺追求,使得“诗可以群”的范围和功能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行为方式和创作实践上能够有机结合的同时,艺术手法也就能不断地推陈出新,不断促进近体诗声律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完善,律诗的体式更臻于成熟、完备,并最终达到定型。
[1]吴承学,何志军.诗可以群——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J].中国社会科学,2001(5):165-174.
[2]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125.
[3]汤燕君.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J].浙江社会科学,2012(7):133-138.
[4]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第二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3):10.
[5]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M].上海:上海书店,1990(8):197.
[6]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
[7]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12):171.
[8]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
[9]陈伯海.唐诗学史稿[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5):493.
[10]邓乔彬.进士文化与诗可以群[J].文学评论,2006(4):119-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