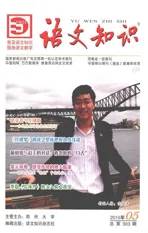《窗》:两个“突然”的微妙意味
——兼谈小说陶冶功能的实现路径
2015-02-13江苏省如东县教师发展中心龚建新
☉江苏省如东县教师发展中心龚建新
《窗》:两个“突然”的微妙意味
——兼谈小说陶冶功能的实现路径
☉江苏省如东县教师发展中心龚建新
《窗》是苏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下册“小说之林”单元的一篇课文。与教材配套的《语文教学参考书》这样分析:“通过对同病房的两位重病人相互之间所持态度的描写,表现了美与丑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灵,体现了极其深刻的扬善贬恶的道德力量。”也有人认为“通过一扇心灵之窗写出了人性的美丑与冷暖,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也看到了人性的卑劣,更看到了人性的冷漠。”阅读重心基本落在对比手法上,并在社会历史的框架里寻求对于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解释和分析。
细读小说,尤其是细细品味和把握文中的两个“突然”的微妙意味,我们读到的可能不是“美丑”的对比,也不是“扬善贬恶的道德力量”,甚至也不是对人性美丑的标签式理解。
有论者认为“靠窗的病人进行编造,其目的是想解除同伴的痛苦”。纵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小说自始至终,没有描写“靠窗病人”的心理活动,文章根本没有所谓“相互之间所持态度的描写”。“想解除同伴的痛苦”的揣测难免有游离文本、过度诠释之嫌。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两位重病人之间的心灵对比,作品的主题不是通过两个人物的对比表现出来的。
相反,小说花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不靠窗病人的”心理活动。“很显然,这个窗户俯瞰着一座公园,公园里面有一泓湖水,湖面上照例漫游着一群群野鸭、天鹅。”句中的“很显然”一词,公园的景象是“不靠窗的病人”在听了描述后在脑海中呈现的心理图景,应该说这幅图景不仅仅是靠窗病人描述的公园景象,更有他自己听了以后的想象。“津津有味地听这一切。这个时刻的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受。……仿佛亲眼看到了窗外所发生的一切。”叙述的都是不靠窗的病人的内心感受。至于“一天下午,当他听到靠窗的病人说到一名板球队员正慢悠悠地把球击得四处皆是时,不靠窗的病人,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以后,作者叙述更聚焦于他的纠结、挣扎与沉沦。
作者为什么把目光聚焦于他“挨着窗户”的欲念产生后的纠结、挣扎与沉沦?要想理解其中的奥妙,必须把握两个“突然”,这两个“突然”是解析“不靠窗病人”的心理和文本深刻意蕴的切入点。
一天下午,当他听到靠窗的病人说到一名板球队员正慢悠悠地把球击得四处皆是时,不靠窗的病人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偏是他有幸观赏到窗外的一切?为什么自己不应得到这种机会?他为自己会有这种想法而感到惭愧,竭力不再这么想。可是,他愈加克制,这种想法却变得愈加强烈,直至几天以后,这个想法已经进一步变为:紧挨着窗口的为什么不该是我呢?
他白昼无时不为这一想法所困扰,晚上,又彻夜难眠。结果,病情一天天加重了,医生们对其病因不得而知。
一天晚上,他照例睁着双眼盯着天花板。这时,他的同伴突然醒来,开始大声咳嗽,呼吸急促,时断时续,液体已经充塞了他的肺腔,他两手摸索着,在找电铃的按钮,只要电铃一响,值班的护士就立即赶来。
两个重病人,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病房里,几乎是生活在孤独与绝望之中,假设没有后面同伴“突然”发病,根据上文情节的发展(“病情一天天加重了,医生们对其病因不得而知”)可以预见:某一天的早晨,医护人员定然会静悄悄地将“不靠窗病人”的尸体抬了出去,丝毫没有大惊小怪。如果将我们“摆”进这样的境地,遭遇他们的世界和人生,很多人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欲念。在这样的情景中,面对“靠窗病人”每天两个小时能够亲眼看到窗外的特殊待遇,产生“挨着窗户”的欲念是“突然”的,但是这个“突然”的想法,对走在人生边缘的人来讲,也在情理之中。当读者在体味、感受着,甚至“同情”着他的因为“克制”而备受煎熬的时候,同伴在一天夜晚“突然”发病,小说情节发生陡转,这个“突然”不仅是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窗口”,更是展现一个人人性善恶的“窗口”。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夜晚,面对着突然到来的可能“占据窗口那张床位”的机会,“不靠窗病人”的曾经惭愧、竭力克制的欲念,陡然变成了一种“占据”的恶念。一旦恶念形成,他便不再惭愧,不再克制,最后纹丝不动、盯着天花板,看着同伴在绝望和痛苦中死去。
也许正是情节和感情的逆转,尤其是因为见死不救而“导致”同伴死亡,让不少读者在不齿、甚至痛恨他的时候,对小说的真正立意产生了误读,即在同情“靠窗病人”的死亡的同时,以美好和善良的意图来推测他虚构窗外景象的动机。但是解读作品,分析人物形象,不能凭借脱离文本的推测。从小说情节发展来看,“靠窗病人”没有对情节发展方向产生直接影响,只是辅助性角色,他的形象是模糊的,因此,不能认为两个人物形象有对比的效果,也不能通过两个人物的对比来探究作品主题,而应该从“不靠窗病人”心理和行为,尤其是两个“突然”所造成的情节逆转来探究作品的意蕴。
叔本华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一种盲目的不可遏制的生命冲动,个体接受这种冲动的驱使,不断产生欲望,欲望意味着欠缺,欠缺意味着痛苦。因此,有评论者说:文学就是要面对欲望和恶,好小说的特征就在恶。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随时(“突然地”)都有可能因某种“欠缺”产生“占据”的欲念,如果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这个欲念的实现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失去,因为伦理约束,我们可能会“克制”这个欲念,这种“克制”就造成了更为痛苦的体验,所以“欲望是痛苦之源”。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人性中潜在的“恶”,一个人被压抑的“占据”欲念可能是可怕的。帕斯卡尔说:“欲念乃是我们全部行动的根源”,一旦遇到“突然”可能实现的机会,就会变成一种不顾一切的恶念。恶念又往往如“不靠窗的病人”一样是“突然”产生的,而恶念必然会导致恶行,从而可能产生毁灭性的力量,毁灭别人,也毁灭自己。这种恶行有时不在于你做了什么,有时还在于你该做的时候没做什么,如同“不靠窗病人”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一动不动,见死不救。这就是这篇小小说震撼人心、意蕴深刻之所在。它通过两个“突然”打开了人性的幽暗层面,在我们还在对“靠窗病人”因为克制而纠结、痛苦而产生同情的时候,恶行的突然到来,不仅让我们震惊,也让我们对自己的可能产生的“恶”保持一种警醒。“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禽兽;但是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帕斯卡尔)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不承认恶,这本身就是恶;它使我们成为站在破坏狂一边的帮凶。”只有敢于正视并约束自己的恶,才有可能不断发现并选择善,才有可能实现灵魂的救赎,而不是简单地居高临下地鞭挞或者唾弃“不靠窗病人”。这应该是读者从“窗”中看到的。
阅读小说不能以所谓的“批判”“揭露”为旨归,总是以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者立场睥睨作品中的人物。长此以往,文学教育就会沦落为虚假的道德说教,而虚假道德说教只会是伪善,文学作品就会失去对学生精神成长的促进作用。有学者告诫说:“阅读小说,首先不是去‘解释’,而是把自己‘摆’进去,带着自己的人生经验去遭遇小说的世界,遭遇小说里的人生。”通过文本细读,情感体验,引导学生“摆进去”,让学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病人”,都有可能在生活中某个“病房”里成为“靠窗的病人”,在这样的阅读移情中,产生灵魂自省,才有可能真正地读懂人生、读懂社会、读懂自己,才有可能发挥小说陶冶和净化心灵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