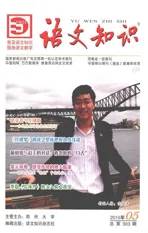“择所适”:《放鹤亭记》的哲理取向
2015-02-13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高华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高华
“择所适”:《放鹤亭记》的哲理取向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高华
苏轼的《放鹤亭记》写于谪贬徐州期间,记述了苏轼拜访云龙山人的一番问答及讨论。在教授《放鹤亭记》集体备课时,有的老师认为,“放鹤”“招鹤”表明作者仍在隐与仕之间的矛盾与徘徊;有的认为,课文表现的是苏轼随遇而安的消极情怀……苏轼的《放鹤亭记》情感取向到底是怎样的?
一、归隐:非《放鹤亭记》主要情思
归隐是不是《放鹤亭记》的主要情感取向?这要看苏轼为官经历与写作《放鹤亭记》时的政治生活情形。
《放鹤亭记》写于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这一年,苏轼在徐州做太守,也就是知州。教参上说是因为“被贬”。这次“被贬”与黄州时的“被贬”有什么不同呢?这就要对苏轼为官经历做一梳理。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21的苏轼赴京参加朝廷科举考试。翌年,他以《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赏识。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苏轼服满还朝,仍授本职。当时,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宰相并变法,苏轼与之政见不合,自求外放。1071年(熙宁四年),苏轼先到杭州做了2年零9个月的杭州通判,后被调往密州任知州(1074年)。后来又转任徐州知州2年。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任湖州太守3个月时,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入狱,坐牢103天,后被降为黄州团练副使。
从以上史料看,苏轼“被贬”徐州与黄州时有明显的不同,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苏轼的“自求外放”“超然于尘埃之外”,不过是远离朝廷斗争的是是非非。因为苏轼每到一处都“政绩显赫,深得民心”。他在徐州时曾积极“抗洪灭蝗,贩贫救孤”。可见,写作《放鹤亭记》时,苏轼还是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此时心情是无关“隐与仕之间的矛盾与徘徊”的。他对云龙山人张君张天骥强调了“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但作为郡守,他还不至于到达“弃官归隐”的地步。也就是说,“隐与仕之间的矛盾与徘徊”的说法,站不住脚。
而如何理解《放鹤亭记》中些许向往隐居生活的情丝?《放鹤亭记》中云龙山人张君养鹤、放鹤,苏轼则观鹤、谈鹤。这些都与“鹤”文化的道家取向相关。
“鹤”又叫仙鹤,性情雅致,形态美丽,素以喙、颈、腿“三长”著称。“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跟仙、道、人的精神品格有着密切关系。道家文化中,“鹤”冰清玉洁,超凡脱俗,云游世外,是清闲洒脱、自由自在的隐士形象的写照。古人多以白鹤称赞高尚的贤达君子,誉之为“鹤鸣之士”“仙风道骨”。比苏轼稍早的林逋,隐居杭州孤山时植梅养鹤,就是显示自己的清高自适。
《放鹤亭记》中的云龙山人张君,也是这样的道人。他隐居在云龙山。1078年,他在山顶上建了放鹤亭。现在,云龙山还有“张山人故址”。其东侧便是“放鹤亭”,亭西侧有“饮鹤泉”,泉南高耸之处有“招鹤亭”。至今,泉、亭相依已逾千载。当年,张山人以鹤为伴、修建放鹤亭等,表达的只是他的道教情怀,这都构不成《放鹤亭记》的“归隐”主题。当时,苏轼愿意为放鹤亭写“记”,甚至苏轼还喜欢鹤,并不能说明苏轼就要归隐,也不能说明归隐是主要情感取向。
《教学参考》认为,作品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有的老师便附会出“有明显的出世归隐思想”……顺着这种思考,有的老师认为,鹤“甚驯而善飞”,在西山飞翔得很自由,并据此认为西山为隐逸自由之地。而鹤长期受“其余以汝饱”,表明鹤受东山之人的束缚,而“西山”才代表自由。这就表明了苏轼的隐与仕的矛盾思想。我以为,这说法非常勉强。我们能凭借“甚驯而善飞”和“其余以汝饱”来断定鹤是否自由吗?“其余以汝饱”,只是张山人隐居清闲生活的一个环节而已。哪里就能据此断定鹤回东山吃粮食,在东山就是不自由的呢?东山不自由,可闲云野鹤般的张山人就在东山啊!这岂不与“隐居之乐”矛盾?难道苏轼为张山人写篇“记”,还要挖苦鹤在东山受束缚吗?
二、“择所适”:乃《放鹤亭记》哲理取向
苏轼的亭台楼记,从来都不是为记而记,为他人而记,而总是由此及彼,点化议论,以借题发挥。阅读《放鹤亭记》时,我们要注意三个意象:云龙山人张君、放鹤与招鹤、苏轼。
云龙山人张君是隐士,身上充满着道家精神。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迁草堂事件”上。课文第一句有“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所以,“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张君非常“识时务”,他果断地将草堂迁于“故居之东”。可见,张君懂得“择所适”的道理。
张君懂得“择所适”,“鹤”怎样呢?“放鹤”“招鹤”也懂得“择所适”。“放鹤”之时,张君“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他“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让鹤自由高飞。“放鹤亭”为什么适合“放鹤”?一是“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二是因为“山人之亭,适当其缺”。从“放鹤之歌”来看,“鹤飞去兮西山之缺”,可以“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同时,由山顶“放鹤”,鹤可以“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也就是说,张君“放鹤”善于选择地方——“适当其缺”,而鹤也可以“择所适”。因此,“放鹤”时的“择所适”,与迁草堂于“故居之东”的“择所适”,是同一道理:积极适应自然,顺应自然。
“招鹤之歌”中强调,鹤终日于涧谷之间“啄苍苔而履白石”,因为有“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有“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所以要“招鹤”使之“归来兮”。“招鹤之歌”为什么说“西山不可以久留”?因为张君“不适”。“西山”象征什么?是隐逸自由吗?其实,“西山”不是隐逸自由的象征,而是不适之处的象征。比如张君在“西山”时,“水及其半扉”;比如鹤飞西山,“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者担心鹤不适,才努力“招”回。张君离开了“西山”、“鹤”不能久恋“西山”和苏子的“自求外放”,皆是因为“西山”不可长久停留。可见,这三个意象都涉及道家思想——“择所适”。
张君、鹤和苏轼三个意象是什么关系?我以为,前两个是“择所适”的形象,苏轼引出这两个意象,还是在“讲述苏轼自己的故事”。课文表现的就是苏轼独特之悟:“择我适”。苏轼并不是在向往归隐,也不是在隐与仕之间徘徊,他强调的是要“择所适”。联系苏轼此时状态看,神宗熙宁四年,苏轼因政见不合,“自求外放”。苏轼的“自求外放”本身就是“择所适”的表现。在徐州,他“抗洪灭蝗,贩贫救孤”是“择所适”;写作《放鹤亭记》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也是“择所适”。苏子本有道家倾向,所以,他才乐与张山人相识相处,才乐意为张山人的放鹤亭写文章。也就是说,《放鹤亭记》在强调,人要学会“择所适”,即道家主张的积极顺应自然,学会适应,自得其“适”。
三、鹤、酒相比:强化“择所适”的审美厚度
如果说《放鹤亭记》中张君、鹤和苏轼三个意象是生活中存在的,那么,由眼前之物展开的精神联想,则是理解课文的关键。
苏轼“握山人而告之”的内容,是建立在对张君、鹤的“择所适”基础上的。“子知隐居之乐乎?”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你了解隐居的快乐吗?”它还隐含着“你知道隐居为什么是快乐吗?”因为后面的“《易》曰”“《诗》曰”不仅仅是“隐居是自由快乐”的答案,还是“隐居为什么是自由快乐”的答案。所以,“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既是表象,还是因由;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当然,“《易》曰”“《诗》曰”还隐含着这样的思考:“鹤为什么能够给人们带来自由快乐?”这样,才生成后面的推测:“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而隐居为什么是“自由快乐”的呢?上文说过——“择所适”;鹤为什么能带来“自由快乐”?上文也说过——“择所适”。而苏轼自己应该怎样让自己“自由快乐”?显然,这是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思考。
为了强化“择所适”,苏轼把自己的观点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去审视。这就是苏轼在联想到“《易》曰”“《诗》曰”诗句后,再次深入联想到的两个文史典故。这也是深入理解《放鹤亭记》借题发挥的关键。
鹤、酒是道家宠爱之物。鹤本是清远闲放之物,好鹤本是一大雅事,有助于修身养性。“隐德之士”如果“狎而玩之”后,“有益而无损”,可是“卫懿公因好鹤则亡国”。酒本是“荒惑败乱”之物,纵酒狂歌向来是隐士的嗜好,是以“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但刘伶、阮籍却因酒而出名,——他们以狂歌纵饮而逃避现实,在全身远祸时守真养性。卫懿公好鹤为什么会亡国?酒乃“荒惑败乱”之物,刘伶、阮籍之徒为什么会因“酒”而“全其真而名后世”?原因就在这“择所适”上。“择所适”则存,“择不适”则乱。南面之君“亡其国”,是因“择不适”;而山林遁世之士,酒饮得“荒惑败乱”,犹不能为害,皆因“择所适”。“亡其国”“全其真”的结局,应该如何理解?无论鹤之爱还是酒之爱,苏轼不是强调两种生活情趣的迥然不同,而在强调看问题要辩证地看。这恰如云龙山人张君之住在西山“水及其半扉”,苏轼立于朝廷而麻烦不断一样。可见,无论是人之居、鹤之爱,还是酒之饮、官之处能不能“为害”,“择所适”非常重要。此刻,苏轼“自求外放”,来到徐州“饮酒于斯亭而乐之”,便是“择所适”。他游目骋怀,临风放鹤,有张君山人相伴;他把酒临风,举杯痛饮,以刘伶、阮籍为师。此等逍遥自在,此等痛快淋漓,不正是“择所适”的结果吗?这就是后文中苏轼说“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的原因。
苏轼由“鹤酒相比”生成的这一段经典论述,是放在“放鹤之歌”与“招鹤之歌”的背景下进行的。从“招鹤之歌”来看,这就是一幅隐居的清闲生活素描图。“招鹤之歌”“招”生出一片清闲生活、自由飘逸生活,这就是作者认为“不能为害”的适应和生存方式。“招鹤之歌”中“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是非常重要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是苏轼心中“择所适”的形象。他自由清闲,安然自适。这实际是苏轼对张山人生存方式的一种肯定,也是苏轼生存方式的自我反思、自我关照。生活中,“鹤”都能坦然的“出”与“入”,作者应该如何做呢?这才是理解作者的正确思路。这样看来,《放鹤亭记》是一篇自我反思的小品。
四、徐、黄相比:“择所适”的情感格调不同
徐州时,苏轼在政治、经济、人际等方面的情形还是比较好的。可以说,他的“择所适”观念是在生活之乐、隐居之乐中形成的。在徐州时,苏轼的《放鹤亭记》表达的“择所适”,与被贬黄州做团练副史时写的《赤壁赋》中的“随遇而安”选择心态一样吗?我以为,二者在内容与写法上有相似之处,但还是有质的不同。
写作《赤壁赋》时,苏轼的情形与徐州时大不相同。《赤壁赋》写于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这时苏轼以带罪之身谪居黄州已近四年。距离徐州写作《放鹤亭记》已经过了四年。试想,苏轼无辜遇害,谪居黄州,郁愤之情,实在难免。但他又能坦然处之,以达观的胸怀寻求精神的解脱,而不被颓唐厌世的消沉情绪所压倒。这样看来,说《放鹤亭记》中弥漫着“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实在没有道理。我们看《赤壁赋》中的这一段——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赤壁赋》中的这一段,由设问引发议论的写法与思路,与《放鹤亭记》中的下面一段基本一致:
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
试比较一下这两段的写法、思路与主张,我们能够看出苏轼的行文风格与内容差异。《赤壁赋》中的这一段是苏轼针对“客人”的人生悲观论而写。苏轼从宇宙变化说到生存哲理,他认为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一刻也不会不变,因而,人生短暂,自然可悲。但从不变的角度看,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在此基础上,苏轼提出他的随遇而安的生存观——“况且天地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苏轼强调,一切看淡以后,便能随遇而安。人世间的荣辱、得失、忧乐便不足为念了。此段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表达的就是到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上寄托的渴望。这样才能与自然相适,随遇而安。只是苏轼《赤壁赋》中强调的是随遇而“适”,与《放鹤亭记》强调的“择适”、主动顺应自适,是大不相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不同?苏轼在徐州时的被贬,是自贬,——他还做着徐州知州。这种“被贬”方式,苏轼多多少少是快乐的,也能够看到别人的“隐居之乐”。这就是《放鹤亭记》中为什么能够大谈“隐居之乐”,为什么苏轼能借助《放鹤亭记》借题发挥,大谈“择所适”。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放鹤亭记》可以理解为:人在某些时候要善于选择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只是《放鹤亭记》中的“择所适”,不是被动选择环境,而是积极顺应、善于选择。因为人生只有选择好适合自己的环境,“纵鹤所如”才能“高翔而下览”。
《放鹤亭记》中,苏轼借鹤言说“西山不可以久留”。其意主要在反思“择所适”的“外放”式选择。这种主动选择和后来在黄州时的经遇是大不相同的。当然,徐州时期,苏轼形成的“择所适”生存观,多少有些超然思想。苏轼的“择所适”思想,还是道家看问题的传统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