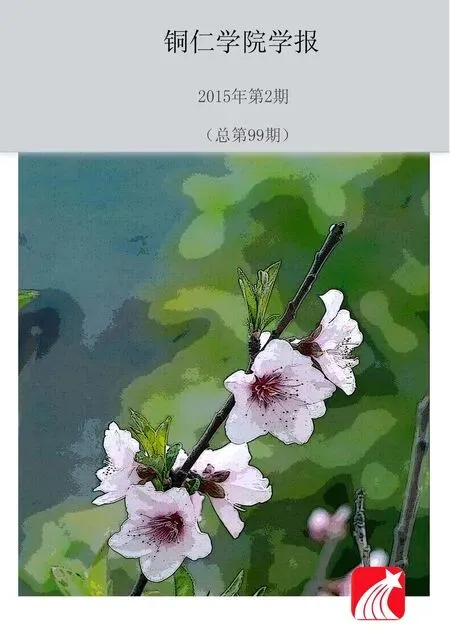李泽厚对实践美学的建构与解构
2015-02-13封孝伦
封孝伦
(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李泽厚对实践美学的建构与解构
封孝伦
(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李泽厚先生最先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语录提出并阐述了实践美学的核心精神,从而“创建”了“实践美学”。面对“实践美学”存在的诸多问题,他作了多次修补。在修补中,“实践美学”渐渐被他解构。
李泽厚; 实践美学; 修补; 解构
一、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
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是把“实践”定义为人的“本质”或“本体”。我们知道,哲学对“本质”的解释是“现象”得以发生的“内在规定性”。说人的本质是实践,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行为都被这个实践所规定。而人的一切行为及其成果则都是这个“实践本质”的外在表现。“实践美学”认为,美是由人类的社会实践产生的,美的事物是人的“社会实践”这个“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我们欣赏美的事物不是欣赏它的什么,只是欣赏这个事物中显现出来的人的“社会实践”这个本质力量。事物所以美,根本上,在于它“确证”了人的“社会实践”这个“本质力量”的存在。
众所周知,“实践美学”的最早创始人是李泽厚。虽然开始他不愿意承认,后来还是认下了。他最早提出用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来解释美的本质问题。他所重视和坚持的“实践”这个概念的出处,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践”这个概念,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本来是使用黑格尔提出的动态、宏观、辩证地认识事物的关于人类活动的哲学观念,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静止、抽象的人本主义。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里的“实践”,实际上是理解人的一个角度,即认识“人”必须看到人的“能动性”。在马克思看来,不从实践这个角度理解事物和人的感性,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缺点,但这个缺点并不能抹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优点。马克思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1]17很显然,马克思是利用黑格尔的“能动”的历史辩证法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的静止的抽象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把“现实、事物、感性”都看成是人的实践的结果,这与黑格尔把所有的“现实、事物、感性”都看成是绝对精神的对象化的结果——而人的实践不过是绝对精神对象化的工具——有理论渊源关系。马克思正是在批判性地接受黑格尔的过程中接受性地批判费尔巴哈。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把“实践”看作人的本质。他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8他并没有说人的本质是实践。他只是认为对于人的本质要从社会关系的总和来抽象,而不能从单个人来抽象。他认为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1]18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18就是说,只要把人看成能动的、实践的,就不会把人的社会生活理解为某种神秘现象的产物。因为能动的、实践的、在历史过程中存在的人,其复杂性是可以在历史的复杂关系中得以揭示和解释的,并不神秘。
1956年,李泽厚在他的《论美感、美和艺术》中引用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都是确定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也就是他的对象,也就是他本身的对象。”[2]25这段话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找到,译文稍有出入。照一般人的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这个“他”,就是人类。照黑格尔的理解,这个“他”,就是他提出的所谓“绝对精神”。李泽厚则有自己的理解,他指出:“这里的‘他’,不是一种任意的主观情感,而是有着一定历史规定性的客观的人类实践。自然对象只有成为‘人化的自然’,只有在自然对象上‘客观地揭开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时候,它才成为美。”[2]25这段话的前半段符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提出的“什么事物都应当作实践来看”思想,而在后半段,李泽厚把“人类实践”几乎就说成“人的本质”的代名词,因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就是由人类实践展开的。
李泽厚通过评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进一步展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定义比较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只是“生活”这个概念比较抽象空洞。李泽厚根据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个论断,指出,“社会生活,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①1980年结集出版时,他在注释里面为“社会实践”加上了“科学实验”这一项,以与毛泽东关于实践的说法相一致。见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他说:“人的一切思想,感情都是围绕着、反映着和服务于这样一种实践斗争而活动着,而形成起来或消亡下去。……这也就是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理想。”“美正是包含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有着具体可感形态的现实生活现象,美是蕴藏着真正的社会深度和人生真理的生活形象(包括社会形象和自然形象)。”[2]30说人的一切——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一切”——思想、感情“都是”围绕着、反映着和服务于“社会实践”在活动、形成或消亡,这隐含两个问题:一是实践的内容很宽泛,可以说无限宽泛,因为凡是与人的一切思想感情有关的都是实践。李泽厚的这个说法导致了日后有的美学家对“实践”内涵的泛化,而这恰恰又是他所反对的;二是思想感情太狭隘,只围绕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产生思想和感情,除此之外都不能产生思想和感情。李泽厚从始至今很明确并且多次地把“实践”限定在“三大项”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上。因此,按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很难解释与这三大项无关的审美活动和审美内容。如自然现象,如人体,如性爱。
李泽厚在这里还趁便运用他的实践观改造黑格尔的理论,“黑格尔说,‘理念’从感官所接触的事物中照耀出来,于是有‘美’。这‘理念’如果颠倒过来,换成历史唯物主义所了解的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理想,就可以说是接近于我们所需要的唯物主义的正确说法了。”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理想——即“社会实践”——从感官所接触的事物中“照耀出来”或显示出来,就是美。这个说法后来被他归纳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被有的理论家归纳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因为人的本质力量就是实践的力量。人的本质就是实践。在1956年的这篇文章里,李泽厚只是陈述观点,而没有论证观点。我们不清楚,人的本质为什么只是“社会实践”而不是别的?也不知道,把“实践”替换掉“理念”,怎么就实现了对黑格尔的“颠倒”?黑格尔的“颠倒”是精神决定物质。我们如果要把它“颠倒”过来就应该是物质决定精神。比较一下“实践”和“感官所接触的事物”两者,谁更“物质”,谁更精神呢?“感官所接触的事物”是精神吗?如果说它们都是物质,那就是物质决定物质,精神到哪里去了呢?
仔细阅读马克思原著,马克思并没有说人的本质是实践,他只是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只是说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其实就是人发出的一种行动。人的行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而“决定”人发出行动的那个“内在规定性”,才是人的本质。把人的行动说成是人的本质,然后说人的行动决定人的思想和感情,这恰好是把本与末颠倒了,实质上是把决定人何以要行动和如何行动的那个根本性的东西——真正的本质——忽略了,抛弃了。不过,这个“实践”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给美学讨论带来极大的兴奋,对当时的美学建构至少有两方面功劳和价值:一是它肯定人的活动对美的产生的决定意义,强调人的主观活动的物质性和社会性,这一点在朱光潜、高尔太虽然也强调人的主导地位但却被戴上“唯心主义”帽子饱受攻击的时期,对于保留人在审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至关重要。二是它可以作为时代英雄主义美学观的理论基础,因为它强调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对于我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文艺大力歌颂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的英雄提供了美学支持,这也为美学自身在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的生存加了分。
到20世纪80年代,“实践”这个概念还顺利实现了与“自由”这个时代概念的对接。因为恩格斯1876年写《反杜林论》时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3]153恩格斯的这个关于自由的说明,恰好与李泽厚所说的“实践”的内涵——掌握规律,改造自然——是一致的,这对于他把“人化自然”这个概念表述转换成“美是自由的形式”提供了方便。“美是自由的形式”响应了“文革”结束后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和呼唤,人们并不仔细推敲李泽厚说的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反正“自由”成了审美的最高旗帜,这又在中国大地迅速掀起了新一波美学热潮。我们后来从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里发现他关于人性的一些思考,其实就是他选择“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定义的根源所在。他认为人性不等于动物性。人性“应该是区别于动物而为人所特有的性质或本质”[4]423。他说:“人性是否等于动物性呢?人性是否就是吃饭、睡觉、饮食男女呢?……这是我不同意的。人性恰恰应该是区别于动物而为人所特有的性质或本质,这才叫人性。”[4]423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哪里呢?他认为在于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改造自然,这就是他非常看重的“实践”。他又进一步表述说:“人性应该是感性与理性的互渗,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融合。”[4]423这个表述与前面的表述存在矛盾。说区别就难说互渗,说互渗就难言区别。“区别点”是什么,感性还是理性?自然性还是社会性?在他看来显然是“理性”和“社会性”。而理性与社会性,恰好与“社会实践”相一致。
二、实践美学的逻辑困难
实践美学一经提出就存在困难,但人们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困难,因为“实践美学”在与“典型美学”的论战中坚持了人的核心地位,这是当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思考文学理论、艺术创造、审美活动所必争的一个理论立足点;是当时对付极左思潮,保留人在艺术和审美中的位置,坚持“文学是人学”所需要的一个桥头堡。因此,实践美学理论是至今为止拥有最多守望者的理论。在“文革”已然结束30多年,改革开放已然进行了30年后的今天,人们已不必仰仗某一把尚方宝剑——哪怕这把剑还没有完全铸成——就可以自由讨论学理问题的时候,实践美学创建之初就存在的一些问题,必然会日益明显地呈现出来,更为强烈地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些在创建之初看起来不显眼的问题,现在变得非常刺目。就像一间打扫得十分整洁的房间,偶尔出现一粒尘砂或落叶,都会让人觉得非常刺目一样。
实践美学太难解释许多看起来与人类实践无关的审美现象了。
首先是自然美——尤其是那些不可能经受过人类实践活动作用过的自然现象的美。太阳,月亮,高山,大川,大海,雪山等。如果说人化自然是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为什么在同一时期有的自然美,有的自然不美?有的自然此时看来是美的,彼时看来是不美的?从“人化自然”的逻辑来解释自然美,应该是“人化”的程序越是深入越是普遍就越是美,但为什么不是人类实践渗透得越深的自然越是美?
人体美也是实践美学解释的致命难点,它自古很少经过人类实践的改造,但人体从来是审美的重要内容。当代流行整容,这已是“实践”染指了人体的自然状态,应该说整过的容貌——这里排除失败的整容——一定是美的。但是不然。许多人不能接受自己的“丑妻”整容。而且,有的美人,当你知道他或她是整过容的,先有的美感就会锐减而不会增加。整容的美如果能够成立,真与美的关系就被颠覆了,美则美了,但是假了。而实践美学恰恰坚持的是真、善、美的统一。
实践美学也难以解释有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是美的,而有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丑的。它也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结果投入的实践活动多反而不美,而有的结果投入的实践活动少却很美很美。有的结果科技含量高不美,有的结果科技含量不高却很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实践美学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难以回答:美感的心理基础在哪里?实践美学把审美看成是一种反映,一种认识,一种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对“实践”的“确证”,对人的自由的“确证”。这与黑格尔美学观相一致。即看到了,证明了,对了,就美了。但我们在与美相遇时那种激动得心跳的愉悦感是怎么产生的?其心理基础和心理过程与人的生命动机有没有关系?是怎样一种关系?实践美学难以说明。李泽厚总是说心理学还不成熟,还解释不了审美中的心理过程。上世纪说要等到21世纪,这世纪说还要等到22世纪。其实,人类审美不断,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审美,这个心理过程是怎么产生的,都是有体验的,只是,我们被某种理论暗示了,被引向了一个不正确的方向。我们总是走不出认识论的梦魇,总是达不到真切把握美的彼岸。
另外,不论号称什么美学,它所坚持的逻辑起点必须是第一逻辑起点,其理论才可能彻底。如果不是第一逻辑起点而是第二逻辑起点,这个理论的解释范围就会有漏洞。从第一逻辑起点到第二逻辑起点之间的地带是它所不能覆盖的。人类的实践没有第一决定者吗?人类像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那样生而“实践”吗?人类为什么要实践?人类不实践行不行?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人类要生存,所以要实践。这样看,实践并不是人类行为的第一决定因素,而生命的生存需要才是第一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实践并不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第一逻辑起点。它充其量是由人类生命需要决定的第二逻辑起点。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与实践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审美现象实践美学解释起来如此困难。
对实践美学的质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发生了。潘知常、杨春时、汪济生以及后来的生态美学学派,都从自己的思考对美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潘知常提出要从人的生命的角度认识审美问题,否则美学就是无根的美学。这是真知灼见。杨春时明确提出要构建后实践美学理论,这实际上是举旗向实践美学挑战。汪济生则从人与动物的共同性入手,从根本上动摇实践美学的人学根基。许多人对实践美学的反思是不动声色的。人们仿佛已经厌倦了文革时期那种互不相容的否定批评方式。动辄以“唯心主义”帽子相扣,不容辩驳,比谁引用的语录更多。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年生命美学沉默耕耘之际,“生态美学”的活跃。生态美学一开始就引起了美学界较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生态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是反对以人为中心,同时与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相呼应。因此它一下子有许多工作可做,还来不及思考生态美学与实践美学是什么关系。其实生态美学一提出就受到追捧,与人们对实践美学的失望有关。生态美学与实践美学在一个问题上的正相反对有指标性的意义:实践美学强调对自然的改造,生态美学强调对自然的尊重;实践美学强调人的中心地位,生态美学反对以人为中心。中国美学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争吵,仿佛又回到原点。
“人类实践”可以有两解。一是作动词解,即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作动词解的时候,动作的实施主体为什么要实施这个动作,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个因素决定了人何以要实践,如何实践,达成什么目的。而实践美学仿佛从来不追问这个因素,只讨论如何实践——制造、使用工具——而不问为什么实践。在实践美学体系中,“实践”这个概念是抽象的,无人类目的的,人不过是“实践”达成实践目的的工具。二是作名词解,即“社会实践”,指的就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就是掌握规律,人化自然。这实践是规定性的,就是说,人类的一切实践内容在行动之前设定好了的,实践的结果不过就是把这些早已规定好的内容展现出来,对象化出来。如果实践产生的结果恰好能证明、能显示那早先设定好的内容,就行了,就对了,就美了。这就有一个问题,这些内容是谁规定的?先验的还是上帝给予的?李泽厚认为,是人类的实践活动“积淀”下来的。紧接着产生的问题是,是怎么“积淀”下来的,是通过什么方式“积淀”下来的?是把历史发生的所有的东西都沉淀下来呢,还是有所选择地进行积淀?如果有选择,选择的标准是什么?设立标准的依据是什么?李泽厚又把它交给未来世纪的心理学来回答。
三、李泽厚对实践美学的修补
像李泽厚这样的有智慧的哲学家,不可能不发现他所创设的实践美学中真正的问题所在,也就不可能不对他的理论进行修补。这些修补,一方面显示了他的坚持,一方面也显示了他的改变。
他做了三个重要修补。
第一个修补是关于“人化自然”的修补。这个修补进行了两个轮次。首先针对“人化自然”难以解释人类不曾有过实践改造过的自然何以美的问题。他提出的修补方案是从狭义走向广义。他说:“其实,‘自然的人化’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种,通过劳动、技术去改造自然事物,这是狭义的自然人化。我所说的自然人化,一般都是从广义上说的,广义的‘自然的人化’是一个哲学概念。天空、大海、沙漠、荒山野林,没有经过人去改造,但也是‘自然的人化’。因为‘自然的人化’是指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尺度,指的是整个社会发展达到一个阶段,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自然人化’不能仅仅从狭义上去理解,仅仅看作是经过劳动改造了的对象。”[5]96这个修补仿佛可以解决没有经过改造过的自然现象何以美的问题了,虽然牵强,却也能在理论上自圆其说。但是,却经不起深入追问: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应该是等量的、相同的,何以有的自然现象是美的,而有的自然现象却是不美的甚至是极丑的?另外,按照实践美学的逻辑,按照“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逻辑,应该是,人越是深入地切入自然,越是巨大地改变自然,所产生的后果越是美。但这常常不合审美实际。我们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下追求最为原始的,最没有人迹扰动的自然。
对这个问题,李泽厚作了他第二轮次的修补,他提出“人的自然化”概念。从文字概念上看,“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是两个反向的提法。既然要求人自然化,干吗还要自然的人化?李泽厚是这样说的:“人自然化是建立在自然人化基础之上,否则,人本是动物,无所谓‘自然化’。正是由于自然人化,人才可能自然化。正因为自然人化在某些方面今日已走入相当片面的‘极端’,才需要突出人自然化。”[6]57显然,这是从历史任务的角度来说明的,就是说,前一时期“自然人化”搞得太过火了,今天才要提出“人自然化”。这个提法与今天生态美学的思考相一致,但它从根本上颠覆了“自然的人化”的逻辑,颠覆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逻辑。
他的第二个修补,是从反动物性向动物性的修补。李泽厚主张人性是与动物性相区别的特性。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地方就是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也就是实践。这个观点特别注意对规律的把握和运用,特别强调人高于动物的精神境界。凡做美学的人都记得马克思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过“美的规律”,强调人只有在不食人间烟火的条件下的创造才符合美的规律。话是这样说的:“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说到这里,人已不是动物,是黑格尔的“理念”的化身。否则,他的生产如何是“全面的”?他如何“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看清了这一层,下面的“两个尺度”就好理解了:“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7]96-97实践美学也贯穿了这个精神。但这个精神实在难以解释文艺创作中的许多充满感性的现象。所以李泽厚在后期的著作中一再对这个偏颇进行补救。他开始强调人的动物性,强调人的物质需要。开始注重人的个体和生死。吃饭的问题明显地纳入了他的哲学视野。他也比较大声地强调人的情欲。2006年他对他早先提出的四种心理因素中的“情感”重新作出解释:“情有关欲望。欲望是属于自然性的东西。过去是衣、食、住、行,我后来加上性、健、寿、娱。……不仅仅限于吃饱,还有一个吃好的问题,也就是衣、食、住、行、性、健、寿、娱不断提高的问题。”[6]53他甚至高调重视生命的生与死,“人作为个体生命是如此之偶然、短促和艰辛,而死却必然和容易,所以人不能是工具、手段,人是目的自身。”[5]271所以他呼吁:“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吧。从而,也就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来吧!不再受任何形上观念的控制支配,主动迎接、组合和打破这积淀吧。艺术是你的感性存在的心理对映物,它就存在于你的日常经验中,这即是心理——情感本体。在生活中去作非功利的审视,在经验中去进行情感的净化,从而使经验具有新鲜性、客观性、开拓性,使生活本身变而为审美意味的领悟和创作,使感知、理解、想象、情欲①这四个概念在这里第一次从“情感”变成“情欲”,别有意味。。处在不断变换的组合中,于是艺术作品不再只是供观赏的少数人物的产品,而日益成为每个个体存在的自我完成的天才意识。”[5]272从这个修补我们看到,李泽厚早期强调“区别点”而不得不丢掉的“动物性”被他捡回来了。我们真正看到了他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说的:“人性应该是感性与理性的互渗,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溶合。”[4]423但这样一来,自然性和感性摆在一个什么逻辑位置上呢?是感性决定理性、自然性决定社会性呢?还是相反?这使得他有了第三个修补。
第三个修补是对逻辑起点的修补。这就是他提出的“双螺旋”理论。我们知道,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是“实践”,它强调理性,强调社会性,而轻视感性和自然性。由于社会审美文化和艺术发展不断地把“感性”与“自然”坚决而且铺天盖地地置放在美学的面前,让每个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它们的存在并考虑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它。面对这种理论困窘,有人把实践的概念泛化,以缓解非实践产生的审美现象与实践美学的矛盾。但李泽厚首先坚持,实践的概念不能扩大。“如果实践的概念无限扩大,最终会取消这个概念。如果把人的一切活动、行为,把讲话、看画、写文章、吃梨子都叫实践,那要实践这个概念干什么?那不就是人的行为与活动吗?我一直是不同意随意扩大实践的概念,特别强调‘狭义’实践的重要性和本源性。”[6]37怎么来解决实践美学不能解释的审美现象呢?他借助生物学中DNA的双螺旋结构作比喻,提出了一个双螺旋理论。所谓双螺旋,就是并行两个逻辑起点:工艺本体(有的地方说工具本体)和情感本体。就是说,在“实践”的旁边,并列站着“情感”这个本体。这不成了二元论了吗?李泽厚说:“我讲两个本体,也不是不可以。笛卡尔不是也讲二元吗?……我讲两个本体怎么就不行呢?”[6]44但他同时强调说:“这二者是有先后的,工艺本体在先,情感本体在后。尽管在制造工具本身的过程中,这两个就出现了。为什么要讲两个本体和先后呢?是为了强调前者的基础性和后者的独立性,因为后者本身对人类构成意义。”[6]44
把两个本体分出先后,这又回到了一元论,但是,说情感在工艺之后,这明显搞颠倒了。没有实践就没有情感?有了实践才有情感?在我们看来恰恰相反,有了情感,才有实践,在实践中会产生新的情感,但是决定实践得以产生的那个情感才是具有本体意义的情感。李泽厚在后面的论述中也把情感摆在了很重要的地位。情本体的提出,为他回答和解决现实的审美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方便。所以他对“情本体”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这也显示他提出“情本体”不是心血来潮,不是偶尔言之,而是深思熟虑的。他说:“大家也许没有特别注意,我一方面强调唯物史观,但另方面我又认为要走出唯物史观。走到哪里?走向心理。所以,我谈情本体、心理本体。”[6]49-50“现在,有许多犯罪,包括杀人啊,吸毒啊,等等,这里面当然有社会因素,但很多是心理原因。心理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所以,我就提出了心理本体或情本体。”[6]50他甚至说:“先秦儒学讲的是礼乐,汉代儒学讲的是天人,宋明理学讲的是心性,我是第四期儒学,我讲自然人化,情本体,实用理性,积淀,度,文化心理结构,等等,概括地说是情、欲,是儒学在现代的真正发展。”[6]54“情、欲”竟升格成了他的“儒学思想”的标志。仔细分析和体察,“情、欲”在他看来已是比“实践”更为重要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本体”。改革开放30年,学界似乎已经打破了“唯心主义”禁忌,泽厚先生显然已不在乎有人把他说成是“唯心主义”了。
李泽厚的这三个重要的修补有三个特点:一是“改造世界”的调子明显降低了,他从狭义的“人化自然”,到广义的“人化自然”,再到“人自然化”,“实践”征服自然的那种强烈愿望和气势减弱了。二是人的自然性在理论建构中的地位提高了。人作为生物存在,已经得到了他的承认并在论述中有明显的强调。三是逻辑起点明显前移了。原来强调实践的基础性和唯一性,后来转而强调情感。虽然没有放弃实践,但地位明显被弱化了。通过这些修补,我们突然发现,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已悄然发生了变化,他已明显修改了他提出的实践美学理论体系。
我们知道,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是实践,它是第一逻辑起点,犹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第一逻辑起点。双螺旋的提出,情感本体——有时候他表达为情欲——被鲜明地凸出了。虽然他说工具本体先于情感本体,但是有时他也承认,情感产生实践,这也就是心理决定实践,心理是什么决定的呢?是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的。愚公要搬掉太行王屋两座大山,先有想搬山的心理,然后有搬山的实践,而不是先有搬山的实践,然后有搬山的心理。那么这搬山的心理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愚公与山的关系决定的。山挡住了愚公的去路,所以他产生了搬山的心理,并在这心理的支配下发出了搬山的“实践”。显然,双螺旋理论的提出,实践已不是第一逻辑起点。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已被双螺旋结构消解。
四、李泽厚对实践美学的解构
提出“双螺旋结构”,必然会受到学术界的质疑。李泽厚自己也说,“有人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本来讲了工具本体,现在又讲了情本体,怎么有两个本体。责难我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8]77对此,李泽厚分辨说:“这个‘情本体’即无本体,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这个形而上学即没有形而上学,它的‘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情本体’之所以仍名之为‘本体’,不过是指它即人生的真谛、存在的真实、最后的意义,如此而已。”[8]75说“情本体”就是“无本体”?那么扔掉算了。干干净净坚持“实践”本体——工具本体得了。但他并不。好不容易弄出一个“情本体”,而且大家也都还认可,扔掉可惜。在该书中他还提到:“也有人说,本体是最后的实在,你到底有几个本体?因我讲过,‘心理本体’,‘度’有本体性,这不又弄了两个本体出来?有几个本体了。其实,我讲得很清楚,归根到底,是历史本体,同时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向外,就是自然的人化,是工具——社会本体;另一个是向内,即内在自然的人化,那就是心理——情感的本体了,在这个本体中突出了‘情感’。所以文化——心理结构又叫‘情理结构’。至于‘度’,人靠‘度’才能生存。在使用工具的原始狩猎过程中,就要掌握好距离远近、力量大小,便要有度。生产上是这样,生活上也一样,感情交往上也是这样,发乎情,止乎礼义,没有度怎么行?那就是动物性情感了。度掌握得好,烂熟于心,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哪里都有个度的问题。所以‘度’具有人赖以生存生活的本体性。这三点其实说的是一个问题,也就是有关人类和个体生存延续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8]77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李泽厚坚持“实践”基础上的“工具本体”时,大家一片叫好,并且处处加以运用。但当大家发现“工具本体”解决不了全部问题时,他增加一个“情本体”,学术界仍然一片叫好,只是觉得“情本体”他尚未说清,步步追问。同时,觉得“情本体”和“工具本体”难以合而为一时,他说,这是“双螺旋”结构。现在学术界没有叫好,而是有点讶异,有点纳闷,有点疑惑,于是他说“情本体”就是“无本体”。最后的本体仍然是“工具本体”。但完全否定掉“情本体”他又不舍,干脆把“工具本体”和“情本体”都纳入一个“历史本体”(“历史本体”其实也就是为了强调他所坚持的“积淀”一说)。合二为一,仍然是一元化的本体论,两个本体不过是这个一元本体的分本体。为了缓解对“情本体”的穷追不舍,又提出了“度”的本体性。当然,“度”——分寸感——无论在哪里都是重要的,正如粮食无论何时都是重要的,但这个重要性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这个“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才是本体,而被决定的东西尽管重要也不可能成为本体。似乎在李泽厚先生手里,只要为了强调某个事物的根本重要性,他就可以指认它为“本体”。“本体”这个概念还是原来的意义吗?“本体”还是本体吗?对“本体”的指认,在李泽厚先生手里,未免太随意了吧!我不相信,智慧如李泽厚者,会如此随意地对待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本体”。
哦!我们突然恍然大悟,他利用这样多的“本体”,实际是把他原来所坚持的“实践”本体“解构”了。我们不能说李泽厚是“解构主义”者,但他在这里的确使用了“解构主义”手法。“解构主义”对对象采取的基本倾向是:否定本原,疏离中心。解构主义十分强调边缘,坚持对中心权威加以颠覆而消解中心,而且并不承诺以某一边缘为中心,坚持若干边缘的“多元齐生”。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说:“这里没有中心,在在场——存在模式中,中心是不可想象的,它没有自然场所,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使无数符号补替的游戏得以进行的无定点……在中心和本原缺席的时刻,一切都变成话语……毫无疑问,非中心化已构成我们时代的总体的一部分”。李泽厚虽然还信誓旦旦地坚持工具本体,但他又同时提出多个本体。一,本体的词意模糊而混淆了。二,原来成为中心的“本体”不再是中心了。他在承认自己是实践美学创始人之后,又亲手把实践美学的基石搬除了。这或许并非他的本意,但实际效果就是如此。
冯宪光教授说得好:解构并不是目的,解构指向的是一种新的结构。李泽厚如此费心地解构存在了数十年的实践美学,他想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本体概念呢?或者他同意什么样的本体性概念呢?我们也许从他下面这段话中可看出端倪:
我正是要回归到认为比语言更根本的“生”——生命、生活、生存的中国传统。这个传统自上古始,强调的便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个“生”或“生生”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生”首先不是现代新儒家如牟宗三等人讲的“道德自觉”、“精神生命”,不是精神、灵魂、思想、意识和语言,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的动物性的生理肉体和自然界的各种生命。其实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人(我)活着”。人如何能“活着”,主要不是靠讲话(言语——语言)而是靠食物。如何弄到食物也不是靠说话而是靠“干活”,即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干活”不只是动物式动作,而是使用工具的“操作”,“操作”是动作的抽象化、规则化、理性化的成果,并由它建立能动的抽象感性规范形式,这就是“技艺”的起源,也是思维、语言中抽象的感性起源。[9]4-5
“实践”(干活)仍然是重要的,但决定“实践”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生命。
生命才是最后的本体。
[1] 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编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李泽厚.美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3] 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编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李泽厚.美学四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 李泽厚.李泽厚近年答问录[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7] 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编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李泽厚.该中国哲学登场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9] 李泽厚.中国哲学如何登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to the Practical Aesthetics by Li Zehou
FENG Xiaolun
(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
Mr Li Zehou puts forward and expounds the core spirit of the practical aesthetics in accordance with Karl Marx's related quotations, based on which Mr Li establishes the “practical aesthetics”. As there exist many problems in the practical aesthetics, he revises it many times, and in the course of revision, he deconstructs it gradually.
Li Zehou, practical aesthetics, revision, deconstruction
B83
A
1673-9639 (2015) 02-0009-08
(责任编辑 白俊骞)(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何历蓉)
2015-01-10
封孝伦(1953-),贵州省黄平县人。文学博士,教授,现为贵州大学常务副校长。曾发表《走出黑格尔》、《对自由与美关系反思》、《从自由、和谐走向生命──中国当代美本质概念的嬗变》等多篇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已出版学术著作主要有《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中国当代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生命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对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生命之思》(商务印书馆,2014)和《美学与艺术的集思》(贵州大学出版社,2014)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