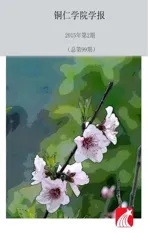到底什么是国学
2015-02-13刘梦溪
刘梦溪
(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029 )
到底什么是国学
刘梦溪
(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029 )
文章系作者在2103年4月22日由浙江大学举办的“马一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辞,后经整理而成。主要梳理了国学概念的历史嬗变过程以及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国学内涵与外延的不同认知,重点彰显了马一浮关于国学就是六经之学的基本理论观点,而以“自性的庄严”为国学之文化品格的核心。
国学; 梁启超; 马一浮; 六经; 自性的庄严
国学概念的渊源与流变
“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唐代也有,你看庐山下面有个——现在也还叫——白鹿洞书院,这个书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那么,“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就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了。要知道,这两位都是1898年戊戌政变的时候被处罚的人员,梁启超跟他的老师康有为跑到海外,而黄遵宪呢,当时在湖南参加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黄遵宪也受到了处分。他有在日本的经历,有外交经验,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其实他很稳健,在湖南时就提出主张渐进的变革,反对激进的变革,实际上他跟康、梁的激进是有区别的,但还是处分了他。
在慈禧太后政变后的晚些时候,被革职的黄遵宪回到广东老家,而这个时候梁启超有一段时间在日本。他们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启超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看不到了,我们看到的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信。黄遵宪在信里说:“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办《国学报》是不是时候,我们探讨国学概念可以暂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这一年,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黄遵宪——试想,他们在晚清,是何等样的地位,何等样的人物——他们提出了并且使用了“国学”的概念。 而在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吐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我们知道,在1898年——维新改革最高涨的时期——当年五月,张之洞,晚清的大人物,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劝学篇》。他在《劝学篇》的“外篇”里面有一节专门讲“设学”——设立学校——他说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可是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转述张之洞的主张,他说,自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国一时以为“至言”——以为这个话讲得太好了,谁都同意。可是,他在转述的时候做了一个改变:张之洞本来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转述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判断,一个晚清以来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断,就被所有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的人记在脑子里了,而忘记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本来讲的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我们今天研究“国学”这个概念的渊源与流变,我可以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梁启超转述的时候讲的“中学”,跟“国学”的概念——梁启超和黄遵宪1902年讲的“国学”的概念——几乎是同等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套传统的学问。可是,当时虽然这么讲了,对于什么是“国学”,没有人作分疏。
时间一直到1923年,大家知道,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这个时间很重要。在1923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北大这个《国学季刊》的发刊词请胡适之先生来写,胡适之先生就在这个发刊词里讲——他因为有西学的底子,又有中学的底子,他喜欢下定义——什么是国学呢?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是谁提出来的呢?他说自从章太炎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对国学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太宽,所以胡先生这个定义事实上没有被学术界采纳,后来很长时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不讲这些了——后来到“国学”的概念继续讲的时候,都不见再有人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为什么呢?“国故”这个概念太庞杂,古代的社会制度、古代的人物、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衣饰都包括在里面了。如果“国学”就是研究这些漫无边际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你很难把握住哪些是这一“学”的主要内容。 所以,事实上,学术界没有采纳胡先生的定义,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三十、四十年代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什么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呢?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当然唐代的文化内容多了,经学在唐朝也很发达,有《五经正义》——但唐朝的佛学的地位格外突出。而到宋代的时候,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出现了,就是理学,以朱子为集大成的理学。而到明代,则出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清代中叶的时候——主要是乾隆和嘉庆时期,清代的学术比较发达——这时候的学问,以考据为主要特征,也叫“朴学”,甚至也叫“清代汉学”。
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史的流变,大家觉得这就是“国学”。你看钱穆先生在北大讲国学的时候——后来整理成书叫《国学概论》——他首先讲,“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恐不立”,然后说明,他书中讲的是“本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变迁”。而马先生(马一浮)给“国学”重新下定义的时候,也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只不过他并不认可这个定义。因为人家会问:你是指哪个时代的学术呢?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讲中国的学术,不仅有儒学,还有道家,还有道教,还有佛学,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呢?所以,马先生觉得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还是太笼统,太宽泛。
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在1938年5月,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请马先生去做了一次国学讲座。竺可桢是大气物理学家,哈佛的博士,也是中研院的院士——他1936年刚到杭州就任浙大校长,就听说此地有个马一浮,学问超群,立刻登门拜望,邀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马先生拒绝了。要知道,马先生不愿在大学里任教,文章他也很少写,观念上与当时的潮流不合。
不久,竺校长又带着人去了,再次恳请马先生来学校任教,马先生又没有同意。第三次,他又去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礼仪,事不过三,三次邀请,对方不好再拒绝了——于是谈到用何种名义去开讲座,马先生想到是否可以用“国学讲习会”的名义。因为马先生不是教授,也没有职称,他觉得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名义。他自己提出,可不可以就叫“国学大师”。以马先生的学问和身份,“国学大师”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浙江大学的领导研究,说是以“研究会”的名义肯定不行,那是要成立“组织”了,需要上面批准。至于“大师”的名字,认为有点像佛教,也不好,就没谈成。
第二年,日本人打来了,浙江大学迁移到江西的泰和了,马先生自己也去逃难了。开始他逃难到了桐庐一带,几个亲戚,几个私淑弟子,一百箱书,他没有太太。马一浮先生这个时候想,如果跟浙江大学一起逃难是不是会好些?于是马先生给竺校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措辞之典雅,表达意思之婉曲,只有马一浮写得出来。竺校长接到此信,立即将马先生接到了泰和,就在1938年5月的一天,开了国学讲座。
马一浮国学讲座的第一讲,就是从“揩定国学名义”开始,他提出,时下关于“国学”是固有学术的提法,还是太觉“广汎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孔子之教。马一浮先生认为,国学就应该是“六艺之学”,这是他给出的新的不同于已往的国学定义。“六艺”就是“六经”,是中国学问的最初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
马一浮提出这样一个国学定义,它的了不起之处在哪里呢?它可以跟教育结合起来。你讲“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那是关于学术史流变的学问,专业人员研究起来尚且不无困难,你怎么可能叫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其他学科都来关注这样一个“国学”呢?一般民众更不用说了。但是,既然叫“国学”,就不能跟一般民众不发生关联。如果定义“国学”是“六艺之学”,就是“六经”,跟全体民众都会有关系。马先生的两位朋友——刚才讲到的熊十力和梁漱溟——熊先生就讲过,“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你要了解“基本依据”这四个字,实际上是说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和根底在“六经”。所以,如果把“国学”定义为“六经”的话,它就可以进入现代的教育。
国学和“六经”的价值论理
“六经”的文词很难读,怎么进入呢?我告诉大家,《论语》和《孟子》可以看做是“六经”的简约的、通俗的读本,因为孔子和孟子讲的思想,就是“六经”的思想。孔、孟阐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我把“六经”的基本义理概括为“敬”、“诚”、“信”。刚才杜先生讲到“诚”、“信”,但是我把“敬”放在了最前面。这个“敬”是什么?就是人的“自性庄严”。你看马先生在《复性书院演讲录》里面,主要讲的就是一个“敬”字。“敬”是个体生命的庄严,是人性的至尊至重,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我甚至认为“敬”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这种“自性的庄严”,是不是一般人不能实现呢?马先生当然实现了。我刚刚讲的陈寅恪,一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然也是“自性的庄严”的表现。马先生对这个“敬”字的解释,有一极重要的特见,他说《论语》里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马先生说“志”就是“敬”。因此这个“敬”是不可以被“夺”的,已构成个体生命的价值信仰,当然不可以“夺”。
学者、知识人士应该有“自性的庄严”,一般人士、没有文化的人有没有“自性的庄严”?当然有。我们看《红楼梦》,当贾赦要娶鸳鸯做妾的时候,鸳鸯坚决不允,做了很多极端的举动,包括破口大骂,甚至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所彰显的就是鸳鸯这个年轻女性的“自性的庄严”。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更是人的“自性的庄严”的突出体现。人的“自性的庄严”,就是人的良知,匹夫匹妇都可以做到,男女老少都可以做到,有文化没文化都可以做到。我们当下所缺的,就是这种人的“自性的庄严”。当代文化价值理念的建构,亟需添补的,就中国传统这一块,我讲的以“敬”来带领的这些价值理念,包括诚信、忠恕、仁爱、知耻、和同等,应该是最重要的亟待填补的精神价值。 而以“六经”为内容的国学,就可以通过教育的环节,和全体国民联系起来。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在现代知识教育体系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当然,文化价值的建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代文明的观念、途径、方式、礼仪,也需要填补建构。在这方面,中外的价值理念可以互阐。
What on Earth is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LIU Mengxi
(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China )
This article, originating from a speech of “MaYifu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 hosted by Zhejiang University on 22,April of 2013, is formed by means of adaption, which mainly explain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concepts and the different cognition of its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and highlights the basic theoretical viewpoint that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is the Six Classics. The dignity of one's nature is the core of Chinese Classics' cultural character.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Liang Qicao, Ma Yifu, the Six Classics, the dignity of one's nature
G122
A
1673-9639 (2015) 02-0005-04
(责任编辑 白俊骞)(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何历蓉)
2015-01-10
刘梦溪(1941-),原籍山东,生于辽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艺术美学暨文学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专聘教授、文艺学学科博士生导师。201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著作有《红楼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文学的思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文艺学:历史与方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红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学术思想与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陈寅恪与红楼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情问红楼》(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中华书局,2007),《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三联书店,2008),《论国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书生留得一分狂》(作家出版社,2010),《牡丹亭与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国学与红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三联书店,2012),《陈宝箴与湖南新政》(故宫出版社,2012)和《大师与传统》(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