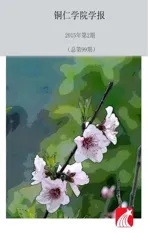文人画笔墨概念的确立及涵义分析
2015-02-13江波
杨?江波
( 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 )
文人画笔墨概念的确立及涵义分析
杨?江波
( 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 )
文人画最强调“笔墨”,“笔墨”概念的成熟是有发展过程的,既有技法层面的涵义,又有哲学内蕴的特质。这种状况的出现奠定了文人画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因此,梳理其发展过程,分析其形而上的意蕴,是全面深入了解“笔墨”这一中国画代名词的必要功夫。
笔墨; 合一; 材料; 意蕴; 石涛
中国文人画的“笔墨”概念是立足于本民族审美体系之上的,既有技法层面的涵义又有哲学意义上的阐释。众所周知,“笔墨”已成为中国画的代名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笔墨内涵是一个无限的载体,它承载着画家的才情与素养,元代绘画把笔墨独立的审美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笔墨可以在脱离具体物象的基础上有抽象意义的美,线条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无不寓含了作者本人当时的情绪与修养。所谓“笔墨风格”是指画家或画家群体现在作品上的笔墨的气质和样态。它是由被描绘对象和画家两种因素综合决定的,是一种物我交融情况下呈现出的第三种样态。
宋代陈思①陈思,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宋理宗时期(1225~1264),字续芸,宋临安(杭州)人。性嗜古,曾编刊《宝刻丛编》、《海棠谱》、《书苑英华》、《小字录》及《两宋名贤小集》等,其书卷帙浩繁,有较大的文献价值。的著作《书苑菁华》收有东汉书法家蔡邕所著的《笔论》一文,是一篇重要的书论。东汉书法艺术发展很大,汉隶方面以蔡邕为代表书家,草书方面以杜度、张芝、崔瑗为代表书家,张芝在章草的基础上创立了今草被称为“草圣”,草书的确立兴盛为书法与绘画的相融做足了条件。因为草书善于抒发性情,笔法自由。崔瑗写的《草书势》是第一部理论专著,其后又有蔡邕的《九势》、《篆势》,杨泉的《草书赋》,南朝梁萧衍的《草书状》等著述出现。书法理论的发展完善给研究书法之笔法带来了条件,如“下笔”和“掠笔”这样的笔法名词开始出现,如东晋卫铄《笔阵图》“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莫重乎银钩。”
魏晋南北朝时政局动荡,朝代的更替频繁。但文化思想却成就斐然,玄学兴起,画论、书论、文论很多,其中数量最多的还属书法理论,王羲之写有《用笔赋》、卫恒写有《四体书势》、王僧虔写有《论书》等。在创作上,楷书、行书、草书三种书体在东晋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微在《叙画》中提出了“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这是从形而上的哲学本体理念来阐释“笔”,从此“笔”的美学内涵开始确立。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还是谢赫提出的“骨法用笔”。“骨法”在魏晋时是一个人物品藻方面的概念,主要是指士人从“骨相”来审视人的志气、寿命、贫贱富贵等,用在书法理论上则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因此,“骨法用笔”更多的是强调笔的力量感。“笔”的概念发展至此已具备了其“太虚之体”的美学内涵和外部“力”的属性。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认为笔有四势:“笔绝而不断谓之筋;起伏成实谓之肉;生死刚正谓之骨;迹画不败谓之气。”[1]608
关于“墨”的论述很早就出现了,使其理论概念真正具有理法意义的是五代时期的荆浩。关于荆浩,据《宣和画谱》记载:
荆浩,河内人,自号为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专门,颇得趣向。尝谓“吴道玄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浩兼二子所长而有之。盖有笔无墨者,见落笔蹊径而少自然;有墨而无笔者,去斧凿痕而多变态。故王洽之所画者,先泼墨于縑素之上,然后取其高低上下自然之势而为之。今浩介二者之间,则人以为天成,两得之矣。故所以可悦众目,使览者易见焉。[2]106
他在《笔法记》中说:
夫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晕墨章,兴我唐代。[1]608
他把“笔”和“墨”同时提出并对各自功能作了大概阐述,“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底晕淡,品物深浅,文采自然,似非因笔。”[1]606
荆浩对几位代表性的画家还作了具体评价:
王右丞笔墨宛丽,气韵高清,巧写象成,亦动真思。李将军理深思远,笔迹甚精,虽巧而华,大亏墨彩。项容山人树石顽涩。棱角无足追,用墨独得玄门,用笔全无其骨,然于放逸,不失真元气象,无大创巧媚。吴道子笔胜于象,骨气自高,树不言图,亦恨无墨。陈员外及僧道芬以下,粗升凡俗,作用无奇,笔墨之行,甚有行迹。[1]608
荆浩认为在“笔”、“墨”结合方面最为成功的画家如王维和张璪①唐代画家,江苏吴郡人,著有《绘境》一篇。他生活于大约8世纪后期,作品创作富于激情,不求巧饰而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理念。,王维叹服水墨的表现力,强调:“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1]592荆浩对张璪的笔墨评价曰:“张璪员外树石,气韵俱盛,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旷古绝今,未之有也。”[1]608很明显,他对王维之类文人画作品的笔墨最为推崇,而批评吴道子、李思训之类的作品有笔而无墨,在效果上便“笔胜于象”。
自荆浩提出完整的“笔墨”概念之后,历代画论家便不断地完善这个理论,使之成为一个最能代表中国画特征的核心名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笔”和“墨”功能的合一性
在唐代,张彦远把“笔墨”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阐释,“骨气形似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历代名画记》曰:
夫阳阳陶蒸。万象错布,玄化亡言,神工独运,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飏,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粹,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3]28
他提出“意”为“笔墨”之本,“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而用笔也是表现这个“意”的,这就把两者从功能上相融合,更强化了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北宋画家韩拙说:“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我们可以看出,这时对“笔”和“墨”功能独立阐述时也不是截然分开了,笔中有墨,墨中有笔,理论上更具有了哲学的理念。这以后的画家在阐述“笔墨”观时也如此。如清画家龚贤说:
墨中见笔法,始灵;笔法中有墨气,则笔法始活,笔墨非二事也。(清龚贤《龚半千课徒稿》)
清沈宗骞说:
盖笔者墨之帅也,墨者笔之充也。且笔非墨无以和,墨非笔无以附。[4]102
笔墨二字,得解者鲜,至于墨,尤鲜之鲜者矣。往往见今人以淡墨水填凹处,及晦暗之处,便谓之墨,不知此不过以墨代色而已,非即墨也。且笔不到处,安得有墨?即墨到处,而墨不能随笔以见其神采,尚谓之有笔而无墨也。[4]28
清布颜图②姓乌亮海氏,字啸山,号竹溪,以蒙古入籍镶白旗,授官职绥远城副都统。他创作重章法,喜用淡墨渴笔来表现。《画学心法问答》是淮阴戴德乾交游京师时,布颜图授以画学所作。《画学心法问答》曰:
笔为墨之经,墨为笔之纬,经纬连络,则皮燥肉温,筋缠骨健,而笔之四势备矣。[5]251
方薰《山静居画论》曰:
气韵有笔墨间两种,墨中气韵人多会得,笔端气韵世每少知。[1]230
二、材料变化对“笔墨”风格的影响
生宣纸在元代亦有出现,但在明代以后大为兴盛,“笔墨”概念理论的发展与此也大有关系。因生宣纸从水槽中抄出烘干后不经过上矾、拖蜡等程序,吸水性能好,水墨互渗,如能充分利用其性能则其墨色变化微妙活润。清代画家盛大士在《溪山卧游录》中说:
作画忌用矾纸,要取生纸之旧而细致者为第一。若纸质粗松,灰涩拒笔,皆不可用;然比矾纸,则犹为彼善于此。盖惯画灰涩粗松之纸,一遇佳纸,更见出色;若惯用矾纸,则生纸上不能动笔矣。[6]58
盛大士在此强调的“生纸”即是生宣,“矾纸”即是熟宣。生宣便于水墨在纸纤维中渗透交融,其笔墨效果更为浑化滋润,他喜用生宣甚至“忌用矾纸”。清代画僧石涛也认为生纸墨漏长处在于擅长表达笔墨的意味,“纸生墨漏,画家之一厄也,何能见长?在过三十年后,观此纸又别有意味,世恐未有知之者。”[7]91生宣纸因其对水墨的极度敏感性,用笔快慢不同笔墨的效果便随之变化,因此画家的情绪修养便更真实地在画面上得以流露,也就是说,“笔墨”这种载体更适合表达形象背后的情感“意味”。可见明代以后,生宣在画家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材料的改变也深刻影响“笔墨”的审美理论。
三、“笔墨”内在精神意蕴的成熟发展
唐宋注重禅学,明清时代,心学大行其道,反映在笔墨艺术上,则笔墨性情趋向内敛,其审美与“本体论”连在一起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如明陈继儒《妮古录》曰:
世人爱书画,而不求用笔用墨之妙。有笔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笔不妙者,有笔墨俱妙者,有笔墨俱无者。力乎巧乎?神乎胆乎?学乎识乎?尽在此矣。总之不出蕴藉中沉着痛快。[5]234
明茅一相《绘妙》曰:
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用笔之难,断可识矣。故爱宾称王献之能为一笔书,陆探微能为一笔画。非谓而能一笔可就也,乃自始及终连绵相属,筋脉不断,所以意存笔先,笔周意内,像应神全,思不竭而笔不困也。[5]237
王时敏《西庐画跋》曰:
得奇趣于笔墨之外。[8]18
清王原祁《麓台题画稿》曰:
笔墨一道,同乎性情。非高旷中有真挚,则性情终不出也。[5]241
清沈复曰:
画性宜静,诗性宜孤,即诗与画必悟禅机,始臻超脱也。[9]172
以上“笔墨”论都指出笔精墨妙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心”,心性修养“高旷真挚”则笔墨有“奇趣”,而得“奇趣”的重要方法是“悟禅机,始臻超脱”。
“笔墨”内在精神意蕴的成熟还表现在把“有无”、“繁简”、“浓淡”、“色墨”这几个对立矛盾的名词在具体操作上统一起来。清恽寿平《南田画跋》:
今人用心,在有笔墨处;古人用心,在无笔墨处。倘能于笔墨不到处。观古人用心,庶几拟议神明,进乎技已。[5]241
画家在布置笔墨时,无疑背后的空白也是考虑的因素。“有”和“无”处在相互联系之中,古人讲“计白当黑”即如是。按照现在的美术理论来讲,就是进行空间分割,他们在共同塑造着笔墨空间,创造着一个完整而灵动的生命场。王原祁《麓台题画稿》曰:
笔不用繁,要取繁中之简;墨须用淡,要取淡中之浓。要于位置间架处,步步得肯,方得元人三昧。[10]69
“繁”也可以表现“简”,“淡”也可以表现“浓”,髡残的笔墨繁密但其意境简逸,倪云林笔墨清淡但意味浓厚隽永。高手总是能把两种看似两极对立的矛盾调和在一起,这受益于道家的“阴阳谐和”的观念。
“色法”在水墨画中也归化于“墨法”,其中的媒介是“气”,墨用得好会生五彩,色用得好会“不碍墨”而相得益彰。如王原祁《麓台题画稿》曰:
画中设色之法,与用墨无异,全论火候,不在取色,而在取气。故墨中有色,色中有墨。[8]160
这个“笔墨”的观念在此又被升华延伸了,“笔墨”不仅仅局限于黑白的浓淡,它的核心是“气”的运用,是“气”把用色和用墨融汇在一起而变成了一个观念性的“笔墨”。关于“气韵”,谢赫在六法中提出“气韵生动”,对此唐岱阐释曰:
气韵由笔墨而生,或取圆浑而雄壮者,或取顺快而流畅者。用笔不痴、不弱是得笔之气也。用墨要浓淡相宜,干湿得当,不滞、不枯,使石上苍润之气欲吐,是得墨之气也。[1]865
四、石涛对“笔墨”的理解
“笔墨”理念在清代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石涛作为合三教文化于一身的禅僧,其笔墨观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理念高度。他提出著名的“一画论”:
笔与墨会,是为絪絪,絪絪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画于山则灵之,画于水则动之,画于林则生之,画于人则逸之。得笔墨之会,解絪絪之分,作辟混沌乎,传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者得之也。
不可雕凿,不可板腐,不可沉泥,不可牵连,不可脱节,不可无理。在于墨海中立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盖以运夫墨,非墨运也;操夫笔,非笔操也;脱夫胎,非胎脱也。自以一分万,自万以治一。化一而成氤氲,天下之能事毕矣。[7]29
石涛身上道、禅思维兼而有之,在他的“笔墨”观里,这个概念已完全理念化,“絪絪”是阴阳,笔与墨的关系实际上是阴阳相生发的关系。太极生阴阳两仪,“混沌”为生命的原初,这个“混沌”应该讲的是“无极”。老子在《修身》章里说自己取法于道,对于世间的分别相不执着,人们沉浸于外物纵欲狂欢而他却淡泊宁静,“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因此看来,老子之“混沌”乃回归于先天的状态,心性无为纯朴的状态。
关于“一画”,杨成寅先生在《石涛画学本义》中认为是绘画的根本规律和法则,在哲学上是“太极”的概念。《老子》曰: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11]97
“太极”是“无极”之后最原始的生命秩序状态,“得一”即是回归到那个生命源动力,外部呈现的美学状态是“清、宁、灵、盈、生、正”。石涛在“笔墨”的修养上,还提出了“蒙养”和“生活”的重要性:
“写画一道,须知有蒙养。蒙者,因太古无法,养者,因太朴不散。”它们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画家笔笔生发,从无中生有,然后笔墨浑然一体,意境拔尘脱俗,可谓:“自万以治一,化一而成氤氲”。[11]9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成熟的“笔墨”观既讲到生命力的原初,又讲到尊重艺术的根本规律,最后还强调其外在生动的笔墨表现。在石涛这里,显然已打破了往昔“笔墨”理念的局限性,正确的“笔墨”标准是协和的、统一的、生机勃勃的,“笔墨”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场。
[1] 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2] 王群栗,点校.宣和画谱[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3]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4] (清)沈宗骞,著.李安源,刘秋兰,注释.芥舟学画编[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
[5] 殷晓蕾,编著.古代山水画论备要[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6] (清)盛大士,著.叶玉,校注.溪山卧游录[M].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2008.
[7] (清)石涛,著.周远斌,点校.苦瓜和尚画语录[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8] 杨亮,何琪,点校.清初四王山水画论[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9] (清)沈复.浮生六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10] (清)王原祁,著.张素琪,校注.雨窗漫笔[M].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2008.
[11] 饶尚宽,译注·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cepts about the “Brush and Ink” of Literati Paintings and the Analysis of its Connotation
YANG Jiangbo
(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China )
Literati paintings particularly emphasize the “Brush and Ink”, the maturity of whose concepts is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embodying the connotation both technically and philosophically. This situation establishes literati paintings' position in the art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refore, analyzing the developing process and the implications are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brush and ink” comprehensively and thoroughly, which is an alternative noun of Chinese painting.
brush and ink, unification, material, implications, Shitao
J209.2
A
1673-9639 (2015) 02-0017-04
(责任编辑 白俊骞)(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何历蓉)
2015-01-10
杨江波(1976-),山东平度人,文学博士,2014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系,专业方向为中国诗学传统画论与中国画创作,导师为范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