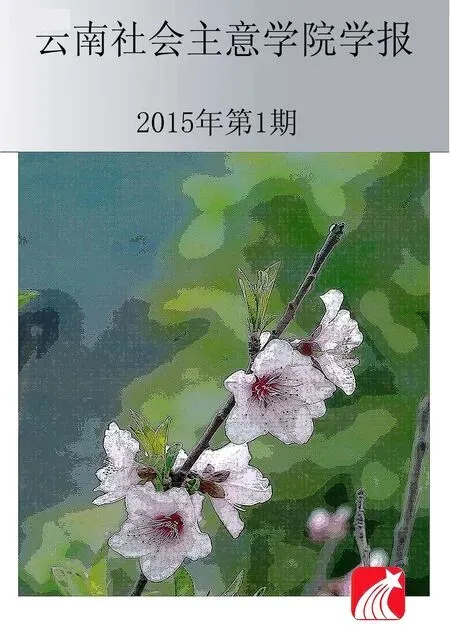影片《卧虎藏龙》跨文化叙事与民族形象塑造研究
2015-02-12黄配配
黄配配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影片《卧虎藏龙》跨文化叙事与民族形象塑造研究
黄配配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影片《卧虎藏龙》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在跨文化的传播视域中对我国文化符码的呈现以及民族形象的成功塑造。影片对中华民族传统的建筑文化、书法文化、竹文化、功夫文化以及道家哲学精神进行了很好的域外展示。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导演李安采用西方视域下的叙事主题,运用表象化与奇观化的西方叙事方式,使得西方文化因素与东方文化意象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中国当代导演应当以此为鉴,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做到文化表达的多样性与民族形象塑造的多元化,注重文化传播的自觉性与民族形象的“自我”及“他者”问题,将塑造民族形象作为“文化中国”传播的间接目标。
民族形象;《卧虎藏龙》;跨文化;传播
民族形象是指人们对于一个民族的总体印象,它既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既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军事等国家硬实力的体现,同样也是文化、艺术等民族软实力的呈现。电影作为一种现代的综合艺术形式,能够同时从视觉、听觉、想象力等多种角度向观众传递信息,其在构建与传播民族形象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作用也越来越突出。近年来,《黄土地》、《红高粱》、《卧虎藏龙》、《白鹿原》、《晚钟》、《菊豆》、《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等影片不仅在国内得到国人的认可,在海外各大电影节上也摘得大奖。这些影片在塑造和传播我国的民族形象时既有得也有失,一方面这些获奖影片将苦难斗争中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彰显中国人民面对苦难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又将文化中国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展现古老而文明的伟大民族形象。但是,与此同时,这些获奖影片描写的又是落后、野蛮、愚昧的中国形象,使得国外观众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男人妻妾成群、文化科技相当落后的一个地方。导演李安既了解中国文化又了解西方文化,张艺谋曾经评价“李安是唯一可以在中西文化间游刃有余的导演”,其影片《卧虎藏龙》在跨文化的传播视域中对我国的文化传播以及民族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文章通过分析影片《卧虎藏龙》在民族形象研究视域下的跨文化传播方式与策略,希望更多的当代中国电影导演能够以此为鉴,更加游刃有余地在跨文化传播中积极塑造中华民族形象。
一、电影《卧虎藏龙》与中国文化元素呈现
《卧虎藏龙》是一部唯美的电影,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都能发现电影的“画面美”与“情义美”,“画面美”即是对中国古建筑文化、书法文化、“竹文化”等的展示,“情义美”指的是影片中所体现的中国功夫文化、道家哲学文化的轻柔之美以及李慕白、俞秀莲、玉娇龙之间的友情、爱情之美。在影片《卧虎藏龙》中,中国文化符号参与的种类是多样的,形式也是多样的。
首先是中国古建筑文化符号的呈现。影片中多次镜头描写的都是中国的古建筑,尤其是在影片的开始,出现的不是主人公,而是青山碧水之间的一片古建筑群落。通过观看电影,我们能够总结出中国古建筑文化的三个特点:一是简约朴素之美。影片刚开始出现的古建筑群屋顶都是高低有别、错落有致的,而且都是乌瓦白墙。从整体上看去,给人一种素静之美、整齐之美、简约之美。这也在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中不张扬与简约朴素的特点。二是“小桥流水”的意境之美。中国古代的建筑都喜欢依山傍水而建,尤其是中国江南的园林建筑,没有山和水那是不行的。这是中国人对于自然山水热爱的一种体现。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三个特点便是斗拱、飞檐,这是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优美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斗拱与飞檐正是中国道家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中国人积极进取、寻求向上的宝贵精神品格。影片《卧虎藏龙》通过中国古建筑文化的呈现凸显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积极塑造我国的民族形象并将其展现在“他者”面前,得到了“他者”的认同和接受。
其次是中国书法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参与。我国的书法艺术与京剧、武术、针灸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四大国粹,书法艺术已成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精髓的代表。在影片《卧虎藏龙》中,多次出现我国的书法对联,这些对联有的刻在门楣上,有的装裱好挂在屋内墙上,有的则是字画一体的;有的是行书,有的是草书,字体多种多样。导演安排这些书法对联的目的就是在向观众展示我国的书法文化,体现了我国人民所具有的艺术创新精神。在影片中,作者甚至还借着玉娇龙练字的一幕来展现我国的书法之美妙。在书房内,刚开始玉娇龙写的是楷书,后来俞秀莲来访,玉娇龙则拿俞秀莲的名字来练着玩,俞秀莲一语点破:“书法剑法,道理好像是相通的。”中国书法艺术的美不仅在于其字体的变化多样,更在于其在书写的过程中所体现的行为之美。有人说:“要了解西方文化,须听其音乐;要了解中国文化,须观其书法”。这句话正印证了书法艺术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体现了我国人民在艺术上所具有的创新精神,是民族形象的另一种呈现。
再看中国功夫文化及道家哲学精神的弘扬。作为武当派的弟子,李慕白的武功以及他的言行都体现并遵循着道家哲学精神。影片中一些话语便是中国功夫及道家哲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影片开端,李慕白来到镖局看望俞秀莲的时候对她说了一番话:“此次闭关静坐的时候,我一度进入了一种很深的寂静,我的周围只有光,时间和空间都不存在了……”李慕白的这几句话正是道家修道过程达到忘我、虚无境界的一种体现。在竹林时李慕白拿起秀莲的手贴着自己的脸颊上说:“秀莲,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李慕白与玉娇龙在古寺交手时,玉娇龙说:“想当我的师父,谁知道你是不是浪得虚名?”李答道:“‘李慕白’是虚名,宗派是虚名,剑法也是虚名,这把青冥剑还是虚名,一切都是人心的作用。”李慕白还直接引用《道德经》上的话来晓谕玉娇龙剑法和做人的道理:“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勿助、勿长、不应、不辩,无知无欲,‘舍己从人’才能‘我顺人背’。” 导演安排这些话语及电影情节的目的就是为了弘扬中国功夫文化以及道家哲学精神。
二、电影《卧虎藏龙》的跨文化传播方式
在电影《卧虎藏龙》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李安使用了自己的一些阐释方式,其核心便是在西方视域下让东西方的文化达到融合状态。影片《卧虎藏龙》的叙事主题和叙事方式都是西方文化视角下的,在这样一种西方因素的影响下使得东方的意象得以很好地呈现,从而将我国的文化符码展现在西方人面前,使中华民族形象得到“他者”的认同和接受。
(一)西方视域下个人主义、女权主义等西方叙事主题的自我运用
传统的功夫武侠电影主要以男性作为影片的主角,以男性形象作为电影精神传播的载体,女性只是男性的一个附属品,是男性欲望实现的垫脚石。而影片《卧虎藏龙》则改变了这一点,“在通常以男性为主体的武侠片中注入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思想”[1]。俞秀莲和玉娇龙是影片中重要的两位女性形象,她们和影片中的男主人公李慕白一起,共同对中国的传统功夫文化以及道家哲学精神进行了阐释,更重要的是她们具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特征,向传统的男性霸权地位提出了挑战。
在中国古代,封建礼教对人的控制是很严的,其中突出体现的一点便是年轻人的婚姻大事由父母安排,如有违抗,便会被看作是不孝,是对“伦理道德”的最大亵渎。而在影片《卧虎藏龙》中,玉娇龙身为千金大小姐,却与“西部牛仔”罗小虎私定终身,还对李慕白的一番好意毫不领情,在影片结尾纵身飞下悬崖,她以死亡的方式来向封建礼教挑战。另外,在影片中,她做事我行我素,不听李慕白的教导,不听俞秀莲的规劝,大闹酒楼,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玉娇龙的行为正是与中国传统式集体主义对抗下个人主义的体现。在影片中,堪称江湖女豪杰的俞秀莲担任的是镖局的主管,这是男人的职务;另外,俞秀莲还以长者的身份来规劝玉娇龙,在这一方面她和李慕白的角色是一样的。影片中俞秀莲的这些方面行为都“表现了中国女性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至高无上的男权的挑战”。[2]影片中俞秀莲和玉娇龙这两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是在向传统男权地位提出挑战,一方面又是现代女性主义崛起的体现。广大女性在摆脱男性的统治,寻求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都是导演李安刻意安排的好莱坞叙事模式:即故事的传奇性+视觉奇观+美国现代观念。好莱坞个人主义和女权主义叙事主题的运用意在为了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影片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涵能够更好地得到西方观众的认同与接受,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民族形象进行成功地塑造和传播。
(二)表象化与奇观化的西方叙事方式
《卧虎藏龙》传达出来的文化其实是非常表象化的,甚至可以说只是某些文化共同性的奇观化表达。中国的第五代导演最擅长使用表象化和奇观化的西方叙事方式,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陈凯歌的影片《黄土地》、《霸王别姬》等等。这些影片都对中国的文化意象进行了表象化的呈现。“从世界电影史上看,把影像的奇观性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并非自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始,好莱坞的西部片,欧洲大量的民族风情电影,日本黑泽明、大岛渚、今村昌平的电影,都无不在发掘民族的文化资源,利用本民族的影像奇观来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3]在影片《卧虎藏龙》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古建筑以及中国的书法艺术,这些都是导演刻意安排的,目的就是让中国的文化意象在表象化的层面进入西方观众的视野。
但是在表象化与奇观化的西方叙事方式引导下,许多中国海外获奖电影在国内却得不到观众的认同,甚至招来诟骂。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电影在将中国的文化意象进行了表象化呈现的同时却失去了自己的中心,影片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然而李安则不同,他在影片中把中国人讲求仁义礼信、孝顺父母、宽容忍让的精神内涵进行了最大限度的阐释。这样就使得中国的国家形象在文化层面上得到了很好的塑造和传播,完成了电影塑造和传播民族形象的使命。同时也能够使我国的电影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拥有立足之地,可谓一举两得。因此说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引领了中国大片时代的到来,之后的《英雄》、《十面埋伏》等影片都是高投入、精制作,但它们在文化及民族形象塑造层面上始终没有超越影片《卧虎藏龙》。
(三)西方文化因素和东方文化意象的融合
在文化全球化的社会大环境下需要全球文化的混合,“文化混合指的是亚洲、非洲、美洲、欧洲文化的混合:混合就是将全球化文化制作成全球性杂烩——在这过程中对边缘与中心、全球性与本土性、独裁霸权与少数派、政治组织与反文化或亚文化之间的那种等级进行一种模糊、反稳定化或者颠覆。”[4]“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李安打着东方审美意蕴的旗帜将西方的文化观念融入进来。李安在影片《卧虎藏龙》中对中国和美国的文化进行了很好的混合。
影片所采用的叙事主题和叙事方式是好莱坞式的,但传统建筑、书法、竹林、道观、服饰等这些文化意象却是东方的。另外,影片中的大漠青年罗小虎就像大多数美国电影中的西部牛仔一样,拥有狂放不羁的性格,是自由的象征和代表,这正好符合西方观众的审美期待。但同时罗小虎对玉娇龙的爱是深刻的,为了爱情从大漠来到中原,到最后无奈地看着玉娇龙飞下悬崖,这恰是中国人为爱执着、温文尔雅的一面。在影片中,美国西部不再粗犷而代之以中国古典的世外桃源,牛仔的含蓄与中国人的温文尔雅融为一体。正如李安自己所说的,“当传统的伦理道德被冲突打破时,东西方的表现是相同的。”他用西方的叙事策略来阐释东方的文化意象,这样更利于西方观众理解和接受这些文化意象以及它们背后所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
三、电影跨文化传播与民族形象塑造问题
影片《卧虎藏龙》之所以能够在第73届奥斯卡中获得10项提名,最终斩获最佳外语片等4项大奖,关键在于导演李安懂得如何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来打动西方观众。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起,“全球化”这一概念开始从经济学领域向社会及文化学等领域延伸。电影作为文艺实践的一种,如何在全球化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很好地利用跨文化传播方式来向外走出去,这成为电影能否发挥优势塑造民族形象的关键问题所在。
(一)文化的多样性表达与民族形象的多元化塑造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文化核心是“西部牛仔式”的,强调的是个人自我的张扬以及敢于冒险精神的体现。影片《卧虎藏龙》的文化核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导演李安却用另外一种方式将其展现了出来。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只是一种概括化、抽象化的描述,这种描述意义重大,但是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个案。李安自己认为,“对我来讲,地域性跟共通性有的时候并不犯冲突,他们是你的左右两手。”[5]李安对中国和美国的文化精髓都很了解,他具有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他深知如何在影片中来对不同的文化进行剖析和解读。在影片《卧虎藏龙》中,李安以一种宽容的姿态来挖掘中方和西方这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性,采用“共存互补”的方式,打通这两种文化间的审美隔阂,获得中西方不同文化接受群体的接受认同。但是,于此同时,李安也没有抛开中国文化自身的特性,影片从始至终一直在通过叙事、画面等多角度来展现中国功夫文化的轻柔之美及其博大精深,向观众展示了我国道家哲学文化的精髓。总之,李安为影片《卧虎藏龙》设计了一条符合西方人口味的路线,西方观众能够非常轻松地理解影片中所体现的中国功夫文化以及道家哲学精神,这也恰是民族形象在文化层面上的多元化塑造与传播。
(二)文化传播的自觉性与民族形象的“自我”塑造及“他者”期待
导演及其创作团队在文化传播与民族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导演不仅是艺术的创作者,同样还是一件艺术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传播者。综观李安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李安对中国当代电影的贡献不仅在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形式与策略上,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在西方视域下塑造中国的民族形象,在本土文化关怀与他者视野下实现了中华民族形象的双向塑造。李安的这一点贡献恰是中国当代大多数导演所缺乏的最基本的实现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与塑造民族形象的能力,要想做到这一点,导演应该首先认清电影在塑造民族形象中的“自我”与“他者”,只有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意识到它们在塑造民族形象中的作用,我们才能够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电影构建民族形象应该是“自我”主体地位上的构建。当今世界仍然是以西方为主导,电影创作者为了电影作品能够在海外各大电影节上获奖,在创作电影时站在西方的视角之下,自觉或不自觉的使得作品凸显出“媚西”主题,主要体现在对于原始、落后、愚昧的中国人形象的塑造以及神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这些表现民族劣根性和神秘、原始、‘奇观式’的中国场景、画面与镜头,是首先能够抓住西方观众的地方。”[6]然而,笔者认为,作为电影创作者应当肩负起积极构建民族形象的责任,站在“自我”构建的主体地位上,摆脱“他者”影响,从而积极构建民族形象,向外传播我国的优秀文化,让“他者”了解真正的中国,认同接受我国的文化价值观念。
电影构建国家形象可以对“他者”给予适当关注,从“他者”中寻求自我完善。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西方社会在经过高速发展后逐步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以往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观点在西方也遭到普遍质疑,西方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念。我们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的对照,与“他者”文化进行对比,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自身、改进自身。李安的影片正是起到了这一作用。电影将所构建的国家形象传播到国外时,肯定会引起外国人的关注与评价,他们会在电影所构建的基础上对国家形象进行想象与再次构建,由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再次构建的形象会缺乏真实性。那么,作为电影创作者或电影评论者,应当及时对“他者”想象与再次建构的内容进行客观看待,对“他者”的评价进行梳理与总结,从“他者”评论中找出自身构建国家形象时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与不足,为今后的电影构建国家形象提供参考依据,将我国的正面形象积极传播到国外,使得我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得到“他者”的认同。
(三)将塑造民族形象作为“文化中国”传播的间接目标
民族形象的构建应当在全民族文化弘扬与传播的基础上来完成,即中国大陆以及台湾、香港、澳门文化的共同参与。20世纪80年代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提出了“文化中国”这一概念。他认为:“文化中国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观念,不是一个狭隘的种族观念,也不是完全语言的观念。”[7]也就是说“文化中国”是一个跨地域、跨种族、跨语言的概念。导演李安的华语片对于“文化中国”的构建就是非常成功的,在他的影片中,中国的文化符码主要通过武术、婚礼、书法、建筑等形象表现出来,这些文化符码表面是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其实质上是对“文化中国”的构建,挖掘文化符码背后的文化精神内涵,民族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只是“文化中国”构建的间接目标。
在中国当代电影走出去的过程中,许多导演刻意追求西方视角的认同,而忽略了电影在文化传播的同时承载塑造中华民族形象的重任。《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白鹿原》等这些在西方各大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影片在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精神传播上的作用比较微弱,有的影片甚至对我国的国家形象进行了丑化。为了满足西方观众的心理、获得“他者”认同,将中国描绘成一个落后、愚昧、文化极其落后的国家。在后现代主义社会,电影尽管是一种商业品,但同时它也是传播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因此,电影在考虑经济利益的同时应该担负起塑造和传播民族形象的重要责任。美国电影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是为了金钱的获取,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进行民族形象的塑造。美国的科幻大片始终在向观众展现美国作为世界保卫者的“世界警察”形象;影片《泰坦尼克号》展现了美国年轻人的爱情观念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积极态度,同样展现了美国人在危难之时保护弱势群体这样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当幸福来敲门》这样的影片则表现了美国人在困难面前敢于积极抗争、不向苦难低头的精神品格。美国的这些影片在文化传播的同时将美国的大国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利用好莱坞电影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将塑造的形象传播到世界各地。达到了把塑造和传播美国国家形象作为美国文化传播的间接目标。
电影作为一种现代的综合艺术形式,“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物,它们的存在语境决定了其物质本质最终必然服务于它的社会本质。而其社会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多重本质属性: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是一种影像语言,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电影是一种文化产业,所有这些关于电影的定义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8]电影既是特殊的语言符号,同样也是一种文化载体。“他者”视域下的观众通过观看电影能够了解异国人民的生活习惯、风俗人情、价值道德观念以及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观众通过电影解读异国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价值体系、道德标准等表层和深层的文化。电影是一种具有超强传播力量的艺术形式,它的传播途径非常广泛,可以把网络、光盘等电子媒介作为传播载体,这样相对于印刷文本而言,其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将一国的国家形象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全球化的今天,当代中国电影应该从美国电影、韩国电视剧、日本动漫中吸取宝贵的跨文化传播经验,积极塑造我国的民族形象,将历史悠久、古老文明、和谐发展的中华民族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塑造和传播民族形象,电影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媒介,其作用日益突显。
[1][台湾]焦雄屏.影像中国[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90.
[2]孙慰川.当代台湾电影(1949-2007)[J].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138.
[3]颜纯钧.全球化:文化差异与文化资本[A].孟建,李亦中.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0.
[4]江·比斯特.作为混合的全球化[M].胡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352.
[5]李安.站在好莱坞与中国电影之间[J].上海大学学报,2006(6).
[6]李朝全.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7:272.
[7]杜维明.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EB/OL].(1995-03-20)[2012-08-30].http://guoxue.com/ddxr/dwm4.htm
[8]贾磊磊.镌刻电影的精神——关于电影学的范式及命题[J].当代电影,2004(6).
责任编辑:诸 芳
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研究”(主持人:徐放鸣 项目编号:12AZW003);江苏师范大学2014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一般项目“叙事学视角下电影与国家形象的‘自我’与‘他者化’塑造——以1980′s以来中国海外获奖电影为例”,项目编号:2014YYB011。
黄配配(1989—),男,江苏连云港人,江苏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审美文化学。
D91
A
1671-2811(2015)01-013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