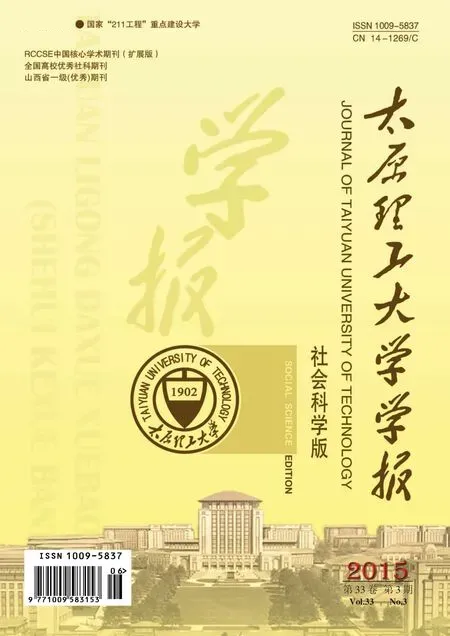论公物利用侵权的司法救济——以主观公权利与司法救济的对应关系为线索
2015-02-11梁君瑜
论公物利用侵权的司法救济
——以主观公权利与司法救济的对应关系为线索
梁君瑜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公物利用是一种复合型主观公权利。因主观公权利与司法救济存在对应关系,所以归纳公物利用侵权形态并分析其损及的主观公权利类型,是完善我国相应司法救济的逻辑起点。我国公物利用侵权的司法救济在救济方式之实效性、救济对象之覆盖性、救济利益之明确性、救济模式之全面性等方面存在不足,应通过推动撤销判决彻底化、理顺一般给付判决的覆盖面、延展课予义务判决的适用场域、引入居民诉讼制度等方式来达致相应司法救济的理想归结。
关键词:公物利用;侵权形态;主观公权利;司法救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
作者简介:梁君瑜(1988-),男,广西贵港人,武汉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行政救济法学、行政法学。
中图分类号:DF3文献标识码:A
行政法视域下的公物利用是一种由公众从公物中实现利益满足的活动。对应于公物最为传统的二元分类,公物利用被细分为公众用公物利用与公务用公物利用。其中,前者是指公众直接使用公众用公物的物理形态而获利,如利用公路出行;后者则指公众享受由行政主体借助公务用公物所提供的服务而受益,如行政主体借助执法器械维护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公共利益,公众因之间接受益。随着人权保障理念之勃兴,公物利用已被赋予愈来愈浓厚的权利色彩,其不再是天然自由或反射利益,也不再是单一形态的自由基本权利,而是一种包含自由权、社会权、保护权、参政权在内的复合型主观公权利[1]。无疑,坚守权利救济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救济自应当仁不让地背负使命,但令人遗憾的是,导致前述主观公权利受损的侵权形态随处可见,而对此实施的司法救济却面临救济途径不畅、救济方法乏善等制度隔阂,亟待论者从各侵权形态所损及的主观公权利类型出发,引导公物利用侵权的司法救济走向实效化、完备化、明确化与全面化。
一、公物利用侵权司法救济的逻辑起点
日本学者原田尚彦在分析主观公权利与司法救济的对应关系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撤销诉讼适用于自由权的保障,而对于受益权的保护则需要更加积极的课予义务诉讼等,参政权则进一步需要诸如选举争讼等制度性保障”[2]。由此看来,当作为复合型主观公权利的公物利用遭受侵害时,司法救济可因循受损权利之性质展开,而作为桥接权利性质和司法救济的侵权形态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焦点。就这层意义而言,借助类型化处理的侵权形态来揭示受损的主观公权利类型,是研究公物利用侵权司法救济的逻辑起点。
(一)自由权之殇:以滥用职权方式妨害公物利用
滥用职权是指行政主体基于不合法动机所作出的违背法律目的之不公正、不合理的行为。以滥用职权方式妨害公物利用的例子十分普遍,如地方政府于公路两旁砌起高耸的“遮羞墙”,不仅未给民众带来任何福祉,还给沿线居民利用公路出行造成不便;原本提供公众自由使用的广场被改为商品房楼盘、公共图书馆被转卖或出租为娱乐场所、乡村公立小学沦为村干部用作抵债的工具……从受侵害权利的性质来看,此种侵权形态主要损及公物利用者的自由权。作为基本权利诞生伊始的主要内容,自由权表现出防御公权力侵害之功能,系指公民有权请求国家以消极不作为的姿态来保障前者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不受干预的自由,前者在此自由空间内可凭己之力追求最大幸福。针对公物利用者自由权的司法救济,法国行政法采取了如下举措:行政机关不得侵犯公共道路沿途不动产所有者的道路便利权(les aisances de voirie),否则,受害人有权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销之诉[3]。
(二)社会权之痛:怠于履行公物给付职责
设立公物的目的主要是以使用关系的形式为公众提供特定服务,因此,公物的主要活动领域为给付行政[4]。给付效果之良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用目的是否完好发挥,鉴此,维护公物,排除其在设置与管理上的瑕疵便成为行政主体的法定职责,例如在下水道井盖缺失、公共桥梁显现断裂迹象时,行政主体应及时、积极地采取维护措施。否则,将构成怠于履行公物给付职责。从受侵害权利的性质来看,此种侵权形态主要损及公物利用者的社会权。社会权也称受益权,它伴随福利国家、给付行政等理念而进入基本权利的范畴,表现出要求国家积极为民提供生存照顾、实现社会与经济上实质平等的受益功能。笼统地说,它一般不是针对“持有者”而言,而是赋予“未有者”的权利[5]。针对公物利用者社会权的司法救济,德国行政法院在判例中指出,对生存照顾和基础设施的给付(如道路的维修)能够成为一般给付之诉的标的[6]。同时,若在给付之前存在一个行政处分,则课予义务之讼将被优先考虑。
(三)保护权之困:疏于排除第三者的侵害
在公物利用法律关系中,因行政主体集公物支配权与公用目的维护职责于一身,故当第三者侵害公物利用时,公物利用者可选择对第三者提起民事诉讼或对未尽职责的行政主体提起行政诉讼。从受侵害权利的性质来看,此种侵权形态主要损及公物利用者的保护权。保护权源自对国家保护义务的对立面之设想,即请求国家积极排除来自私方的第三者侵害的权利。但依传统见解,国家保护义务仅为基本权利客观法面向的内容之一,并不当然赋予受保护者主观请求权,对此,德国学者巴杜拉、黑塞就曾分别从国家保护义务的性质、避免基本权利冲突的必要性来否定保护权的存在[7]。此外,按照耶利内克的理论,主观公权利仅包含自由权、社会权与参政权,三者均体现“个人——国家”的两面关系。保护权未被纳入,很可能与其体现出“个人——国家——个人”的三面关系有关。但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即当今社会存在众多具备压倒性实力的私法团体,它们侵害个人的可能性及程度较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传统上专以对抗国家的自由权、社会权与参政权均无法提供适足救济。鉴此,已有学者提出客观法“再主观化”的论断:“国家保护义务乃客观法上的国家任务,于其中则可得出个人主观公权利”[8]。这为保护权的正名提供了理论支持。针对公物利用者保护权的司法救济,日本学者认为,当产生公害的工厂把超出取缔基准的污染物排入公共水域而规制机关又怠于发动取缔权时,应允许受污染所困的居民提起要求向行政机关发动规制权限的课予义务之诉[2]。
(四)参政权之忧:阻止利用者参与公物决策
保证利用者参与公物决策是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实现公物利用法治化的必由之路。在现实生活中,公务用公物利用存在明显的利益错位现象。与公众用公物利用的直接性有别,公务用公物利用由公众间接受益,因而给行政主体在借助公物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牟取私利留下了缺口,典型例子如奢华办公楼的兴建、公车的超标配置。显然在以上场合,行政主体已取代公众成为公物利用事实上的唯一受益者,但因公务用公物的设置一贯被作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看待,公众并没有获得听证等直接参与公物决策的机会。从受侵害权利的性质来看,此种侵权形态主要损及公物利用者的参政权。参政权即公民能动地参与到国家意志形成过程的权利,针对公物利用者参政权的司法救济,日本《地方自治法》第242条之二规定了居民诉讼制度,即居民在地方公共团体的机关或职员进行违法或不当的公款支出以及财产的管理、处分时,经过监察委员对居民监察请求作出处理后,所提起的客观诉讼。尽管居民诉讼并非直接参与行政意志的形成,但通过请求法院的合法性控制,居民获得了一种消极性、间接性的参政权[9]。
综上,四种侵权形态分别损及不同主观公权利,并对应不同行政诉讼类型。放眼域外有关公物利用侵权的司法救济现状,法国、德国、日本对自由权、社会权、保护权、参政权的救济方式均依托本国相对成熟的诉讼类型法制,如法国的越权之诉可实现自由权的救济,德国的课予义务之诉和一般给付之诉可实现社会权与保护权的救济,日本的居民诉讼可实现参政权的救济。尽管我国大陆地区尚无成型的行政诉讼类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公物利用侵权的司法救济毫无体系。依台湾学者陈清秀的观点,行政诉讼类型的本质乃“人民实现其公法上权利所不可或缺的救济方法”[10]。因此,在域内研究公物利用侵权的司法救济问题,可选取与主观公权利相对应的救济方法(即行政判决方式)为中心,搭建相应的制度体系。
二、公物利用侵权司法救济的现实困局
以受损害的主观公权利为标准,公物利用侵权形态可归为前述四种情形。若细加分析,便会发现四种侵权形态均涉及我国当前司法救济所难以企及的某些角落,公物利用侵权司法救济的现实困局即源于此。
(一)侵权形态遭遇救济方式之实效性不足
从公物利用者的主观公权利来看,自由权、社会权、保护权、参政权呈递进关系,即利用者对国家从消极、积极到能动的地位推进。其中,自由权是最起码亦最普遍的权利诉求。当公物利用者的自由权因行政主体的违法作为而遭受侵害时,撤销判决将被频繁运用。然而,我国撤销判决的实效性并不强,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对预防性诉讼理论研究的迟滞,禁止判决至今仍未确立。而法国撤销判决的实效性则相对突出,体现如下:其一,在1995年2月8日以前,法国行政法院虽“不会在行为撤销的基础上,再明示行政在撤销判决后应当采取的措施,并命令其实施之”,但撤销判决的拘束力依然令人敬畏,其“包括恢复原状义务、禁止反复即禁止作出与被撤销行为同一内容的行为等”[11]。其二,1995年2月8日的法律规定,行政法院可以在裁决中配合使用禁令和逾期罚款,当行政机关没有任何选择自由时,还可以在撤销时明示应采取某项特定的措施[12]。相比而言,我国因缺乏禁止判决的制度设计,法院于撤销时尚不能防范侵害自由权的相同行为二度发生。
(二)侵权形态深陷救济对象之覆盖性不足
公物运营涉及大量事实行为的运用,公物利用侵权形态频繁地肇因于事实行为。若论事实行为与公物利用之牵连,最主要体现在公物的维护方面。例如,排除“遮羞墙”修建不仅要否决包含修建内容在内的行政决定,还应针对附近居民最为关心的“停工”诉求予以回应,旨在“停止一项事实行为”;又如,要求维修道路的公众并不在乎行政主体是以法令还是行政行为的方式作出回应,只在乎维修行为的真正落实,即“实施一项事实行为”。当前,有关作出或禁止一项事实行为的诉求,并未获得我国于2014年11月1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称《行诉法》)的明确肯认。《行诉法》第2条将起诉对象限定为“行政行为”,第4条将审理对象限定为“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第69、70、71、74、75、77条均以“行政行为”作为判决对象,第97条则以“行政行为”作为非诉执行对象。尽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著的“权威读本”宣称,新法中的“行政行为”也包括学理上的事实行为[13]。但这也仅是停留在学理解释层面,更何况“权威读本”还将被学界寄予厚望、认为是对事实行为提供救济的“一般给付判决”立法例的第73条解读为专门针对“行政给付行为”设置的相应判决[13]。由此看来,无论是请求停止公物修建的消极给付,还是维修公物的积极给付,都将因事实行为的定性而难以获得法院判决的支持。
(三)侵权形态面临救济利益之明确性不足
当公物利用遭受侵害时,受损的权利抑或反射利益往往不易区分,由于保护规范理论将对二者的判断权完全交由法官对立法者实定法意的解释,使得同一侵权形态可能面临可诉与不可诉的迥异结局。根据保护规范理论,反射利益是指当法律规范并无保护个人利益之意旨时,个人于事实上所获得的、无法诉诸司法救济的利益。纵观公物利用的发展历程,作为最普遍利用方式的“一般使用”,起初就被各国公物理论视作反射利益的典型。随着各州道路立法的发展,德国通说开始认为一般使用构成主观公权利,即“行政机关违法限制一般使用权的,关系人对该采取防御措施的行政机关享有防御请求权”[14]。然而,由于当时的学者大多尝试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有关“一般自由权”的规定以及第3条第1款有关“平等权”的规定来推导一般使用的权利属性,故以今日之理论加以审视,昔日的一般使用不过是一种不完全的主观公权利罢了,其“仅限于在公用道路上通行,不包括新设置特定的道路、寻求既有特定道路的存续、请求中止对道路种类进行变更等”[15]。换言之,其仅具备单一的自由权属性,而“人民之行动自由,并不包括请求国家修筑或维持特定道路之权利在内”[16],故社会权、保护权、参政权在当时尚披着反射利益之外衣。甚至今日,要求“过度禁止”的自由权与要求“不足禁止”的保护权仍存在明显张力,因自由权根深蒂固的地位,保护权常被视作反射利益,一个侧面的印证在于,课予义务之诉能否要求行政主体对实施侵害的第三者发动规制权尚存疑问。而“新行诉法”第2条将救济利益的范围界定为“合法权益”,其是否包含反射利益?换言之,能否对公物利用者的保护权提供一体救济?缺乏明确性。
(四)侵权形态被困救济模式之全面性不足
域外公物利用侵权的司法救济模式包括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前者以维护主观公权利为目的,后者则以维护客观法律秩序为目的。受传统主观诉讼理念之浸淫,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尚缺乏客观诉讼的立法例,“新行诉法”亦未规定公益诉讼条款。在日本,作为客观诉讼的居民诉讼是保障公物利用者实施其参政权的有效途径。而在居民诉讼尚告阙如的我国,面对行政主体超标设置公务用公物等违法支出公款的行为,由于属内部行政行为的范畴,复议、诉讼及听证渠道皆被封堵。目前,这主要依靠人大代表提出其认为不合理的公务用公物设置的质询议案,要求行政主体作出回应,即以人大监督权和人大撤销权来影响公物决策,以防止行政主体使用公务用公物谋利。但是,人大的监督、撤销始终存在间歇性与滞后性等不足,居民诉讼依旧是对公物利用者参政权实施司法救济的有益借鉴。
三、公物利用侵权司法救济的理想归结
欲走出公物利用侵权司法救济的现实困局,必须致力于“四化”的实现,即救济方式实效化、救济对象完备化、救济利益明确化、救济模式全面化。
(一)以推动撤销判决彻底化实现救济方式实效化
撤销判决的彻底化是指通过一次诉讼彻底实现对当事人的救济。在我国,撤销判决是救济公物利用者自由权的主要手段。例如,针对行政主体作出废止某市民广场的行政决定,理想的司法救济方法应为撤销该行政决定,同时禁止行政主体基于相同的事实、理由重新作出相同决定,即附带的禁止判决。我国至今未规定禁止判决,其原因无外乎禁止判决违背了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存在司法权侵越行政权之嫌。但实际上,正如田中二郎、原田尚彦二位先生所言,对于行政机关即将作出违法的首次判断权的危险非常明确且紧张时,为了排除这种瑕疵,参照现实违法状态的排除请求,由法院直接作出禁止判决并不会对行政裁量构成侵害[2]。与此相应,日本终于在2004年修改通过《行政事件诉讼法》时增加禁止之诉的规定。而在英国,“调卷令与禁令有着类似效果并可同时适用,其本质差别在于对象的时间点相异。调卷令旨在撤销一项已经达成的决定,禁令旨在阻止越权或违反自然公正的决定,二者往往相辅相成,前者面向过去,后者则控制未来行为的合法性”[17]。两国推动撤销判决彻底化的努力可见一斑,值得我们借鉴。
(二)以理顺一般给付判决的覆盖面实现救济对象完备化
对公物利用者社会权的救济,因大量涉及事实行为的给付,需仰赖一般给付判决的运用。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第23条规定,原告申请被告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的理由成立,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而拒绝或者拖延履行义务且无正当理由的,法院可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该条将《行诉法》中条文立意不明的第73条明确界定为“一般给付判决”,从而与《行诉法》第72条的“课予义务判决”作了鲜明划分。但上述司法解释对一般给付判决的引入,至少给人两点疑惑:其一,从文义来看,所列举的“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社会保险待遇”主要涉及金钱的给付,是否也包括事实行为的给付,不得而知;其二,倘若承认事实行为的给付也在其中,那么便与《行诉法》第6条“只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规定不符。唯一合理的解释,或许在于此处的“行政行为”并非是与德国、日本、台湾地区的“行政处分”相对应之概念,进而可以理顺我国一般给付判决的覆盖面:也包含事实行为的给付。
(三)以延展课予义务判决的适用场域实现救济利益明确化
公物利用者保护权处于给付行政与警察行政(即秩序行政)的交叉地带。课予义务之诉适用于给付行政领域,这点毫无异议。但在警察行政领域,课予义务之诉能否要求行政主体发动规制权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又有无具体范围的限制?在德、日行政法中,传统观点认为警察行政的唯一目的是维护公共秩序,专门服务于公共利益,个人从中获得的仅为反射利益。“除非法有特别规定,否则每个国民,无论受到来自于第三人的警察违反状态如何困扰,都不具有向警察行政当局请求取缔警察行政违反者的权利。”[2]应当指出,此种观点是建立在否认国家保护义务“再主观化”的基础之上的。德国行政法院在1960年8月18日的一个判决中有所突破,承认住宅区内受违法建设工地噪声所困扰的居民有要求行政机关对该工地所有者作出禁止营业处分的请求权[2]。此种要求对第三者发动权力的权利被德国学者称为“警察干预请求权”,等同于本文的“保护权”概念,本案判决使保护权的性质再度成谜。在实践中,要求公物利用者判断在何种范围内形成主观公权利、何种范围内仅享有反射利益是困难的,同样的问题若交由法院来判断则是随意的。德国学者亨克曾主张:“通过不断积累就个案所作的慎重审查与决定等经验来正确界定警察干预请求权的界限。”[2]换言之,与其重复探讨保护权是权利还是反射利益,不如结合经验法则与个案情节来权衡救济与否。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法释[2015]9号”文件第22条明确规定了课予义务判决,即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被告违法拒绝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的,法院可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原告请求的法定职责;尚需被告调查或者裁量的,应当判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结合《行诉法》第12条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也位列其中。这表明课予义务判决同样适用于警察行政领域,保护权获一体保护业已明确。
(四)以引入居民诉讼制度实现救济模式全面化
如前文所述,损害公物利用者参政权的实例集中表现在公务用公物的设置方面。早在2006年,湖南省常宁市的普通公民蒋石林就以市财政局超出年度财政预算购买两台公车为由,诉请法院“确定被告拒不履行处理单位违法购车和给原告答复的法定职责行为违法”,但法院最终以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裁定不予受理[18]。由于公务用公物的设置属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依传统观点,内部行政行为不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公物利用者既无诉权也无听证权利。但是,公务用公物的超标配置意味着公共财产的挥霍,正如学者所言:“必然会造成行政成本的急剧上升,甚至造成行政主体负债,当这些不必要的开支挤占真正应当用以行政公务的财产时,行政机关又必然会向人民伸手,设立不合理的行政收费以弥补行政经费的不足”[19]。如此而言,公务用公物的超标配置损害的公共利益就“不再仅仅是法律主张其自身的权威、威严这样一种单纯的概念上的利益,而同时也是一种谁都能感受得到,谁都能理解得到的非常现实、极为实际的利益”[5]。居民诉讼正是为因应此种利益诉求,对消极性、间接性的参政权予以保障的制度,它可以弥补我国单一主观诉讼模式的不足、扩大司法救济的疆域。
四、结论
伴随权利意识的觉醒,公物利用已发展为包含自由权、社会权、保护权、参政权在内的复合型主观公权利,其中每一项权利都有受到侵害的可能。以主观公权利与司法救济的对应关系为线索,有助于周延地归纳出损及不同权利的侵权形态,完整地揭示出侵权形态在我国当前的司法救济方式、对象、利益及模式上的困局,逻辑地演绎出我国公物利用侵权司法救济的理想归结在于救济方式实效化、救济对象完备化、救济利益明确化与救济模式全面化。本文认为,唯有通过推动撤销判决彻底化、理顺一般给付判决的覆盖面、延展课予义务判决的适用场域、引入居民诉讼制度,方能对达致上述理想归结有所期待。
参考文献:
[1]梁君瑜.作为复合型主观公权利的公物利用[J].时代法学,2015(2):41-47.
[2][日]原田尚彦.诉的利益[M].石龙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34,83,76,54,80-82,87.
[3]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61.
[4][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77.
[5][意]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M].刘俊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07,67.
[6][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M].莫光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06.
[7]梁君瑜.聚焦基本权利之第三者效力理论——以基本权利之二重性质对该理论的影响为切入[J].研究生法学,2013(4):13-21.
[8]陈慈阳.宪法学[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358.
[9]江利红.日本行政诉讼法[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630-631.
[10]陈清秀.行政诉讼法[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139.
[11][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M].王天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195.
[12][法]古斯塔夫·佩泽尔.法国行政法[M].廖坤明,周洁,译.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305.
[1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8,202.
[14][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M].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97.
[15][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M].吕艳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08.
[16]陈敏.行政法总论[Z].2004:1019.
[17]David Stott,Alexandra Felix.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M].London:The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1997:158.
[18]毛广坤.浅议在税收工作中如何关注民生[N].经济信息时报,2009-01-09(07).
[19]余睿.公共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属性[J].江西社会科学,2015(1):148-153.
On Judicial Relief of Infringing the Utilization of Public Properties
——Taking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Public Right and Judicial Relief as the Clue
LIANG Jun-yu
(SchoolofLaw,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China)
Abstract:The utilization of public properties is a compound subjective public right. Because of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public right and judicial relief, summing up the forms of infringing the utilization of public properties and analyzing the styles of the damaged subjective public right ar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o perfect corresponding judicial relief in China. Judicial relief of infringing the utilization of public properties in China is faced with deficiencies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relief ways, the coverage of relief objects, the definition of relief interests,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relief models etc.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rresponding judicial relief, we should promote thorough revocation of verdict, straighten out the coverage of general payment decision, expand the applicable scope of the judgment for administrative omission and introduce the resident litigation system.
Key words:the utilization of public properties; the forms of infringement; subjective public right; judicial relief
(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