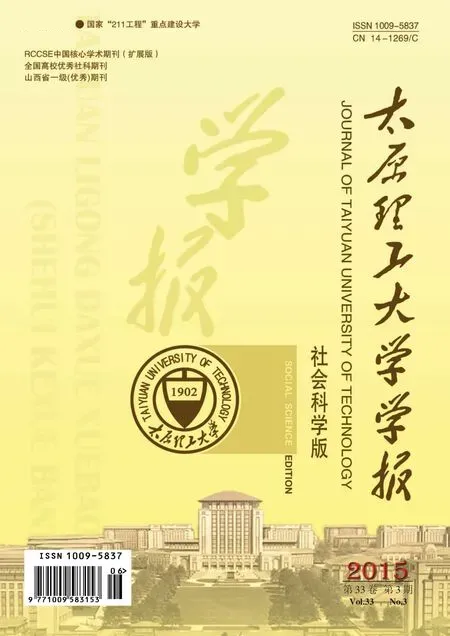重塑与误读:议《在中国屏风上》与近代中国社会
2015-02-11张晗,刘积源
重塑与误读:议《在中国屏风上》与近代中国社会
张晗1,刘积源2
(1.兰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2.西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在中国屏风上》是英国现代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于1920年沿中国长江流域游览后发表的一本游记。文章试图以该游记为蓝本,分析、解读毛姆对中国的另类想象,归纳其笔下的中国人及在华英国人的形象。毛姆对中国文化既有认同又有否定,但也存在诸多误读之处。对这些人物的塑造和文化的误读也表明:毛姆试图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面对中国文化,并同中国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与沟通,但同时也折射出毛姆内心潜藏的西方式傲慢与民族偏见。
关键词:《在中国屏风上》;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中国书写;形象塑造;文化误读
基金项目:兰州理工大学校
作者简介:张晗(1980-),女,陕西汉中人,兰州理工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刘积源(1976-),男,甘肃兰州人,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南京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欧美文学、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712.47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游记作品《在中国屏风上》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这源于其游记题材已经日益成为新世纪以来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热门话题。游记不仅会记录旅行者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内心感受,还记录了沿途风光及旅行目的地的地理风貌,让旅行者以“他者”的身份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审视“自我”内心的主观愿望。在跨国界和跨文化背景下写出的游记更会产生跨学科、跨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国内有学者指出:“游记研究已成为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的一个热点,并且取得了大量成果。”[1]作为殖民主义话语的组成部分,西方作家的游记不可避免地体现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和强烈的文化中心意识,它不仅反映外部世界,而且还表现出旅行者的主观理想和愿望。自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来华通商开始,到近代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后,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得以沿长江而上深入中国内地,同时撰写出了大量的游记。除此之外,毛姆的作品之所以广受读者喜爱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的写作中总是充满异国情调和对异国的想象。毛姆的足迹曾遍及整个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属诸岛以及香港地区和中国内地。在旅行过程中,他记录下这些异国经历并对西方文化进行反思。因此,本文试图以《在中国屏风上》为蓝本,分析、解读毛姆对中国的另类想象,进一步梳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否定,阐明其中的诸多谬见与误读。
(一)对中国的另类想象
英国学者杰弗里在《英国的中国游记》序言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想象的中国为西方脱离单调乏味提供了一个积极的‘彼岸’。”[2]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此岸”的西方世界越来越多地暴露出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弊端,人们的精神开始濒于荒漠化。一些英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东方,憧憬彼岸世界的美好。带着此种希冀,毛姆来到中国,希望可以找到东方文化昔日的荣光,找寻他心目中宋唐时期的辉煌。正如济慈在古瓮上所看到的希腊一样,毛姆眼中的中国是画在屏风上的流彩。从1922年开始,毛姆开始把他在中国的见闻落笔成文,“东方题材”系列文章包括了《在中国屏风上》《刀锋》《彩色的面纱》和《苏伊士之东》等著作。《在中国屏风上》一书集中展现了他想象的中国以及在中国旅行途中遇到的各种人与事。在《在中国屏风上》一书的序言部分,毛姆写道:“它们会给那些乐于使用想象力的读者一个真实而生动的中国图画”[3]。无论读者在读完游记之后是否会实现毛姆的这一期望,我们仍然可以从作家的笔端一窥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毛姆笔下的中国,虽然有些愚昧落后,但仍然可见唐宋时期的辉煌。《在中国屏风上》一书共有58篇小散文,详实记录了毛姆的中国之行,全书人物众多,风景瑰丽,事件新奇。在开篇第一章《幕启》中,读者会看到茅草房、城门、驼队、商店等场景,有“身着提华的丝织黑色长袍和小夹袄、站在路边闲谈”的两位矮胖老爷,他们提着鸟笼比较两只鸟儿的可爱。这些描写画面感十足,在静态的背景下,“一匹毛色光洁的骡子,拉着一辆北京轿车缓缓行来”[3]。毛姆据此展开想象,猜测坐在马车中的是怎样的人,“也许是一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正应诺前去拜访一位朋友,他们将秉烛夜谈。共同追忆那一去不返的唐宋盛世;或是一位歌女,身着玲珑绸缎制成的鲜艳衣裳,乌黑的头发上簪了一块翠玉,她此刻正被召往一个宴会,在席上她要演唱小曲,还要与那些风流倜傥的公子哥们雅致地酬答”[3]。饱学之士和穿绸戴玉的歌女就是最先闪现在毛姆脑海中对中国最鲜明的记忆。这些描写也为全篇定下基调:毛姆来中国最想寻觅的是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古典思想如孔孟之道,唐诗宋词,神秘优雅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赛义德曾经指出:“东方是西方人创作出来的想象的地域及表达。”[4]尽管已经踏上中国的土地,亲眼看到了中国的社会景象,可是毛姆仍然一心想寻觅他心目中理想的中国。而此时的中国社会,国弱民贫,虽然摆脱了清王朝封建专制,但是在经历袁世凯称帝、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割据下,举国各地天灾人祸、民不聊生。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逐步叩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妄图进一步蚕食中国。对国人来说,毛姆对中国的想象过于艺术化、理想化,恰如古代唐宋时期的水墨画卷,而非20世纪20年代的真实面貌。
(二)中外人物肖像描写
毛姆乃刻画人物之高手。《在中国屏风上》中有很多小散文描绘了毛姆在中国游历期间接触到的各种人物角色,其中既有中国人也有西洋人。在毛姆所刻画的在华英国人中,三类人物最为常见:传教士、商人和政客。首先来看看他对传教士的描写。在《恐惧》一篇中,毛姆对传教士们的评价是:“他们可能是圣徒,但他们不常常是绅士。”[3]在《恐惧》的开篇部分,传教士温格罗夫先生就被叙述者认定为“绅士”,他来中国传教已经有17年,很少休假;他的夫人认为中国人是“说谎的人,是不能信任的,残酷的和肮脏的”,每听到此,温格洛夫先生就会为中国人做辩解:“中国人天性善良,孝敬父母,疼爱孩子”。因此,他的妻子对他做出了总结:“他听不得一个反对中国人的字,简直就是爱他们”[3]。但是,当一位当地中国妇女走进来,向温格洛夫夫人报告事务之时,温格洛夫先生的脸上却会“流露出极其明显的厌恶表情,好像有某种使他恶心的气味把他的脸弄歪扭了”[3]。不过,这样的表情只发生在一瞬间,传教士随之马上就会挤出愉快的笑容,继续和叙述者交谈。后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对方脸上的表情变化,于是“吃惊地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伪善的教士面孔下面的真相:“凡是他意识上都爱的,灵魂上都厌恶”[3]。口口声称喜爱中国人的传教士先生在内心深处却厌恶中国人,他对中国人的辩解和仁爱不过是伪善的面具。温格洛夫先生迫使毛姆开始重新审视在华传教士群体,意识到某些真相之后,作者感到十分兴奋,因为这趟中国之行使他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这是一个探险者经历一场盲目的冒险旅行之后,来到一个面貌崭新、一切出人意料的异邦后才可能有的感觉。当毛姆看着自己的同类,并以“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国家的人与文化之时,他的确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另一类毛姆着墨较多的是在华商人。《亨德逊》里的主人公亨德逊先生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他是外资银行的经理,经常标榜自己的民主自由思想,时不时评论罗素等民主人士的作品。尤其特别的是,他十分怜惜黄包车车夫。他坚持如果坐黄包车就违背了人人平等的观点。可是有一次,当毛姆和他同行前去办理一件紧要的事情时,亨德逊先生不仅坐上了黄包车,而且还指挥车夫在上海的大热天里来回奔跑。毛姆对车夫不禁心生怜悯之情,而亨德逊却回答:“这是他们的好运道,你不必对中国人有任何关心。你明白,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们惧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3]。显然,这些话充分暴露了亨德逊先生虚伪的面目,他所谓的民主平等思想不过是用来骗人的装饰品。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潜存着白人种族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在该文中,读者很容易感受到洋人根深蒂固的西方式思维与观念: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东方人永远并且仅仅是英国殖民地统治的肉体物质。而作者毛姆的态度则更加耐人寻味:“我没说一句话,我甚至也不想笑。”[3]毛姆对下层劳动民众明显抱有同情,当然也对亨德逊的做法心存鄙视,然而他却选择了沉默,此处的留白值得思考。在另一篇《麦卡利斯特医生》中,麦卡利斯特先生代表了在中国的殖民者形象。麦卡利斯特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后来脱离教会,依靠洋人的身份用极低的价格买卖土地,建造学校、商场发家致富,在上海过上了发号施令、纸醉金迷的殖民者生活。当他在中国发生蜕变,脱离当初穷苦破落的窘境变成彬彬有礼的绅士坐在毛姆对面时,毛姆不禁大为吃惊:“他是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今天我在此认识的这个人的”。
毛姆作品中还有许多在华官员,他们个个飞扬跋扈、依仗殖民者身份在中国为所欲为。《范宁夫妇》中刻画的范宁先生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这位范宁先生跟中国人说话时,总会提高嗓子,粗声粗气,好像在发号施令。他虽然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是当某个佣人做了什么不如他意的事情时,他总会用英语大骂他一通。究其原因,范宁先生实际只是用这种方式让别人惧怕自己以彰显自身的权威,而英语就成了权力的象征。
许多英国作家都热衷于描写殖民地的人物风情,但是与其不同的是,毛姆始终对那些普通的小人物情有独钟。对于那些西洋人,特别是在华的英国人,毛姆总会无情地揭露其自大虚伪和表里不一的特质。每每谈及中国人,他都会对那些贪婪自私的官员大加讽刺和挖苦,同时对饱学之士的智慧表示钦佩,对普通市民(包括苦力)给予深切的同情。在《内阁部长》一篇中,他把政府部长称之为“恶棍”,当此人向作者炫耀自己搜刮来的奇珍异宝的时候,毛姆会敏锐地指出,那肯定是“用极端憎恶的手段获得的巨大财富”;在《戏剧学者》一篇中,毛姆遇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戏剧学者,在与他们的交谈中,他掩饰不住对中国文化的倾慕;而《哲学家》一篇则详细记述了作者和辜鸿铭见面的情景。两位饱学之士热烈地探讨东西方文化,他们的思想和观点的交流或许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一种态度。毛姆始终深切同情中国的劳动人民,他着墨最多的人物群体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苦力。他认为这些苦力是“有趣的”动物,就像牲畜一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劳作着,却没有丝毫怨言。毛姆与挑夫告别时,后者却哭了起来,这使毛姆大为吃惊,他想象不到那些类似牲畜的苦力竟然也有感情。在他笔下,中国人总体上都是善良的,他们安于现状,勤劳而忠实。中国人的相貌并不符合种族主义者的审美标准,所以被视为丑陋、神秘的。他还认为中国人是难以理解的。他们“一方面善良、热忱、孝敬父母、疼爱孩子;而另一方面则圆滑、残忍、好说谎、不可信任”。显然,这些描写并未摆脱西方对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偏见。尽管如此,毛姆用敏锐的笔触描绘了一群不同职业、形象各异的人物类型。作家对这些人物的刻画既具有客观性,又极富艺术性。他仿佛能够进入人物的灵魂最深处。人物的所思所想,希冀与彷徨、痛苦与欢乐、动作举止、神情顾盼等,都可以在一两句话中得到高度、富有深意的概括。在《序言》中毛姆指出:“我喜欢各种各样的人,包括那些我不愿再见面的人。当你知道这辈子你们只会见上一面的时候,没有人会让你厌烦。”[3]或许正是基于这种精神,他笔下的人物才真正具有了神采。
(三)重塑与误读
根据史料,毛姆曾经溯江而上,游历中国四个月。从游记《在中国屏风上》一书亦可以看出,他当年曾游历中国各地,广泛考查了中国的风俗人情、山川地理、建筑宫庙等多种文化元素,并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思考。因此,这本游记也是毛姆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一番对话;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一次深度交流;同时,也记录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个人理解,包括认同与否定。中国学者吴超平曾指出:“一般说来,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这个世界!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5]由于毛姆曾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读中国文化,加之他在中国的时间较短,并未深入了解和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因此当东西方文化相遇时,难免就会产生偏差或者误读。
毛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主要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在物质文化层面,毛姆在描写中国的建筑时采用了白描手法,但对其中的含义却知之甚少。例如,在《幕启》一篇,毛姆眼中的城墙已经年久失修,早已坍塌,然而外形还依稀可辨,看上去就像“古画中一座十字军占据的巴勒斯坦城堡”[3]。这个城墙依然打上了西方建筑的烙印,巴勒斯坦城堡就像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象征。在毛姆的笔下,《燕子窝》中的鸦片烟馆温馨惬意,学者和苦力都能和谐同处,共同放松,恰如西柏林的小酒馆。毛姆甚至把鸦片烟馆比做“家”一样的地方,安逸而舒适。尤其当他在鸦片烟馆看到一位男子摇摆抚弄着婴儿时,他把中国人对孩子的疼爱和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理解成“东方人所特有的对孩子的激情”[3]。而在西方文化中,父母会尽早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这与中国文化对下一代的理念是有差别的。
在《天坛》一篇,毛姆眼中的天坛庄重辉煌,“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3]。这段文字真实地还原了毛姆眼中的天坛,但在最后作者认为天坛就是祭拜皇族先祖的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误读。事实上,天坛历来是皇帝祭祀天神和祈谷之所,而非祭祀祖先之地。明清时期,祭祀祖先需要到太庙;如果遇上少雨的年份,还会进行祈雨的仪式;祭祀时皇帝要率领百官朝拜祷告,以祈求上苍垂怜。天坛处处昭示着中国正统神文化所特有的寓意和象征手法,而毛姆的理解则显得简单而有失偏颇。
在精神文化层面,毛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主要体现在《雨》一篇里毛姆对老庄思想的理解。他认为:“庄子是个人主义者,僵硬的儒家学者对他皱眉。”[3]毛姆将庄子等同于一个“个人主义者”,显然是一种文化误读。老庄的道家思想和个人主义在强调个性方面的确有相似之处,然而道家的思想和态度又与西方现代个人主义完全不同。西方个人主义主张个体的价值在于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强调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上一切以个人价值取向为坐标,每一个人都被视作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特个体。而道家认为,人的最高价值是自我保存,以“道法自然”为总体原则,追求“心的自由”。毛姆早年在大学期间非常欣赏叔本华的哲学,同时对老庄思想也有所了解,因此就下意识地认为庄子追求自由的思想就等同于个人主义,作为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认识尚浅的毛姆来说,才会产生这样的误读。
(四)结语
毛姆在游记《在中国屏风上》以深邃的观察力描写了想象中的中国,以冷静犀利的笔风描写了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及在华英国人的形象,构绘了一幅别样的中国画卷,集中展现了他心目中的近代中国社会。通过这些形象的构筑,毛姆试图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方式寻找古代中国的灿烂文化,并同中国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和交流。由于文化的差异,文中不可避免产生了一些对文化的误读,但是毛姆对此所做的尝试仍然值得称道。毛姆以“他者”的视角在异域文化中审视“自我”,从而更好地反思自身以及西方文化。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再次审视《在中国屏风上》这本游记,细细品读毛姆对20世纪初中国的再现,或许对我们回顾历史,从跨文化视角认识自身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王小伦.文化批评与西方游记研究[J].国外文学,2007(2):56-64.
[2]Jeffrey Twitchell-Waas.British Travel Writing from China,1798-1901[M].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10:3.
[3]毛姆.在中国屏风上[M].唐建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4,3,43,44,45,42,58,57,117,1,51,23,95.
[4]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1979:5.
[6]吴超平.试论毛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6):127-130.
Remolding and Misreading:
OnTheChineseScreenand the Modern Chinese Society
ZHANG Han1, LIU Ji-yuan2
(1.SchoolofForeignLanguages,LanzhouUniversityofTechnology,LanzhouGansu730050,China;
2.SchoolofForeignLanguages,Nor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LanzhouGansu730030,China)
Abstract:On The Chinese Screen is a travel book published by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an English modern writer, who travelled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in 1920. Taking the travel book as the chief source, this paper analyses and interprets Maugham’s alternative imagination about China and sums up the images of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characters in China. In terms of Chinese culture, Maugham has both recognition and oppositon, but there are many misreadings. His characterization and cultural misreading show that Maugham attempts to take a calm and objective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culture and to converse, exchange ideas and communite with it and meanwhile, reflect the western arrogance and national prejudice hidden in Maugham’s heart.
Key words:OnTheChineseScreen;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Chinese writing; image creation; cultural misreading
(编辑:张文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