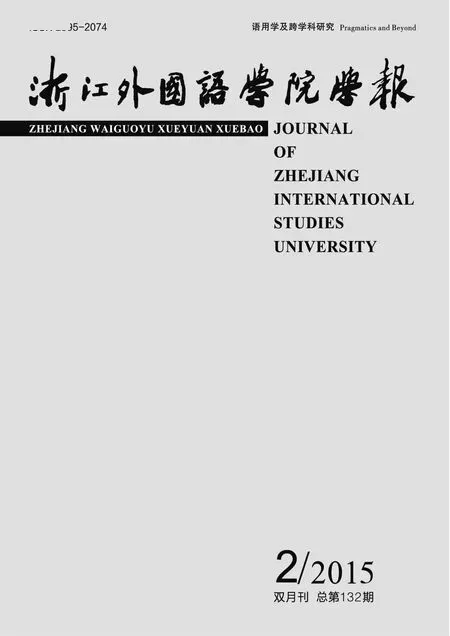典籍英译中的形制研究
——以《九歌》为例
2015-01-31卓振英
卓振英
(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典籍英译中的形制研究
——以《九歌》为例
卓振英
(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文章采用描述、个案研究、文献研究、互文参照等方法,对《九歌》的篇数等颇有争议的形制问题进行辨析,阐明《九歌》有九篇而并非十一篇,进而论证形制研究在典籍英译中的重要性。
典籍英译;《九歌》篇数辨析;形制研究
一、引言
文学作品的所谓形制,狭义上是指形式、体裁。本文从广义上使用形制一词,用以指特定典籍在体裁、体式、篇目、结构、编排、题材、形神关系和文体风格等方面所遵循的规约。典籍英译“属于研究型翻译的范畴”[1]25,而形制研究又是典籍英译中研究工作的构成部分,其作用不容低估。若疏于研究,就可能造成张冠李戴、狗尾续貂的错误,影响译作质量。
根据《楚辞》现有各种主要版本的形制与编排,《九歌》共十一篇。然而,关于《九歌》的篇数,学界历来都有争议。争议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九歌》中的“九”到底是实指还是虚指?有的学者认为《九歌》共有九篇;有的则认为多于九篇。在前者眼中,“九”是实指,在后者看来则“九”是虚指,意思是“多”。主要问题之二是,若“九”是实指,应如何对待或整合原有十一篇?对此同样众说纷纭。有主张合并《湘君》与《湘夫人》的,有主张合并《大司命》与《少司命》的,也有主张将《国殇》《礼魂》排除在《九歌》之外的,等等。认为有十一篇的见解属于主流,其代表作之一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金开诚(2000)基本上亦持十一篇的看法。他认为:“《九歌》之‘九’和祭祀神鬼的歌词篇数是并无必然联系的。”[2]155
总而言之,《九歌》的篇数及如何整合的问题迄今尚无定论。就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探讨,以揭示《九歌》在形制方面的本来面目,这对于楚辞研究及英译本复译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本文将采用描述、文献研究、个案研究、互文参照等方法展开辨析、研究,以解决有关《九歌》的篇数等问题,展现《九歌》的本来面目,并据此阐明形制研究在典籍英译中的重要性。
二、《九歌》之“九”是虚指还是实指?
首先,《九歌》与《九招》《九辩》密切相关。《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竹书纪年》说“帝启十年舞《九招》于大穆之野”。 因此,《九辩》和《九招》的形制就有助于我们了解《九歌》。
经过研究,高亨(1961)得出了“九招这个乐曲当包括九章”的结论[3]44。王冰、王丽娟(2012)在高亨所做研究的基础上,对《九招》作了这样的描述:它是集歌、乐、舞三位于一体的文艺形式,称为韶乐,共分为九段,或曰九个乐章;乐队的编配既有鼙(军用小鼓)、鼓、钟、磬、鞀(鼗鼓)、椎(捶击具)等打击乐器,又有笙、管、篪等吹奏乐器;歌队(人抃)列于一旁,边鼓掌边歌唱;由化装成凤鸟和山鸡的人员组成的舞蹈队则跟随着乐歌的节奏翩翩起舞;乐舞的内容是“康帝德”,即宣扬大自然主宰万物的功德[4]52-53。毫无疑问,在《九招》中,“九”是实指。这就使得《九歌》中的“九” 作为实指的用法有了横向的参照依据。
其次,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就“九”的用法而言,屈原具有什么样的写作思维习惯。写作思维习惯是作家在长期写作与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作家个性的表现,也是读者了解作家、解读作品的依据之一。一般来说,写作思维习惯是具有连贯性的,否则就可能在文字及其意义等方面造成混乱,影响创作意图的实现,这是一切成熟的作家所忌讳和竭力避免的。
屈原的写作思维习惯是有轨迹可寻的。在他的诗句中,“九”既有用作虚指又有用作实指的情况。例如“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句中的“九”为虚指,而“地方九则”(《天问》)中的“九”则为实指。
那么,在作品的数目方面,屈原对“九”又有什么样的用法呢?我们不妨检视一下他的《九章》。《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和《悲回风》。这些诗篇的创作时间和地点不同,内容也没有太多内在的联系,然而,诗人还是把它们集结为九篇。于此可见,与《九招》一样,《九章》中“九”的用法也是属于实指。
根据诗人的写作思维习惯和《九歌》与《九招》《九章》的关联性与互文性,我们可以推而知之,《九歌》中的“九”也应是实指,其所指应为《九歌》的实际篇数。
三、《九歌》十一篇应如何整合?
如果《九歌》的实际篇数是九篇,如何解释和看待原有的十一篇就成了必须解答的又一学术问题。
主张《九歌》原有篇数为九的专家学者不乏其人,但在对十一篇应如何看待的问题上却莫衷一是。普遍的情形是,就研究个体而言,对某一问题的见解言之成理,对另一问题或有关细节的看法则纯属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黄凤显(2002)对有关篇数的研究进行了梳理[5]208-219。加上黄先生自己的看法,大致上有以下八种见解:
周用《楚辞注略》认为当将《湘君》《湘夫人》合而为一,《大司命》《少司命》合而为一[5]208-209。
黄文焕在《楚辞听直》中认为,《山鬼》《国殇》及《礼魂》“虽三篇实止一篇”,理由是,三篇所指俱为鬼[5]209。
陆时雍在《楚辞疏》中以“《九章》止九篇”为由,认为《九歌》应为九篇,故主张将《国殇》《礼魂》删去[5]209。
钱澄之在《屈诂》中认为《河伯》《山鬼》两篇不能算数,因为河伯所在的黄河“非楚地域所及,而《山鬼》涉于邪,屈原虽仍其名,而黜其祀,故祀神之歌,实为九篇”[5]209。
王闿运在其《楚辞释》中认为应排除《国殇》,而《礼魂》则是“每篇之乱也”[5]209-210。
郑振铎认为,《东皇太一》是迎神曲,《礼魂》是送神曲,“不该计入篇数之内”[5]210。
贺贻孙在其《骚笺》、许清奇在其《楚辞订注》中主张并《湘君》《湘夫人》为一篇,并《国殇》《礼魂》为一篇。林庚在他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中持相近见解[5]209。
黄凤显在其有关壮族师公戏的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认为《九歌》的篇数问题“其实只是这一组诗作的表层问题”,这组诗作的主祭歌是“代表着九歌的命意的”《国殇》。除了《国殇》《礼魂》,其余“9篇请神、娱神以慰灵的祭歌,就是‘九歌’”[5]210-219。
对于以上的见解,下文将逐一加以辨析。
第一,将《大司命》《少司命》两篇合而为一是否合理?
回答是否定的,理据是:从身份、地位和职能看,大司命、少司命互不从属,各司其职。前者掌握百姓的寿夭,后者则负责男女匹配,保护儿童;从内容看,《大司命》《少司命》各自独立成篇,且二者之间并无相互呼应的内容和可供对唱的唱辞。
第二,说《山鬼》《国殇》及《礼魂》所指俱为鬼,物以类聚,虽三仍一,这种说法牵强附会。
首先,根据典籍,山鬼即山神。《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 北齐人樊逊在 《天保五年举秀才对策》里说:“山鬼效灵,海神率职”;汪瑗认为:“谓之《山鬼》者何也?……盖鬼神可以通称也,此题曰《山鬼》,犹曰山神山灵云耳。”[6]137其次,《楚辞》中的“山鬼”美丽、率真,形象美好,类神而不类一般意义上的鬼;至于“国殇”,诗人是满怀敬意地用“神以灵”指称他们的,国殇也非一般意义的鬼。再次,《山鬼》与《国殇》在内容上没有内在联系,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综上所述,该三篇不可合并为一。
第三,陆时雍在《楚辞疏》中谈及《国殇》《礼魂》两篇时说,“想当时所作不止此,后遂以附歌末”,李光地在《离骚经九歌解义》中认为九歌“疑当尽于此”①,故尔主张应将该两篇删去[5]209。他们未能举证说明,只凭臆测,不足为信②。
第四,因河伯所在的黄河“非楚地域所及,而《山鬼》涉于邪”,而主张将《河伯》《山鬼》两篇从《九歌》中剔出,理据不足。
正如上文所述,山鬼即山神,并非邪祟。虽然河伯原来是指黄河之神,但到了战国时代,人们就把各水系的河神统称为河伯,巫风盛行的楚国更是不必顾忌源于中原的“祭不越望”的规矩。一般说来,神仙不会因某处与其距离遥远而断了香火。南方人拜玄武大帝以求风调雨顺;北方人祠南极星君以祈福禄寿全;黄大仙的出生地浙江金华非香港“地域所及”,但这并不妨碍港人崇拜黄大仙。
第五,在谈及《礼魂》时,汪瑗与王闿运持同样的看法。他说:“盖此篇乃前十篇之乱辞。”[6]144但《礼魂》所礼者乃魂也,只适用于《国殇》,而不适用于涉及诸神的其他篇章。理由如次:
首先,灵有别于魂。《九歌》中对神的称谓一般是“灵”,指神灵,偶尔也称为“君”或“帝”。例如,“灵偃蹇兮姣服”(《东皇太一》),“灵皇皇兮既降”(《云中君》),“灵衣兮被被”(《大司命》),“夕宿兮帝乡”(《少司命》),“灵之来兮蔽日”(《东君》),“灵何为兮水中”(《河伯》),“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山鬼》),“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大司命》),等等。而魂与魄则是对人而言的。根据旧时对于人的生命的认识,魂主精神,而魄主身形。魂就是离开死者的体魄、回旋升空的阳气。“魂,阳气也”(《说文》),“人生始化为魄,既生魄,阳曰魂”(《左传·昭公七年》)。
其次,从《礼魂》的内容看,“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春秋各以具有明显季节性的兰菊献祭,这合乎祭祀亡者的习俗和《孝经》的所谓“春秋祭祀,以时思之”。但礼魂的时令和祭品却并不完全适用于祭拜大司命、少司命等神灵。
逐一对照起来,《礼魂》之外的原《九歌》其余十篇中,能够以《礼魂》为尾声的就只有祭奠为国捐躯将士的《国殇》。二者具有连贯性和相互适应性,其合并也合乎礼俗。
第六,《东皇太一》理应独立成篇,把它当作“迎神曲”是错误的。
太一乃太极,是“万物之源”[6]108。根据王逸、朱熹、洪兴祖等楚辞学大家的见解,东皇太一乃楚国尊神,这是毫无疑义的。再说,《东皇太一》的内容也并不适合作为其他各篇的迎神曲。根据其开头两句“吉日兮良辰,穆将愉兮上皇”,金开诚(2000)针对“迎神曲”的说法质问道:“难道他们③也能称为‘上皇’?”[2]153此可谓一语中的。
第七,林庚(1981)认为:“《湘君湘夫人》的内容文字如此相像,倒正因为两篇原来就是一篇。”[7]154他与贺贻孙、许清奇等主张将《湘君》《湘夫人》合而为一,将《国殇》《礼魂》合而为一,这是很有见地的。
湘君与湘夫人的原型就是舜及其原配娥皇、女英。根据传说,舜巡察南方,在苍梧亡故。娥皇和女英闻讯前往,一路上失声痛哭,眼泪洒在山野的竹子上,使之成了斑竹。她们最后投身湘江,殉情而死。所谓二湘“乃敌体者也,而又有男女阴阳之别,岂可谓之一篇乎”[6]109的质询不堪一击:男女情爱乃伦理之基,故尔《诗经》纳“关雎”,梨园唱梁祝,孔雀飞东南。舜与二妃的爱情深沉执着,并非野合乱伦,是以历来备受尊崇。置《湘君》《湘夫人》于一篇,有何不可?
文本分析表明,两篇存在对唱的唱词。例如,《湘君》开篇的“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与《湘夫人》开篇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可谓珠联璧合;《湘君》篇结尾的“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与《湘夫人》篇的“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亦可谓一一相对。
《湘君与湘夫人》无疑系由扮演湘君与湘夫人的男巫、女巫的对唱。正如汪瑗所指出的,“二篇为彼此赠答之词无疑”[6]115。
关于合《国殇》与《礼魂》于一篇,后者是前者的尾声,其理据已在上文有所陈述。
第八,说《国殇》《礼魂》之外的“9篇请神、娱神以慰灵的祭歌,就是‘九歌’”,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将《国殇》《礼魂》排除在《九歌》之外。说主祭歌是《国殇》,诸神只是请来聚会的“主持者或参与者”[5]217,其主要依据是对师公戏的考察,缺乏有关《九歌》的形制、旨趣、历史等证据,难以形成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链。
神是被人格化了的,高高在上,俯视人间。众神各有其诞辰、职守和处所,迎神各有其时序、仪式和意旨。根据民俗,人们在七月十五拜鬼王公,在八月十五拜月,在“司命公生(诞辰)”拜司命帝君,在“妈祖生”(农历三月二十三)拜妈祖。可见,神祇是不能想请就请的,必须遵照一定的规矩和体制。说“请”东皇太一为国殇主持仪式,并“请”其他诸神参与祭奠国殇的活动,实际上是把神的地位从主宰降低到从属,把凡人的想法强加于神,把今人的臆测硬套在楚人头上。从《九歌》的文本看,娱神活动所用供品多样,迎神、送神的地点不同(如九坑、南浦等),歌辞的内容、笔调和所要求的气氛也有诙谐、肃穆、怨叹之别;众神有在地上的,有来自空中或水上的。为了国殇这一所谓“主体”而同时将众神作为宾客迎来的假设,也难以解释迎神、娱神、送神的地点等问题。总而言之,将《国殇》作为主祭歌而将其从《九歌》中排除出去的见解不足为信。
四、关于整合后的形制与内容
林庚有关应将《湘君》与《湘夫人》,《国殇》与《礼魂》分别合并的见解是可取的,但对某些细节的看法却颇值得商榷。为了正确复原作品的形制,下面将对有关看法加以探讨,并就《九歌》英译的形制预设提出建议。
(一)关于《湘君与湘夫人》
林庚认为湘君湘夫人会了面。他说:“反正最初湘君说来而没有来,后来却终于来了,在故事里是叙述得很明白的。这故事的型有点像牛郎织女会面的故事”,“从巫的口中说出湘夫人如何在北渚忧愁的神情,如何终于得到湘君来临的消息,于是召了巫去,在水里筑了一个富丽的行宫,最后是湘君来了与湘夫人偕逝升天而去”[7]157-158。
然而,情形并非如此。由于双方所到达的地点不同(一是北渚“夕弭节兮北渚”,一是西澨“夕济兮西澨”),因而并未见面,这才将礼物“委之水滨”,“以阴寄吾意,而冀其或将取之”[8]45。若果真如林先生所说的,湘君与湘夫人“偕逝升天而去”,那么,礼物就完全可以当面互赠,双方也就不必叹息“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了。
林庚还认为:“湘君湘夫人的故事虽是一篇,演出时可能是两幕……第一幕是由巫饰湘夫人……第二幕是巫自己的表演……第一幕可以说是《迎神曲》,第二幕可以说是《送神曲》。”[7]158
《湘君与湘夫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无《迎神曲》和《送神曲》的痕迹。若分为两幕,必然割裂两篇间一唱一和的有机联系,不但使内容松散,而且影响审美效果。再说,湘君与湘夫人的唱词都那么长,是难以一气呵成的;若各自从头至尾一气唱完,不但表演者难以得到喘息的余地,而且会使表演呆板单调。
按林先生的看法,迎神的是湘夫人,送神的是巫,而作为男主角的湘君竟然隐身匿迹,没有出场,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原《湘夫人》篇中的“予”就是湘君的自称,捐袂、遗褋的也是湘君而不是巫。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一节是湘君的内心独白:他憧憬着有朝一日在九嶷隆重欢迎湘夫人的到来。并非湘夫人“召了巫去,在水里筑了一个富丽的行宫”。由于并没有相遇,也就不存在湘君与湘夫人偕逝升天而去的情形。
《九歌》系多角色演唱的唱本,而“不同角色的区分有助于文本解读”。只有如此,“诗歌的脉络才清楚,意义才连贯,我们也才能领悟娱神歌舞的诙谐多趣”[9]69。出演《湘君与湘夫人》的,不仅有扮演湘君的男巫和扮演湘夫人的两位女巫,还应有扮演“远者”和“下女”的男巫、女巫。各版本中原有的《湘君》是湘夫人的唱词,《湘夫人》则是湘君的唱词。主演《湘夫人》的应该是饰湘君的男巫,而不是“巫自己”。
说《湘君》是湘夫人的唱词、《湘夫人》则是湘君的唱词,这还可以通过文本分析得到如下依据:
原《湘君》篇的演唱者称呼对方“君”(“望夫君兮未来”),其侍从为女性(“女婵媛兮为余太息”),其情感表现为哭泣(“横流涕兮潺湲”),这些都适合女性的一般特征和言行习惯,故主演者为饰湘夫人的女巫;而原《湘夫人》篇演唱者则称呼对方“帝子”“公子”“佳人”,这些称呼合乎作为尧女的娥皇、女英的身份与性别,情感表现为发愁(“目眇眇兮愁予”),这些都适合自制力较强的男性的言行习惯,故主演者是饰湘君的男巫。
从所赠物品看,女赠男以玦、佩,男赠女以袂、褋,比较合乎礼仪。“玦”的一种意义为“佩玦”,另一种意义为“戴于右拇指助拉弓弦之器,俗称扳指”。不论所指是其中哪种物品,都适合男子佩戴、使用。“古代君子,必佩玉”(《礼记·玉藻》)。《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范曾“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
舜在九嶷,湘夫人在洞庭。湘夫人企望着湘君“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这也是符合传说中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的。
(二)关于《山鬼》和《国殇》
林庚说:“《山鬼》《国殇》均为单纯一人之辞,而其余七篇则错杂变化,类如戏剧的表演,它们所以原是两个类型的作品。”[7]134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
文本分析表明,从形制看,《山鬼》《国殇》也都是为多角色演出而创作的唱词,其中不同角色的化妆、道具与唱词都不相同。《山鬼》篇中,扮演山鬼的巫“被薜荔兮带女罗”,而娱神的巫则“被石兰兮带杜衡”;其中的“子慕予兮善窈窕”一句又可进一步说明,表演者中既有“子”(“你”,指娱神的巫),又有“予”(“我”,即山鬼)。就《国殇》而言,前四句写两军交战时“士争先”的场面,应是众将士齐唱共舞;后续六行以特写手法刻画一位驾驭战车的武士在“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的情况下顽强奋战的情形及战后惨烈的结局,应是独唱独舞;接下来四句写战士们“身首离兮心不惩”的豪气,参加歌舞的应是众将士;最后四句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以及《礼魂》是祝颂之辞,用以歌颂、抚慰为国死难将士的英灵,“歌舞者应是迎神或领祭的巫”[10]70。
由此可知,《山鬼》《国殇》和其他各篇一样,决非“单纯一人之辞”。
(三)《九歌》英译的形制预设
一般说来,中国的典籍,包括奏折、条陈、诗赋、楹联、文告、请柬、碑文等,都各有形制,翻译的时候有必要加以审度。辨明源文本的形制之后,译者就可以根据目的语文化在审美、行文习惯、语篇建构等方面的特征和取向,预设出适当的目的语文本的形制。
根据以上辨析、研究,新的英译《九歌》的篇目编排可预设为:HymntotheSovereignoftheEast(《东皇太一》),HymntotheLordofCloud(《云中君》),TheLordandLadiesoftheXiangRiver(《湘君与湘夫人》),SongtoFatetheGreat(《大司命》),SongtoFatetheMinor(《少司命》),HymntotheSunGod(《东君》),SongtotheCountoftheYellowRiver(《河伯》),SongtotheGoddessofMountains(《山鬼》),EulogyontheMartyrsoftheState(《国殇》),将《国殇》的尾曲《礼魂》译为Epilogue——TributetotheHeroicSouls。
考虑到英译的可接受性问题,《九歌》的文本形式可预设为:每篇划分出不同角色的唱词,并在每段唱词前加上诸如“(Sing Fate the Great Incarnate)”“(Sing the wizard as usher)”等说明性文字加以交代。
和其他篇章一样,《湘君与湘夫人》中不同角色的唱词也应是相互交错的。其文本形式可有两种不同预设:其一,像其他篇章一样,依次编排不同角色的唱词,这样,九篇的体例一致,且相互呼应的唱词相距较近,易于激发观众或读者的审美愉悦;其二,考虑到文本在流传中的特殊性,可以基本上保留“湘君”与“湘夫人”相对独立的原貌,根据对唱的次序,将原有两篇的唱段分别按单数系列(1,3,5……)和偶数系列(2,4,6……)进行编码,这样,既能让读者明白对唱的顺序,又可以留下文本整合、变迁的痕迹。
五、结语
以上论证说明,《九歌》原本只有九篇,其中的两篇各被误分解为二,从而多出了两篇。《湘君》与《湘夫人》本来同属于一篇;《国殇》与《礼魂》本来也同属于一篇,《礼魂》是《国殇》的尾曲。
从形制看,与《九歌》的其他篇章一样,《湘君与湘夫人》及《国殇》皆系由多角色演唱,“不同角色相互唱和”[10]68。
《九歌》的篇数等有关形制的论证说明,在典籍英译中,形制的辨析、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中的有关描述仅包含了形制辨析和研究的一些方法,绝非包罗万象。文本、文化等因素不同,方法也不尽相同,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文制宜。
典籍英译应反映典籍研究的最新成果。译者应在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按最新的发现和最可靠的学术见解对待《九歌》的形制与内容,使英译在对源文本的认识与解读方面成为集大成之作。上文有关《九歌》形制的预设、内容考辨以及篇目英译等等,仅可视为对复译或英文本修订的建议。
在《大中华文库·楚辞》英译的过程中,笔者因循旧说,采信了《九歌》共有十一篇的主流见解。以上论证说明,所采信的见解是错误的。笔者在此谨向楚辞学界、典籍翻译界和广大读者致歉,并希望译者、读者引以为戒,对典籍英译中的形制研究予以更多的关注。
注释:
①“此”指《山鬼》——笔者注。
②有人说,这不是臆测,唐代欧阳询、宋代米芾所书写的《九歌》里就没有《国殇》《礼魂》二篇。然而,其中隐含的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有可能是由于书法家出于某种考虑而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将它们收入,绝不能据此断定《九歌》中没有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更具说服力的应是年代更久远、影响更重大的版本,例如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及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等等。它们都是包含了上述两篇的。
③“他们”指山鬼、少司命等。
[1]卓振英. 汉诗英译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金开诚. 屈原辞研究[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3]高亨. 上古乐曲的探索[J]. 文史哲,1961(2):39-47.
[4]王冰,王丽娟. 齐国《韶》乐追根溯源[J]. 管子学刊,2012(4):52-55.
[5]黄凤显. 屈辞体研究[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6]汪瑗. 楚辞集解[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7]林庚. 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朱熹. 楚辞集注[M].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
[9]卓振英. 典籍英译中的考辩——以楚辞为例[J]. 中国翻译,2005(4):66-70.
[10]卓振英. 汉诗英译论纲[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ASurveyoftheFormativeNormsintheTranslationofClassics:IllustratedwithCaseStudiesofTheNineHymns
ZHUOZhenying
(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There have been disputes over the number of pieces inTheNineHymns,which center on the following issues:Is the figure “nine” of virtual or actual reference? If it actually refers to the number,how should the eleven pieces be integrated? The present paper,by means of description,case study,literature review and text studies,testifies that there are originally nine pieces inTheNineHymns,thatSongtotheLordoftheXiangRivershould be merged withSongtotheLadiesoftheXiangRiver,and thatTributetotheHeroicSoulsis the epilogue ofEulogyontheMartyrsoftheState. Furthermore,it expounds that,as part of the research in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s,formative-norm stud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verification of the number of pieces inTheNineHymns;formative-norm studies
H315.9
A
2095-2074(2015)02-0062-07
2014-07-26
卓振英(1945-),男,广东陆丰人,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