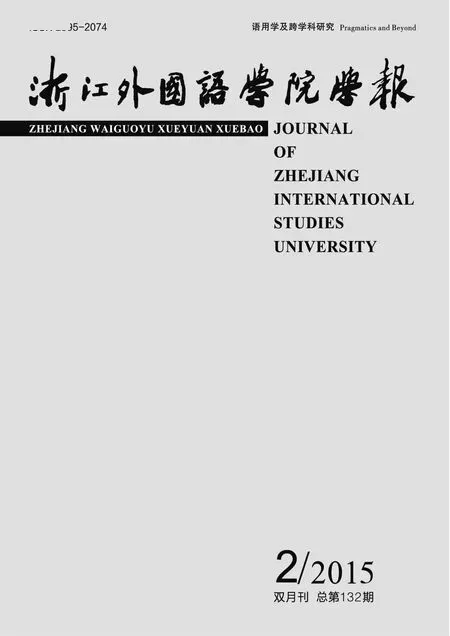京师同文馆创办之前士大夫阶层对外语学习及西方的认知
2015-01-31张美平
张美平
(浙江树人大学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15)
京师同文馆创办之前士大夫阶层对外语学习及西方的认知
张美平
(浙江树人大学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15)
任何一场社会变革,必定以思想启蒙为先导。魏源等启蒙思想家相继发表了关于外语学习和翻译的言论,对奕等洋务运动领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奕等人在中西交涉中,发现所接触的外夷并非全是来自化外之邦的“蛮夷”之辈,是可以学习和打交道的。因此,这些士大夫对外语学习和西方的正确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京师同文馆的创办。
京师同文馆;外语和翻译;外夷;西方认知
一、前言
创办于同治元年(1862)的京师同文馆(以下简称同文馆)是近代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后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外国语学堂,是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文馆创办之前,以魏源、冯桂芬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相继发表了关于外语学习和翻译的言论。这些言论对同文馆的创办者奕等为代表的洋务运动领袖或多或少地产生过影响。而且,奕等人对西方也有独特的见解。他们在中西交涉中,发现所接触的外夷跟历史上强弓劲矢的“化外之民”或称“蛮夷”,多少有些不同,是可以学习和打交道的。
这些封建士大夫关于外语学习和西方的言论和见解成为同文馆创办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虽然同文馆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成果密集,但对作为同文馆创办的先导因素——士大夫阶层对外语学习及西方的认知鲜有较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二、近代启蒙思想家关于外语学习和翻译的言论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遇惨败,暴露了敌强我弱、技不如人的窘况,“唤起了中国知识界的觉醒”[1]92,使得“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2]35成为开明士大夫的共识。启蒙思想家魏源、王韬、郭嵩焘、冯桂芬等人陆续发表的关于外语学习和翻译的言论,对同文馆的成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魏源:“立译馆、翻夷书”
继林则徐组织编译《四洲记》(1841)之后,陆续有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梁廷枏的《海国四说》(1846)、姚莹的《康輶纪行》(1846)、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8)、何秋涛的《朔方备乘》(1860)等大力鼓吹了解海外情势和中外关系的新著新作面世,表现出了中国人最初的世界意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在《四洲记》基础上经多次修订和扩充而成的一百卷《海国图志》,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世界史地著作。
作为最早明确提出学习西方的先知先觉者之一,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的目的在于对身处固步自封大环境中的封建士大夫进行西学知识的启蒙。他从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的要求中,概括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师夷长技以制夷”。他在《海国图志·原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3]207魏源所谓的“师夷”,即是学习西方强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2]9所谓“制夷”,就是“以守为战”,克敌制胜。
魏源深知“师夷”“制夷”,就得先“悉夷”,掌握沟通媒介,即外国语言文字,才能了解西方列强的历史地理、风俗民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2]35。 “立译馆、翻夷书”是当时实现“悉夷”的重要路径。魏源在《圣武记》中陈述了“立译馆”的理由:“夫制御外夷者,必先洞夷情。今粤东番舶,购求中国书籍转译夷字,故能尽识中华之情势。若内地亦设馆于粤东,专译夷书夷史,则殊俗敌情,虚实强弱,恩怨攻取,瞭悉曲折,于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于驾驭岂小补哉!”[2]518外夷借助翻译,对中华之情势了然于胸。所以,为了“制御外夷”,必须“洞夷情”,设馆译书。这样,译书→悉夷→制夷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魏源的这一思想远比那些“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人情平日置之不讲,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若雷霆”[4]10的封建士大夫高明。
魏源“立译馆、翻夷书”的建议,表明其由注重器物的学习,逐步扩展到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学习,使得“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成为一个可具体操作的措施。关于魏源的学术地位及在思想界的影响,邓嗣禹(Ssu-yü Teng)说他“几乎可以与十七世纪的顾炎武和十八世纪的戴震相媲美”[5]29。钱存训(Tsuen-Hsuin Tsien)说:“半个世纪以来,《海国图志》是了解外国情形的最具权威性的书籍,在中日两国拥有大量的读者。”[6]315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载体,《海国图志》还被同文馆等近代新式学堂采用为教科书,借助学生这一媒介,其传播效应不言而喻。
(二)王韬:“设立译馆”
近代思想界提出设立外语学堂之动因滥觞于启蒙思想家王韬“设立译馆”①的主张。1849年,王韬赴上海,受雇于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Medhurst)所办的墨海书馆,协助翻译宗教和科学书籍,广泛接触西学。1862年,他因向太平军献策,遭清廷通缉,遂逃亡香港。在港期间,王韬协助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尚书》《左传》等中国经书。王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西人接触,和他们合作翻译书籍,接触到大量西方先进的自然和人文社科知识从而眼界大开。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7]26,封建士大夫们守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时,王韬却敏锐地发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提出向西方强国学习,“仿行西法”,“以其所长,夺其所恃”[7]27。针对清政府昧于西方情势,他提出应“备览西事,谙熟洋务”,即“设议院、广贸易、开煤矿、筑铁路、兴织纴、造轮船、办学校”[8]1444。为实现其主张,王韬提出国家应重视翻译,“设立译馆”,培养“以备他日之用”的外语翻译人才:
西人凡于政事,无论巨细,悉载日报,欲知洋务,先将其所载各条一一译出,日积月累,自然渐知其深,而彼无遁情。国家亦当于各口岸设立译馆,凡有士子及候补人员愿肄习英文者,听入馆中,以备他日之用。果其所造精深,则令译西国有用之书。西国于机器、格致、舆图、象纬、枪炮、舟车,皆著有专书,以为专门名家之学,苟识其字、通其理,无不可译。如此,则悉其性情,明其技巧,而心思材力之所至,何不可探其秘钥哉?将见不十年间,而其效可睹已。[7]26
王韬主张,“欲知洋务”,必须将西人报刊上的相关资料一一译出。同时,国家应在各通商口岸设立译馆,招选“士子及候补人员”学习西方语言文字。深通西文不仅可以“通彼此之情”,而且可以从事西人书报翻译。经过日积月累,自然就能更彻底地了解西方,从而避免“于其性情日益隔阂,于其国政、民情终茫然罔有所知……一旦交涉事起,局促无据,或且动援成例以为裁制”[7]25的尴尬。
王韬“设立译馆”的观点形成于“国家方讳言洋务”的19世纪50年代。虽然没有具体的措施,但观念很超前,这说明他对外语作用的认知走在了同时代其他士大夫的前面,成为后来启蒙思想家系统提出创办外语学校的先声。
(三)郭嵩焘:首倡设立外语学堂
近代中国第一次比较明确、具体地提出设立外语学堂的是后来成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被李鸿章称为“学识闳通,志行坚卓”[9]7的郭嵩焘。1852年,郭嵩焘为曾国藩筹集军饷,途经上海,参观了外国人创办的墨海书馆。在那里他遇见在馆翻译西书的李善兰和王韬,他还接触了致力于传播福音和西学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等传教士,并得到了他们所著的西书和刊物,眼界大开,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1858年,郭嵩焘了解到俄罗斯曾将一批极有价值的俄文书籍赠送清政府,但由于找不到通晓俄文的译员,这批书籍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今此书目所载,如舟师记、舟师信函、水师名将传、兵技战策、炮法……可以知海外诸国之虚实。倘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10]188他认为,这批西书如能顺利译出,不仅有利于海防和国家安全,而且对于国计民生也有很重要的价值。他了解到外夷已开始千方百计地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如俄罗斯早在雍正五年(1727)就派青年学子来国子监“习满汉语言文字”[10]191,就连当前的敌人“英夷”也“在广东、上海率以重赀雇中国读书人,审正文字声音”[11]670,这使他的紧迫感与日俱增。于是,郭嵩焘于1859年将多年来的思考以《请广求谙通夷语人才折》之名具疏上奏,正式提出创办外语学堂的建议:
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中国不能钩致夷人,自可访求蒙古汉人之通夷语者。广东、上海与诸夷相接,恰克图、库伦等处与俄夷相接,语言文字积久谙习,当不乏人。合无仰恳皇上饬令江广督臣、黑龙江将军、库伦办事大臣,推求此等人才,资送入京。命理藩院岁蠲银数千两,给之薪米,使转相传习,亦可以推考诸夷嗜好忌讳,以施控制之略。[11]670
可见,郭嵩焘的认识在魏源、王韬等人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推进。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比较明确、具体地提出设立外语学堂的主张,把“通知夷情”与外语人才的培养结合起来,而且有具体的措施跟进,强调不能依赖夷人,要通过多种途径寻觅教习,培养“熟悉其语言文字者”,是为其一。 其二,把外语学习与“御夷”联系在一起,认为熟悉其语言文字为“今日御夷之窍要”。其三,除了传习夷语以外,还要学习西方文化,“推考诸夷嗜好忌讳”,将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结合在一起。这实为郭嵩焘的独特创见。
(四)冯桂芬:“设一翻译公所”
启蒙思想家冯桂芬在同治初年入江苏巡抚李鸿章幕府。他学养深厚,《清史稿》称其“自未仕时已名重大江南北”[12]13438。1860年,冯桂芬避居上海。此时,上海已是中西交往的前沿,华洋杂处,新与旧、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在此交融碰撞,给冯桂芬“出入夷场”提供了契机,“桂芬立会防局,调和中外杂处”[12]13438,负责协调中外联合镇压上海的太平军及其他行动。这段经历,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致使他对于外语在突破语言障碍中的作用,以及外语与西学关系的认识高度,远超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是年,冯桂芬将他的认识和见解写进了著名的《采西学议》一文中:
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闻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进书千余种存方略馆,宜发院择其有理者译之。……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与焉。三年之后,诸文童于诸国书应口成诵者,借补本学。诸生如有神明变化,能实见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请赏给举人。如前议,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矣。[13]210
冯桂芬首先阐述了学习和掌握西学,即“采西学”的具体路径是在广东、上海设一专习西学的新式学堂——“翻译公所”。其操作步骤是考选十五岁以下的颖悟文童,住校学习。聘请外国教习教授外国语言文字,并教授经史及算学诸学。这里,冯桂芬特别强调“自不可不学算”,因为算学是学习和掌握西方科技、“制洋器”的基础。他明确主张“师夷人”,这是“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门考求”[4]22的封建士大夫所达不到的境界。其次,他建议翻译近代西方科技书籍,举凡天文、算学、物理、化学、轮船、火器等,只要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书籍,均在译介之内。借助这些书籍,对中国民众进行西学补课,以达到更新知识、扩充视野、转变思想的目的。再次,规定了学制。完成三年的学业后,优秀学生应再补修应试科举所需的内容,即冯桂芬所称的“本学”,并赏给“举人”等功名。
冯桂芬言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创办“翻译公所”不以学习外国语文为终极目的,而是以之作为进一步研究西学的工具。因此,冯桂芬设立“翻译公所”方案的设计,比魏源、王韬的“立译馆”的主张和郭嵩焘的创办外语学堂的方案更丰富、更具体,更具操作性。
魏源、王韬等“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先觉者提出设立译馆与创办外语学堂等主张表明,自鸦片战争开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已经有一部分开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外语学习在“师夷”“制夷”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最先把突破语言障碍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结合起来,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奕、李鸿章等人设立同文馆等外国语学堂的主要认知依据。虽不能说同文馆的创办完全是受了这些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但舆论引导的作用还是明显的。学者苏精认为,1861年奕奏呈的《通筹善后章程折》中,“关于学习外国语文一条的内容,多与郭嵩焘的建议相同”[14]2。另一学者孙子和也说:“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之雏形,已具见于魏源之思想也。”[15]141862年,奕在关于创办同文馆的奏折中提及:“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16]37他们的这点认识,是被洋鬼子打出来的;同时,也是国内有识之士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人反复呼吁促成的[17]78。而且,在有关学校事务的决策方面,奕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领袖多有联系,互有影响[16]10。李鸿章设立上海同文馆的奏折的母本就是冯桂芬的《采西学议》《制洋器议》和《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就在同文馆成立五年后,奕在上呈朝廷的奏折中云:“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16]44可见,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一直受到奕等洋务重臣的推重。
三、开明士大夫对“夷人”的认知
晚清时期,人们普遍以“夷”来指称与外国有关的人和事,如称“英国人”为“英夷”,称与外国交涉的事务为“夷务”等。根据辞海,“夷”有三种意义:一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亦称“东夷”;二是用以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三是用以称外国人[8]782。古代文献中的“夷”,更多的是指少数民族,如北宋王钦若等著的《册府元龟》载,“东方曰‘夷’,被发而文身。南方曰‘蛮’,雕题而交趾。西方曰‘戎’,被发而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而穴居。”[18]11237这些少数民族被视为尚未开化、文明落后、仍与禽兽为伍的族群。《新唐书·突厥列传》云:“礼让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兽夷狄也……圣人饮食、声乐不与之共,来朝坐于门外,舌人体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19]4585后来,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步入近代社会,“夷”的概念普遍由指称少数民族转而指向非华夏的域外文明。
“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其对外的交涉,总是把外国人当作夷狄看待,不承认他们和中国有对等的地位。”[20]10近代以降,中外交涉事件大幅增加。在同夷人的实际接触中,国人对他们的认知也在不断变化。对他们的态度,由当初的傲慢、轻视转而视不同情形予以区别对待。清政府的地方大员中,对夷人认知较深刻的当属两广总督林则徐。他在查禁鸦片、处理夷务的过程中,相信夷人中也有“奸夷”和“良夷”之别:“至夷馆中惯贩鸦片之奸夷,本大臣早已备记其名,而不卖鸦片之良夷,亦不可不为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责令呈缴鸦片,并首先具结者,即是良夷。本大臣必先优加奖赏,祸福荣辱,惟其自取。”[21]244林则徐将“奸夷”和“良夷”进行区别对待的务实态度,有利于对敌斗争,最终取得了禁烟斗争的胜利,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在对待夷人的态度上,持同样深刻认识的还有魏源。他在《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中说:“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故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兽然,以不治治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乎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察物情,贯穿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为夷狄乎?”[2]1889虽然魏源仍称洋人为“夷”,但强调与传统中国所惯见的“夷狄”迥异,是“奇士”“良友”。
在中央政府这一层面,对“夷人”持务实态度的代表性人物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恭亲王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军队侵入北京,皇帝西狩热河,奕留下来代表政府与侵略军周旋。正是这样的与“夷人”直接交往和接触的经历,使得奕对他们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现他们也有正面的地方。法国领事馆的翻译美里登(De Meritens)曾问奕:“你认为我们是蛮夷人吗?”奕回答:“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从前与你们没有接触,所以没有定见。但现在,我确实不这样认为。”[22]94
然臣等揆时度势,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佛、咪(按:指法、美)从而阴附之。窃谓大沽未败之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以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就两者轻重论之,不得不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23]5754
上述引论的中心意思是夷人讲究信用,与以往“残虐性情”“未知王化”[2]1889的夷狄不同。虽然“夷祸烈极”,但可用不同的“御夷之策”。他还以三国时蜀国对吴国使用的策略作比,认为夷人也是可以打交道的,“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仅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23]5741由此可见,相较于那些“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4]23的满汉官僚,奕对外夷的认知有了相当大的不同。可以说,他对外夷“似与前代之事稍异”的认识和林则徐的“良夷”说、魏源的“良友”与“奇士”说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奕等洋务领袖有了这种新认识,才准备以认真,甚或是以较平等的态度对待曾被称为“天朝皇帝所任命的官宪脚下的尘埃”[24]150的外夷了。
四、同文馆的创办
注释:
①王韬的“设立译馆”与魏源的“立译馆”是不同的,王韬是指设立外语培训机构,魏源是指设立翻译馆,从事译书事务。当然,译馆也有可能有培训的功能,但魏源似乎未专门提及。
[1]黄运红. 晚清京师新式学堂教师聘任初探——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5):91-96.
[2]魏源.魏源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1.
[3]魏源.魏源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姚莹.复光律原书[M]//东溟文后集:卷八. 同治六年安福县署刻本.
[5]Teng Ssu-yü,Fairbank J 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6]Tsien Tsuen-Hsuin. 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J].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954,13(3).
[7]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8]夏征农.辞海(缩印珍藏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9]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李鸿章全集1[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10]郭嵩焘.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M].台北:清水印刷厂,1972.
[12]赵尔巽.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4]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师生[M].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
[15]孙子和. 清代同文馆之研究[M].台北:台湾嘉新水泥公司,1977.
[16]高时良. 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17]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8]王钦若. 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9]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M].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20]吴宣易. 京师同文馆略史[J].读书月刊,1933,2(4).
[21]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2]王宏志. 翻译与文学之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23]贾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Z].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1930.
[2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 张汇文,等,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2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 北京:三联书店,1957.
[26]Martin W A P(丁韪良). The Lore of Cathy [M].Fleming H. New York:Revell Company,1912.
[27]欧阳恩良,翟巍巍. 从“鴃舌之音”到京师同文馆的建立——近代中西语言接触看清廷观念的转变[J]. 甘肃社会科学,2008(1):56-59.
Scholar-officials’KnowledgeofForeignLanguageLearningandtheWesternersPriortotheEstablishmentofthePekingT’ung-wenKuan
ZHANGMeiping
(ForeignLanguageSchool,ZhejiangShurenUniversity,Hangzhou310015,China)
Any social reform is preceded by an ideological campaig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Wei Yuan and some other Enlightenment ideologists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ranslation,which had some influence on Yi Xin and some other leaders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hile dealing with the westerners,Yi Xin found that not all the foreigners they had met were barbarians from uncivilized nations,but there were some they could have dealings with and learn from. So the right knowledge of these scholar-official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westerners promoted,to some extent,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king T’ung-wen Kuan.
the Peking T’ung-wen Kuan;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ranslation;foreigners;western cognition
H319
A
2095-2074(2015)02-0055-07
2014-11-07
张美平(1964-),男,浙江遂昌人,浙江树人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