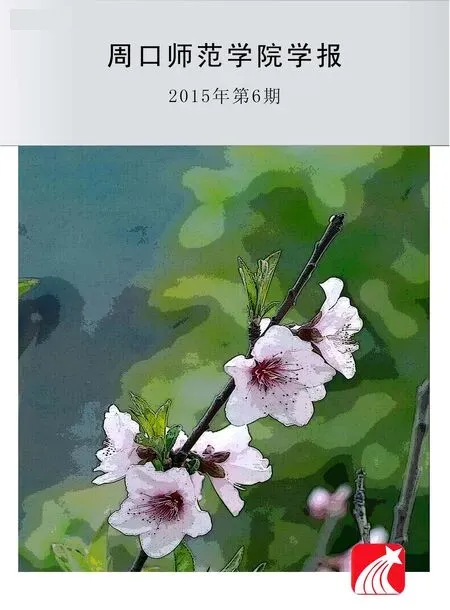贯通与独特:先秦时期河汾诗歌的女性审美
2015-01-31郝建杰
郝建杰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太原030031)
大量事实证明,人物审美具有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地域文化环境和时代潮流的变化而变化。西周至春秋时期,华夏族人聚居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处于内涵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圈,因此形成了大致相同或相近的人物审美观念。然而,由于地域文化具体内涵的差异,其人物审美观念在大体一致的情况下又互有差别,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一、女性的手部之美
女性的本相美表现在诸多方面,而手部审美独具魅力,诗歌中女性手部的不同审美形态和表现艺术反映了审美观念的地域性特征。《葛屦》云:“掺掺女手,何以缝裳。”《说文解字》:“攕,好手貌。《诗》曰:‘攕攕女手。’”[1]251“好手”仅笼统言之,至于何为“掺掺”,汉杨雄《方言》的解释要比《说文》明确得多,其云:“掺,细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细貌谓之笙,敛物而细谓之揫,或曰掺。”[2]122“掺掺女手”即女子的纤纤细手。秦、晋指周代的秦国、晋国,而魏地恰在二者之间。由此可见,魏地人的女性手部审美强调手形、手指纤细的特点。诗中那位缝制裳服的女子之所以被同情,正是因为缝制工作有损于她的纤纤细手。《国风》尚有其他诗篇描写女性手部之美,如产生于河淇文化区的《卫风·硕人》:“手如柔荑”。柔,谓柔嫩。荑,为白柔春天启土冒尖之貌。此处强调女性手部皮肤的柔嫩白皙、指尖的尖细、指腹的饱满匀和。就二者的审美内容而言,魏人将女性手部与缝制裳服相联系,取其纤细灵巧善制裳服的实用价值,而卫人则超越功利之心,单纯欣赏。可见在审美理想上,魏人在审美时兼重实用,卫人则纯粹审美而毫无功利色彩,二者区别鲜明。
就艺术表现方法而言,“掺掺女手”属写实之笔,而“手如柔荑”则使用了比喻手法。这直接造成了艺术表现力的差异:“手如柔荑”使手部之美更加形象且富于艺术想象力和艺术张力,而“掺掺女手”则简括质实,显得单薄。一般而言,采用不同艺术表现方法的直接原因是艺术思维方式的差异,而造成艺术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之一就是诗人审美观念的差异,而诗人审美观念的差异又是其所在文化圈层中现实审美观念的一种变相。从上述关于女性手部审美的不同形态和艺术表现手法可以推知,魏地人与卫地人在审美观念上存在差异,魏地人简洁质实而拙于想象,而卫地人则超脱实际而长于想象。
二、女性的仪容之美
女性的姿态、仪容之美是周代诗歌表现的重点,魏地注重女性安舒而不失谨慎的内敛式姿容美,具有与其他地域不同的特点。诗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提提,通作媞媞、徥徥、姼姼、折折[3]319,是秦晋一带的方言,《方言》:“自关而西,凡细而有容谓之嫢,或曰徥。”[2]122毛《传》:“提提,安谛也。”[4]757《说文解字》:“徥徥,行貌也。”[1]43又,“姼,美女也”[1]260。《礼记·檀弓》:“吉事欲其折折尔。”[5]2792郑玄《注》:“安舒貌。”[5]2792由上述可知,“提提”是状美女行走时步履安舒的姿态。“宛然左辟”为一种仪容之美。辟,是“便辟”之辟,杨伯峻《列子集释》引唐殷敬顺《列子释文》:“便辟,恭敬太过也。”[6]209《大雅·板》:“无为夸毗。”《尔雅·释训》:“夸毗,体柔也。”[5]5638郭璞《注》:“屈已卑身以柔顺人也。”[5]5638邢昺《疏》:“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却为恭,以形体顺从于人。”[5]5638从诗的内容可知,“好人”显然属贵族身份。可见,贵族女性安舒的步态和柔和恭顺的仪容切合魏人的审美习惯。《诗经》中亦有其他描写贵族女性姿态之美的诗歌,如产生于河淇文化区的《鄘风·君子偕老》:“委委佗佗,如山如河。”毛《传》:“委委者,行可委曲踪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无不容,河无不润。”[4]661《尔雅·释训》云:“委委佗佗,美也。”[7]5632郭璞《注》:“皆佳丽美艳之貌。”[5]5632邢《疏》引三国魏孙炎《注》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长之美。”[7]5632综此,“委委佗佗”,是形容该妇女雍容自得且步态优美之貌。又如产生于河洛文化区的《郑风·有女同车》:“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将翱将翔”是对“彼美孟姜”轻捷翩跹的步态之美的描写。又如淮水文化区的《陈风·东门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不绩其麻,市也婆娑。”“婆娑”是对子仲之子活泼舞姿的描写。又如《陈风·月出》:“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舒夭受兮,劳心惨兮”。马瑞辰曰:“窈纠犹窈窕,皆叠韵,与下忧受、夭绍同为形容美好之词。”[3]417产生于汉水文化区的《周南·关雎》有“窈窕淑女”之句,《方言》:“窕,美也……陈、楚、周南之间曰窕。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或谓之窕。”[2]116又曰:“秦、晋之间……美状为窕……美心为窈。”[2]116郭璞注“窈”曰:“言幽静也。”[2]116又注“窕”曰:“言闲都也。”[2]116如此,则“窈”即是女子美好之意,是一个笼统的说法。“窈宨”还有更为具体的内涵。毛《传》:“窈窕,幽闲也。”[4]570如果结合诗意,则“窈窕”当指女子幽静的姿态美。由此可见,魏地以女性安舒而不失谨慎的姿态为美,表现为内敛式的姿容美,而卫地、郑地则强调姿态的动感,对表现式、张扬式的姿容美更钟情。至于陈地似乎更为复杂些,一方面有舞蹈时近乎癫狂的状态,凸显对活泼之姿态美的喜爱,一方面又有月下的幽静之姿态美的品赏。陈地的女性的幽静之美显然与周南地区有贯通性,淮水文化区和汉水文化区地域毗连、文化相近的缘故。
三、女性的装饰之美
周代诗歌中的女性装饰美同样具有地域文化内涵,魏地贵族女性装饰美的特点是俭朴而不失高贵。诗云:“佩其象揥。”象揥是一种用象牙磨制而成的簪子。在《诗经》时代,女性注重装饰美属于普遍现象。如《鄘风·君子偕老》:“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扬且之晳也。”就诗中装饰品种类而言,显然前者少而后者多;就艺术表现而言,魏地“好人”之装饰美的描写像一幅简笔画,粗见点画而已,而卫国妇人之美的描写更像工笔画,甚为详细。若考察二者一简一繁的文化原因,则仍与魏地尚简洁质实而卫地人尚精致丰赡的审美习惯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好人提提”一语还可见出魏人以女性体形娇小为美的审美观。清钱绎《方言笺疏》:“凡好与小义相通。孟喜《中孚注》:‘好,小也。’《广雅》:‘细,小也。好人媞媞’即细而有容,言行步之安舒也。”[2]123此处的“好”,已非普遍意义的容貌之美,而是特指体形娇小之美。从诗意可知,“掺掺女手”者与“好人”非指同一人。以常理揆之,“掺掺女手”必为体形娇小者所有。如此一来,“好人”与“掺掺女手”显示出魏人的一个共同的审美心理,即女子以娇小有容为美。这一审美观念在《诗经》时代是具有特色的。
与魏人不同,晋人对女性体形、体态的审美标准是硕大丰满。《唐风·椒聊》:“彼其之子,硕大无朋。”“彼其之子,硕大且笃。”硕大,指妇人体形硕大丰满。《尔雅·释诂下》:“笃,固也。”[7]5597可见,在晋地至少有一种女性审美标准是体形硕大丰满且体格健壮结实。以妇女体形硕大丰满为美的观念,存在于周代的诸多地域。如《卫风·硕人》:“硕人其颀”“硕人敖敖”。又如《陈风·泽陂》:“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又如产生于泾渭文化区的《小雅·白华》:“念彼硕人”。又如《车辖》:“辰彼硕女,令德来教。”可见,在卫地、陈地、晋地、西周王畿,这一面积广大的地域,均有一个时期存在以女性的硕大丰满为美的观念。同以硕大丰满为美,而各地也有所差别,如卫人强调“颀”“敖敖”,即体形修长。陈人则强调“卷”。“卷”即“婘”,美好貌;《太平御览》引《韩诗》曰:“有美一人,硕大且 ”[8]75。西周王畿之地则在强调女子体形丰腴之时,增以美好品德。晋人不强调“卷”“俨”“颀”“敖敖”之类,也不强调“令德”,而是强调“无朋”“笃”。结合全诗内容,晋人以成熟女性的硕大丰满、体格固实为美且注重实用的审美观念来源于对妇女生育能力的重视,是扩大人口生产的功利目的的表现。卫人、陈人则不太强调实用功利性,而基本上属于纯粹审美的超脱境界。西周王畿人则注重内在修养和美善之德。
四、新娘之美
新娘审美是周代突破地域界线的女性审美对象之一,虽然具有普遍文化意义,但在不同地域中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诗经》中关于新娘的诗篇为数不少,《唐风·椒聊》《唐风·绸缪》《周南·桃夭》《卫风·硕人》《郑风·有女同车》《齐风·东方之日》等皆是。可见,晋地、周南、卫地、郑地、齐地均存在歌唱赞美新娘子的风俗。关于《椒聊》中“彼其之子”审美的地域内涵如前述,此处讨论《唐风·绸缪》一诗。诗云:“今夕何夕,见此粲者。”粲者,即美女,在此诗中指俊俏的新娘。单纯以“粲”形容物之美,在《诗经》中并不鲜见。如《郑风·缁衣》《羔裘》《唐风·葛生》《小雅·伐木》《小雅·大东》诸诗的“粲”皆为鲜明貌。“粲”也用来形容人物之美,如《绸缪》即是。另外,《国语·周语上》载密康公之母曰:“女三为粲”及“夫粲,美之物也。”[9]8密康公之母用“粲”称美女,而密国在今甘肃东部。由此可见,以“粲”这个词来指貌美女性的内涵虽不具体,然而至少是黄河流域一带的一个语言指称习惯。《桃夭》以“桃之夭夭”比新娘,较《绸缪》的“粲者”富于艺术想象。《东方之日》:“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以日月比喻美女,也较形象活泼。比较而言,上述诸诗对新娘之美的描写均相对简单,而《硕人》《有女同车》则不然。《硕人》:“硕人其颀,衣锦褧衣”“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诗中的“硕人”指卫国国君妇人庄姜,其时嫁于卫国。诗歌对庄姜的体形、衣着、手部、皮肤、领项、牙齿、发式、眉形、笑态、眼神等做了精细准确的传神描摹。《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诗写姜姓新娘嫁至郑国,新娘如花的容颜、翩跹的步态、佩带的玉饰、时尚的气质、恰当的表现等亦得到颇为传神的描绘。这种简单概括与细致精确的描写不是单纯的艺术手段的差异,而是诗人审美观念的表现,同时反映着各地审美文化的差异。人物审美的精细化和传神描写说明郑、卫两国人具有精细的观察力和艺术想象力。郑、卫之地处于当时华夏文化圈的中心区域,地势多平坦,交通方便,商业发达。商业的发达,必然要求城市娱乐文化的繁荣,社会风气的开放,在诗歌艺术方面,产生了独具特色的郑卫之音,《硕人》《有女同车》正是这种文化气候的产物。《有女同车》云“旬美且都”。“都”,本为都城之意,由于都城人的装束常成为引领国人审美观念,“都”因此被引申为美丽时尚的代名词,这正是都会文化的反映。周南位处南方,诗人自然受南方风物影响并具有浪漫气质,因此有“桃之夭夭,灼灼其花”之比。齐地位居东土,风尚活泼张扬,因此有“东方之日”“东言之月”之比。相比之下,晋国时为小国,又处于戎狄之间,崇尚节约简朴,因此对人物之美的关注很少,表现在艺术作品中也不详细精确而仅用简括之语。
由上述分析可知,表现在《魏风》《唐风》中的人物审美观念与魏、晋两地的地域文化和时代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与《诗经》中的其他地域诗歌中的人物审美观念相比,既存在贯通性,也存在独特之处。这说明魏、晋地所在的河汾文化区作为黄河文化圈的一部分,既有与其他文化区在文化上的相似性、一致性,又存在明显的区别,而这正是早期华夏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一个侧面反映。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钱绎.方言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嘉庆刊本,2009.
[5]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嘉庆刊本,2009.
[6]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尔雅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嘉庆刊本,2009.
[8]李昉.太平御览:第4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9]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