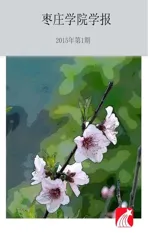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制度研究
2015-01-31高寒
高寒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1)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制度研究
高寒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1)
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制度的内涵出发,对制度进行理论与实践的两个层面的解读,希望找到目前制度建构的欠缺所在并加以完善。从而将这一原则性的规定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使得未成年人调查制度在实践中得以良好运行,避免制度流于形式。
刑事诉讼;未成年人犯罪;调查制度①
未成年人犯罪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的社会性问题,为了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挽救涉罪的未成年人,国外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已经从关注案件事实本身转化为调查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原因,以此从根本上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了关于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该制度对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的法律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制度基本内涵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制度,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可以根据情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进行调查,并且制作出书面的社会调查报告。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综合相关规定可以发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是围绕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展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是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以未成年人为核心,目的是通过社会调查的内容了解未成年人犯罪人格形成的原因,以此判定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并且根据调查内容对其适用有针对性的处遇,使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二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科学性。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是对未成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全面的了解,通过对未成年人所处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可以有效的对未成年人进行帮扶。通过科学的分析,从资料中找出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并且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估,从而作出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处置措施。
三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的结果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全过程。换言之,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抑或审理阶段都可以对引起未成人犯罪的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等进行调查。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制度的理论解读
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从研究与实践的情况来看,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理论解读。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制度的名称术语的解读
从我国少年刑事司法调查程序的制度发展历史来看,社会调查的用语应该源于《北京规则》。《北京规则》对于调查名称的英文原文表述是“social inquiry report”,按照字面通常翻译即为“社会调查报告”。其后,有关法律规定和规范性文件也都采用“社会调查机关”表述,以至于“社会调查”作为法律术语被不断地使用。于是,我国学术界与司法实务部门的众多观点也都采用了“社会调查制度”的用语。然而,将调查制度称之为“社会调查”并不恰当。第一,在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与解释中,仅最高人民检察院使用了“社会调查”的用语,而最高法发布的司法解释以及公安机关的相关规定,并未采用这一用语。第二,通过对于调查的实施主体、性质等的进一步分析可看出,所调查的内容是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社会情况,但调查的性质及主体并不是完全社会性的,用“社会调查”来限定公检法机关实施调查行为的性质并不能完全吻合。因而采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报告”或“调查报告”更加适宜。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实施主体的解读
明确调查制度主体,对于确立职责分工、保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制度的有效运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各种观点中,争论较大的是司法机关可否委托其他机关或团体、个人进行调查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明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权是不是司法权。如果调查权是司法权,那么司法权只能有司法机关行使,绝对不能够委托其他机关、团体或是个人行使;如果调查权不是司法权,那么委托其他机关、团体进行调查,或是以司法机关为主、依托其他机关和社会团体进行的方式就都是可行的了。对于司法权的认识,笔者认为可采这一观点:“司法权应界定为裁判权。在程序方面,司法权具有六个基本特征:被动性、公开和透明性、多方参与性、亲历性、集中性和终结性。”[1](P31)司法权的目的是作出终局性的裁决,为各方提供最权威的救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在特征上与司法权的特征并不契合,并且调查行为以及所形成的调查报告的目的是在适用强制措施,法官在量刑等方面起到参考作用,并不能达到作出终局性裁决的目的。因此,无论从特征还是目的等方面来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权都不是司法权。那么委托其他机关、团体进行调查,或是以司法机关为主、依托其他机关和社会团体进行的方式就都是可行的。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解读
对于是否应当将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未达成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从社会调查程序的目的出发,社会调查全面掌握涉案少年的个人情况,是为了使法院在定罪特别是量刑的时候,能够采用一种最有利于矫正少年被告人再社会化的刑罚执行参考,这种参考不具有定罪量刑依据的法律意义,所以,社会调查报告不是定罪量刑的证据”。[2](P754)持肯定说的则认为,调查报告满足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要求,应当被视为证据。[3](P68)也有观点认为,调查报告应为专家意见[4](P107)或者是鉴定意见。[5](P47)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调查报告不能被作为定罪的证据,但是可以成为量刑的证据。[6](P31)
对于调查报告的性质,我们认为应当坚持“参考说”的观点。因为调查报告是对未成年犯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它反映的是未成年的背景资料,而不是犯罪事实。目前我国并未建立品格证据这一规则,不能有悖于现行的法律规定,因此,不能将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只能作为司法机关办案的参考资料。[7](P46)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调查报告没有意义。在严格程序之下得出的详实的调查报告,可以作为移送案件与否、起诉与否、法官量刑的依据和参考。这是符合未成年刑事诉讼特殊规则的,体现出了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与处遇。
(四)调查报告作用与效果解读
观察发现,受制度理念接受程度不同及社会调查资源充裕程度不同等因素影响,我国不同地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率呈现较大差异。比如,在较早践行调查制度的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2013年1~6月,对93名涉罪未成年人全部开展了社会调查,适用率达到100%。河南省法院系统通过全面建立调查报告制度等机制对未成年被告人依法尽可能多地适用轻缓刑,未成年被告人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比例逐年上升。不过,这种非罪化、轻刑化、缓刑化的适用倾向使得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被误读为一种“照顾性”的制度,被异化为对涉罪未成年人轻缓出发的倾向性依据,[8](P129)而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的精神和重罪案件刑罚适用的更加复杂性、慎重性,对涉及重罪案件的未成年人被告人更应进行调查。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制度的完善
(一)以司法行政机关作为调查主体,由其指派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
其优势之处在于:(1)不仅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执行阶段也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的个人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将审判和执行良好衔接。(2)我国司法资源中公检法三部门工作繁重,人员不足,若再将社会调查这一任务负担于这三部门之上,效果不会理想。有人建议在司法行政机关下设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招聘组建专业的调查队伍,并且对调查员的培训和管理都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负责。[9](P99)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建议。
(二)建构调查员的诉讼权利
为了确保这一制度能够有效运行,应当明确调查员的诉讼权利。这其中,会见权和阅卷权是关键。因此,建议在制度层面明确调查员在调查过程中享有与涉罪未成年人(包括羁押)会见交流的权利和到办案机关查阅、摘抄、复制与涉罪未成年人有关的案卷信息的权利。当然,对于这些处于诉讼过程中的案件信息,调查员负有保密的义务。另外,建立调查员出庭规则。调查员的出庭规则可以考虑设置如下: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调查最后阶段出示,而且以调查员宣读调查报告的形式出示;在审判长的主持下,控辩双方围绕调查的主体资格,调查的方法、步骤、内容及其真实性和相关性进行发问;调查员应当回答控辩双方的提问,并就控辩双方对调查报告中有争议、矛盾或表述模糊方面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
(三)规范调查制度的制约机制
我国立法在这一领域的规定仍然缺失,不利于调查制度在全国的推广。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建立调查制度的监督机制并从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着手。司法监督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有权监督调查员的工作并且审查调查报告。对违反程序性规定的行为,应当予以纠正。其次,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应对调查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调查报告是随卷移送的,如果三机关认为调查报告不够全面或者内容有偏差,可以要求出具调查报告的司法机关进行补充调查或者自行调查。社会监督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权对调查组织的工作进行监督。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设置监督电话及意见箱,在官方网站上公布调查员的职能和权限,将调查工作的进程及时予以更新,接受社会监督。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制度作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其重要性已无需多言。在对制度进行构建时,应该有选择性与针对性地吸收外国先进经验,以我国社会与法制的现实情况为基础进行综合考量。
[1]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J].法学研究,2000,(5).
[2]徐建.青少年法学新视野[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3]吴燕,吴翎翎.少年品格证据若干问题初探[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5).
[4]罗芳芳,常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分析[J].法学杂志,2011,(5).
[5]王建喜.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背景调查制度的构建[D].复旦大学,2008.
[6]万扬.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研究[D].湖南大学,2013.
[7]郭欣阳.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性质及其在审查起诉中的运用[J].人民检察,2007,(11).
[8]蒋雪琴.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实践考察[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9]康黎.论被追诉人人格调查[J].西部法学评论,2012,(2).
[责任编辑:吕艳]
D915.3
A
1004-7077(2015)01-0078-03
2014-11-30
高寒(1989-)男,江苏徐州人,回族,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诉讼法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