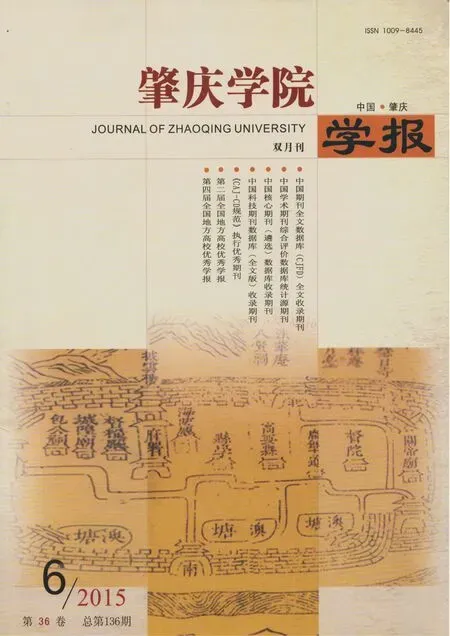《白鲸》的喜剧因素研究
2015-01-31黄永亮韩山师范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广东潮州521041
黄永亮(韩山师范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广东潮州 521041)
《白鲸》的喜剧因素研究
黄永亮
(韩山师范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广东潮州 521041)
大多数人更多注意到的是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的悲剧性,但对其喜剧因素却关注不够。事实上,书中的语言、人物、场景,乃至整部小说的谋篇布局都渗透着喜剧精神,与埃哈伯的悲剧形成了对照。叙述者以实玛利的幽默暗含对西方文化的抨击,悲、喜剧性的交错正是人类生存状况的写照。对以实玛利来说,喜剧精神成为他在逆境中的生存智慧。
喜剧因素;以实玛利;讽刺;智慧
一、引言
梅尔维尔的《白鲸》以气势磅礴的捕鲸故事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埃哈伯的角度来看,该小说是部悲剧[1]502,论者多因埃哈伯这个人物而强调作品的悲剧性。事实上这部小说不乏喜剧性的笔致。E.H.Rosenberry认为它的喜剧性和悲剧性对于理解故事的内涵具有同样的重要性[2]597。Wyn Kelley也指出它含有喜剧的成分[3]。从国内的研究情况来看,我国学者大多注重分析作者的悲剧思想[4]。近年来,国内关于《白鲸》的研究虽呈现多样化,但其喜剧性仍未得到重视,笔者尝试分析其喜剧性的具体表现和作用。
二、喜剧性人物和场景
作者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刻画了斯德布、季奎格、独臂船长、船医等喜剧人物,塑造了一系列闹剧情节。斯德布是小说中重要的喜剧人物。他无忧无虑、嘻嘻哈哈的性格跟埃哈伯和以实玛利的性格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三者的性格比较下文将另有论述)。他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笑着迎接任何灾祸,睡觉和别想事是他的原则。他将跟鲸鱼搏斗看成与吃饭一样轻松,把“意味着死亡的鲸鱼嘴”当做安乐椅,“他至今是不是想到过死,大概也是个问题”①本文引文皆引自《白鲸》一书,梅尔维尔著,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他一刻不离烟斗,下床还没穿裤子就已把它塞到嘴里,连跟鲸鱼拼杀的时候也是嘴不离烟斗。他说话幽默诙谐,常有夸张口吻。例如,看到一头鲸鱼排泄出东西使海水咕咕冒泡时,他说:
“谁有几片止痛药?”“我怕它是胃痛病发作啦,天哪,想想看,这胃痛区就有半英亩地大!逆风叫他闹肚子啦,……你瞧,以前有鲸鱼这么摇摇晃晃前进的吗?它准是丢了它的舵把啦。”
他喜欢捉弄人,他对厨师弗利斯和玫瑰骨朵号的船长的捉弄是令人难忘的闹剧。他给水手鼓劲的叫喊也很有特色:
扳桨啊,扳桨,我的好人儿;扳桨啊,我的孩子们;……为这一金杯抹香鲸油欢呼吧,我的英雄们哪!……慢着,慢着;别急躁——别急躁。你们干吗不扳桨呀,你们这些坏蛋?……轻点儿,轻点儿!对啰——对啰!桨要扳得时间长,扳得狠。使足劲呀,使足劲!让魔鬼把你们抓了去,你们这些流氓,这些地痞,你们全都睡着啦。……冲着你吃的鮈鱼和姜汁饼,你到底扳不扳?……
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经常出现带有亲昵感的咒骂,体现了一种狂欢精神。这里的“像开玩笑又像发脾气”的叫喊,就像拉伯雷的咒骂,让水手们没有一个“不豁出生命划船,然而却又是为了开心而划船”。
读了《白鲸》的人都不会忘记以实玛利在鲸鱼客栈过夜的闹剧。由于床位已满,掌柜让他跟一个陌生镖枪手(季奎格)合床。这个镖枪手听起来很是吓人,他是来自一个原始部落的野蛮人,还到处兜售收集来的人头骨。很晚了他还没露面,以实玛利一个人在床上忐忑不安。半夜时他终于回来,由于缺乏相互沟通,结果他便和以实玛利产生了误会和闹剧。整个情节弥漫着神秘恐怖的气氛,首先是掌柜对镖枪手诡异的描述,接着是他房间里古怪的物品,然后是他吓人的面容和怪癖的行为。然而恐怖神秘的气氛里依然渗透着滑稽喜剧的味道。以实玛利对镖枪手的态度从最初的恐惧厌恶,到最终的接受并成为密友,这个大转变本身就富有耐人寻味的喜剧性。掌柜的神态言行,以实玛利因被捉弄的大惊小怪,他试穿镖枪手“蹭脚垫”的滑稽举动及其看到镖枪手时的心理活动,他和镖枪手因误会而生的大呼小叫,第二天醒来他发现脖子被镖枪手紧紧地搂着,这些细节都不乏喜剧性。叙述者以实玛利以幽默的口吻来处理他俩初遇时的恐怖,体现了他与生俱来的幽默可亲,也体现他能够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周围一切事物(哪怕是敌意的),从而跟埃哈伯的偏执和单一视角形成了对照。
作者善于将喜剧的和悲剧的场面形成对照,恩德比号和单身汉号这两艘船上的狂欢气氛与披谷德号上的压抑气氛的对照就是一例。又如第34章中,他将船上两种不同的用餐风格进行对比:一种代表官方正统的文化,即船长埃哈伯和三个副手的;另一种代表民间下层的文化,即三个异教徒镖枪手的。开饭时,埃哈伯他们按顺序进了船舱,三个副手摆出谦恭温顺的可怜相。谁该吃什么,谁该先离开,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整顿饭在沉闷死寂中进行,连刀盘的碰撞声和嚼肉声都几乎没有听到。而镖枪手们大吃大嚼的声音老远就可以听到。“他们吃饭像爵爷们,把肚皮填得足足的,像整天装着香料的印度货船”,以致厨师不得不端上整大块的腌牛肉。要是他动作慢点,他们就用叉子捅他的背,或把他整个抓起,将脑袋按到木盆里,或用餐刀在他的头上威胁着。作者用夸张的笔法将他们开放自由的民间狂欢精神和长官们压抑拘束的等级气氛进行了对比。苏联文艺评论家巴赫金一生关注狂欢文化,他指出狂欢作品常有夸张的吃喝排泄的描写,比如夸大了的食物和餐具的滥用。这些形象代表节庆、生长和胜利。比如《堂吉诃德》中桑丘的大吃大喝埋葬了堂吉诃德那种孤僻、抽象、僵死的理想主义[5]27。埃哈伯身上也体现了这种孤僻抽象的精神追求,因为他认为白鲸是“面具”,一道隔断认识事物真相的“墙”。他追杀白鲸不是为了得到物质的鲸油,而是为了复仇,更是为了揭开“墙”后面的真相。他“空有崇高的悟性,却缺乏低等的享受能力”,“所有可爱的事物”在他都是痛苦的。此处三个蛮子自由开放的大吃大喝,埋葬了埃哈伯极端的个人主义、自我封闭的性格和抽象的精神追求。
总的来说,书中的喜剧人物和埃哈伯形成了对比。前者言行举止给人喜感,一出场就是闹剧;后者神态威严,说着一种“豪迈简练、遒劲而又高雅的语言”。前者身份卑微,过着普通的百姓生活;后者具有崇高情思,他对白鲸的穷追不舍是史诗式的壮烈行为,他是“全国人口花名册中独一无二的人物——一个专为崇高的悲剧而设置的叱咤风云、万众瞩目的人物”。作者指出“所有伟大的悲剧人物之所以伟大,正是由于某种病态”。平凡人物的喜剧反衬了埃哈伯病态的伟大和悲怆的孤独,正如他将自己孤立在船舱中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埃哈伯身上也有喜剧性。他将一头鲸鱼当做死敌,有堂吉诃德将风车幻想为敌人的可笑;他对凶猛无比的白鲸穷追不舍,有蚍蜉撼大树的可笑。不过,他的可笑更突出了他的可悲。
三、亦庄亦谐的叙述者
《白鲸》的风格深受许多作家的影响,如拉伯雷、塞万提斯、斯特恩、卡莱尔等,这一点已广为人知。梅尔维尔继承他们的风格,幽默诙谐背后常有冷峻的批判和讽刺。叙述者以实玛利滑稽幽默、讽刺嘲弄的言辞就是很好的证明。像拉伯雷的《巨人传》、斯特恩的《项狄传》和卡莱尔的《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等作品的叙述者,以实玛利常在叙事中插入发问、调侃、说俏皮话、发出感慨或呼喊等内容,这些插科打诨式的表达内容往往产生了亲昵滑稽的效果。例如,在介绍鲸鱼脑袋时他突然说:“瞧那耷拉着的下嘴唇!正撅着嘴生大气哩!”又如第26章,他向民主之神发出吁请:“您这位公正的平等之神啊,既然您把人道的大氅覆盖了我的同类,那么,您就该在指责我的凡夫俗子之前为我证明我做得对!……您不曾拒绝赋予班扬这个黑囚犯以洁白的诗才;您也曾经给穷愁潦倒的老塞万提斯的断臂披上两次的纯金叶子;……上帝啊,证明我做得对吧!”这一段与《项狄传》第3卷第23章和第9卷第24章中叙述者向神灵祈求创作的灵感很相似。叙述者在叙事中插入大量离题章节,是对传统的直线叙事方式的抵抗[1]491,这种做法也可以在拉伯雷等人的作品中找到源头。有时叙述者会突然来一段夸张离奇的话语,例如,他说恩德比号上的包子坚硬异常,吞下去还能摸出来,能在肚子里滚来滚去,假如人弯腰过度,包子就像台球一样冲出来。这种夸张的口气类似拉伯雷的诙谐,而E.H.Rosenberry认为它是美国边疆幽默的格调[2]594。
作者常通过叙述者的声音讽刺揶揄官方的、正统的文化,小说多处对西方的宗教、哲学、文化和种族观念进行讽刺,体现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其中双关语和粗俗的幽默是他惯用的手法。Robert Shulman指出书中有关生殖器的笑话和意象表面上看似“开玩笑的和无恶意的”,实际暗含“敌意和蔑视”[6]501。例如,以实玛利用毕达哥拉斯的箴言(吃豆子容易使肚子气胀放屁,不利于净化精神)来取笑站在后甲板的司令吸的是船头水手排泄的气息。排泄和双关语“astern”(既指后甲板,又指屁股)是巴赫金狂欢文化中具有降格作用的“肉体下部”[5]430,能够颠覆一切官方的、神圣的、精神的东西。叙述者一方面颠倒了代表官方文化的司令和代表民间文化的水手两者的地位,另一方面暗示哲学只不过是放屁[7]74。以实玛利还在另一处讽刺了哲学,揶揄自称哲学家的人为“消化不良的老妇人”。又如他将披着“法衣”(鲸鱼生殖器的外皮)的剁膘手比为大主教职位的候补人和教皇的小厮,将剁下来的膘比为圣经纸。作者在“大主教职位”(archbishopric)一词后面故意加上字母“-k”,使“archbishoprick”变成含有生殖器意思的双关语。这里用有性暗示的拉伯雷式或项狄式的双关语[5]504和肮脏的杂务来戏仿神圣的宗教仪式,达到嘲笑颠覆的目的。
第一人称叙述者以实玛利既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能对自己的经历体会和所见所闻加以评价,例如,他对淳朴真诚的季奎格的描述评论常含有讽刺西方文明的口吻。季奎格是个蛮子,他离家去国的目的是想到基督国度求得教化,却发现事实上的基督国度是个卑劣邪恶的世界。他跟以实玛利的初遇虽有些滑稽,后来两人却成为密友,他成为后者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镜子。以实玛利感觉他那泰然安详的神态“象征着一个其中并无暗藏着的表面文明的伪善和貌似和善的欺诈的天地”。有一次季奎格救了一个落水的人之后,众人对他的态度从原先的讥笑转为称赞。以实玛利借此讽刺地说:“他看来不曾想过自己完全应该得舍己救人协会的奖章。他只要了些水,淡水,好洗净身上的咸水。……(他)温和地瞅着周围的人,好像在跟自己说:‘这是个相互合作的世界……我们食人番必须帮助这些基督徒。’”在以实玛利眼里,代表原始文化的季奎格使基督文明所自以为是的优越性黯然失色。跟他相处,以实玛利跨越了文明和野蛮的界限,处在两者之间的交界处[8]。这边缘的位置使他能够将两种文化进行对比,发现文明世界中的虚伪造作,并颠覆西方文化中的传统观念和信仰。
四、喜剧性中的生存智慧
一部悲剧中的喜剧性可以起到缓和悲剧气氛的作用,重要的是它能解救人于困境之中,体现一种苦中作乐的豁达精神。读者可以感受到小说中人与鲸鱼生死博斗的场面中不时有轻松的笔调,要么是一段喜剧性的插曲,要么是叙述者诙谐幽默的插科打诨。例如,第61章中作者在描述追杀鲸鱼过程时反复插入斯德布抽烟的描写,悠闲的抽烟和紧张的捕鲸混在一起,体现一个长期在海上打打杀杀而对生死已经不在乎的水手形象:
“鱼溜啦!”有人喊起来,紧接着这一声音宣告,斯德布掏出火柴,点着了他的烟斗,……大家放下了桨板,哗哗地扳起长桨来。斯德布嘴里继续喷着烟,一边给他的水手鼓劲,发动攻击。……斯德布喊道,一边说着话,一边嘴里噗噗地喷着烟。……[斯德布]还在给他的水手鼓劲往前冲,一边嘴里始终喷着烟。……由于索子越来越快地转,麻绳直冒青烟,和烟斗里不断吐出来的一股股烟混在一起。……鲸鱼的喷水孔里一直在痛苦地喷着一股股白烟,那位首领则兴奋得嘴里一口又一口地猛吐着香烟。
这些喜剧性话语和小说中凝重的悲剧气氛形成了一张一弛的节奏感。实际上,全书的情节是在紧张和轻松气氛的不断更替中发展的。例如,第31章中斯德布喜剧性的梦,第34章末镖枪手的狂欢式用餐,第35章中关于桅顶瞭望的描写,第39章中斯德布滑稽的独白,第40章中水手的狂欢场面,第64—65章中关于斯德布的晚餐和鲸鱼佳肴的介绍,这些都是穿插在紧张叙事中的轻松笔调。
这种悲剧性和喜剧性相融的文风是莎士比亚所开创的传统。早期的西方作品悲剧和喜剧界线分明,互不相容。莎士比亚大胆地打破陈规惯例,实现两者的融合,特别擅长在悲剧中融入诙谐幽默的插曲,如《哈姆雷特》中掘墓人一幕和《麦克白》中守门人一幕。有论者认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喜剧插曲与其说表现了悲、喜剧性事物同时交织在一起时外部世界的混乱,不如说表现了此刻人们内心世界的困惑[2]614。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生活中的喜和悲经常混在一起,或并肩而来,或相互交替。拉伯雷的《巨人传》就描述过这种困境的喜剧:高康大的儿子出生了,而妻子却因难产而死,要为妻子去世而悲呢,还是要为儿子出生而喜?他感到困惑,经过了一阵犹豫之后,他觉得人死不能复生,所以应该为新生的生命庆贺。
莎士比亚和拉伯雷作品里悲喜交融的现象体现了巴赫金所说的狂欢世界的双重性,即“伪与真,恶与善,黑暗与光明,凶残与爱抚,死与生的经常混合”[5]503。《白鲸》的某些描写也体现了这种怪诞的双重性。季奎格的斧子烟斗既可取人首级,又可用来抽烟,安抚自己的灵魂;为死人所备的棺材却成了救生器;阿萨息提斯树林的鲸鱼骷髅上爬满了生机勃勃的藤蔓,“生命拥抱着死亡,死亡支撑着生命”;龙涎香可作为香料,却来自鲸鱼恶心的肠道;水手与鲸鱼混战的“惊惶恐怖的中心”出现了年轻鲸鱼的恋爱场面。
最突出的例子是当水手与鲸鱼相搏时,枪矛擦着人身体飞出去,艇子不断摇晃,人随时会葬身鱼腹。在这生死交替的时刻,以实玛利发现了他的“亡命徒式的乐天哲学”:他将宇宙看作是一个针对他自己的“恶作剧”;生活是一个大杂烩,存在一切事故、教条、信仰、派别和难处;在某些时刻,一切生的死的、喜的悲的、安全的危险的,都会随时发生,而这无非是一个“看不见也闹不清的老丑角”不失善意地“赏你一拳而已”。1851年梅尔维尔在给亲戚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生活中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特别是不幸,都只不过是玩笑。”[9]
以实玛利之前还把生死的问题看作是一件严肃的大事,如今将其视为玩笑,虽然没有高康大的哈哈大笑,其所蕴含的狂欢精神却是一样的。这种态度的转变发生在与鲸鱼生死相搏的危机时刻,即巴赫金的狂欢文化里的“边沿”(生与死的临界线……)[10]。这是一种非正常的生活,人人面临着同样的危险,所以摆脱了日常生活中身份、地位、社会规则和伦理道德的限制。在这“正往死神的血盆大嘴里送”的时刻,却听到了“日常餐桌上决所听不到”的“快活的俏皮话”“嘻嘻哈哈的打闹”“精彩的玩笑”和“敏捷的对答”。笑能够埋葬一切恐惧,包括对权威和死亡的恐惧[5]105。弗洛伊德认为残酷环境中的幽默具有反叛性,“它不仅表示了自我的胜利,而且表示了快乐原则的胜利,快乐原则在这里能够表明自己反对现实环境的严酷性”[11]。生命垂危的恐怖时刻却有欢声笑语,这种荒诞的“绞刑架下的幽默”让以实玛利得到顿悟,重新认识世界和人生,也使他从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生力量,这体现了死亡瞬间的边沿生活的双重性和解放作用。Bainard Cowan指出了以实玛利的“亡命乐天哲学”的悖论(paradox):它揭示了人的生命处在随时可以决定生死的力量里面,同时是一个具有解放作用的发现,使他摆脱了陆地上的等级观念和虚假的虔诚[7]116。
以实玛利面临的问题不仅来自外部世界,也来自内心世界,残酷而神秘的世界让他感到不安,也令他陷入了忧思冥想之中,然而他说:“在我的内心犹如不时狂风大作的大西洋,但我自己岂不是仍然始终处之泰然,毫不声张;而当种种忧患痛苦犹如一座座大山从四处向我袭来时,我在内心深处依然自我沐浴于永恒的欢乐的春风之中。”所以笑是他战胜自己,驱除精神压力的武器,是一种超然的生存之道。
针对书中那些具有双重性的描写,王誉公指出作者“重点阐述了宇宙万物具有双重意义的思想,而且明确指出了人们在认识上的片面性”[12]。以实玛利是故事中唯一真正能用多视角的眼光来观察事物的人,超然的态度使他成了处在“这场热闹边缘的局外人”。在他眼里,笑也有双重性,既能解救人,也能祸害人。他的笑不同于以斯德布为代表的其他水手的笑,后者的嘻嘻哈哈是一种冷漠麻木的盲目乐观。大副斯达勃克这样指责斯德布的盲目乐观:“疯子!如果你的两眼瞎了,就借我的这双眼看看吧。”当斯德布对着被白鲸毁坏的小艇残骸大笑时,埃哈伯这样评价他:“我还不知道你的像大无畏的火那样的勇敢(也同样没有头脑),我敢发誓你是个胆小鬼。”而以实玛利“既不会对好人好事视而不见,对怪异可怖的人事也很快便能辩明”;在笑的同时,他知道大海美丽的表面下隐藏着险恶;他意识到追捕白鲸不是让他们“在迷宫中一无所获地打转”,便是让他们“半路上在大海中沉沦”;他认识到在捕鲸的危险时刻,人不能纹丝不动,要凭着“某种自行调节的浮动和同时产生的意志力和行动”,才不至于沉沦。这说明人在困境之中不能像斯德布一样无动于衷,而要调节好心理机制,凭着意志力和行动,避免灾难的降临。他的笑也展现了他性格灵活性的一面。别人对他的捉弄,他说“哈哈乐上一乐总是一大快事”“一个人身上要有足以使人开怀大笑的地方,那就可以肯定,此人身上定有比你想的也许更大的价值”。教堂里的碑文让他产生了对死亡的冥想,“不过,也不知怎么,我又变得高兴起来啦……”他愿当一个低贱的水手,认为“谁又不是奴隶呢”?这些都体现了其豁达的人生态度和襟怀,以及能用不同的思维来思考问题的特点。这灵活的性格使他既不像斯德布那样盲目乐观,也不像埃哈伯那样不能自拔,偏执成狂,更不会像皮普那样,因恐惧过度而变成痴呆。
五、结语
综上所述,《白鲸》中的喜剧因素确实值得关注,它们体现了作者对人类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怀,它们对于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喜剧因素既是轻松愉快的,又是严肃批判的。以实玛利的超然幽默使人们对这部小说有了不同于埃哈伯的悲剧的另外一种解读。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传统的讽刺手段和缓解悲剧气氛的配料而存在,而且是一种在困境中的解放力量,让人们认识了人类的生存状况,也是以实玛利在危险重重的捕鲸生活里的生存哲学。
[1]Martin,Robert K.Moby-Dick:Our Hearts’Honeymoon [M]//A.R.Lee.Herman Melville:Critical Assessments, vol.iv.East Sussex:Helm Information Ltd,2001.
[2]Rosenberry,Edward.H.Melville and the Comic Spirit [M]//A.R.Lee.Herman Melville:Critical Assessments, vol.iv.East Sussex:Helm Information Ltd,2001.
[3]Wyn Kelley.Herman Melville:An Introduction[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8:58.
[4]杨金才.理论、文献与学术的交汇——评〈剑桥赫尔曼·麦尔维尔导论〉[J].外国文学评论,2008,87(3):149-152.
[5]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6]Shulman,Robert.The Serious Functions of Melville’s Phallic Jokes[M]//A.R.Lee.Herman Melville:Critical Assessments,vol.ii.East Sussex:Helm Information Ltd, 2001.
[7]Cowan,Bainard.Exiled Waters:Moby Dick and the Crisis of Allegory[M].Baton Rouge&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2.
[8]Porter,Carolyn.Call Me Ishmael,or How to Make Double-Talk Speak[M]//R.H.Brodhead.New Essays on Moby Dick.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82.
[9]Parker,Hershel.Herman Melville,vol.i[M].Baltimore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96:862.
[10]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94.
[11]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143.
[12] 王誉公.赫尔曼·麦尔维尔[M]//吴富恒,王誉公.美国作家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79.
(责任编辑:卢妙清)
On the Comic Elements in Moby Dick
HUANG Yong-li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 521041,China)
ract:Most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tragedy in Herman Melville’s Moby Dick,while focusing less on its comic elements.In fact,this novel is full of comic air with regard to its language,characters,scenes and the composition as a whole,which forms a contrast to Ahab’s tragedy.The humor of Ishmael,the narrator, indicates his satire against Western culture.The combination of tragedy and comedy is a true picture of human existence.For Ishmael,his comic spirit is the wisdom to survive in adversity.
ds:comic elements;Ishmael;satire;wisdom
I712.074
A
1009-8445(2015)06-0021-05
2015-01-19
黄永亮(1982-),男,广东汕头人,韩山师范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