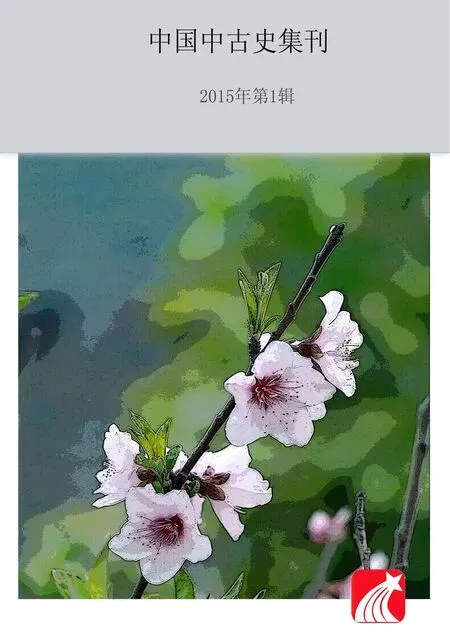唐五代时期的凶肆与丧葬行业组织考论
2015-01-30崔世平暨南大学历史系
崔世平(暨南大学历史系)
唐五代时期的凶肆与丧葬行业组织考论
崔世平(暨南大学历史系)
凶礼是儒家五礼之一,其主要内容是丧葬礼仪,包括丧葬仪式、丧服制度、祭祀仪式等。丧葬礼仪非常复杂,需要很多相关的葬具、明器和仪仗用具,凶肆就是适应这种需求而产生的。凶肆,是指出售、租赁丧葬用品,提供丧葬服务的店铺,通常既可指单个的店铺,又可指同类店铺聚集之处。虽然“凶肆”一词始见于唐代,但出售丧葬用品的店铺出现得很早。东周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城中出现了市。[1]参见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很多地区的中小型墓葬普遍随葬有大量的仿铜陶礼器[2]刘兰华:《从墓葬出土陶器的变化看商周两汉时期丧葬文化的演变》,《景德镇陶瓷》1994年第1期。,这些仿铜陶礼器很多规格一致,可能是从市中购买的商品,市中可能已经存在出售丧葬用品的肆。在传世的秦汉陶文中常常可见到一种“某亭”、“某市”的戳记,新中国成立后发掘的东周至秦汉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也发现许多带有同类戳记的陶器和陶片,如三门峡市秦汉墓所出印“陕亭”与“陕市”戳记的绳纹陶罐,这种戳记当为某地之“亭”、“市”制品的标记。[3]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据《汉书·原涉传》载:“涉乃侧席而坐,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分付诸客。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皆会。”[1]《汉书》卷92《原涉传》。《后汉书·梁冀传》载,袁著为避梁冀追捕,“乃变易姓名,后托病伪死,结蒲为人,市棺殡送”[2]《后汉书》卷34《梁冀传》。。《后汉书·方术列传上》载,郭凤“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敛具,至其日而终”[3]《后汉书》卷82上《方术列传上》。。以上史料说明,至迟在秦汉时期,从棺椁葬具,到殓葬、饭含、随葬用品,都可以在市中买到了。
凶肆性质的聚落,在北魏就已经存在。据《洛阳伽蓝记》卷4载,北魏洛阳城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 车为事。有挽歌孙岩,娶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因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毛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4]《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0页。慈孝、奉终二里内之人经营丧葬行业,不仅有出售棺椁和租赁 车者,还有专门唱挽歌者,与唐代凶肆内的情况已经很相似。北魏慈孝、奉终二里可以说是唐代凶肆的前身。本文主要考察唐五代时期凶肆的特点和变化,并探讨其社会历史意义。
一、唐五代时期凶肆概况
关于唐代凶肆,最为人熟知的是唐白行简《李娃传》中所载的长安城凶肆。据《太平广记》所收《李娃传》,唐天宝年间,郑生到长安应举,居住在位于皇城西的布政坊,一次访友途中,在平康坊鸣珂曲见到李娃,为其美色吸引,与其同居了一年,钱财荡尽后被设计抛弃,只好回到布政坊的邸店中借宿,由于心生怨愤,绝食三日,遘疾甚笃。“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绵缀移时,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繐帷,获其直以自给”,后来郑生因善唱挽歌,在东西二凶肆之争中助东肆取胜。[1]《太平广记》卷484,第3985—3991页。
丰邑坊是长安城西墙南门延平门内大街北第一坊,位于西市西南。宋敏求《长安志》卷10“丰邑坊”条注曰:“南街西出通延平门,此坊多假赁方相、车、送丧之具。”[2]《长安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0页。《太平广记》卷260《房姓人》引《启颜录》曰:“唐有房姓人,好矜门第,但有姓房为官,必认云亲属,知识疾其如此,乃谓之曰:丰邑公相(注曰:丰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亲?曰:是某乙再从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侄儿,只堪吓鬼。”[3]《太平广记》卷260,第2027页。则长安丰邑坊有凶肆。清人徐松认为《李娃传》中的西肆就是丰邑坊。他在《唐两京城坊考》中注道:“按《李娃传》:凶肆有东肆、西肆。传言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则西肆在街西,东肆在街东,西肆当即丰邑,未知东肆是何坊,俟考。”[4]《唐两京城坊考》卷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6页。
日本学者妹尾达彦认为,天门街西有两个凶肆,一个在丰邑坊,另一个在西市内。[5]〔日〕妹尾达彦著,宋金文译,周蕴石校:《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古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30页。1975年,在发掘长安城西市西大街遗址中部时,发掘者发现了唐后期的残陶俑和陶俑头部,宿白先生推测该处可能属于凶肆遗址。[1]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西市位于布政坊西南,与布政坊隔街斜对。郑生在布政坊病倒,被邸主送到凶肆,邸主应该不会舍近求远,绕过西市将其送到西市西南的丰邑坊,因此该凶肆可能是西市内的凶肆。虽然东肆的位置不明,但应与西肆相似,也位于东市内或东市附近。
由于史籍对凶肆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其内部的经营方式和组织模式只能大略推知。唐、五代的凶肆主要从事三个方面的经营:商品出售、器具租赁和提供劳动力服务。
凶肆向丧葬之家出售的商品有棺椁葬具、随葬明器及其他一次性的丧葬用品。棺是墓葬中不可缺少的葬具。《清异录》载:“天成、开运以来,俗尚巨棺,有停之中寝,人立两边不相见者,凶肆号布漆山。”[2]《清异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天成(926—930)为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年号,开运(944—946)为后晋出帝石重贵的年号,巨棺高可过人,可见五代时期凶肆出售的葬具规格之高。
墓葬中除了随葬墓主生前使用的物品外,还根据墓主地位高下,随葬数量和尺寸不等的明器,如镇墓兽、人物俑、模型明器。唐代负责丧葬器物制造的官署有将作监的左校署和甄官署,其中左校署主管棺椁等木质葬具和明器,甄官署主管石、陶质料的地面石刻和随葬陶器、陶俑等。《唐六典》卷23《将作监》“左校署”条载:“凡乐县簨虡,兵杖器械,及丧葬仪制,诸司什物,皆供焉。”文后又自注曰:“丧仪谓棺椁、明器之属。”[3]《唐六典》卷23《将作监》“左校署”条,第596页。同卷“甄官署”条载:“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丞为之贰。凡石作之类,有石磬、石人、石兽、石柱、碑碣、碾硙,出有方土,用有物宜。凡砖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准。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文后自注曰:“别敕葬者供,余并私备。”[1]《唐六典》卷23《将作监》“甄官署”条,第597页。可见只有“别敕葬者”才能享受朝廷提供明器的待遇,其余官员丧葬使用的明器也要在凶肆中购买。长安西市遗址发现的陶俑,应该就是凶肆出售的商品。长安醴泉坊曾发现过烧造随葬品的唐三彩窑址[2]呼林贵、尹夏清、杜文:《西安新发现唐三彩作坊的属性初探》,《文物世界》2000年第1期。,应是为凶肆供货的陶瓷窑之一。棺椁葬具的使用也是如此,只有少数敕葬的高官由朝廷赐给左校署制造的棺椁,大部分官民仍要到凶肆中购买棺椁。五代时期凶肆中出售的巨棺“布漆山”,绝非普通平民所能购买,主要是为官宦富商之家制作的。
《新五代史·姚凯传》载:“晋高祖立,罢凯为户部尚书。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无余赀,尸不能殓,官为赗赠乃能殓,闻者哀怜之。”[3]《新五代史》卷55《姚凯传》。姚凯卒后,靠朝廷赗赠才得以殓葬。赗赠是赠予谷物钱帛,姚凯的家人要持朝廷赗赠的财物到凶肆上购买凶器才能终其丧事。
除了一次性的丧葬用品外,丧礼中还需要不少威仪用具,如运送棺椁明器的车轝、代表威仪的翣扇等。这些器具有的可以重复使用,不需埋于墓中,凶肆的业务之一是出租这种威仪用具。《李娃传》记载长安东西“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轝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后来两肆展示各自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自旦阅之,及亭午,历举辇轝威仪之具”。这些辇轝威仪之具,即是凶肆用来出租盈利的。至北宋时,凶器租赁市场已经非常成熟。《东京梦华录》卷4“杂赁”条载:“若凶事出殡,自上而下,凶肆各有体例。如方相、车轝、结络、彩帛,皆有定价,不须劳力。”[1]《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10页。唐五代凶肆中不同的威仪用具,也应有相应的租赁价格。
除了出售商品和租赁器具,凶肆还为丧家提供抬棺、执器、挽丧车及唱挽歌的人力。《李娃传》中,郑生被邸主送到凶肆中,病稍愈后,“凶肆日假之,令执繐帷获其直以自给”。长安东、西二凶肆展示的项目中除了车轝等威仪用具外,还有挽歌。唱挽歌者,一般是以挽丧车者兼任。郑生因唱挽歌“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才被东肆长发现并高薪聘请。
唐代的丧葬仪式,基本上与古礼相似,起殡之后,要将棺柩抬到 车上,运至墓地。抬棺仅限于在家中把棺柩从殡处抬上 车和在墓地把棺柩从 车上抬下[2]参见《通典》卷139《凶礼六》“引 ”、“ 出升车”、“到墓”、“下柩哭序”诸条,中华书局 1988年版,第3538—3543页。 车形制为鳖甲形四轮车,山东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出土的汉代石椁画像石第三、四石上有一幅送葬图,图中有 车形象。参见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不存在直接用人抬棺长途运送的情况。这种情况到五代时似乎有所改变。《旧五代史》卷96《郑阮传》载:郑阮,洺州人也,后唐末帝时为赵州刺史,性贪浊,“尝以郡符取部内凶肆中人隶其籍者,遣于青州,舁丧至洺,郡人惮其远,愿输直百缗以免其行,阮本无丧,即受直放还”[3]《旧五代史》卷96《郑阮传》。。从青州至洺州,路途遥远,故凶肆中人不愿应役,可知此时已经出现用人舁丧的现象,但一般仅限于近处。
五代以后,长途舁丧就比较常见了。宋人郭彖《睽车志》卷1载:“左贲字彦文,有道术,游京师依段氏,甚礼重之。段氏母病,贲为拜章祈福,乙夜羽衣伏坛上,五鼓始苏,怆然不怿久之。段氏甚惧,诘之,贲曰:‘太夫人无苦,三日当愈,禄筭尚永。’段问:‘先生何为不怿?’贲曰:‘适出金阙,忽遇先师,力见邀,已不可辞,后五日当去。贲本意且欲住世广行利益,今志不遂,故不乐耳。’既而段母如期而疾良已。越二日,贲竟卒。段氏悲悼,具棺衾敛之。贲兄居洛,段命凶肆数人舁棺送之,既举棺,辞不肯往,云:‘棺必无尸。某等业此久矣,凡人之肥瘠大小,若死之久近,举棺即知之。今此甚轻,是必假致他物,至彼或遭训诘。’段与之约曰:‘苟为累,吾自当之。’既至,兄果疑,发视,衣衾而已。段言其故,乃悟其尸解。”[1]《睽车志》,《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4078页。
凶肆中有舁棺者,长期从业,经验丰富,棺内尸体大小甚至死亡时间,举棺便知。京师开封府,距洛阳甚远,凶肆之人只是担心棺内无尸而遭训诘,并不是因路途遥远而拒绝舁送,自然是早已习惯了此类业务。运送棺柩,五代以前均用车,五代以后用人抬棺运送增多,甚至长途舁丧,一直到近代仍是如此,这是古代葬俗一个重大变化。
从《李娃传》的描述看,凶肆内部的组织结构中,有肆长、师[2]郑生与其父相认后,其父以其混迹凶肆,有辱家门,在曲江杏园中将其鞭至数百而毙,幸其同党前往相救而得存活。《太平广记·李娃传》作:“其师命相狎暱者阴随之,归告同党,共加伤叹,令二人齎苇席瘗焉。”《类说》卷28“汧国夫人传”条作:“其凶师告同党往瘗焉。”曾慥编纂,王汝涛等校注:《类说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36页。可知“师”又称“凶师”。,有挽歌者及其前辈耆旧,有执繐帷、翣、扇、铎者等。凶肆中的主体应是各店铺的店主,即“二肆之赁凶器者”,他们是拥有资产的商人。师与挽歌者,执繐帷者等可能是技艺相传的师徒关系,他们是靠出卖劳动为生的阶层,统称“同党”。由于财力和经营品种的限制,不可能每个店铺都有一套人力班子。凶肆内的运作方式应该是根据各店铺的业务情况,调配劳动力,而统合商人和劳动力的是肆长。肆长可能是从财力雄厚的商人中产生的,负责凶肆的日常管理,代表凶肆组织活动等。
肆长在凶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需要对凶肆的管理和公共活动负起责任,这在《李娃传》描写的长安东西凶肆之争中表现得很明显:“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1]《太平广记》卷484,第3988页。
唐长安城内二凶肆大会是经常举行之事,双方都相互了解,故西肆之挽歌者“恃其夙胜”,以为东肆仍然不可能压倒己方。而东肆长知道郑生在歌唱方面的天赋,悄悄以高薪将他从西肆挖到东肆,请能者教其新声,并封锁消息,使“人莫知之”,最后将其作为秘密武器掷出,出奇制胜。这一过程中,东肆长因平时了解到郑生的才能,从而“索顾焉”,类似今日之“猎头”。雇用郑生的二万巨资靠“醵钱”得到。醵钱,即众人集资,出资方当然是东肆的各店铺。而西肆长在输掉比赛后“为众所诮,益惭耻,密置所输之直于前,乃潜遁焉”。西肆长留下的五万钱应该也是在西肆醵集而来。
二市之争不仅是争一时之胜,更是长远的市场之争。胜出者能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取到份额更大的丧葬业市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肆长为了本肆的利益,平时要注意发现本行业潜在的优秀人才,并不惜巨资雇用。为了集体活动,肆长还有权向本肆店铺摊派费用和使用公共资金。可见,唐代凶肆内部的组织和运作已经非常成熟了。
二、凶肆中的丧葬行业组织与“行人”
至迟在晚唐时期,凶肆中出现了丧葬业的行业组织,称为“供作行”或“供造行”。据《唐会要》卷38《葬》:“会昌元年(841)十一月,御史台奏请条流京城文武百寮及庶人丧葬事:‘……伏乞圣恩,宣下京兆府,令准此条流,宣示一切供作行人,散榜城市及诸城门,令知所守。如有违犯,先罪供造行人贾售之罪,庶其明器并用瓦木,永无僭差。’”[1]《唐会要》卷38《葬》,第816—817页。
“供造行人”从事贾售明器,显然是凶肆中的店主。该奏文将“供作行人”与“供造行人”并称,似乎称呼尚不固定,然凶肆内出现了“行”和“行人”是可以肯定的。
《李娃传》中对凶肆的描述相当详细,尚无“行”的名称,而会昌元年奏文中已经出现“供作行人”和“供造行人”,那么供作行或供造行出现的时间,大约应在《李娃传》产生后至会昌元年之间。《李娃传》是一部9世纪初以长安街头艺人说唱的长篇故事《一枝花》为基础,经过文人压缩编写而成的文学作品,改写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9世纪初[2]〔日〕妹尾达彦著,宋金文译,周蕴石校:《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古史(六朝隋唐卷)》,第517页。,张政烺先生则认为白行简作《李娃传》的时间是在贞元十一年(795)。[3]张政烺:《一枝花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20本下册。那么,凶肆中可能在8世纪末至9世纪中期,产生了“行”。
五代时期有“葬作行”,应该是唐代“供作行”及“供造行”的延续。据《五代会要》卷9《丧葬下》载,后唐长兴二年(931)十二月二十六日,御史台奏:“今台司准敕追到两市葬作行人白望、李温等四十七人,责得状称:一件,于梁开平年中,应京城海例,不以高例及庶人使锦绣车轝,并是行人自将状于台巡判押。一件,至同光三年中,有敕着断锦绣,只使常式素车轝。其轝,稍有力百姓之家,十二人至八人,魂车、虚丧车、小轝子不定人数。或是贫下,四人至两人。回使素紫白绢带额遮帏,轝上使白粉埽木珠节子,上使白丝,其引魂车、小轝子使结麻网幕。后至天成三年中有敕,条流庶人断使轝,只令别造鳖甲车载,亦是紫油素物,至今行内见使者。今台司按葬作人李温等通到状,并于令内及天成四年六月敕内详,稳便制置,定到五品至八品升朝官,六品至九品不升朝官等,及庶人丧葬仪制,谨具逐件如后。”[1]《五代会要》卷9《丧葬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2页。
此段奏文之后,又按五品至六品升朝官、七品至八品升朝官、六品至九品不升朝官、庶人四个等级,分别叙述了各等级可使用的人数物色,即舁轝车的人数,威仪用具和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和尺寸等内容。奏文中“海例”、“高例”之意殊难理解,推测“海例”可能是某种规定或惯例,“高例”当指与庶人等级接近的社会阶层。
御史台“追到两市葬作行人白望、李温等四十七人”,并责得两状,这是为了解以前丧葬制度的相关情况,而向“葬作行人”进行查问并记录其供状。这四十七人明确属于“两市”,则后唐时期,市中存在“葬作行”,内有为数不少的“行人”。这些行人是丧葬行业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凶肆的店主。因第一件行人供状提及梁开平年(907—911)中,“行人自将状于台巡判押”,可知至迟到后梁开平年间,葬作行就已经存在了。御史台向行人查问后梁时的丧葬业情况,正是要吸取前朝的管理经验,制定本朝的政策。
御史台列举过上述五品升朝官至庶人四个等级的丧葬仪制后,又奏言:“已上每有丧葬,行人具所供行李单状,申知台巡,不使别给判状。如所供赁不依状内及逾制度,仍委两巡御史勒驱使官与金吾司并门司所由,同加觉察。如有违犯,追勘行人。请依天成二年(927)六月三十日敕文,行人徒二年,丧葬之家即不问罪者。”[1]《五代会要》卷9《丧葬下》,第144页。
唐五代时称导从仪卫人员为“行李”[2]如《旧唐书》卷165《温造传》:“臣闻元和、长庆中,中丞行李,不过半坊,今乃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拟之嫌,若不纠绳,实亏彝典。”,与此义相关,行李又可指仪仗用具。葬作行人向台巡提供的行李单状,即是丧葬之家购买和租赁凶器的清单。
天成二年(927)敕文内容见《五代会要》卷8《丧葬上》。天成二年六月三十日,御史中丞卢文纪奏:“奉四月十四日敕:‘丧葬之仪,本防逾僭,若用锦绣,难抑奢豪。但人情皆重于送终,格令当存于通理,宜令御史台除锦绣外,并庶人丧葬,更检详前后敕格,仔细一一条件,分析奏闻。冀合人情,永著常令者。’令台司再举令文及故实条件如后。凡铭旌,三品已上长九尺,五品已上长八尺,六品已上长七尺……凡丧葬皆有品第,恐或无知之人,妄称官秩,自今后除升朝官见任官亡殁外,余官去事前五日,须将告诰或敕牒于本巡使呈过判押文状,行人方可供应。佐命殊功,当朝立功,名传遐迩,特敕优旨,准会要例,本品数十分加三分,不得别为花饰。右具本朝旧本例如前,今后令两巡使,只据官秩品级与判状,其余一物以上,不得增加,兼勒驱使官,与金吾司并门司同力辖钤。如有大段逾越,即请据罪科断行人,兼不得追领丧葬之家,别有勘责。”
“奉敕:如过制度,不计尺寸事数,其假赁行人徒二年,丧葬之家即不问罪,仍付所司。”[1]《五代会要》卷8《丧葬上》,第135—139页。
后唐长兴四年(933)五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龙敏的奏文重申了天成二年敕令的规定:“京城士庶丧葬,近有起请条流,臣等参详,恐未允当。伏见天成二年敕内,事节分明。凡有丧葬,行人须禀定规,据其官秩高卑,合使人数物色,先经本巡使判状,自后别有更改,不令巡使判状,只遣行人具其则例申台巡。今欲却勒行人,依旧先经两巡使判状,其品秩物色定制,不得辄违。别欲指挥行人,于丧葬之家,除已得本分工价钱外,保无内外邀难,乞觅文状,送到台巡,如有故违,必加惩责。”[2]《五代会要》卷9《丧葬下》,第144页。
据以上史料可知,除升朝官见任官外的其余官员亡殁后,购买或租赁丧葬用具,要提前五日将告诰或敕牒提交巡使判押文状,作为向行人购买或租赁“行李”的凭证。行人则要将租赁的清单提交给御史台巡使,巡使对清单进行审查,如果发现供赁出的“行李”与判状不符,僭越了制度规定,就要对行人处以徒二年的惩罚。
葬作行在五代丧葬制度的执行中承担了很大的责任,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行人要负责提供官府所需的情报,记录官民在丧葬礼仪中租赁的人数物色,并呈报御史台两巡使审查。行人为了避免丧家逾制罪及己身,只能对租售的丧葬用具的数量和等级进行限制,协助官府监督丧葬逾制情况。葬作行实际上承担了官府的一部分职能,这在唐代凶肆和供造行中是看不到的,反映了五代丧葬业的新情况。
《李娃传》中的郑生初在西肆谋生,后来东肆以重金将他挖走,并没有遇见任何阻拦,说明郑生在凶肆内仍有人身自由,他的同党应该大多是自由的雇佣劳动者。郑生混迹于凶肆,其父得知后怒斥他“志行若此,污辱吾门,何施面目,复相见也”,甚至不惜将其鞭打至死,可见凶肆中人的社会地位较低,为士族所不齿。前引《旧五代史·郑阮传》载郑阮为赵州刺史,“尝以郡符取部内凶肆中人隶其籍者,遣于青州,舁丧至洺”[1]《旧五代史》卷96《郑阮传》。,可能凶肆中有的人另有籍,有别于一般平民。
从唐到五代,行人一直为官民的丧葬逾制受惩罚,其地位明显低于一般平民。官府对逾制的丧葬之家,往往不予问罪,只追究工匠或行人的责任。后唐天成二年敕文即规定了行人的责任,还规定了发现丧葬逾制后对行人处以二年徒刑的惩罚措施。
此类规定唐代已有,如元和六年(811)十二月条流文武官及庶人丧葬,重订章程,“伏以丧葬条件明示所司,如五作及工匠之徒捉搦之后,自合准前后敕文科绳,所司不得更之。丧孝之家,妄有捉搦,只坐工人,亦不得句留,令过时日”[2]《唐会要》卷38《葬》,第814页。。又如会昌元年(841)十一月御史台奏疏:“伏乞圣恩,宣下京兆府,令准此条流,宣示一切供作行人,散榜城市及诸城门,令知所守。如有违犯,先罪供造行人贾售之罪。”[3]同上书,第817页。
在唐代,五作工匠之徒丧葬违制,要依敕文科绳;丧孝之家违犯章程,却只惩罚工人、行人,或者首先归罪于行人。五代时只惩罚行人的规定与此是一脉相承的。厚葬虽然违制,却是儒家思想中“孝”的表现,如果因为厚葬而惩罚丧家,便有违崇尚孝道的精神。官府在处理这一矛盾时也有自己的考虑。《五代会要》卷8载后唐天成元年(926)御史台奏:“……今则凡是葬仪,动逾格物,但官中只行检察,在人情各尽孝思,徇彼称家之心,许便送终之礼。台司又难将孝子尽决严刑。只以供人例行书罚,以添助本司支费,兼缘设此防禁。比为权豪之家,多有违礼从厚,若贫穷下士,尚犹不便,送终必无僭礼,可以书罚。两京即是台司举行,诸州府即元无条例者。”[1]《五代会要》卷8《丧葬上》,第133页。
穷困之士,能够做到备礼而葬就很困难了,基本不存在僭越礼制的问题。违礼厚葬者都是权豪之家,要处罚他们恐怕是很难执行的。官府只好借口难以对孝子尽决严刑,而只处罚供应凶器的行人,一方面捞取办公费用,另一方面通过对葬作行的监督来控制丧葬用具的租赁,从而间接遏制丧葬逾制行为。
五代时期城市中还存在“伍作行”。据《太平广记》引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杀妻者”条:某人之妻为奸盗所杀,此人被妻族执入官丞,不胜严刑,乃自诬杀人,甘其一死。从事怀疑有冤情,“遍勘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来应与人家安厝坟墓多少去处文状”[2]《太平广记》卷172,第1270页。。元和六年条流文武官及庶人丧葬疏也提到了“五作及工匠之徒”[3]《唐会要》卷38《葬》,第814页。。其中“伍作”和“五作”,当即后世的“仵作”。仵作原是以代人殓葬为业的人,由于职业原因,也兼任官府中检验死伤的差役。[4]参见杨奉琨:《“仵作”小考》,《法学》1984年第7期;徐忠明:《“仵作”源流考证》,《政法学刊》1996年第2期;崔勇、牛素娴:《中国古代仵作人探究》,《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9期。后唐天成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御史台奏:“今询访故事,准当司京兆按往例,凡京城内应有百姓死亡之家,只勒府县差人检验,如是军人,只委两军检勘,如是诸道经商客旅,即地界申户部,使差人检勘,仍诸司各具事由,及同检勘行人等姓名,申台及本巡察。”[5]《五代会要》卷8《丧葬上》,第133页。
其中负责检勘的“行人”,可能就是伍作行人。唐代元和时期,“五作”还只是与工匠并称,并未见有成行的迹象,而在成书于五代的《玉堂闲话》中,已经出现了伍作行人,伍作行出现的时间可能是在晚唐五代之际。与供作行、葬作行不同,伍作行只提供殓葬、勘验等服务,不出售和租赁丧葬用品。这种变化显示了晚唐五代之际,丧葬行业分工进一步细化的倾向。
三 凶肆与唐五代的社会变化
唐五代时期,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凶肆的变化既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也与其他方面的变化息息相关。
第一,凶肆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发展。隋唐大一统的国家建立后,不但长安、洛阳两京得以另址重建,各地区的主要城市也都得到发展。长安、洛阳两京的规划,都是在居民区设立规划整齐的坊,外郭城内有专门的市,商人集中于市内经营。唐代继承了北魏洛阳城的传统,将凶肆集中设置在几个区域,纳入专门的坊内,如长安城的丰邑坊和西市,使凶肆成为唐代城市中一个特殊的聚落和空间。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虽然在城市中任官和居住,但仍然与家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以乡村为根据地。[1]参见〔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第四编《六朝名望家统治的构想》,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7—311页。城市虽然是政治、经济中心,但乡村的地位仍然重要,是士族生活的重心所在。隋唐时期改变了这种局面。“隋氏罢中正,选举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2]《通典》卷17《选举五》,第417页。由于国家权力的伸张,士族纷纷走出乡村,向城市迁移,乡里社会对于迁徙到城市的士族来说已经不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重要。毛汉光先生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碑志资料为基础,研究了唐代十姓十三家士族的迁移情况,指出大士族著房著支迁移的目标是两京一带。唐代官僚制度中的选制对地方人物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郡姓大族疏离原籍,迁居两京,以便投身于官僚层。[1]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韩昇先生则进一步指出,除了天下名门,作为地方领袖的世家大族也出现了向城市迁徙的趋势。迁徙的目标不但有京城,还有地方的中心城市。[2]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不但官僚士族向城市迁移,平民和工商业者也积极在城市中寻找机会。城市规模的扩大,需要相应的商业、服务业的扩张,以维持其日常运转,这导致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唐长安城繁盛时居民达百万左右,这些人口主要居住在外郭城的坊市区。[3]宁欣:《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他们脱离了乡村,完全依靠城市生活,一旦有丧事,必然无法像在乡村社会那样可以得到乡里宗族的帮助,而只能依靠社会化的服务。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给丧葬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凶肆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第二,凶肆的发展与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有关。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隋唐时期工商业中出现了“行”。“行”是工商业者结成的行业组织,学者们一般将其视为行会。[4]参见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食货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351页;曲彦斌:《行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页。“行”的出现有利于同行业经营者之间的协调发展,避免恶性竞争,维护本行成员的利益。诸行各有行头,负责配合官府工作,检查行业内不法行为,处理日常事务,组织行内的活动。洛阳龙门石窟群残存有“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北市丝行像龛”、“北市香行社造像龛”三个商业窟,其中北市香行社造像龛内的题记为永昌元年(689)三月八日所刻,是现今所知较早的行会资料。[1]贾广兴:《龙门石窟群中的商业窟》,《中原文物》1989年第2期。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中有大量的唐代行会资料[2]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等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据张泽咸先生统计,纺织业有彩帛行、大绢行、小彩行、小绢行、丝绵行、绢行、幞头行,另有米行(白米行、大米行、粳米行)、生铁行、炭行、磨行、肉行、油行、屠行、果子行、靴行、椒笋行、杂货行、染行、布行等。诸行年代大多在玄宗天宝至德宗贞元时。张泽咸先生还根据《周礼注疏》中贾公彦的疏文推断出,诸行设行头、行首的做法至迟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已经存在。[3]张泽咸:《唐代工商业》,第346—347页。
丧葬业的行业组织,目前所知最早的是唐武宗时期的供作行、供造行,其出现时间晚于其他行,分工也没有其他行细致,未见根据具体的丧葬用品再细分的情况。总体来看,丧葬业中行的出现,和唐代工商业及行业组织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供作行和葬作行有责任协助官府监督丧葬制度的执行,与其他行配合官府的功能也是相同的。
此外,五代时期的葬作行参与监督官民丧葬,还与御史台的变化有关。据研究,与唐代相比,五代时期御史台职权范围更为广泛,所负责的事务更加繁剧,还增加了许多御史台本职工作以外的事务。如道士有不法行为本应属祠部管辖,却转由御史台查禁。甚至妇女服饰异常宽博,民间丧葬规格逾制,民间不讲孝悌、不恭尊长等本属于地方府县管辖范围的事,也都要御史台出面查禁,御史台因此往往困于人手不足。[1]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158页。因此,御史台必须较多地利用社会力量。
对于丧葬逾制的现象,自唐代就屡屡有官员上疏议论,《唐会要》卷38《葬》中记载颇详。如太极元年(712)六月,右司郎中唐绍上疏曰:“臣闻王公以下,送终明器等物,具标格令,品秩高下,各有节文。孔子曰:‘明器者,备物而不可用,以刍灵者善,为俑者不仁。’传曰:‘俑者谓有面目机发,似于生人者也。以此而葬,殆将于殉,故曰不仁。’比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行,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请王公以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并陈于墓所,不得于衢路舁行。”[2]《唐会要》卷38《葬》,第810页。
此后,从元和三年(808)五月至会昌元年(841)十一月,京兆尹郑元修、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及御史台曾先后就文武官员及庶人丧葬制度上疏。[3]同上书,第812—816页。
唐代上疏论丧葬制度者有御史台,还有尚书省右司郎中,京兆尹,地方观察使等,涉及的部门众多。而在五代,督察官民丧葬逾制主要是御史台的职责。当御史台发现行人呈上来的行李单状与判状不符合及逾制时,“仍委两巡御史勒驱使官与金吾司并门司所由,同加觉察。如有违犯,追勘行人”[4]《五代会要》卷9《丧葬下》,第144页。。主要负责人是两巡御史,具体执行的是驱使官和金吾司、门司等官吏。御史台既要管辖日益繁杂的事务,又没有足够的人手,只好依靠葬作行人来间接行使职能。
凶肆的发展和丧葬行业组织的产生,促进了丧葬的专业化,对丧葬礼俗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凶肆是随葬品的集散地,从随葬品的商业化和模块化生产来看,同一地区的凶肆,会出售技术风格相同甚至是同一家手工作坊(或陶瓷窑)生产的明器,使得本地区同一时期墓葬的随葬品具有相同的特征,这在考古发现中也可以证实。随葬品的形制和风格可以作为无纪年墓葬断代的重要标准,通过与标准器的比较,确定随葬品的年代,进而推断墓葬的年代,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常用方法。另外,丧葬习俗是由人来具体传承的,同一凶肆提供的丧葬服务,除了人数多寡,威仪用具繁简的区别外,基本的礼仪是相同的,执行者也是同一批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同一地区葬俗的趋同化。凶肆内部的师徒传承关系,也有利于将丧葬礼俗延续下来。因此,在古代丧葬礼俗的研究中,凶肆的作用是不可不考虑的因素。
总之,唐五代时期的凶肆及凶肆中的丧葬行业组织在城市规模扩大、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适应丧葬礼俗的要求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在丧葬礼仪的执行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探讨凶肆和丧葬行业组织的发展变化,对社会史、考古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