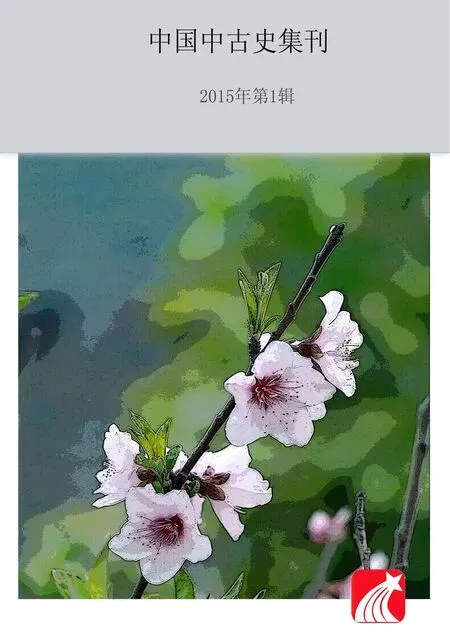晋南朝“清水道”研究
2015-01-30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吴 羽(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晋南朝“清水道”研究
吴 羽(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引言
东晋南朝时期的天师道、上清派、灵宝派、三皇派,对后世影响深远,备受学界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李家道、帛家道、干家道、太平道、清约大道、清水道等道派,这些道派曾经颇有影响,后来淡出了历史舞台。对这些流行一时的道派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观察当时各种宗教信仰形态互相影响与竞争的历史细部,从而对认识东晋南朝道教整合甚至文化整合的历史进程大有裨益。这是笔者研究清水道的初衷。
清水道以“清水”为信仰核心,用清水治病是其最重要的行道方式。杨联陞先生云:“关于清水道,《法苑珠林》卷四十九引《述征记》曰:‘北荒(疑邙)有张母墓。旧说是王氏妻,葬有年载。后开墓而香火犹然。其家奉之,称清水道。’与《抱朴子》所记不同,也许不止一派。又《抱朴子》内篇《道意》卷第九记,有人卖洛西古墓中水,以为有神,可以治病,后来遭官禁绝。不知与清水道有关否。”[1]杨联陞:《〈老君音诵诫经〉校释》,《杨联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认为清水道是五斗米道的一个支派。[1]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8页。刘昭瑞先生在肯定清水道“本亦出自天师道”之外,发掘出《比丘尼传》、《三天内解经》、《道学传》中的清水道史料,指出晋简文帝司马昱信仰清水道,道师是王濮阳,推测孙恩、卢循教派属于清水道[2]刘昭瑞:《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320—335页。,将清水道研究推向了崭新的阶段。其他学者对清水道大都一笔带过。[3]盖建民:《道教“尚医”考析》,《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4期;钟国发:《民间黄老道派末世论与陆修静宗教改革的初步尝试》,《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4年第21辑,丁红旗:《东晋南朝谢氏家族病史与道教信仰》,《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2页;王永平:《东晋中后期佛教僧尼与宫廷政治之关系考述》,《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9期。
尚待研究的是:清水道在何时何地兴起?是江南本地产生的信仰还是从别处传来?和其他道派有何关系?在兴起和传播过程中有何遭遇和变迁?这正是笔者力图解答的问题。
二、兴起在北邙
关于清水道的起源,《法苑珠林》卷36《华香篇第三十三·感应缘》引《述征记》曰:“北荒有张母墓。旧说是王氏妻,葬有年载。后开墓而香火犹然,其家奉之,称清水道。”[4]《法苑珠林校注》卷36《华香篇第三十三·感应缘》,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56页。然而,《太平御览》卷868《火部一·火上》也引《述征记》之文,与《法苑珠林》所引有异,其文云:“北征有张母墓。旧说张母是王氏妻,王家葬经数百载。后开墓而香火犹燃,其家奉之,称清火道。”[5]《太平御览》卷868《火部一·火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850页。《太平御览》卷981《香部一·香》又引《述征记》此条,也微有不同,其文曰:“北芒有张母墓。旧说是王氏妻,葬有年载。后开墓而香火犹燃。”[1]《太平御览》卷981《香部一·香》,第4344页。
张母墓究竟是在“北荒”,还是“北征”,抑或“北芒”?和张母墓相关的宗教信仰团体究竟是应该如《太平御览》所引称作“清火道”,还是当从《法苑珠林》所引名为“清水道”?
其实,《述征记》乃郭缘生随刘裕西征入长安返回之后所记见闻[2]史料参见《雍录》卷7“霸水杂名”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3页;《隋书经籍志考证》卷21“史部十一·《述征记》二卷,郭缘生撰”条,《续修四库全书》第915册,第350页。专门研究参见〔日〕森鹿三:《刘裕北征西伐从军行纪》,《东洋史研究》1937年第3卷第1号,第28—39页。,郭缘生撰成《述征记》的时间当在义熙十三年(417)九月后不久。《述征记》中确实有不少洛阳和邙山的记载,《太平寰宇记》卷3《河南道三·河南府一》数引其文。[3]《太平寰宇记》卷3《河南道三·河南府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7、56页。
同时跟随刘裕西征的还有戴祚,戴祚撰有《西征记》以记见闻[4]《隋书经籍志考证》卷21 “《西征记》二卷,戴延之撰”条,《续修四库全书》第915册,351页。〔日〕森鹿三:《刘裕北征西伐从军行纪》,《东洋史研究》1937年第3卷第1号,第28—39页。,《太平寰宇记》卷3《河南道三·河南府一》引《西征记》云:“邙山西岸东垣亘阜相属,其下有张母祠,即永嘉中此母。有神术,能愈病,故元帝渡江时,延圣火于丹阳,即此母,今祠存。”[5]《太平寰宇记》卷3《河南道三·河南府一》,第47页。按,东垣在洛阳城西[6]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46—47页。,则张母祠在洛阳城偏西北邙山附近。
郭缘生《述征记》所载“张母”与戴祚《西征记》所载“张母祠”中的“张母”是同一人,只是郭氏偏重记载起源,戴氏侧重记载所见及流变,既可互证,又可互补。故而《述征记》中之张母墓必在“北芒”,即北邙山。只是并非在洛阳正北方向,而是偏西北方向。
同时,笔者认为,以张母墓被开为契机形成的宗教信仰团体的名称,当从《法苑珠林》引《述征记》所载,为“清水道”。理由有二:其一,《法苑珠林》中其他地方涉及“清水道”(详见后文),表明作者释道世对清水道有了解,引错的可能性较小,尤其重要的是“清火道”不见于《太平御览》引文之外的任何文献,而“清水道”则屡载于其他典籍。其二,虽然《太平御览》所引《述征记》之文被归于《火》、《香》之目,且前揭《太平寰宇记》引《西征记》称“延圣火于丹阳”,均与“火”有关,似当称“清火道”,但是,《太平御览》卷42《地部七·邙山》亦引《西征记》此文,“圣火”作“圣母”[1]《太平御览》卷42《地部七·邙山》,第199页。,故《西征记》此文不能和《太平御览》互证。即使以“圣火”为是,亦不能证明这个道派应该称作“清火道”,原因在于:一方面,围绕此道派的传说必定很多,其中张母祠中的“香火”可能即为其一,香火有神异之处并不意味着这个道派一定会叫“清火道”;另一方面,祠庙香火延至他处的情况很多,却大都不以“香火”为名,例如妈祖信仰,很多地方都会把祖庙的香火延至他处,但并不会因此将妈祖信仰称为“香火”信仰,也不妨碍妈祖仍然是海神。
另有一则材料与《西征记》的记载好像非常密切,对本文的立论有重大影响,需要加以辩证。许嵩《建康实录》卷5 《中宗元皇帝》注文云:“初,随帝过江有王离妻者,洛阳人,将洛阳旧火南渡。自言受道于祖母王氏传此火,并有遗书二十七卷,临终始行此火,勿令断绝。火色甚赤,异于余火。有灵验,四方病者,将此火煮药及灸诸病,皆愈,转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死,而火亦绝。时人号其所居为圣火巷。在今县东南三里禅众寺直南出小街。或云齐时复有圣火事,具齐卷内。”[1]《建康实录》卷5《中宗元皇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4页。承蒙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姜望来先生指教此条材料,对笔者完善论证有重要意义,谨此致谢。
如果此文与《西征记》之文所说是同一事,则《西征记》中所说“张母祠”和《述征记》所说清水道无关,甚至《述征记》中所载之事是否是清水道也极为可疑。
为了进一步验证《建康实录》此则材料,需要先其中的讹误加以辨正。文曰“临终始行此火”,“始”当作“使”,《景定建康志》卷50《拾遗》、《说郛》卷59下引《建康实录》均作“使”。文中“王离妻”后漏“季氏”,《说郛》卷59下引《建康实录》有,且若无则与之后云“及季氏死”无法照应。
既然许嵩说“或云齐时复有圣火事,具齐卷内”,本文有必要将齐时的圣火事件也罗列于后,以便比较。《建康实录》卷15《世祖武皇帝》:“初,十一年秋七月,月入太微。先是匈奴中谣言云:‘赤火南流丧南国’,于是匈奴始视为寇,帝方患而忧之。是岁,果有沙门从北来赍此火而至,火色赤于常火而微,云以治疾。贵贱争取之,多得其验。二十余日,京师咸云‘圣火’。诏使吏浇灭之,而民亦有窃畜者。治病先斋戒,以火炙桃板七炷而疾愈。吴兴丘国宾好事士也,窃还乡邑,邑人杨道庆虚疾二十年间,形容骨立,依法灸板一炷,能坐,即全瘥。是月,帝崩。”[2]《建康实录》卷15《太祖高皇帝》,第587—588页。
这两则故事相同之点很多,第一,都是从北方带来的“圣火”;第二,火的颜色都比常火“赤”;第三,都用来治病;第四,影响很大;第五,都被官方明令禁止。不同之点是“季氏”之火及身而灭,僧人之火流传不绝。而许嵩说“或云齐时复有圣火事”,明显是许嵩关于圣火的此两种记载得自传闻,而且传闻中这两件事被混为一谈,只是许嵩认为两件事并非同一件事,《南史》卷4《齐本纪上第四》又对后者有明确记载,所以将较难信的“异事别闻”入注,把可信者入正文。因此这两个故事其实很可能是同一个故事的变形。
北宋初释赞宁《东坡先生物类相感志》卷5“河南火”条也记载了这个传说,云:“东晋初,过江有王离妻李氏将河南火过江,自去(当为云)受道于外祖母王氏,有遗书二十卷,临终使勿绝火,遂常种之,世相传二百年,火色如血,世谓圣火,至宋齐间有李氏姫,年九十余,遂一火治病多愈,及姫死,火亦绝。姫葬,呼为圣火冢。母(当为每)阴雨之夕,由见火光出冢门矣。”[1]《东坡先生物类相感志》卷5“河南火”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6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744页。
可见释赞宁和许嵩所听的传闻基本相同。可以将“李氏”视作“季氏”之误。但是李氏既宋齐之间已经90多岁,不可能在东晋初已经嫁给王离为妻,若系王离妻之后人,则不可能姓“李”,李氏圣火传说不符合事实,正因如此,许嵩才删掉了其中关于时代的部分,又有“或云”之语。加上前面对晋初和齐初圣火事件的比较,可以推断,必是后来的人在记忆往事时将齐武帝末年的圣火的特征加到了晋初从洛阳带火到江南的李氏或季氏头上。
这就意味着,这则传说中,除了李氏或季氏曾从洛阳带火到江南之外,其他均不足采信。
或云,两件东晋初和齐时圣火事件确有诸多相类之处,故而后人将两件事混同。笔者认为,即便如此,亦难以认为许嵩此记载和《西征记》、《述征记》所载是同一回事,因为李氏火季氏传说中未有“张母”之说,和《西征记》不符;记载如此详细,而不云有“清火道”或“清水道”,更无墓开之说,明显与《述征记》不同;《述征记》、《西征记》唐时仍存,许嵩当可见之,既然许嵩能在记述此则故事之前引用山谦之《南徐州记》,说明许嵩很重视南朝的地理学著述,如果《西征记》、《述征记》的记载和这个传说有关,许嵩应不会不提明确的文献记载,反而采用自己都感觉有矛盾的传闻;另外值得重视的,若李氏或季氏真是随司马睿过江,则必定和皇室关系密切,以圣火治病有效,恰可增强江南人士对皇室的凝聚力,无官方禁止之理。
因此《建康实录》此文与《西征记》所记虽有相类之处,所指却不相同。不过《建康实录》此文却表明东晋初包括洛阳在内的北方宗教信仰南传江左是很常见的事情,反而可以加固笔者的看法。
考证至此,笔者可以说,由于邙山张母墓开,在洛阳一带逐渐形成一个颇有影响的地方信仰—清水道。清水道起初未必有严密的组织,也不可能有精密的理论,更与五斗米道、太平道无关。清水道随司马睿渡江而流传到江南。
由于郭缘生、戴祚的记载过于简略,这里难以看出张母墓之开与“清水”治病有何关系。
其实,魏晋时期,以清水治病在洛阳曾经非常流行,其影响上及皇室,下及庶民,《三国志》卷3《明帝纪》记载景初二年(238)十二月:“初,青龙三年中,寿春农民妻自言为天神所下,命为登女,当营卫帝室,蠲邪纳福。饮人以水,及以洗疮,或多愈者。于是立馆后宫,下诏称扬,甚见优宠。及帝疾,饮水无验,于是杀焉。”[1]《三国志》卷3《明帝纪》。
尽管此事与清水道关系不大,但是说明,在洛阳有用清水治病的氛围,容易被人接受。
葛洪《抱朴子内篇》卷9《道意》的一段记载对理解清水道的兴起更有帮助,其文云:“洛西有古大墓,穿坏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疮,夏月,行人有病疮者烦热,见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疮偶便愈。于是诸病者闻之,悉往自洗,转有饮之以治腹内疾者。近墓居人,便于墓所立庙舍而卖此水。而往买者又常祭庙中,酒肉不绝。而来买者转多,此水尽,于是卖水者常夜窃他水以益之。其远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遗信买之。于是卖水者大富。人或言无神,官申禁止,遂填塞之,乃绝。”[1]《抱朴子内篇校释》卷9《道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6页。
众所周知,葛洪生活在两晋之际,曾经到过洛阳,遍访异书,详记所见。《抱朴子内篇》这里所载之事发生在“洛西”,地点、时间均与清水道同,而且葛洪所说的这个地方信仰形成的契机是由于“古墓穿坏”,也与清水道相合。然而葛洪没有提到墓开之后“香火犹然”,而且葛洪说这个地方信仰“乃绝”,而清水道一直到刘宋初期还颇有影响,有不合之处。
即使不能完全坐实葛洪所说就是清水道之事,这则史料对理解清水道的兴起依然很有帮助,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利用古墓中之清水治病在清水道兴起的洛阳西北、邙山脚下很常见,非常容易被当地社会接受。清水道最初形成时,也应当是张母墓被开,随后被王氏利用墓中之水治病,祭祀张母,很快形成了一个地方信仰,西晋末大乱,张母墓中之水难以携带,遂带祭祀张母祠中之火南渡。
无论如何,清水道兴起之初与五斗米道、太平道等道教派别和法术无关。
三、南传于江左
由于史料稀少,清水道在江南的情况不甚清晰,但仍有迹可寻,梁释宝唱《比丘尼传》卷1《新林寺道容尼传十》曰:“道容,本历阳人,住乌江寺。戒行精峻,善占吉凶,逆知祸福,世传为圣。晋明帝时,甚见敬事,以花布席下验其凡圣,果不萎焉。及简文帝,先事清水道师,道师京都所谓王濮阳也。第内为立道舍。容亟开导,未之从也。后宫人每入道屋,辄见神人为沙门形,满于室内。帝疑容所为也,而莫能决。践祚之后,乌巢太极殿。帝使曲安远筮之,云:‘西南有女人师,能灭此怪’。帝遣使往乌江迎道容,以事访之,容曰:‘惟有清斋七日,受持八戒,自当消弭。’帝即从之,整肃一心,七日未满,群乌竞集,运巢而去。帝深信重,即为立寺,资给所须,因林为名,名曰新林,即以师礼事之。遂奉正法。后晋显尚佛,道容之力也。逮孝武时,弥相崇敬。太元中,忽而绝迹,不知所在。帝敕葬其衣钵,故寺边有冢云。”[1]《比丘尼传校注》卷1《新林寺道容尼传十》,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页。
此文虽是尼传,却对考察清水道在江南之事非常珍贵。刘昭瑞先生前揭文已经指出此条史料与清水道有关,在笔者看来,这条史料既牵涉到东晋时期清水道道师王濮阳与东晋皇室关系密切的时间段,也关系到清水道在东晋皇室宗教信仰中的淡化,还有助于考察清水道在各个方面变迁的时间下限。很有必要对之作进一步审视。
与此条史料很接近的还有《法苑珠林》所引的一条《冥祥记》。《冥祥记》,南齐王琰撰,《隋书》卷33《经籍二》有著录,《法苑珠林》卷42《受请篇·感应缘》引《冥祥记》中关于道容的故事[2]《法苑珠林校注》卷42《受请篇·感应缘》,第1325—1326页。,除不载“乌巢太极殿”事之外,与《比丘尼传》大体相同而略有差异,刘飖博士比较了两条史料的异同,指出《新林寺道容尼传十》中有不见于《冥祥记》的内容,《新林寺道容尼传十》应该还利用了其他史料[1]刘飖:《释宝唱与〈比丘尼传〉》,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86—93页。,此不具录其文。《法苑珠林》卷31又引《晋南京寺记》,载道容帮助简文帝驱除乌巢太极殿之事(详见后文),与《新林寺道容尼传十》大致相类,也有所不同。故而《新林寺道容尼传十》不是释宝唱简单拼凑这两种材料而成,而是还参照了其他今天已经看不到的史料。可见,《新林寺道容尼传十》所载清水道事并非孤证,有较高的可信度。
关于清水道道师王濮阳及其与东晋皇室关系密切的时间段。王濮阳很可能便是东晋清水道的宗师,因为前揭《述征记》载王氏创立了清水道,王濮阳正是姓王。除前揭材料之外,还有更早的材料记载简文帝信奉王濮阳之事。刘敬叔《异苑》卷4云:“晋简文既废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濮阳令在帝前祷至三更,忽有黄气自西南来逆室前,尔夜幸李太后而生孝皇帝。”[2]《异苑》卷4,见《异苑 谈薮》,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8页。
据唐长孺先生考证,刘敬叔是东晋末刘宋时人。[3]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65页。南朝陈时候的马枢《道学传》除沿袭了《异苑》此文外还记载到:“濮阳,不知何许人也,事道专心,祈请即验,郑鮷(音啼)女脚患跛躄,就阳请水濯足。余以灌庭中枯枣树,枣树即生。脚亦随差。”[4]《三洞珠囊》卷1《救导品》引,《道藏》第2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页。陈国符先生对《道学传》有辑佚,参见《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83页。司马昱的世子司马道生被废于晋穆帝永和四年(348)[5]《晋书》卷32《简文顺王皇后传》。,孝武文李太后孕孝武帝于辛酉(361)[6]参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说明王濮阳及清水道至迟在永和年间已备受司马昱崇奉。
不仅记载异事的文献提到王濮阳,更为严肃的世俗文献也有涉及。《太平御览》卷560《冢墓四》引刘宋何承天《礼论》曰:“又问:墓中有何面为上?荀纳以为缘生奉终,宜依礼坐。蔡谟难,据周公《明堂位》,东西以此(笔者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此’为‘北’,当以‘北’为是)为上。与纳反。纳又引庙位以答王濮阳,北墓向南,以西为墓上。”[1]《太平御览》卷560《礼仪部三十九·冢墓四》,第2530页。
荀纳当为荀讷[2]《太平御览》卷562《礼仪部四十一·忌日》引《晋书》曰:“穆帝纳后,欲用九月九日……博士曹耽、荀纳等并谓无忌月之文。”检《晋书》卷21《礼志下》此处“荀纳”作“荀讷”,故《太平御览》此处系把“荀讷”误作“荀纳”。,晋穆帝时为博士,永和二年(346)曾论纳后之礼[3]《晋书》卷21《礼志下》。,蔡谟卒于永和十二年(356)[4]《晋书》卷77《蔡谟传》。,此论必在穆帝永和十二年前,可以佐证前面所说王濮阳在永和年间时已经颇有影响的判断。
进而言之,这些材料也可和《西征记》、《述征记》所云司马睿过江带来清水道信仰的史实互相印证,说明东晋皇室极可能是世奉清水道,清水道在江南颇有影响。
关于清水道在东晋皇室信仰中的淡化。《新林寺道容尼传十》云简文帝事尼竺道容为师,“遂奉正法”,虽未记载确切时间,但是却说简文帝在崇奉道容之后为其建立了新林寺,新林寺的建立时间应该视为佛教与清水道竞争的一个关键时刻。《法苑珠林》卷31《妖怪篇第二十四·感应缘》引晋《南京寺记》云:“波提寺在秣陵县新林青陵,昔晋咸安二年,简文皇帝起造,本名新林寺。时历阳郡乌江寺尼道容,苦行通灵,预知祸福,世传为圣。咸安初有乌巢殿屋。帝使常筮人占之曰:西南有女人师,当能伏此怪。即遣使至乌江迎圣,问:此吉凶焉在?曰:修德可以禳灾,斋戒亦能转障。帝乃建斋七日,礼忏精勤。法席未终,忽有群乌运巢而去,一时净尽。帝深加敬信,因为圣起此寺焉。”[1]《法苑珠林校注》31《妖怪篇第二十四·感应缘》,第989页。
这就告诉我们简文帝咸安二年(372)为道容建了新林寺。说明佛教在简文帝咸安年间对东晋皇室世代信仰的清水道形成了重大威胁。很难判断是否从此之后东晋皇室放弃了清水道信仰,但是表明清水道生存的宗教环境并不平和,这就要求对其周遭的情况进行考察,并观察其变迁。
四、变迁至消亡
清水道兴起之初虽与太平道、天师道、佛教无关,但是,形成后却不能与之无关。
首先,清水道和五斗米道不能不发生关系。从尊奉清水道的晋皇室家族来讲,西晋的赵王伦、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均与五斗米道关系密切;从东晋皇室周围的重臣来看,不乏世奉五斗米道之家[2]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第1—40页。唐长孺:《钱塘杜治与三吴天师道的演变》,《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175页。。从教法上看,以符水治病是五斗米道行道的一个重要内容。两者必然会发生关系乃至存在竞争。
其次,清水道也与上清派在不少场合相遇。东晋简文帝祈嗣之事,据前揭《异苑》记载,与清水道的王濮阳有关,而《晋书》、《真诰》则将简文帝得嗣归功于上清派的许迈。[3]陈寅恪先生已经揭示出《太平御览》卷666所引《太平经》中濮阳及《晋书》、《真诰》中上清派和简文帝求嗣之关系的材料,见《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第7—8页。但是陈先生未指出《太平御览》所引《太平经》实际上出自更早的东晋末刘宋时刘敬叔的《异苑》,也未区分这则材料和《晋书》、《真诰》实际上说的是清水道、上清派两个道派的事情。虽然东晋简文帝得嗣与两派的仪式肯定毫无关系,但是表明清水道的王濮阳、上清派的许迈均在同一时间和简文帝有密切交往,清水道也就不得不和上清派发生关系。事实上,清水在上清派的教法中也有重要作用,《洞真上清青要紫书金根众经》卷上云:“紫书诀言:凡修上清之道,兆身父母、伯叔、兄弟于世上死亡,兆身未得绝迹,故在人中,身履死秽者,三日,当取清水一瓫,真朱一两投于水中,兆于庭中南向,临水叩齿九通,咒曰:气化成神,尸变入玄,三化五炼,升入九天之劫,更度甲身,甲身更化,得为真人。毕,男死思玉童三人,女死思玉女七人,请瓫水以灌死人之尸。毕,取水自洗手面,仰天吩嗽。毕,又阴咒曰:天气已清,人化已生,得升上天,九变受形。五苦三途,断落死名。超度穷魂,还反南庭。止。”[1]《道藏》第33册,第429—430页。
上清派用清水的途径和方法还有不少,无须多举。其他如太平道、李家道等用符水治病的道派、术士亦所在多有,此为学界所熟知,不必一一列举。
最后,如前所考,清水道在简文帝咸安年间受到了来自佛教的有力竞争。
由于清水道的相关情况文献缺载甚多,所以很难将之与上清、天师道等教派和信仰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研究,也难以断定清水道何时开始变迁以因应业已流行的道派及教法。不过,我们却知道清水道兴起之初,只是用清水治病,祭祀张母,并无严密的理论和炫目的仪式。故而,通过有限的史料,还是可以察觉,和兴起之初相比,清水道至迟在东晋中后期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迁,变迁大致有三:
第一,关于清水道在神学理论上的变迁,刘宋初期的天师道经典《三天内解经》卷上曰:“又有奉清水道者,亦非正法。云天师有奴,不知书注,难以文化。天师应当升天,愍其敬心,敕一井水,给其使用。治病疗疾,不应杂用澡洗、饮食。承此井水治病,无不愈者,手下立效。奴后归形太阴,井水枯竭。天师以此水给奴身,后人不解,遂相承奉,事者自谓清水之道。其清明求愿之日,无有道屋、厨覆、章符、 仪。惟向一瓮清水而烧香礼拜,谓道在水中。此皆不然也。”[1]《道藏》第28册,第415页。
清水道“谓道在水中”,明显是清水道在坚持自己核心的“清水”信仰的同时,加强了自己教法与“道”的关系的论述。天师道教徒在《三天内解经》中讲清水道是其祖师张道陵传给“不知书注”的家奴的简便法门,“亦非正法”,不太可能是清水道自己承认的说法,因为没有哪一个教派愿意承认自己的教法是另一教派的低等形式。不过这则材料却从侧面证明至迟在东晋末,清水道已经吸取了天师道中关于陵井的神话[2]关于“陵井”传说的研究,参见傅飞岚:《张陵与陵井之传说》,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6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40—217页。傅飞岚先生的成果给本文许多启发,不过傅飞岚先生未利用《三天内解经》此则材料,也未提及清水道吸收陵井传说之事。,承认天师道祖师张道陵和自己的教法有关,积极向天师道靠拢。前揭《异苑》之文说王濮阳“令在帝前祷”,则此时的清水道神灵谱系中除了张道陵之外还有“帝”,而且前揭《新林寺道容尼传十》说清水道道舍内“神人为沙门形,满于室内”也表明清水道的道舍内已经不是一个“张母”,而是有多个神。总括而言,清水道在坚持自己核心的“清水”信仰的同时,借鉴天师道、上清派关于“道”的理论和神话,加强了思辨性,完善了神灵谱系,增加了一些仪式,有向天师道靠拢的迹象。
第二,在神职人员的行为上,更加注重个人修为并重视和世俗知识界交流。前揭《道学传》云王濮阳“事道专心”及《礼论》记载王濮阳和礼学家荀讷论礼可为明证。
第三,清水道在至迟在东晋末已经有了分化的迹象。王濮阳在司马昱府中有“道舍”,而另一批人则如《三天内解经》所言“其清明求愿之日,无有道屋、厨覆、章符、 仪”。
值得指出的是,正因清水道完善了自己的理论,在将自己的清水信仰和道联系起来的同时,坚持了自己的核心信仰—“清水”,且在当时颇有影响,所以造作《三天内解经》的天师道教徒才一方面承认清水道是天师张道陵传下来的诸种道法之一,和天师道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却说它“亦非正法”,只不过是张道陵传给奴的简便法门。
应可推断,清水道正是在佛教的挑战下逐渐丧失了在东晋皇室宗教信仰中的主导地位,又在天师道、上清派、灵宝派等有精密理论的道派包围下处于弱势,备受攻击,所以渐趋消歇,以致隋唐时期已经踪迹难觅。
清水道的兴衰,不仅仅是一个信仰团体的兴衰,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两晋之际一些地方信仰被道教各派别(天师道、上清派等)及佛教影响、整合、排挤的历史过程,折射出晋唐道教艰困曲折的整合之路;呈现了各种信仰和文化形态在魏晋南北朝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情境中大交锋、大整合的一个细部;展示了这种社会环境里弱势信仰团体面对挑战、调适自我、维持生存,但遭遇困境,最终消歇的历程。
附记:本文初稿完成后,承蒙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魏斌先生、姜望来先生不吝指教,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