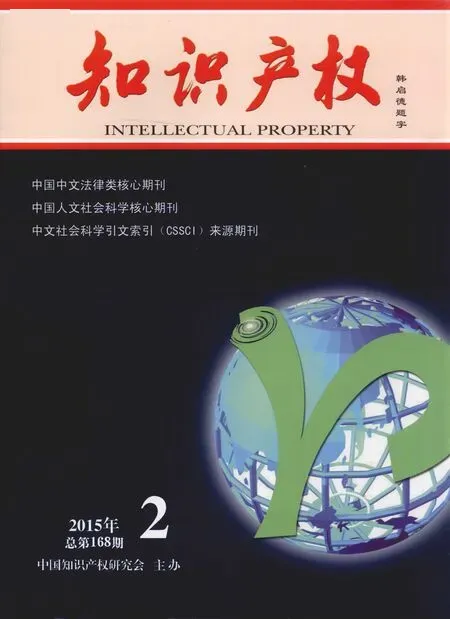论美国联邦反不正当竞争诉权的司法裁判标准
2015-01-30宋建宝
宋建宝
论美国联邦反不正当竞争诉权的司法裁判标准
宋建宝
对于《兰哈姆法》规定的反不正当竞争诉权,法院要判断原告的利益是否属于该法所保护的利益范围,同时也要判断原告的损害是否由被告违反该法的行为直接造成。法院适用“利益范围”标准和“近因”要件就能够确定哪些人享有反不正当竞争诉权。
不正当竞争 诉权 兰哈姆法 利益范围 近因
引 言
美国《兰哈姆法》第43条第1款规定了广泛的制止不正当竞争的内容,这使得该法成为与州一级反不正当竞争法并行的联邦一级的反不正当竞争法。①李明德著:《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23页。但是对于如何判断原告是否享有联邦反不正当竞争诉权问题,美国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适用的裁判标准却不尽相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在Lexmark案中也提出了其认为合适的裁判标准②Lexmark v. Static Control, 572 U. S._(2014).。本文认为,要想解决好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问题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再寻找、比较和论证出解决问题的合适方法。为此,本文将首先分析反不正当竞争诉权的法律性质,再进一步讨论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判标准。
一、美国联邦反不正当竞争诉权的法律性质
(一)美国宪法对诉权的一般规定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美国《宪法》第3条对司法权所作的限制以及权力分立原则,总结出了“不能再缩减的、合乎宪法最低要求的”③Lujan v. Defenders of Wildlife, 504 U. S. 555, at 560 (1992).诉权构成要件,即原告已经遭受了具体特定的“事实上的损害”或者受到具体特定的“事实上的损害”的现实威胁,并且该损害能够合理地追溯至被告的被诉行为,也能够通过司法裁判予以补偿。④Ibid.
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最近审理的Sprint案中认为“联邦法院在司法职权范围内履行司法审判的义务不应当是消极懈怠的”⑤Sprint Communications, Inc. v. Jacobs,571 U. S._(2013).,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要求对待诉权应当坚持“谨慎”原则。目前诉权的“谨慎”原则至少包含三条宽泛的规则,即“禁止当事人依据他人的法定权利提起诉讼;适合由国会解决的普遍化的问题,法院不得裁判;原告要求保护的利益应当属于其援引法律所保护利益的范围。”⑥Elk Grove Unified School Dist. v. Newdow, 542 U. S. 1, at 12 (2004).
(二)美国联邦反不正当竞争诉权的法律性质
如上所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将原告要求保护的利益范围归属于诉权的“谨慎”原则之下⑦Id., at 12.,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再从属于该原则。例如在Associated General Contractors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将《克莱顿法》(the Clayton Act)第4条规定的“私人法律救济的范围”以及“制定法赋予了哪些人享有提起私人损害赔偿诉讼的诉权”都看做是法律解释问题⑧Associated General Contractors, 459 U. S., at 529, 532.,并最终认为,《克莱顿法》规定的原告仅限于那些因被告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而遭受直接损害的人⑨Id., at 532-533.。后来一些案件也认为,Associated General Contractors案是依据制定法,而不是出于“谨慎诉权”原则的考量⑩Holmes v. 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ion, 503 U. S. 258, at 265-268 (1992); Anza v. Ideal Steel Supply Corp., 547 U. S. 451, at 456 (2006).。
因此,判断原告要求保护的利益是否属于其援引制定法的利益保护范围之内,法院需要运用传统的法律解释方法来判断制定法规定的诉权是否包含具体案件中原告提出的特定诉求。①Steel Co. v. Citizens for Better Environment, 523 U. S. 83, at 97(1998); Clarke v. Securities Industry Assn., 479 U. S. 388, at 394-395 (1987); Holmes, supra, at 288.在具体案件的裁判过程中,法院不是要论证立法机关是否应当允许具体案件中的原告提起诉讼,而是要判断立法机关在事实上是否已经允许具体案件中的原告提起诉讼。在这一过程中,正如法院不能根据自己的司法政策去支持立法机关已经明确否决的某项诉权一样②Alexander v. Sandoval, 532 U. S. 275, 286-287 (2001).,法院也不能因“谨慎诉权”原则而限制立法机关已经授予的某项诉权。
具体来说,判断原告是否享有《兰哈姆法》规定的反不正当竞争诉权,就是要分析《兰哈姆法》规定的诉权是否包含具体案件中原告提出的特定诉求,为此法院应当分析《兰哈姆法》中诉权条款的具体含义。
二、美国《兰哈姆法》的反不正当竞争诉权条款
现行美国《兰哈姆法》第43条第1款具体内容如下:
“任何人,就任何商品、服务或者商品的包装,在商业中使用的任何字词、术语、名称、标志或者上述要素的任何组合,或者使用虚假的来源标识,或者对事实进行虚假或误导的描述,或者对事实进行虚假或误导的陈述,
(1)使得自己与他人之间的附属、连接或者联系可能引起混淆、错误或者构成欺骗,或者造成自己的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活动来源于他人或者受到他人的赞助或者同意而引起混淆、错误或者构成欺骗的;或者
(2)在商业广告或商业促销中,虚假陈述自己或他人的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活动的性质、特点、质量或者原产地的;
应当在认为上述行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的任何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承担责任。”
由上可以看出,《兰哈姆法》第43条第1款实际上包括两种不同的法律责任基础,即第43条第1款(1)规定的虚假联系(false association)和第43条第1款(2)规定的虚假广告(false advertising)③Waits v. Frito-Lay, Inc., 978 F. 2d 1093, 1108 (CA9 1992).《兰哈姆法》第43条第1款(2)规定的虚假广告实际上包含了州法中的“虚假广告”和“商业诋毁”。在美国州一级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虚假广告是指竞争者在商业广告或商业促销中,虚假陈述“自己”的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活动的性质、特点、质量或者原产地。如果竞争者在商业广告或商业促销中,虚假陈述“他人”的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活动的性质、特点、质量或者原产地,则属于商业诋毁。。另外,美国国会在1995年对第43条进行修订时又增加了“禁止对他人的驰名商标进行淡化”,这是美国联邦反不正当竞争法发展中的另一个里程碑。④李明德著:《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24页。其实,“对他人的驰名商标进行淡化”,也属于一种虚假联系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如前所述,判断反不正当竞争诉讼中原告是否享有诉权,实际上就是一个制定法的解释问题,即原告是否享有《兰哈姆法》第43条规定的诉权。单纯地从字面上来看,《兰哈姆法》第43条的用语比较宽泛,好像只要满足了美国《宪法》第3条规定的最低要求,任何人都可以提起该项诉讼。但是,美国国会也不可能允许所有事实上遭受损害的原告都可以要求获得赔偿,因此法院不能对第43条的规定做出如此宽泛的解读⑤Holmes, 503 U. S., at 266.。在司法实践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判断原告是否有权依据《兰哈姆法》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时,适用的司法裁判标准不尽相同。
三、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判标准
对于如何判断原告是否有权依据《兰哈姆法》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问题,目前在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层面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裁判标准。例如美国联邦第三、五、八和十一巡回上诉法院适用“多因素平衡”标准来判断原告是否享有《兰哈姆法》规定的反不正当竞争诉权。⑥Conte Bros. Automotive, Inc. v. Quaker State-Slick 50, Inc., 165 F. 3d 221, 233-234 (CA3 1998); Procter & Gamble Co. v. Amway Corp., 242 F. 3d 539, 562-563 (CA5 2001); Gilbert/Robinson, Inc. v. Carrie Beverage-Missouri, Inc., 989 F. 2d 985, 990-991 (CA8 1993); Phoenix of Broward, Inc. v. McDonald’s Corp., 489 F. 3d 1156, 1162-1164 (CA11 2007).美国联邦第七、九和十巡回上诉法院采用“直接竞争者”标准来判断原告是否有权依据《兰哈姆法》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则适用“合理利益”标准来判断原告是否有权依据《兰哈姆法》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
(一)“多因素平衡”标准(the multifactor-balancing test)
美国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在Conte Bros案中首次提出了“多因素平衡”标准,随后其他一些巡回上诉法院予以采用。Conte Bros案就“多因素平衡”标准确认的相关考量因素包括:“(1)原告诉称损害的性质,即原告诉称的损害是不是属于国会意欲通过为违反《兰哈姆法》的行为提供私人救济而进行赔偿的损害类型;(2)原告诉称损害的直接性或者间接性;(3)当事人对于被诉侵害行为的远近程度;(4)损害赔偿金请求的不确定性⑦在英美法中,存在推测性损害赔偿金的说法。推测性损害赔偿金是指不能确定或者不能以合理的确定性加以证明的损害赔偿请求,从而法院不能判决给予此种损害赔偿。参见《元照英美法律词典》之“speculative damages”词条。;(5)双重赔偿的风险或者分摊损害赔偿的复杂性。”⑧Conte Bros. Automotive, Inc. v. Quaker State-Slick 50, Inc., 165 F. 3d, at 233.
“多因素平衡”标准对一个需要法院查明的相对模糊的问题列出了具体的调查清单,这是值得称赞的努力。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方法稍微偏离了问题的重点。第一个因素可以理解为,原告的损害应当在制定法保护的利益范围之内;第二个因素和第三个因素(有点多余)可以理解为近因(proximate cause)⑨近因(proximate cause),指实质性原因。某项作为或者不作为是造成伤害或损害的近因,指伤害或损害是作为或者不作为的直接结果或合理结果,即如果没有该原因,则结果不会产生。近因不一定与结果在时间上或空间上最为接近,而是与造成结果最为接近。参见《元照英美法律词典》之“proximate cause”词条。远因(remote cause)与“近因”相对,指并不必然或直接造成伤害或损害的原因,如:按一般人的经验并非造成伤害或意外事故的原因;后果不确定或不一定产生后果的原因;通过其他原因才产生后果的原因;不大可能的原因。参见《元照英美法律词典》之“remote cause”词条。要求,但是对上述要件的处理方式是不对的,因为每一个案件都应当满足这些要件,而不是把它们仅仅作为综合考量的平衡因素。第四个因素和第五个因素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正如Conte Bros案所揭示的,如果被告的行为已经直接侵害了制定法所保护的原告的某项利益,那么在确定和分摊损害赔偿金方面存在的潜在困难,并不能成为否决诉权的独立依据。另外,即使原告因没有充分地、确定地量化其损失而不能要求损害赔偿金时,原告仍然有权依据《兰哈姆法》第34的规定请求禁令救济或者依据《兰哈姆法》第35的规定请求被告返还以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的利润。⑩TrafficSchool.com, Inc. v. Edriver Inc., 653 F. 3d 820, 831 (CA9 2011); Johnson & Johnson v. Carter-Wallace, Inc., 631 F. 2d 186, 190 (CA2 1980).最后,司法实践已经表明,Conte Bros.案所采用的方法,像其他开放式的平衡标准一样,不仅会产生难以预期的结果,有时还会产生主观臆断的结果。①Tushnet, Running the Gamut from A to B: Federal Trademark and False Advertising Law, 159 U. Pa. L. Rev.1305, 1376-1379 (2011).
(二)“直接竞争者”标准(the direct-competitor test)
美国联邦第七、九和十巡回上诉法院采用“直接竞争者”标准,认为只有事实上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竞争对手才有权依据《兰哈姆法》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②L. S. Heath & Son, Inc. v. AT&T Information Systems, Inc., 9 F. 3d 561, 575 (CA7 1993); Waits v. Frito-Lay, Inc., 978 F. 2d 1093, at 1108-1109(CA9 1992); Stanfield v. Osborne Industries, Inc., 52 F. 3d 867, 873 (CA10 1995).。
同“多因素平衡”标准相比,“直接竞争者”标准提供了一条界限明确的规则,但是这种方法却是以扭曲制定法的立法用语为代价的。在原告与被告不构成竞争关系的案件中,原告在证明近因要件时,确实常常更加困难。但是这样一条规则以分类的方式禁止所有的非竞争者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这对《兰哈姆法》第45条定义的“不正当竞争”提出了太多的限制。并且,在《兰哈姆法》制定以前,美国普通法上的不正当竞争侵权行为并不仅仅限于竞争者之间的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领域的一位权威专家曾写道,“在不正当竞争中无需存在竞争,就像苏打水中无苏打,葡萄柚中无葡萄,面包果中无面包,晒衣架(a clothes horse)不是马。”③Rogers, Book Review, 39 Yale L. J. 297, at 299 (1929).《兰哈姆法》虽然是为了制止不正当竞争,但是据此推断该法只保护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人的直接竞争对手,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三)“合理利益”标准(the reasonableinterest test)
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适用“合理利益”标准来判断原告是否有权依据《兰哈姆法》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根据“合理利益”标准,如果原告能够表明:(1)对于被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来说,原告存在着合理利益;(2)原告有合理根据认为,该项利益可能遭受被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损害。④Famous Horse, Inc. v. 5th Avenue Photo Inc., 624 F. 3d 106, 113 (CA2 2010).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说,“合理利益”标准容易造成其适用范围过于宽泛。实际上,如此模糊的用语可以理解为反不正当竞争诉权只要满足美国《宪法》第3条规定的诉权的最低要求就可以了。“多因素平衡”标准之所以被较多的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采用,实际上就反映了法院已经疲于如何尽可能准确界定“合理利益”这一问题。⑤Conte Bros., 165 F. 3d, at 231.“合理利益”标准在理论方面造成的困难甚至更为严重,这是因为法院判断原告是否享有诉权时,不是要分析原告要求保护的利益是否合理,而是要分析原告要求保护的利益是否属于《兰哈姆法》所保护的利益范围;法院也不是要分析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是否存在合理依据,而是要分析原告诉称的损害与被告的行为是否直接相关。
四、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确立的裁判标准
考虑到当前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判断原告是否有权依据《兰哈姆法》提起诉讼问题存在分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批准了Lexmark案的调卷令申请,希望能够就该问题给出合适的分析标准。⑥Lexmark v. Static Control, 572 U. S._(2014).在该案的判决中,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目前采用的上述标准中的任何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拒绝适用上述任何标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直接适用“利益范围”标准和“近因”要件就能够确定哪些人有权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
(一)“利益范围”标准
1.“利益范围”标准概述
根据现代“利益范围”标准,只有当原告的利益落入其援引法律所保护的利益范围时,该原告才能享有该法规定的法定诉权。⑦Allen, 468 U. S., at 751.现代“利益范围”标准来自于Association of Data Processing Service Organizations案⑧Association of Data Processing Service Organizations, Inc. v. Camp, 397 U. S. 150(1970).。美国《行政程序法》(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简称APA)将司法复审诉权赋予了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但是“利益范围”标准却是美国法院在审查司法复审诉权实践中形成的一项限制条件,并且从那时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利益范围”标准的适用问题就作出了澄清,即(1)“利益范围”标准适用于制定法规定的所有诉权;(2)“利益范围”标准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要件”;(3)国会立法时已经考虑到“利益范围”标准的限制,并且同意适用该标准,除非国会已经明确否认适用“利益范围”标准。⑨Bennett v. Spear, 520 U. S. 154, 163 (1997); Holmes, at 287-288.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指出,在涉及APA的案件中,适用“利益范围”标准并不是“特别吃力”。⑩Match-E-Be-Nash-She-Wish Band of Pottawatomi Indians v. Patchak, 567 U. S._(2012).在涉及APA的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常常“在利益范围标准中明显地加入‘可争议的’一词,以表明任何存在疑问的利益都归属于原告”,并指出,“只有当原告要求保护的利益与其援引的制定法的立法目的不相关或者不一致,以致于不能合理推断出国会允许原告提起诉讼时,利益范围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才会阻止原告提起诉讼。”①Id., at_(slip op., at 15-16).需要指出,APA的司法复审诉权条款涉及的制定法不仅性质各异,而且数量众多,甚至一些制定法本身并没有规定司法复审诉权。APA的司法复审诉权条款允许当事人就违反这些制定法的各种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因此APA司法复审诉权条款可谓包罗万象,具有包容性的“利益范围”标准自然也就成为维持APA司法复审诉权条款灵活性的适当方法。“但是利益范围标准中‘利益’的范围会因案件所涉制定法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根据宽泛的APA司法复审诉权条款,为了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复审,某项利益可能会落入某一制定法的保护范围,但是对于其他制定法来说,却又未必如此。”②Bennett, at 163.
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对某些制定法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些制定法所保护的利益范围相对宽泛,超出了通常理解的利益范围。③Bennett, at 164.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否享有某一制定法规定的诉权时,“利益范围”标准是一种恰当的分析工具。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确切地讲,法院一直在适用“利益范围”标准,并且从未否定适用“利益范围”标准。
2.《兰哈姆法》中的“利益范围”
对于《兰哈姆法》所保护的利益范围问题,法院不需要推测就能直接确定,因为《兰哈姆法》本身对其立法目的进行了详细阐述。《兰哈姆法》第45条规定,“本章立法目的在于,通过使在商业活动中欺骗性和误导性地使用标志的行为成为可诉行为,规范国会管辖范围内的商业活动;保护商业活动中使用的注册标志免受州立法或者地区立法的干扰;保护在国会管辖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免受不正当竞争损害;禁止在商业活动中使用注册标志的重制品、复制品、伪造品或者似是而非的模仿品进行欺骗和欺诈;对美国与外国达成的有关商标、商号及不正当竞争的条约和协定所约定的权利和救济进行规定。”
根据《兰哈姆法》的上述立法目的不难看出,整个《兰哈姆法》,包括第43条第1款,所保护的只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任何人”,并没有提及消费者或者社会公众,这是因为该法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纯粹的商业性群体的利益,制止不道德的商业行为。④Halicki Films LLC v. Sandersons Sales and Marketing, 547 F.3d 1219(9th Cir 2008).因此,“不正当竞争”在普通法上虽然是一个“弹性”概念⑤Ely-Norris Safe Co. v. Mosler Safe Co., 7 F. 2d 603, 604 (CA2 1925).,但是法院都认为“不正当竞争”与商业信誉和现在及将来的销售有关。⑥Rogers, Book Review, 39 Yale L. J. 297, 299 (1929).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如果原告根据《兰哈姆法》第43条规定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那么该原告应当指出被诉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其商誉或销售方面的商业性利益造成了损害。如果消费者因受到欺骗而购买了不满意的产品,那么该消费者虽然遭受了美国《宪法》第3条所认可的事实上的损害,但是该消费者不能依据《兰哈姆法》请求法院提供法律救济。这在所有的巡回上诉法院中早已经达成共识。⑦Colligan v. Activities Club of N. Y., Ltd., 442 F. 2d 686, 691-692 (CA2 1971); Serbin v. Ziebart Int’l Corp., 11 F. 3d 1163, 1177 (CA3 1993); Made in the USA Foundation v. Phillips Foods, Inc., 365 F. 3d 278, 281 (CA4 2004); Procter & Gamble Co., 242 F. 3d, at 563-564; Barrus v. Sylvania, 55 F. 3d 468, 470 (CA9 1995); Phoenix of Broward, 489 F. 3d, at 1170. Bridge, 553 U. S., at 657.同理,即使一家企业因受到误导而购买了劣质产品,那么它与一般的消费者一样,也不能依据《兰哈姆法》请求法院提供法律救济。
(二)“近因”要件
1.“近因”要件概述
根据“近因”要件,只有当原告的损害是由违反法律的行为直接造成的,这样的原告才享有法律规定的诉权。历经多个世纪,“对于所有涉及损害的案件,法院都将损害归结于近因,而不是归结于任何的远因,这应经成为普通法上一项比较固定的原则”⑧Waters v. Merchants’ Louisville Ins. Co., 11 Pet. 213, 223 (1837); Holmes, 503 U. S., at 287. Harold H. Huggins Realty, 634 F. 3d, at 799.。这项颇受推崇的原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现实,即“司法救济不可能涵盖能够想得到的、可追溯于被诉违法行为的所有损害。”⑨Associated Gen. Contractors, 459 U. S., at 536.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国会应当熟知这项普通法上的原则,并且也不打算以默示的方式否认这项原则。⑩Lexmark v. Static Control, 572 U. S._(2014).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解释诸多联邦制定法规定的诉权时,都将近因作为要件之一。①Dura Pharmaceuticals, Inc. v. Broudo, 544 U. S. 336, 346 (2005) (securities fraud); Holmes, at 268-270 (RICO); Associated Gen. Contractors, at 529-535 (Clayton Act).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近因的分析是难以界定的,并且这些年来,近因已经呈现出多种形式,但是法院在适用近因原则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并且也有大量的先例可供引用和参考。②Exxon Co., U. S. A. v. Sofec, Inc., 517 U. S. 830, 838-839 (1996); Pacific Operators Offshore, LLP v. Valladolid, 565 U. S._(2012) .对于近因的分析,司法实践应当受制于不同制定法下诉权的不同性质,但是总体来说,就是原告诉称的损害与其援引的制定法明确禁止的行为之间是否具有足够密切的联系。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原告诉称的损害与被告的违法行为之间的联系“过远”,近因要件通常就要禁止原告提起这样的诉讼。通常的情形就是,被告的行为致使厄运降临在某个第三人的头上,而原告的损害则纯粹地派生于这样的厄运。③Holmes, at 268-269; Hemi Group, LLC v. City of New York, 559 U. S. 1, at 10-11 (2010).
2.《兰哈姆法》中的“近因”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虽然《兰哈姆法》第43条的用语比较宽泛,但是第43条也应当包含近因要件,对于这一点,应当没有异议。④Lexmark v. Static Control, 572 U. S._(2014).
虽然大多数源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商业性损害都派生于那些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欺骗的消费者所遭受的损害,但是“即使是第三人,而不是原告,相信了某一虚假陈述”⑤Bridge v. Phoenix Bond & Indemnity Co., 553 U. S. 639, 656 (2008).,那么该虚假陈述也可能会对原告直接造成损害。并且,《兰哈姆法》既然允许仅为商业性损害而提起诉讼,那么消费者是否受到欺骗,作为中间步骤,对于《兰哈姆法》规定的反不正当竞争诉权所要求的近因要件来说就不再具有决定性了。⑥Harold H. Huggins Realty, Inc. v. FNC, Inc., 634 F. 3d 787, 800-801 (CA5 2011).
传统的近因原则认为,被告为了增进自己的利益,在明知针对原告产品或者被告产品的一些陈述是虚假的但仍然进行讲述,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认为被告对原告直接造成了损害。⑦Colligan v. Activities Club of N. Y., Ltd., 442 F. 2d 686, 691-692 (CA2 1971); Serbin v. Ziebart Int’l Corp., 11 F. 3d 1163, 1177 (CA3 1993); Made in the USA Foundation v. Phillips Foods, Inc., 365 F. 3d 278, 281 (CA4 2004); Procter & Gamble Co., 242 F. 3d, at 563-564; Barrus v. Sylvania, 55 F. 3d 468, 470 (CA9 1995); Phoenix of Broward, 489 F. 3d, at 1170. Bridge, 553 U. S., at 657.例如,在典型的《兰哈姆法》反不正当竞争诉讼中,某个市场竞争者针对自己的商品或者竞争对手的商品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因此导致竞争对手的客户流失,⑧Waters v. Merchants’ Louisville Ins. Co., 11 Pet. 213, 223 (1837); Holmes, 503 U. S., at 287. Harold H. Huggins Realty, 634 F. 3d, at 799.通过这种方式,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市场竞争者直接侵害了其竞争对手。需要特别指出,客户转移到直接的竞争对手,虽然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的典型的直接损害,但是这并不是《兰哈姆法》第43条规定的唯一类型的损害。当被告诋毁原告业务而损害原告的商誉时,原告遭受的损害直接来源于公众对贬损性陈述的确信。因此,根据《兰哈姆法》第43条的规定,法院不仅对于被告通过名称直接诋毁原告产品⑨McNeilab, Inc. v. American Home Prods. Corp., 848 F. 2d 34, 38 (CA2 1988).的情形应当提供法律救济,对于被告将原告产品等同于劣质产品⑩Camel Hair and Cashmere Inst. of Am., Inc. v. Associated Dry Goods Corp., 799 F. 2d 6, 7-8, 11-12 (CA1 1986); PPX Enterprises, Inc. v. Audiofidelity, Inc., 746 F. 2d 120, 122, 125 (CA2 1984).而损害原告商誉的情形也应当提供法律救济。并且当原告主张因被诉不正当竞争行为而遭受商誉损害的,竞争关系不是近因要件所要求的。①Lexmark v. Static Control, 572 U. S._(2014).
另外,即使被告的目的是为了损害其直接的竞争对手,如果原告也跟着一起遭受了损害,那么竞争关系也不是《兰哈姆法》中反不正当竞争诉讼的近因要件所要求的。②Id.例如两个存在竞争关系的汽车制造商,它们从不同的第三方供应商购买汽车安全气囊。如果第一家汽车制造商为了吸引客户,虚假宣称第二家汽车制造商所使用的安全气囊存在缺陷,那么第二家汽车制造商及其安全气囊供应商都将遭受商誉方面的损害,它们的销售量也会随之下滑。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认为,一方遭受的损害派生于另一方遭受的损害,因为第一家汽车制造商针对安全气囊实施的贬损行为对第二家汽车制造商和安全气囊供应商都直接地、分别地造成了损害。
对于近因要件来说,“超出第一环节的一般性的倾向不能延伸成为近因”③Holmes, 503 U. S., at 271.。之所以提出“一般性的倾向”问题,主要是因为直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与间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之间的联系往往是中断的,以至于后者并不能确定归因于前者,也因此不能确定归因于被告的行为。④Anza, 547 U. S., at 458-459.因此,如果原告的损害与客户受骗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包含了一个中间环节,那么原告的起诉可能就难以满足诉权的近因要件。但是“如果原告诉称的损害属于构成被诉违法行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毫无疑问,就满足了近因要件。”⑤Blue Shield of Va. v. McCready, 457 U. S. 465, 479 (1982).
综上所述,原告依据《兰哈姆法》第43条的规定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时,一般应当证明其经济损害或商誉损害直接源于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造成的欺骗,并且当遭受欺骗的用户不再与原告进行交易时,就视为原告遭受了经济损害或商誉损害。但是当被告的欺骗行为对某个商业竞争对手造成损害,该商业竞争对手所遭受的损害又进一步对原告造成损害的,法院通常认为该原告的诉权不能成立。例如,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导致某个商业竞争对手被迫关门,那么通常来说,该商业竞争对手就其损害有权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但是该商业竞争对手的房东、电力公司或者其他商业性的当事人就其损害无权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因为这些当事人遭受的损害仅仅是那个被迫关门的商业竞争对手无力履行其经济义务的结果。⑥Anza, 547 U. S., at 458.
小 结
在美国,原告以反不正当竞争为理由在联邦法院提起《兰哈姆法》第43条规定的反不正当竞争诉讼时,应当提出并最终证明,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原告的销售或者商誉等商业利益直接造成了损害。需要特别指出,美国联邦法院根据《兰哈姆法》第43条的规定,虽然确认某个原告就反不正竞争诉权问题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但是如果该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因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遭受的损害,他仍然不能获得法律救济,因为法院确认原告享有反不正当竞争诉权,只是表明原告获得了证明其诉讼请求的机会。⑦Lexmark v. Static Control, 572 U. S._(2014).
The cause of action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under the Lanham Act extends only to plaintiffs whose interests fall within the zone of interests protected by the Act and whose injury was proximately caused by a violation of the Act. Direct application of the zone-of-interests test and the proximate-cause requirement supplies the relevant limits on who may sue under the Lanham Act.
unfair competition; right to sue; the Lanham Act; the zone-of-interests test; the proximatecause requirement
宋建宝,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国家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中心副研究员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名称:中国专利司法政策研究,编号:2014T7019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