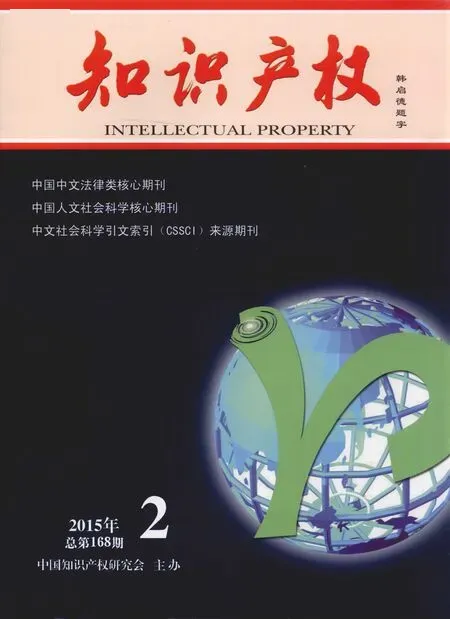伏击营销的商标法审思
2015-04-20周围
周 围
伏击营销的商标法审思
周 围
伏击营销是现代大型文体活动中屡见不鲜的一种社会现象,且行为方式多样、社会评价不一。从商标法角度对伏击营销行为进行剖析,不仅能够明晰伏击营销的基本特性、掌握其合法与非法的界限,而且能够了解伏击营销行为所涉的多重利益冲突。基于利益平衡的思路,提出更好地利用商标法规则化解各相关利益主体的矛盾,从现有制度中找寻解决伏击营销困境的对策。
伏击营销 商标侵权 混淆可能性 利益平衡
一、伏击营销行为概述
伏击营销(Ambush Marketing),又称埋伏营销,主要是指未获得特定活动主办方授权的经营者,通过创造与特定活动的关联并试图利用特定活动的商誉、信誉及声望进行商业活动的行为。①Stephen M. Mckelvey, Atlanta'96: Olympic Countdown to Ambush Armageddon? 4 Seton Hall J. Sport L. 397, 401 (1994).由此可知,伏击营销行为人在主观上须具有创造与特定活动关联的意图,而在客观上与特定活动无赞助合同关系且实施的行为是与特定活动有关联的商业行为。随着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日益增加,伏击营销行为广泛出现在各种文体活动中,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但与此同时,伏击营销也面临着大量的负面评价,尤其是那些已经支付高额赞助费的官方赞助商认为伏击营销更像是一种搭便车的行为,是从其赞助的特定活动中窃取利益的行为。由于过度的伏击营销的确会使消费者对伏击者与特定活动的关系造成混淆,弱化赞助商的广告行为。因此,伏击营销也饱受赛会主办方和官方赞助商的诟病和责难,其中以奥运会对伏击营销的抵制最为严厉。由于奥运会高标准的比赛规格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奥运会期间的伏击营销行为十分频繁。因此,国际奥委会要求赛会主办国政府通过专门立法的方式保护与奥运相关的知识产权并承诺对伏击营销行为予以重点打击。例如,我国国务院于2002年4月颁布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该条例不仅规定未经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为商业目的使用奥林匹克标志,而且还将“北京2008”等容易被伏击者利用的口号和文字也纳入奥林匹克标志的范畴,予以严格保护。但并非所有的文体活动均能通过专门立法的方式对伏击营销行为加以限制,过度泛滥的伏击行为不仅会抑制活动主办方与赞助商之间的合作热情,而且还可能导致消费者对活动赞助关系以及活动衍生产品产生混淆。因此,需要对伏击营销加以分析,以求明晰其违法界限、科学掌握其行为内涵。
二、伏击营销与商标法的交错
根据前述伏击营销的定义,其行为的关键在于创造与特定活动的某种关联,未获得活动主办方授权以及利用该活动实施商业行为只是伏击营销行为的前提与目的。由于商标具有识别商品、指示商品来源、保证商品品质以及广告宣传等功能,因此伏击者通常会利用活动主办方为该活动注册的商标或商标的部分元素来创造关联性。但这种未获得授权的关联也极有可能对消费者造成一定程度的混淆,从而侵犯活动主办方的商标权。例如,在波士顿田径协会诉沙利文案②Boston Athletic Association v. Sullivan, 867 F.2d 22 24(1st Cir. 1989).中,被告从1978年就开始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期间生产和销售印有“Boston Marathon”字样的服装。赛事组织者波士顿田径协会(Boston Athletic Association)于1983年注册了商标“Boston Marathon”和“BAA Marathon”,并随后将这些商标许可给其他商家以负担部分组织比赛的费用,但在此期间被告未取得田径协会的许可。1989年,波士顿田径协会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被告的行为使消费者混淆了其与马拉松比赛的赞助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生产的服装并没有造成与授权服装的混淆且田径协会的权利行使应限于注册商标的使用范围。因此,法院做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波士顿田径协会随即提出上诉。上诉法院鲍恩斯法官认为,该案的核心问题是被上诉人商业行为造成混淆的可能性。由于被告擅自使用了波士顿田径协会注册并运作的“Boston Marathon”商标,并意图利用马拉松比赛提高其服装的销量,因此,法院认为,对混淆可能性的认定调查应该集中于购买服装的消费者是否被误导并相信被告的服装获得了波士顿田径协会的授权。③Id. at 28.鲍恩斯法官进一步指出,波士顿田径协会也曾表示,“担心潜在消费者受被告的商业行为误导并产生混淆进而认为被告生产销售的服装是获得其授权的”。因此,被告虽未直接使用原告的商标,但被告服装上的文字和设计容易使人误解该服装与田径协会长期组织的马拉松活动存在某种关联,并且被告主观上确有明显利用波士顿马拉松赛知名度并从中获利的意图,因此,法院认为,消费者可能对被告服装的产品来源或赞助关系产生混淆。
在随后的Pirone诉麦克米伦公司案④Pirone v. MacMillan, Inc., 894 F.2d 579, 581 (2d Cir. 1990).中,法院就如何判断伏击营销行为的混淆可能性作了进一步探索。在该案中,已故著名棒球运动员贝比•鲁斯的女儿Pirone于1948年8月将其父姓名申请注册为商标。随后,麦克米伦公司在其出版的一本日历中使用了贝比•鲁斯等运动员的照片。于是Pirone向联邦法院起诉麦克米伦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其所持有的商标。法院指出,“Pirone认为她对其注册商标的权利涵盖贝比•鲁斯拍过的每张照片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麦克米伦日历使用贝比•鲁斯的名字和图片是为了指代一个著名棒球运动员,而并非将其作为一个商标来使用”,并且“构成商标侵权的关键因素在于涉案行为是否有可能使大量普通且谨慎的消费者被误导或致使其对于商品来源产生困惑。而公众相信该商标的所有人赞助或认可对商标的使用也是混淆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在该案中,麦克米伦公司已在封面、版权页等位置明示过日历的来源,而且贝比•鲁斯的照片是包含在诸多运动员照片之中的。因此,法院最终认为,一个普通且谨慎的消费者在辨别这些照片时不会遇到任何障碍,也不会对赞助关系产生疑惑,不存在产生混淆的可能性。
在华纳兄弟公司诉盖伊玩具公司案⑤Warner Brothers., Inc. v. Gay Toys, Inc., 658 F.2d 76, 78 (2d Cir. 1981).中,华纳兄弟公司诉称盖伊玩具公司制造的迪克西赛车仿制于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热门电视剧《正义前锋》中的汽车原型“李将军”。尽管盖伊公司并未直接套用剧集中“李将军”的名字,但是该款玩具汽车在外形等许多方面与电视剧中“李将军”都极为相似。华纳兄弟公司指控被告生产的玩具汽车违反了《兰哈姆法》第43条(a)项,因为迪克西赛车会引发消费者对于该玩具车生产和赞助关系的混淆,并可能引发公众误认为迪克西赛车是一款复制“李将军”并获得授权的玩具。一审法院认为,华纳兄弟公司并未涉足玩具车制造行业且没有证据显示存在混淆的可能性。该案在上诉到第二巡回法院后,巡回法院推翻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并认为,“有足够的可能性造成消费者对迪克西赛车来源与赞助关系的混淆。”⑥法院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发现,80%的受调查者已经将迪克西赛车视为“李将军”或《正义前锋》中的汽车,并且推测华纳兄弟公司已经授权给了该玩具汽车。Id. at 79.
由此可见,伏击营销行为与商标法的交错主要集中于未获得特定活动主办方授权的经营者创造与特定活动的关联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具体而言,伏击营销行为要构成商标侵权需满足两个要件。第一,伏击者对特定活动商标的使用。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主要包含商标权人自己或许可他人使用以及他人未经权利人同意而使用两种情形。前者与维护商标权效力有关,后者的使用与是否构成商标侵权有关,亦即他人的使用行为是否构成侵害商标权的使用。我国《商标法》第48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该条主要目的在于规范商标的使用,预防发生商品来源的混淆,其核心是使用行为是否有引起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或损害商标的显著性。这里的使用不限于行为人在商品上的实际使用,在媒体广告、说明书、目录上或网页上使用商标亦有引起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伏击行为若损害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和消费者权益,则会受到商标法的规制。根据《商标法》第48条规定,商标的使用要件包括使用形式是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基本涵盖了伏击营销行为的可能使用形式,而判断一项伏击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标准在于其使用方式是否足以使相关消费者认为其系商标。此判断标准主要是从相关消费者观点出发,由相关消费者的认知检视该使用是否构成商标的使用,是否发挥了商标的基本功能。伏击营销若涉及到商标使用或商标部分要素的使用,则有可能构成商标侵权。
第二,伏击营销行为存在混淆可能性。是否具有混淆可能性是伏击行为构成商标侵权的结果要件。通常,伏击营销会造成两种混淆结果:一是误导消费者使其误认为伏击营销行为与特定商标具有同一来源。这种混淆是指消费者清楚知道两种商品或服务并不相同,但伏击营销涉及的商品或服务与特定活动商标相同或近似,从而使消费者误以为两者来自相同的提供者。例如,在华纳兄弟公司诉盖伊玩具公司案中,《正义前锋》的观众在商场中看到与剧中汽车极为相似的迪克西赛车,就可能会误以为后者也是前者生产的商品。在这种类型的混淆中,商品或服务往往存在着特定的关联性。二是误导消费者使其误认为伏击者具有授权、赞助关系或为关系企业。这种类型的混淆是指消费者非但没有误认两种商品或服务,而且也清楚地知道两者的来源不相同。但由于伏击者使用相同或类似的商标,导致消费者误以为伏击营销行为所涉商品是经过商标权人授权、赞助或认可的商品或服务。当伏击营销行为满足作为商标使用以及具有混淆可能性两项要件时,该伏击行为就有可能构成对特定活动商标的侵权行为,从而受到商标法的规制。
三、伏击营销的法益分析
上述分析不仅明确了伏击营销行为的违法特性,而且也表明现有商标制度对规制违法的伏击营销行为具备基本的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文体活动的主办方与赞助商对现有商标制度关于伏击营销行为的规制手段和力度仍不甚满意,以致于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全球性赛事通常需要通过专门立法的形式来保护其商标权。但这种专门立法为了强化执法效果,往往有悖于基本的知识产权法理。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文体活动并不能采用专门立法的形式来保障其自身权益。鉴此,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伏击营销行为背后的法益关系,以求从现有商标制度中获得解决伏击营销困境的解决思路。
如下图所示,伏击营销行为的利益相关主体主要包括特定活动主办方、活动赞助商以及实施伏击行为的经营者。而连结三个利益相关主体的是三对关系:一是活动主办方与赞助商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二是赞助商与伏击者之间的竞争关系,这对关系中包含赞助商对活动商标的排他使用权以及伏击者的商业言论自由等权益内容;三是活动主办方与伏击者之间关于侵犯商标权和公共利益等内容的冲突关系。

伏击营销行为的利益相关主体图
在这三对关系中,最主要的是活动主办方与赞助商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其法律载体为双方订立的赞助合同。根据该合同,赞助商通过支付一定金额的赞助费以换取活动主办方许可其使用特定活动商标的排他性权利,而该行为实际上是赞助商对商标所代表的特定活动巨大商业潜力的一种合理期待。因此,在面对可能威胁其经济利益和排他性权利的伏击营销行为时,赞助商总是持否定态度,并不断向主办方施压以求对伏击营销行为予以严格打击。一般而言,伏击者是与赞助商有一定竞争关系的营利性经营者,而过分强调赞助商对特定活动商标的排他使用权以及赞助关系使得社会公众普遍缺乏对伏击者商业言论自由的关注。如前所述,赞助商支付赞助费换取商标使用权的行为实际上是基于对商标所代表的特定活动巨大商业潜力的一种合理期待,那么对于与赞助商具有密切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而言,特定活动同样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声誉。而这些商业潜力与声誉并不是由活动主办方或者某个赞助商所独享的。例如,奥运或世界杯等大型国际比赛的声誉是建立在国际及各国活动组织、参与运动的联盟、队伍、运动员以及提供资助的经营者等各方面通力合作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官方赞助商通常属于类别专属赞助(Category Exclusive Sponsorships),因此赞助商只是特定活动的某类别赞助,其赞助关系不能够涵盖围绕该特定活动而产生的所有主题空间(Thematic Space)。⑦Anita M. Moorman, Christopher T. Greenwell, Consumer Attitudes of Deception and the Legality of Ambush Marketing Practices, 15 Journal of Legal Aspects of Sport 2005 183.鉴于此,特定活动的声誉、商业价值乃至吸引力、影响力均为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具有强烈的公共利益属性。这也是隐含在主办方与伏击者之间的法益基础。另外,伏击营销在某种程度上也提升了特定活动的声望与知名度,增加了活动的社会价值,也为特定活动举办城市创造更多的收益,促进了举办城市经济繁荣。⑧E. Vassallo, K. Blemaster and P. Werner, An International Look at Ambush Marketing, 95 Trademark Reporter 1338, 1355 (2005).事实上,尽管伏击营销在每届奥运会中屡见不鲜,但每届奥运会赞助费均有大幅提升。据资料显示,国际奥委会在2001年至2004年间收到超过14亿美元的赞助费。⑨Jenifer Donatuti, Can China Protect the Olympics, or Should the Olympics be Protected From China?, 15 J.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203, 207 (2007).仅国际奥委会最高级别的赞助关系“奥运合作伙伴计划”的赞助费在近些年就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从1985年~1988年间的9600万美元,猛增至2005年~2008年间的8.66亿美元。⑩Id.因此,采用伏击营销策略的经营者并不必然侵犯他人商标权,其伏击行为首先属于经营者商业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有其合法的实施空间。但不可否认,该伏击行为一旦超过一定界限,构成对主办方特定活动商标权的侵犯,则不仅会损害主办方的合法权益,更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四、商标法对伏击营销的回应
在明确了伏击营销的法益脉络后,还需要对形态多元的伏击营销从商标法的规则和实施角度予以完善,才能实现主办方、赞助商、伏击者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利益平衡。
首先,应平衡特定活动注册商标的显著性与商标保护范围的关系。具有显著性的商标与商品相结合并在市场上使用,消费者会立即认为它们指示了该特定商品的来源,使用人无需就它们具有了商标的显著性进行证明,而不具有显著性的商标则不能获得商标注册。我国《商标法》第9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此处“便于识别”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人们看到商标上的某种标识,能够意识到这是表明商品来源的商标;二是意识到其为商标后,还能进一步与同类商品的其他商标进行区分。可见,标识具有独特性只是满足了视觉上的差异效果,但未必能让消费者意识到这就是商标。由于商标的本质在于防止消费者产生混淆并标明商品来源,因此当一个商业标识甚至让消费者都不能意识到是商标时,自然不符合商标注册的显著性条件。由于伏击营销活动常利用活动名称或其它活动特征来创建与该活动的关联,为了防止任何未经授权或赞助的经营者藉由建立与活动的关连获得利益,以保护赞助商的经济利益,活动主办方通常倾向于将活动名称申请注册文字商标。此种文字商标通常为活动名称或其缩写简称、举办年份、举办国家或城市、活动组织等要素的排列组合。这种组合一旦被赋予商标权,就意味着该商标权人以及获得许可使用权的经营者拥有了极大的竞争优势。对于消费者而言,这种组合虽能指示特定活动本身,但仅限于有提醒或告知消费者活动信息或事实的功能,无法实现区别与他人商品或服务的效果。因此,活动主办方为特定活动注册的包含有活动名称等文字内容的标识常存在显著性缺失的疑虑。这种标识不仅不会使消费者认为商品及服务是在活动主办方授权下生产或提供的,而且也不会使消费者认为活动主办方如同商品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一样可对其品质负责。由于活动主办方申请活动文字商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遏制伏击者擅自使用与该活动相关的文字,因此其倾向于将与特定活动相关的文字纳入商标法保护范围,但包含越多越详细的活动相关文字,就越有可能导致该组合标识成为说明性标识而无法获得注册,两者呈现矛盾冲突的关系。这种矛盾关系使得活动主办方在藉由注册商标保护官方赞助商商业利益时,除了考虑商标权的保护要件外,更应斟酌商标权的排他使用效应以及维持包括伏击者商业言论自由在内的公众自由使用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其次,应斟酌混淆可能性的判断标准。如前所述,混淆可能性的判断标准决定了伏击营销行为人使用活动商标或商标部分元素的范围限制。在伏击营销的侵权行为发生后,活动主办方在争讼维权过程中还应关注司法机关对混淆可能性的判断标准。虽然混淆可能性的认定应当依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形而定,但建立判断混淆可能性的基本框架仍有助于司法机关以及伏击行为的利益相关主体对涉案商标的混淆可能性形成基本的预测。在1961年的宝丽来公司诉波乐拉电子公司案①Polaroid Corp. v. Polarad Electronics Corp., 287 F.2d 492 (2d Cir. 1961).中,弗兰德力法官提出了一套混淆可能性的测试法,具有一定代表性。在该案中,原告宝丽来公司控告被告波乐拉电子公司侵犯其“POLAROID”商标。被告波乐拉公司使用该商标的主要业务为销售电视以及产生、接收及度量微波的装置。被告声称其商标是自创并未抄袭原告的商标。经双方举证,原被告仅有一款滤波器在功能上有一定相似性,其余产品均不相同。但原告宝丽来生产的滤波器性能并不稳定。该案中,法院提出应从被侵害商标的强度、商标间的相似程度、产品的近似性、先使用人缩小差距的可能性、实际混淆、被告使用商标的善意、被告产品的质量以及购买人的谨慎程度等因素考虑混淆可能性。除此之外,还应注意混淆可能性的内涵。我国商标法所用的“混淆可能性”在英文中对应的术语为“Likelihood of confusion”。但在美国判例中,仅仅有可能混淆并不等同于混淆可能性,还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要求才能使有可能变成有机会并且才会构成混淆可能性。因此,“Likelihood of Confusion”也是“Probable Confusion”的代名词,但其与“Possible Confusion”仍不同。②J. Thomas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23:3 (Fourth Edition).美国判例法也曾一度认为,由于消费者高度依赖商标来辨识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因此只要有可能混淆,而无论其可能性如何,就可发出禁制令。但在1999年于A & H 运动服装公司诉维多利亚秘密公司一案③A & H Sportswear, Inc.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 166 F.3d 197, 49 U.S.P.Q.2d 1481 (3d Cir. 1999).中,第三巡回法院认为,“依据《兰哈姆法》的规定,商标的侵权判断应该是基于混淆可能性。”④Id. at 205.这一观点随后被美国司法系统所广泛采纳,认为商标的侵权判断应该是基于混淆可能性,而非是有可能混淆误认。
第三,应强化免责声明的适用。为了达到告知信息接受者或消费者当事人之间没有关联的特殊目的,有些埋伏营销会在产品上或在销售场所使用免责声明。免责声明能够有效降低混淆的可能性,有助于减少特定活动商标对伏击者商业言论自由的限制。但免责信息并不能自动转化为预期的影响,也无法立即为信息接受者正确理解,因此,不当的免责声明非但不能澄清混淆,还可能加强消费者的混淆可能性。例如,在乔治亚大学田径协会诉莱特案⑤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letic Association v. Laite, 756 F.2d 1535 (11th Cir. 1985).中,被告莱特以红色与黑色且绘有英国牛头犬的酒瓶销售战斗牛头犬啤酒,而该牛头犬图案与乔治亚大学的吉祥物近似。法院认为,使用与该学校颜色及吉祥物相似包装的行为有暗示经该大学授权、核准或赞助的混淆可能性。即使被告在酒瓶上使用免责声明,但法院认为,该免责声明标示过小且未能澄清混淆可能性,因而无效。因此,伏击者在使用免责声明时,应注意其大小、颜色、在产品上或销售地点的位置等,以显著的方式使消费者知悉此事与活动组织并无关联,则可有效预防消费者混淆可能性。另外,伏击营销在使用显著免责声明的同时,有可能会失去一些重视与特定活动关联的消费者,有损原本营销策略的成效,但这是追求行为合法而不可避免的矛盾,尚需伏击营销行为人自行衡量。但不可否认的是,有效的免责声明的确可防止混淆的发生,从而使伏击营销在法律上有更大的适用空间。fffff5
Ambush marketing is one of social phenomenon with mixed reviews in modern culture and sports activ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mark law,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ehavior of ambush marketing in order to grasp the basic characterize and the lawful boundaries of ambush marketing and understand the various confl icts of interests during the ambush marketing practices. Based on the idea of balance of interests,it is suggested to resolve the confl ict among the all related subjects using the rule of trademark law and seek to solution of ambush marketing issue from existed legal system.
ambush marketing; trademark infringement;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interest balance
周围,武汉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210601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