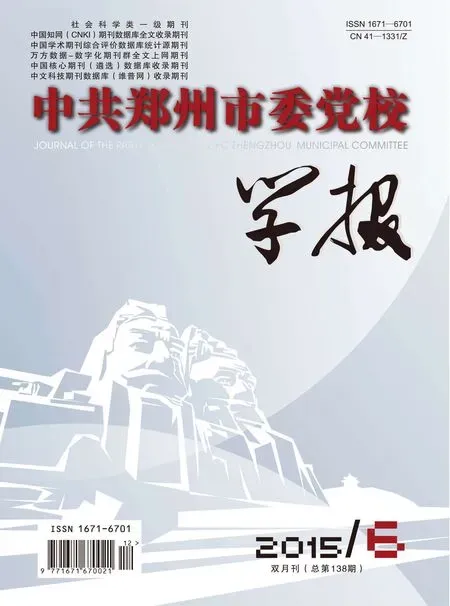移民族群的生存状态变迁与社会融合——对闽北一个移民村落的实证研究
2015-01-30林丽琴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学教研部福建福州350001
林丽琴(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学教研部,福建福州350001)
移民族群的生存状态变迁与社会融合——对闽北一个移民村落的实证研究
林丽琴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学教研部,福建福州350001)
摘要:闽北偏远T村移民族群在历经50年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政治制度的变迁后,移民族与原住民的生存状态存在同质化与异质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与社会融合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过程,探究考察移民迁移后的生产生活、社会融合、身份归属等要素的重塑,探讨生态移民对移民族群的生存状态的变迁及社会融合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此类生态变迁形态对移民主体和迁入地的影响。
关键词:移民族群;生存状态;社会融合
一、研究思路、对象与方法
1.研究思路。本论文以闽北山区的扶贫开发移民村落作为研究对象,在迁出地与迁入地文化经济资源等要素存在多元性差异的条件下,通过对闽北T村移民的专门研究,探究两地原有的文化在调适融合过程中所导致的文化冲突和社会问题,考察移民迁移后的生产生活、社会融合、身份归属等要素的重塑,探讨生态移民对移民族群的生存状态的变迁及社会融合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此类生态变迁形态对移民主体和迁入地的影响。
2.研究对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移民工作。福建闽北于1955年上半年成立移民工作机构,负责接收安置移民。1955 至1966年因战备需要,沿海的福州、福清、莆田、惠安先后有一些居民迁入定居,称为志愿开发山区社会主义建设劳动者。1965年9月20日,55对年轻夫妻从他们的原生地——莆田X村移入闽北偏远T村。2015年正是这批移民在移入地生活历程的50周年,本文以此为研究背景,以T村移民族群为研究对象,探究这批移民族群生存状态的变迁与社会融合。
3.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视野出发,采用理论与实证研究,运用定性调查(田野调查),采用多元的方法收集资料,包括访谈、观察、文献二手资料、实物照片等。田野调查过程重视研究的信度与效度,对整体性的事件、访谈场景进行白描与深描结合,用一个事实解释另一个事实的存在,反映社会事实周围的关联性。围绕“移民族群的生活变迁与社会融合”的研究焦点,进行定性抽样。抽样包括访谈的人、抽样现场、抽样事件、抽样过程、抽样时间,既有调查典型样本也有调查异质样本。采用三角检验法支持研究假设、建立了特定的对比事件与现场并用访谈法、用观察法、用文献法这三种方法从不同维度和不同的命题来支撑研究假设。
二、移民族群生存状态变迁
1.移民家庭结构状况。根据资料统计,1965年55户移民家庭迁入T村,其间户籍返回莆田原生地的3户。2015年9月20日参加自发组织的庆祝移民50周年聚餐的在册登记移民家庭和移民二代家庭已达189户。移民家庭生育的孩子最少的家庭育有二个,最多的家庭育有八个,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留在村落务农的移民二代的婚姻也都是族群内通婚,没有与原住民家庭通婚。婚姻是移民族群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是移民族群团结不散的一块基石。长期的族群生产劳动建构了婚姻关系中的共同文化特质、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的经济基础。这说明移民族群在观念上,仍然保存着对族群文化的执着与眷恋,反映出他们对自己文化特征和经济结构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对族群的团结不散具有正偏离的作用。移民族群通过婚姻关系形成一个庞大的亲族网络,这个网络对族群在村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
2.移民族群的心灵空间。在移民初期,移民族群都本着要迁回原生地的梦想,所以早期建设的住宅都是狭小的土坯房,但最终只有3户能迁回原生地。移民一代对故乡思念表现在每年春节都会返回莆田探亲,日常生活中只要有人回莆田都会委托其携带礼品送给故乡的亲人。访谈中,老人说“你们爱自己娘家,我也爱自己的娘家啊”。他们每次从电视上看到台风来袭福建沿海,就无比担心故乡待丰收的龙眼。故乡的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们的心。由于移民二代多数是在迁入地出生并成长,对迁出地的情感弱于移民第一代的情感,但语言上都会说莆田地方母语。移民的第三代与原住民的通婚情况是普遍的,第三代几乎没有会说莆田地方母语的了,这说明移民的后代历经二代已逐渐融合并共同建构迁入地的社会。
3.移民族群的归属感。移民的归属感是考量移民族群融入迁入地的一项重要指标。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可以被用来解释移民的归属感。按照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场域是存在于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各种关系结合而成的空间结构形态,是行动者实践的场所。惯习是特定场域中的个人和群体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智模式和行为方式。对移民族群来说,移民使他们的生活场域发生了变化。迁入地是一个全新的物质生活空间,又是一个包括各种关系、权力和制度的社会空间。初期,在迁入地移民族群集中居住的方式建构了属于自己的场域,内化于身的惯习依然可以游刃有余,克服了移民在初期表现的一定不适应,如彷徨、焦虑、排斥等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族群在迁入地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得到不断提高,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增强了他们在迁入地的归属感。
4.移民老人赡养状况。55户移民家庭在移入地生活了50年期间,婚姻是核心家庭裂变的基本方式,随着移民二代的“成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分家”,不断产生新的家庭。分家是T村移民家庭裂变的基本方式,儿子成家以后就要分家,并签订分家协议。50年时间过去了,55对年轻的移民夫妇都已是70至85岁的老人,有些已离世,健在的73人。这些老人的赡养方式有几种:一是老人自己住,儿女共同提供生活费;二是老人到几个儿子家轮流住,由儿子赡养;三是老人自己住,儿子平均给父母提供粮食。第一种赡养方式主要体现在郑氏、林氏、方氏等5个家庭。这5个家庭的共同点就是儿女们有的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在城市里工作,有的在外地做生意,儿女们都没有“分家”,儿女不是按照平均原则提供给父母的生活费,是自发与自觉地提供。田野访谈中5个家庭的老人均表达儿女很孝顺,很满足了。第二种赡养方式与第三种赡养方式的占比率是相似的。两者的相同点体现在儿子家庭都是以务农为主要生存方式;两者的差异性体现在第二种赡养方式,且父母已离世一个,采取第三种赡养方式的是父母双亲都还健在。赡养是家庭社会功能的表现之一。养儿防老,是农村赡养的主要模式。在T村移民社区规模普遍较小、子女分户居住情况较多,家庭赡养功能基本得到保持的原因主要在于族群秉承着莆田传统孝文化,保持一种恒稳的族群凝聚力。莆田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誉,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孝文化作为莆田文化的组成,也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从福建省志及莆田历代所编修的孝友传记中可以大致看出其演变过程。清朝的康熙、乾隆、道光时期所修的《福建通志》里面收录了大量莆田地方的孝友传记[1]。T村的移民家庭在迁入地自觉地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宗族社会,莆田传统孝文化在移民族群中依然代代相传与影响。由于移民家庭文化的同质性,移民族群容易形成统一的社会舆论和社会问题。老人以群体的方式直接面对移民族群,形成受大家关注的社会群体。移民族群对于子女孝敬父母视为责任、尊为荣誉,并规范着移民二代的家庭的赡养行为,不赡养老人的行为,在族群中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形成是移民族群这个社会结构所决定。赡养模式的差异性归因于移民二代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性和他们的经济能力。
5.移民社会网络。移民的迁徙不仅是人口的空间迁移和变动过程,也是社会网络变迁的过程。由于迁出地都是莆田的同一个村落,他们在迁出之前都已相识,到了迁入地,陌生的环境和对未来的彷徨更增强了移民族群团结的凝聚力。20世纪70至80年代,移民族群的交往对象同质性强。由于当时迁出地土地资源的匮乏和人口的密集,许多移民的家乡亲戚定期来到T村务工务农。这种存在于群体内部的、彼此熟悉的关系网络构筑了一个具有较强内聚力的生活共同体。它的作用在于族群内人员能够同舟共济、共渡难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迁出地的沿海经济开始蓬勃发展,移民的亲戚很少到迁入地务工务农,移民的亲缘关系有一定程度的削弱,村落中业缘关系逐渐发展。移民族群利用迁入地的山林资源开办竹器产品的加工工厂,增加了村落的劳动力就业机会,改变了村落的经济结构不再单纯以农耕为主。移民族群的生活场域已融合到村落中,增强了两族群的生产劳动协作机会。群际间的交往以及由于这种交往构成的广泛网络所给予的各方面支持,是现代化社会中个体与群体进行社会整合的关键所在[2]。这种两族群紧密配合的生产协作模式形成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发展型的社会资本,为移民族群带来异质性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了村落经济的发展。
三、移民族群的社会融合
1.文化融合。第一,教育融合。“社会化是人们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学习社会知识、技能和规范,从而形成自觉遵守与维护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过程”。闽北T村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大学生是郑氏移民家庭的大儿子于1981年考上了厦门大学历史系,其两弟弟也相继考上了大中专院校。T村的第一位女大学生是林氏移民家庭的小女儿,她于1994年考上了一本院校,其二位兄长也都考上了大中专院校。据统计1990至1994年(大学人数扩招改革之前),T村的移民家庭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子女有7人。而T村原住民的子女都是在1994年以后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可以看出,移民家庭相对于原住民家庭更重视教育。移民家庭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对教育的重视通常寓于日常生活中,通过自身的田间辛勤劳作的行为来言传身教子女刻苦读书。“儿童从一出生起就因为家庭的种族、阶级、宗教、地域特征而具有一种先赋性的角色设定。这一点将对儿童以后的社会化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3]。由于相对丰富的族群活动及其较强的教化功能,移民族群承担了从家庭外移的教育功能。族群教育主要是通过移民族群从移出地带来的民俗活动,如通过对传统习俗的记载,把这些民族苦难历史,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例如元宵出游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祭祀活动对后代进行教育。儿童在成长的历程中传承了莆田历史文化,增强对族群的认同及凝聚力。田野访谈中笔者发现许多70岁以上不识字的老人却能时常道出许多极富有文化韵味的语言,例如“想穿草鞋还是想穿皮鞋,关键在于书读得好不好”“夏天风没空,冬天风找空”“白露秋风,白天晚上对半分”“只要母鸡在家乡,在任何地方的小鸡总会咯咯咯回家”等。这些都是族群教育的文化场域,使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得到族群文化熏陶和共同价值观的树立。田野调研中发现考上大中专院校的移民二代都是集中在几个移民家庭中的兄妹。良好的教育家风、丰富的传统文化和族群教育培育移民二代走出大山、摆脱贫困,并形成良性的连锁反应和竞争环境,不仅影响了移民族群的孩子努力读书,也拉动了原住民的孩子读书的积极性,使T村越来越多的孩子考上了大学。第二,语言融合。1965年移民成员中会说普通话的人很少,文化程度低。特别是移民女性,她们只会说莆田本土方言。虽然语言不相通在早期生活与生产上造成了许多不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与生产的融合,移民族群所有成员都能用普通话与原住民进行沟通。移民族群的语言与原住民语言彼此扩散与渗透形成一种语言融合的语境。语言的融合为两族群的日常生活融合起着重要的推力作用。第三,生活习俗融合。生活习俗是人们长期生活中,在服饰、饮食、居住、建筑等各个方面所形成的一种习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4]。服饰是生活习俗中最具符号意义的体现,也是移民文化变迁进程中外在化的表征。生活习俗既是日常生活中最微观、琐碎的社会现象,也是最能够体现传统文化寻求适应的具体表象。闽越文化构成了莆田区域文化的主体内容,在服饰方面莆田女性的服饰与惠安女的服饰有相似之处。移民女性田间劳作时都是戴细、薄、轻、小的斗笠,头发盘成发髻并插上田间小花。田野调研中发现这批70多岁的移民女性依然保持着莆田传统的特色服饰和发型,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莆田人。饮食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借鉴与交流,但是两族群的婚丧嫁娶的人情往来直到移民的第三代相互通婚才开始。
2.经济融合。第一,农耕合作模式。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农忙时期,特别是夏天双季水稻的“双抢”季节,移民家庭耕种农田面积大,都面临着畜力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移民家庭采用搭套、换工的农耕合作模式。搭套、换工合作模式的特点是一般限于二、三户农家之间进行共同使用畜力、农具和交换人力进行生产劳动。这种小规模的农耕结合形式在提高农耕效率,维持农业生产力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增强了移民族群的团结和凝聚力,形成一个友爱互助的移民族群的村落共同体。第二,租赁劳动力。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带来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工涌入城市造成村落劳动力减少,移民族群解析出贫雇农与富农的阶层,族群内部带有一定共同体感情色彩的农耕合作模式已不能满足不同阶层农民的各方面需求,相对更为适合保护个人利益的有偿租赁劳动力的模式开始成长壮大起来。有偿租赁劳动力、自我中心主义的扩张,弱化了族群共同体成员的农耕合作的亲密感情,分解了族群协作共同体。在政府农业种植技术指导下,全村积极种植烟叶,拓宽了农业种植种类,加快实现农民致富的道路。有偿租赁劳动力已成为T村经济协作主要模式。现在全村农户都在积极耕种烟叶,每户一年净收入可达3万至6万元,家家都盖起了漂亮的小洋楼。因为种植烟叶收益稳定,T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都已相继回归乡土。
3.公共权力的博弈。第一,宅基地与耕地的分配。50年来,移民族群与原住民在同一村落生存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资源竞争与权益的博弈。资源竞争理论认为,冲突是因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在不同人群中的争夺而产生的[5]。早期,T村原住民宅基地都是远离贯穿村落的主要交通公路,并形成村落核心区。主要的原因是以前的农村公路都是沙土飞扬,不适合居住在公路旁。移民族群只能开垦沙土飞扬的公路两旁的空地作为自己的宅基地。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村落的规划建设相应发展。曾经沙土飞扬的公路变成干净、宽广的水泥公路,村落核心区已转移到以公路为中轴线的周边,并建设了村落的农产品交易中心与村委大楼。1965年至1978年(人民公社时期)55户移民家庭组成三个生产小队参加农村人民公社集体劳动。1979年国家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闽北T村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把耕地按每户的人口、劳力承包到户的同时,也把每户应完成的农业税和出售给国家的农产品品种、数量,以及每户应上交给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等落实到户。农户的产品收益,除了完成上述国家任务和集体提留外,剩余部分全部归农户所得。移民族群分到T村最平坦最肥沃的农田耕种,主要原因是每户要求完成的农业税和集体提成,与农田的优劣程度成正比。T村原住民选择了山边的梯田和烂泥田,因为可以少交农业税。原住民认为移民户的主要责任就是开发当地农业,所以应该承担更多的农业劳动。历史证明,原住民当时的选择是狭隘的。国家农业政策在不断改革,集体提成取消、农业税取消,平坦与肥沃的农田更适应耕种,也能带来更高利润的农副产品。例如:竹荪、烟叶等。在村落中,移民族群与原住民基于宅基地与耕地资源的竞争是以双方最初选择决定的,并建构起族群之间的社会边界。50年期间,两族群在宅基地和耕地资源竞争层面的大冲突事件没有发生过,促进了移民族群社会融入和村落经济发展。第二,公共权力的博弈。在村落政治领域,两族群之间发生的资源竞争,集中在公共权力的竞争。谁拥有公共权力,谁就拥有利用社会资源、制度性资源的机会。族群民族主义在理论原理上,相信特定的族群精英能够代表族群的整体利益[6]。每一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两族群都有代表参加村委干部的竞选,竞选的过程也很紧张与激烈。为了拉选票双方都会号召在外地做生意或在城市打工的同族人千里迢迢赶回村落进行投票。50年的时间,虽然两族群在经济生产、社会文化与通婚都深度接触与融合,但在政治领域的竞争,族群边界却依然清晰化。
四、总结
移民的生存状态变迁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复杂的过程。社会融合是移民族群积极应对自然环境变化、生存空间转移和社会环境的一种带有建构意义的调适。第一,返回不了迁出地的事实和移民族群自身强烈发展的愿望共同构成了移民族群社会融合的重要动力。社会融合就是不同的族群经过长期的接触、联系、调整改变原来的性质、模式的过程,是一种新的综合过程。一方面,移民族群在迁入地受到原住民文化的同质化,如移民的第三代对母语的忘却、移民后代对迁出地的情感弱化等都是移民文化被迁入地文化同质化的表象。另一方面,移民族群对迁入地在经济、教育等方向产生了拉力作用。这种拉力作用经过50年时间验证已凸显出来。移民族群的发展对原住民的影响是全方位、宽领域、多途径的,这种外在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迫使原住民做出相应的回应。原住民强烈地感知到自身族群的教育重视度与奋斗精神的差距。于是,两族群形成良性的竞争,促进村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第二,移民生存状态的变迁与社会融合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过程。移民生存状态的变迁与社会融合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移民的社会融合确保了移民生存状态变迁的可持续性,而移民生存状态变迁的过程又不断地促进着移民社会融合。
参考文献
[1]梁艳.从方志孝友传记看莆田传统孝文化[J].莆田学院学报,2014,(1).
[2]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5.
[3]邓志伟,徐榕.家庭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69.
[4]马小平.人类学视野下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10.25.
[5]关凯.社会竞争与族群建构: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J].民族研究,2012,(5).
[6][俄]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M].姜德顺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王亚伟]
作者简介:林丽琴(1976—),女,福建莆田人,硕士,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学教研部讲师。
收稿日期:2015-10-05
中图分类号:D6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701(2015)06-007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