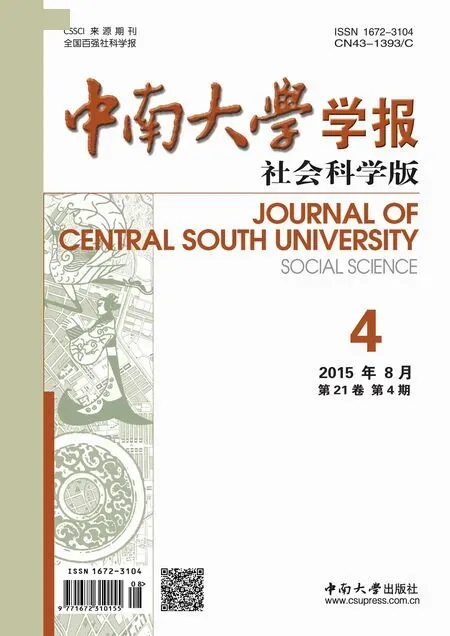论穆旦诗歌对现代“异化”个体的抒写
2015-01-21马春光
马春光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论穆旦诗歌对现代“异化”个体的抒写
马春光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现代社会对生命个体的“异化”是穆旦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穆旦在三个层面上对“异化”展开抒写。一是通过对“被压迫、被蹂躏的肉体”的诗性表达,抒写战争以及现代社会规训体制中身体的异化体验及其反抗;二是通过对“20世纪”“八小时”等现代时间意象的深度观照,彰显“现代时间”中生命个体的“异化”生存;三是通过对现代城市“灿烂整齐的空洞”的象征化抒写,展现现代城市空间中生命个体的“异化”生存景观。穆旦对现代生命个体“异化”的抒写是其对现代中国生存困境的诗性表达,这是穆旦精神探索内在悲剧的外在体现,在更深层上彰显了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的内在困境。
穆旦;异化;身体;生存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性”话语范式在中国新诗研究中的确立,现代主义诗歌日渐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新诗史在“现代性”的视阈中被不断重构,诗人穆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新诗现代性的代表人物被不断讨论。这无疑极大地拓展了穆旦研究的空间,穆旦成为新诗研究中一个持续的热点①,但与此同时,穆旦诗歌似乎承载了过多的学术期许,学界对其诗歌的研究也日渐形成一种“现代性”阐释的内循环,导致对其诗歌文本的“过度阐释”。概言之,穆旦诗歌的研究空间深嵌在“现代性”的话语装置中,已呈现日趋封闭之势。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跳出这一“装置”,从另外的角度对穆旦诗歌及其现代性进行反思,就成为穆旦研究的潜在命题。异化,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一角度。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异化”在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西方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详尽的阐释,“异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它‘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1](163),并在生命个体的生存图景中得以呈现。现代生命个体的异化是穆旦所极力表达的诗歌主题之一,他在诗歌中始终关注生命个体在现代社会的异化遭遇。另外,“对异化问题的思考与对现代性的反思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对现代性的反思不可能回避异化问题”[2](202)。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穆旦的诗歌文本出发,窥测其诗歌对现代异化个体的多维度抒写,并试图探索“异化”抒写背后的内在精神结构,以及这种艺术探询在新诗传统赓续、现代诗歌精神建构等方面的贡献与启示。
一、对身体异化的抒写与反思
早在1946年,穆旦的同学、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就敏锐地指出,穆旦诗歌“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3](158)。查阅穆旦诗集不难发现,“身体”是穆旦诗歌的贯穿性意象,同时构成了穆旦诗歌意蕴生成的基点。正如特纳所言,“一个社会的主要政治和个人问题都集中在身体上并通过身体得以体现。”[4]身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阐释穆旦诗歌的一个关键入口。在早期的《野兽》中,穆旦意义上的“肉体”这样出场:
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翻白的花,在青铜样的皮上!/是多大的奇迹,从紫色的血泊中/它抖身,它站立,它跃起,/风在鞭挞它痛楚的喘息。[3](3)
这首诗写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的1937年11月,穆旦用“野兽”这一意象隐喻战争中受伤的中国,支撑这一隐喻化书写的,正是其诗歌“用身体思想”的抒写特征,即用肉身的切实体验去思考更大更深的人生和时代命题。诗句对“坚实的肉”“血的沟渠”“翻白的花”“青铜样的皮”“紫色的血泊”等一系列被暴力异化的肉体形态的抒写,形象而又充满质感地传达了战争中诗人的异化体验。在此后的诗歌中,穆旦从切实可感的身体体验出发,以凝神睿智的诗性语言,揭示了“身体”在历史、现实中的种种异化情形,并逐渐延伸到“形而上”的哲学高度。写于1942年的《春》以锐利的语言对“肉体”展开探寻,并凸显了关乎“灵与肉”的哲理思考:“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3](74)在这里,穆旦所刻意表现的是“肉体”的封闭感,以及“被点燃”却又“无处归依”的生存悖论。与其说这是青春生命的骚动,不如说它写出了现代意识烛照下“灵与肉”的冲突。正像易彬所言,“‘被点燃’是自然本性,是生命的勃发;但‘无处归依’意味着阻遏,即所谓‘性别’‘思想’一类社会与文化的属性依然紧紧地压在‘肉体’之上,‘青春’或‘肉体’或‘欲望’依然是‘卑贱’的,是不可言说的。”[5]肉体的“紧闭”与“被点燃”形成一种巨大的内在张力,身体的异化状态昭然若揭。如果说这时的肉体是在生命的敞开与压抑的紧张关系中被异化,那么《线上》一诗则为我们呈现了生命敞开之后,来自社会内部的更深层的“身体异化”。
那无神的眼!那陷落的两肩!/痛苦的头脑现在已经安分!/那就要燃尽的蜡烛的火焰!//在摆着无数方向的原野上,/这时候,他一身担当过的事情/碾过他,却只碾出了一条细线。[3](97−98)
穆旦这首诗中“将异化的人生比喻为一条由别人规划完毕的流水线”[6],在这种形象化隐喻的背后,身体已经失却了那份鲜活与张力,被“异化”后迅速地凋敝:“无神的眼”“陷落的两肩”,最终“却只碾出了一条细线”。在这个意义上,穆旦的诗“记录了个体最终垮掉了的肉体和驯服的精神”[7]。这其中浸透着穆旦切身的异化体验,这是一个年轻的生命个体被置身其中的世界侵蚀、异化的过程。在“奖章”和他们“那无神的眼”“那陷落的两肩”的微妙对比中,异化的现实昭然若揭,“奖章”背后的社会秩序不断地要求着身体的自我异化。现代社会了无痕迹地戕害人的身体,“阉割”了作为生命个体存在之源的鲜活肉体,就这样,生命个体在身体被灼伤的同时,“被消解在给定的秩序中,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维度,成为与现状认同的单向度的人”[2](182)。
伴随着异化体验的深入,穆旦对“身体异化”这一历史问题展开了更加深邃的形而上思考。作为现代文明大厦赖以生成的现代知识体系,以及它的精髓——“智慧”,在穆旦的诗歌中获得了悖论式的表达。现代人所构筑的智慧大厦和信仰系统,铸造了生活在既定社会秩序中的“单面人”,“平衡”“平庸”构成了对个体生命超越的阻碍与包围:“零星的知识已使我们不再信任/血里的爱情”[3](66)。所谓“知识”对“血里的爱情”的“毒戕”,正是福柯所言的“心灵是身体的牢笼”的诗性表达。福柯认为,现代社会的规训体制其目的是制造“驯顺的肉体”,“要求其内心皈依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现代刑罚对心灵的控制本身就是一种更加隐晦却更为彻底的身体控制,因为改变心理态度和倾向的目的就在于控制身体的行为”[8]。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穆旦深谙其中道理,而20世纪40年代的参军经历又使他获得了异常丰富的现实感受。正是在沉痛的异化体验和精警的异化之思后,穆旦看到了漫长的历史中思想、文化对身体的独断和压制,企图对压制在“肉体”上的种种“思想”进行祛魅,这集中地体现在《我歌颂肉体》一诗中。
“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岩石/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
…………
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大树的根/摇吧,缤纷的枝叶,这里是你稳固的根基。[3](269−270)
诗人洞察到身体在历史中的扭曲、压抑与遮蔽,基于此,这首诗在思想指向上产生了一种对抗性,穆旦瞄准了思想史上种种对身体的异化,并试图对其进行反驳,这种反传统的立场正是出于对长期以来压抑身体的种种力量进行清理,但又不是惠特曼式的“自然主义”抒写,而是包涵了巨大的思想容量。在穆旦那里,肉体是生之本体,是“岩石”,是“种子”。穆旦对肉体的歌颂建立在对西方自柏拉图以降的灵肉冲突论思想的反叛基础上,尤其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对身体的排斥与遮蔽进行反驳。他清楚地意识到,在漫长的历史中思想和灵魂形成了对肉体实存的遮蔽,而生命个体面对社会异化的唯一的“根”就是我们的肉体,这是一切生命力的来源,它是抵抗社会异化的最坚实的力量。正像有论者指出的,《我歌颂肉体》这一诗歌文本“显示出一种赤裸裸的挑战姿态”[9]。这其中隐藏了穆旦对历史的警醒及对现实的愤怒。在穆旦“歌颂肉体”的背后,是其在1940年代的中国特定语境中对身体异化的敏锐洞见与深刻反思,并彰显出他企图拯救身体、对抗异化的努力。就诗歌思想的锐利与深度而言,穆旦代表了1940年代中国新诗的精神高度。
二、现代时间中的“异化”个体
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时间概念日渐被引介进中国并得以运用,据李欧梵所言,“中历和西历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世纪’的观念”[10]。随着清末民初严复、梁启超等人对西方现代思想的推介,以“世纪”为标示的线性时间观在中国得以落实,时间意义上的“现代中国”成为整体的生存语境。“20世纪”作为整体生存语境,在梁启超、郭沫若的诗歌中出现,彰显了诗人对“现代时间”的敏锐把握。在梁启超的诗歌《20世纪太平洋歌》以及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20世纪”是一个充满新鲜感的崭新时间向度。闻一多在读《女神》后专门撰文称其写出了“20世纪的时代的精神”[11]。如果说梁启超、郭沫若在诗歌中对“20世纪”的表达是对新生事物的一种诗意发现,那么在穆旦的诗歌中,“20世纪”这一时间意象被赋予更加丰富的意蕴,并释放出“丰富的痛苦”。与梁、郭不同,更年轻的穆旦更深地进入“20世纪”的生存场景,以一个诗人的方式,对之展开了洞察与反思。
穆旦着力思考的,是生命个体在“20世纪”所表征的“现代时间”中的困厄与无奈,按照线性时间观的价值逻辑,“20世纪”理应优于以往的任何世纪而呈现人类生存的进步样态,但穆旦以其坚实的生存体验发现,“20世纪”以其更大的“异己力量”对现代生命个体施予更深的异化。穆旦把视野聚焦在“现代时间”中的“农民兵”:“他们向前以我们遗弃的躯体/去迎接20世纪的杀伤。”[3](126)现代战争作为“20世纪”的高级产物,它本身一旦发动,就变成一种“异己”的力量,将“农民”异化为“兵”,“农民兵”这一称谓本身暗示的正是现代生命个体的异化。穆旦深刻认识到,随着“世纪”的直线向前延伸以及现代文明的持续发展,生命个体将面临更加显豁的异化。如《隐现》所言,“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3](239)新的世纪因而呈现出了“黑暗”的生存质地,在组诗《诗四首》中,穆旦以一种沉痛而决绝的语气反复强调,“迎接新的世纪来临!”[3](281),实际上他在“新的世纪”中感受到的,仍然是个体生命日益加剧的生存困境,因为“但世界还是只有一双遗传的手”[3](281),这是“永未伸直的世纪,未痊愈的冤屈”[3](282)。正是基于《农民兵》《隐现》《诗四首》等诗歌对“20世纪”的抒写,穆旦获得了对历史、时间的辩证思考,把诗思的触角更深地钻入“时间之维”中,去抚摸它的黑暗,洞察它对个体生命的杀伤。现代时间以其崭新的方式给予现代人更加“丰富的痛苦”,穆旦对盲目历史乐观主义的弃绝,对现代语境中生命个体的异化本质的揭示,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历史洞察力。
现代时间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一方面是直线向前的线性时间观规约了总体的生存情境,另一方面则是日常生活中周密而繁琐的时间规训体系。时间成为现代生命个体不可或缺的日常生存要素,成为现代社会规训体系的重要表征。如果说穆旦对“20世纪”的抒写体现了他对个体生存处境的鸟瞰式考察,那么他对“八小时”的反复抒写,则说明穆旦对“现代时间”的关注与思考植入了更加繁密的细部。八小时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制度性时间”,在穆旦的诗歌中反复出现:“八小时工作,挖成一颗空壳,/荡在尘网里,害怕把丝弄断,/蜘蛛嗅过了,知道没有用处。”[3](39)“八小时工作”是现代人不变的生活规则,这一时间规则建构了现代社会整饬的生活秩序。作为现代文明的叛逆者、反思者,穆旦在诗歌中呈现出“八小时”中的个体生存场景,从“八小时”中窥见了现代文明对生命个体的异化。《还原作用》运用近乎调侃的笔法呈现出异常醒目的现代时间制度中的异化现实。与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活状态截然不同,现代的“八小时工作”是一种人为的规约,生命的自然状态被消解,结果是“挖成一颗空壳”。“知道没有用处”则是对“八小时工作”意义的二次消解,“八小时”因此构成了现代个体生存的悖论:如果按照现代规训体系的时间要求,获得的是“空壳”和“没有用处”,否则就是“变形的枉然”。《还原作用》写于1940年,是青年穆旦遭遇异化现实的灵魂呼号。随着对现代时间更深地进入,他对“八小时”制度规约下的异化本质有了更加深邃的感知,展开了更加丰富的抒写。
在《线上》一诗中,穆旦在一种更阔大的时空背景中对“八小时”的生活做出描述:“八小时躲开了阳光和泥土/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在人世的吝啬里,要找到安全。”[3](97)“阳光和泥土”是自然意义上的生命之根源,诗歌中“八小时”是“躲开了”作为生命之源的“阳光与泥土”,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生命异化的根源所在。与“八小时”的制度时间相对应的,是“十年二十年”的累积。异化的生命个体正是在“异己力量”的长期规训与制约下,消失了对自身自由的感知与追求,“异化的人是一个抽象物,因为他失去了与人的所有特征的联系。他被简化为在被剥夺了人的多样性和同情的人们之间,对人类的无差别的目标执行无差别的工作。”[1](165)无数个生命个体在“一件事的末梢上”,构成整饬周密的现代社会体系,正是现代时间的规训使然。现代时间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异化”系统:“现代时间的强迫意识不只体现在以生产力为标准的工作范围中,它已经占据了所有生活领域。”[12]穆旦的敏锐洞见在写于1947年的《我想要走》中变成了生命个体对现代时间的“挣脱”结构:“我想要离开这普遍而无望的模仿,/这八小时的旋转和空虚的眼,/因为当恐惧扬起它的鞭子,/这么多罪恶我要洗消我的冤枉。”[3](258)“八小时的旋转”作为生存异化状态的典型表征,伴随的是“空虚的眼”(身体异化)和“恐惧扬起的鞭子”(精神异化),“我想要走”所昭示的,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出走,而恰恰是在时间的层面上对“现代”的挣脱与抵抗。现代时间一旦与空间融合,就铸造了现代时空的异化结构,这在穆旦的《成熟》中被浓缩为一个典型意象:“从中心压下挤在边沿的人们/已准确地踏进八小时的房屋,/这些我都看见了是一个阴谋,/随着每日的阳光使我们成熟。”[3](92)“八小时的房屋”正对应了穆旦写作于1942年的《出发》中的“囚进现在”的经典表述,在这里时间被固定化,生命个体处于非自由的“囚禁”状态。“八小时的房屋”在主体精神上赓续了鲁迅“铁屋子”的隐喻化表述,鲁迅所探寻的生存个体对古老世界的挣脱问题,在穆旦这里延续为新的时代语境中生存个体对异化现实的警醒与反抗。
综而言之,从对“20世纪”的鸟瞰式抒写,到对“八小时”这一时间意象的抒写、批判及反思,“20世纪”“八小时”作为现代时间概念的典型表征反复出现在穆旦诗歌中,“是进入诗人带有强烈的个体经验的感悟世界的一把钥匙”[13]。对现代时间中生存个体异化的思考几乎贯穿了穆旦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成为他诗歌的重要思想主题。现代时间俨然已经内化于现代生命个体的头脑中,“不再是自然律动的象征,而是机器单调重复动作的象征”[14]。这些时间意象在穆旦诗歌中的频繁出现,使得它们超越具体含义而在象征的意义上隐喻了生命个体在现代文明中的异化存在方式,并潜隐着诗人对“现代性”语境中个体生存悖论的深刻反思。
三、现代城市对生命个体的“异化”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于一个现代与传统交错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来自西方的现代思想日益风行,现代工业、现代城市等“资本主义”的社会样态快速崛起,另一方面,传统的各种思想在绝大多数人们的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穆旦敏锐地辨识出现代城市对生命个体的异化,对这一主题展开了别开生面的抒写,并自觉将触角延伸到中国历史社会现实的深层结构,企图寻求对抗“异化”的有效途径。
现代城市意象在穆旦诗歌中的反复出现,隐喻着生命个体在现代语境中的异化。穆旦以锐利之眼“看见到处的繁华原来是地狱”[3](43)。《祭》这首诗正是穆旦运用“反讽”的艺术手法对普通人在现代语境(现代城市、现代战争)中的异化展开的抒写:“阿大在上海某家工厂里劳作了十年,/贫穷,枯槁。只因为还余下一点力量,/一九三八年他战死于台儿庄沙场。”[3](22)作为一种口语化的称呼,“阿大”隐喻了现代都市(上海)中的众多“无名”的生命个体,如果说日常生活造就了“阿大”这一普通生存个体的“非人化”,那么战争则更加具有摧毁性地造就了“阿大”(以及他所隐喻的众多“无名”个体)的“无名”死亡。文本的“反讽”之妙在于,“阿大”的长年“劳作”换来的是“贫穷,枯槁”,现代城市几乎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仍要死于战场。现代城市对生命个体的“异化”,由此可见一斑。
城市对生命个体的异化是现代人生存的一个突出问题,穆旦对现代城市始终保持批判性的思考。穆旦诗歌的“城市”意象成为他诗歌的重要“艺术母题”,构成“异化”探索的重要维度,“呵,钢筋铁骨的神,我们不过是寄生在你玻璃窗里的害虫”[3](275)。在这个“异化”的社会中,生命个体与城市的关系发生错位,作为人类栖居之地的城市反而不断地对生命个体进行戕害:“把我们这样切,那样切,等一会就磨成同一颜色的细粉,/死去了不同意的个体,和泥土里的生命。”[3](275)在这里,“钢筋铁骨的城”不过是“灿烂整齐的空洞”,这是“空虚”与“空洞”的城市,城市所体现并要求的“整一化”“标准化”正是对鲜活的生命个体之独特性、丰富性的全面扼杀与戕害,这种批判思想浸染着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生存世界保持的警醒与锐利。
穆旦时常在诗歌中把城市隐喻为“网”:“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那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3](216)并进而抒写城市生活的封闭、繁琐带来的“围困”感:“我就镌结在那个网上,/左右绊住:不是这个烦恼,/就是那个空洞的希望,/或者熟稔堆成的苍老,/或者日久摩擦的僵硬,/使我的哲学愈来愈冷峭。”[3](332)对城市之“网”的揭示与批判,暗含了穆旦自身的生存痛感,并且彰显了一种城市生存中的普遍异化景观。不难看出,现代城市在穆旦诗歌中“不仅仅具有道德上的不洁感,而是对生命的排斥”[15],穆旦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不是单纯地抒写现代城市对个体的异化,而是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展开思考,在写于1940年的《五月》一诗中,穆旦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封建社会搁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里”[3](36)。对应着这种现代与传统的驳杂与混乱,《五月》这首诗在现代的诗行中夹杂进古典歌谣,使得诗歌的结构呈现出一种驳杂性,诗歌文本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张力。现代战争意象(左轮,三号手提式等)在《五月》中频频出现,现代的战争武器作为终结性命的绝对“异化力量”,在穆旦诗歌中被镶嵌在富有中国古典情调的诗意场景中,某种生存的不协调感也就自然呈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穆旦对这种复杂处境中生命个体的异化问题的思考与探寻,一直延续在他后来的诗歌中。在《原野上走路》《城市的舞》等诗作中,穆旦书写着他对现代城市的异化体验,而在《成熟》《被围者》等诗作中,穆旦则更深层地发掘出传统对生命个体的异化,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人的异化”这一人道主义的显在命题,在穆旦的诗歌中获得了极富思想深度的表达。
正是在这样一种总的生存处境中,现代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着某种程度的改变,人只有通过对自己的异化才能获取生存的资格,而一旦取得这种尊严,就会构成对别人的异化,这样一种生命个体之间的“异化”的循环正是诗人极力反抗的。在写于1942年的《幻想底乘客》中,诗人有这样的表达:“爬行在懦弱的,人和人的关系间,/化无数的恶意为自己营养,/他已开始学习做主人底尊严。”[3](83−84)沿着这一思路,穆旦深深地体会到潜隐在社会肌体里的异化机制。这是整个社会共同构筑的意识形态的枷锁,它消弭人之为人的个性、超越意识和独立思考的意志,以一种莫名的又异常强大的力量把每一个人变成无个性的平庸的人,“还有你,从来得不到准许/这样充分的表现你自己,/社会只要你平庸,一直到死”[3](117)。穆旦认识到,在这种强大的异化力量背后,有一个支撑它的稳固而又坚实的基础,穆旦的异化体验指向极富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圆”,这就是穆旦在《被围者》一诗中所言说的“圆”——保护社会平衡、个人平庸的铜墙铁壁,“圆”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结构,是现代生命个体冲破传统束缚、抵抗种种古旧社会习俗的阻碍。“圆”这一意象的发现以及对它的批判,彰显了穆旦对包围生命个体的种种传统罪恶的发现与批判,“对传统罪恶的发现和批判,客观上使得他独立站在中国抗战时期文化复古主义思潮之外,变成了‘五四’精神的继承人”[1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穆旦在他的诗歌中呼唤那些“突围者”:“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更坏。”[3](100)穆旦对“突围者”的唤醒与等待恰恰是存在主义哲学所倡导的以“自由选择”的行动哲学抵抗生命异化的有效途径,在这个意义上,他继承并延续了肇始于鲁迅的“反抗绝望”的现代精神传统。
四、结语
威廉·巴雷特曾经指出,“在哲学家能够思想存在之前,诗人是它的见证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特殊诗人力图显现的,正是今天历史地属于我们的存在处境。他们正以诗歌的语言拨弄着我们自己时代的先兆之弦。”[17](125)穆旦从肉身体验、现代时间、现代城市等角度对现代中国“异化”个体的抒写,作为某种“先兆之弦”在新时期以来的思想与文学中不断获得回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穆旦以其锐利的“诗歌之眼”洞穿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达到了同时代知识分子所难企及的思想高度”[18]。晚年的穆旦在《沉没》中写到,“身体一天天坠入物质的深渊”[3](341),显然他时时刻刻警惕着身体被物化的危险,并在诗的结尾抒发这样的感喟:“呵,耳目口鼻,都沉没在物质中,/我能投出什么信息到它窗外?/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现在’?”[3](341)在这首诗中,穆旦对生命个体的“异化”抒写在更加多维、综合的层面展开,这既是物欲对“身体(耳目口鼻)”的淹没,同时也是“时间(现在)”对灵魂的囚禁,这“意味着穆旦更深、更彻底地陷入了现代性精神结构的内在困境”[16]。从这个意义上说,穆旦诗歌触及了20世纪历史语境中的典型思想主题,他“情愿把自己摆到他的文明的最重大的问题面前接受拷问”[17](13)。他接过了来自波德莱尔、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诗人精神探索的接力棒,在20世纪中国的语境中,“以一种方法上严苛的彻底性巡视了自身内部在现代性压迫下形成的各个时段:恐惧,身陷绝境,面对自己一心热烈苛求却逃逸入虚空的理想状态时的崩溃”[19]。穆旦对现代异化个体生存的抒写,得益于他卓绝的诗歌艺术以及“以怀疑主义的眼光观照现代生活”[20]的诗歌思想方式,他诗歌中繁复而独异的意象、极富张力的结构以及奇崛锐利的语言显示了他向历史的纵深拓展的努力,以及对个体生命存在本质的执着探寻,进而呈现出现代诗艺的真正成熟。
注释:
① 关于“穆旦研究”的相关资料,详见李怡、易彬编选的《穆旦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其附录中有详尽的穆旦研究专著、文章、博硕士论文等资料目录。
[1] 奥尔曼. 异化: 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概念[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 张严. 异化着的异化: 现代性视阈中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研究[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
[3] 穆旦. 穆旦诗文集(增订版, 第1卷)[M]. 李方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4] 布莱恩·特纳. 身体与社会(第二版导言)[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
[5] 易彬. 穆旦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59−260.
[6] 李怡. 穆旦抗战时期诗歌的基本主题及其文学史意义[J]. 人文杂志, 2011(6): 74−78.
[7] 李荣明. 论穆旦诗歌中的“异化”主题[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3): 249−259.
[8] 加里·古廷. 福柯[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84.
[9] 孙玉石. 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62.
[10] 李欧梵.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6.
[11]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N]. 创造周报, 1923-6-3.
[12] 吉尔·利波维茨基. 超级现代时间[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68−69.
[13] 吴晓东. 二十世纪的诗心[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56.
[14]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00.
[15] 王光明.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318.
[16] 段从学. 穆旦: “被围者”的精神结构及其历史表述[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4(4): 55−61.
[17] 威廉·巴雷特. 非理性的人: 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18] 钱理群. 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96.
[19] 胡戈·弗里德里希. 现代诗歌的结构[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24.
[20]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450.
Writing on the alienated individuals of Mu Dan’s poetry
MA Chungu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lienation of modern society on individual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emes of Mu Dan’s poetry, on which Mu Dan writes at three levels. First, he expresses poetically through the “oppressed and abused body,” namely, war and alienation of modern social discipline system in the body experience and its resistance. Second, he speculates profoundly through modern time imag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ight hours” and so on, to highlight “alienation” of survival in “modern time.” Third, he writes symbolically through “the bright neat hole” of the modern city to reveal the“alienation” of survival in the modern urban space landscape. Mu Dan’s writing on the alienated modern individual life is essentially a poetic inquiry into the modern existence in China, and an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Mu Dan’s spiritual exploration into the internal tragedy, thus at a deeper level emphasizing the inner survival plight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context.
Mu Dan; Alienation; Body; Survival Plight
I207.25
A
1672-3104(2015)04−0197−06
[编辑: 胡兴华]
2014−12−10;
2015−06−16
马春光(1985−),男,山东菏泽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