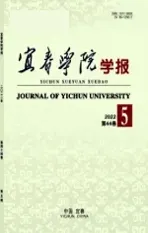《离骚》在19 世纪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
2015-01-13陈笑芳
陈笑芳
(龙岩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龙岩 364012)
《离骚》是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既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政治抒情诗,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首楚辞作品。自其问世以来,《离骚》在汉语文化圈传播广泛,深受人们的喜爱。但直到1852 年,奥地利汉学家奥古斯都·费茨梅尔(August Pfizmaier,1808-1887)才将《离骚》译为德文,使其首次传入西方。1870 年,法国汉学家德理文(Marquis d’Hervey de Saint Denys,1822-1892)的法译《离骚章句》(Le Li-sao,poe?me du IIIe sie?cle avant notre e?re)由巴黎的Maisonneuve et cie,Libraires-éditeurs 出版,并迅速受到英语世界读者尤其是汉学家们的关注。《离骚》自此才开始在英语世界逐渐传播开来。
迄今,关于《离骚》的英译史实,论者为数不多。多数学者将《离骚》视为楚辞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楚辞英译的整体框架内对《离骚》的英译史实加以介绍。1959 年,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在其《南方之歌》(The Songs of the South)一书中对1959年以前的《楚辞》英译版本进行了简略的评介[1](P1-20)。1997 年,马祖毅与任荣珍在《汉籍外译史》一书中简要评介了1879-1959 年间的《楚辞》英译情况[2](P233-235)。2010 年,何文静在《“楚辞”在欧美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一文中介绍了楚辞在欧洲和美国的译介历程[3]。2012 年,张婷在《<楚辞>英译本之描述研究》一文中简要介绍了2006 年以前国内外译者的《楚辞》英译成果[4]。2013 年,洪涛在其《从窈窕到苗条:汉学世擘与诗经楚辞的变译》一书中列出了“《楚辞》序文资料选辑”,包括“《楚辞》英译的编年简目”、“海外出版的《楚辞》英译”与“华人译者的《楚辞》英译”三种[5](P369-411);严婧在《“英国楚辞学”及其研究概述》一文中产生介绍了楚辞在英国的翻译与研究情况[6]。2014 年,魏家海在《<楚辞>英译及其研究述评》一文中介绍2009 年以前的“《楚辞》英译本概略”[7];郭晓春与曹顺庆在《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一文中按发轫期、发展期与成熟期介绍了2010 年以前《楚辞》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8]。总体而言,学界对《离骚》英译史的研究已经颇为深入,但令人遗憾的是,相关论述或存有遗漏,或太过简略,或所述有误。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展开深入考察,对过往论述加以修正补遗,以便尽可能全面而准确地呈现《离骚》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路线图。
二、道格思对《离骚》评介
1870 年,德理文的法译《离骚章句》出版之后,很快就引起英国学界的关注。1870 年7 月9日,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学会》杂志(The Academy)第一卷第十期(Vol. I No. 10)便向读者介绍了该书的出版消息[9]。1872 年, 《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第一卷第一期上又刊登了对该译本的短评,其中涉及对该译本与奥地利汉学家奥古斯都·费茨梅尔(A. Pfizmaier)完成的《离骚》德文译本的对比,但这篇书评的作者佚名[10]。
1874 年9 月12 日,《学会》杂志第六卷新第123 期(Vol. VI,No. 123,New Series)刊登了英国汉学家道格思 (Robert K. Douglas,1838-1913)撰写的关于德理文《离骚章句》的书评。道格思在文中首先介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与主要特色,尤其是将中国诗歌划分为诗、楚辞、歌与赋四大类。然后,他从《史记》编译介绍了屈原的生平,并因此概述式但比较完整地将《渔父》译为英文。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楚辞》英译片断。再后,他对德理文译本进行了赏析与批评,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离骚》中的“扶桑”一词引起了德理文与道格思的极大兴趣。德理文在其译本中增加了《山海经》、《楚辞》和《十洲记》等典籍中与“扶桑”相关的记载,并认为在屈原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发现了美洲大陆,而但道格思对此却持否定意见,并提供了自己找到的证据。总体而言,道格思认为《离骚》并不符合与欧洲的文学标准,但他并不否认其中的文学旨趣,并且建议读者去细读德理文的法文译本。[11]
三、萨缪尔·约翰逊与《离骚》的片断英译
1877 年,美国波士顿的休顿- 米弗林公司(Houghton,Mifflin and Company)出版了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822-1882)的《东方宗教及其与普世宗教的关系:中国卷》 (Oriental Religions and Their Relation to Universal Religion:China)。
萨缪尔·约翰逊是一位美国牧师、作家与超验主义思想家。他在该书第六部分“诗歌”(“Poetry”)中简要介绍了《离骚》(“Li-sao”)。他认为,《离骚》是一首怪诞而伤悲的诗歌,诗中充满着责任感及对人类自身的怀疑;该诗带着秦国征服六国的惨淡凄凉的时代印记,却在战火中存续下来,并收获了最高赞誉,成为民族精神的主要基调之一。他还指出,屈原在诗中使用了许多比喻,特别是将花喻为道德与情感、诗人经历或命运的标志;同时,屈原在诗中探索了所有各种空间与元素、神与人的家园、哲学与巫术,还徒劳地寻找同情、贤妻与贤王,但却只得到了腰带上的花香。最后,萨缪尔·约翰逊还根据《离骚》一诗编译了四句诗,具体如下:
What is the sum of art and talent in this age of ours ?
To turn the back on square and compass,to follow crooked ways as freedom ;
To lay plots with evil means,and make them serve for laws.
'Tis all in vain :there is not one who knows me.[12](P525)
四、庄延龄与《楚辞》的首个英文全译
1879 年, 《中国评论》第7 卷第5 期刊登了《离别之忧,或离骚》(“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or Li Sao”)一文,译者署名“V. W. X. ”[13]。此人其实就是英国汉学家庄延龄 (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14](P147)。
此前,庄延龄的这首译诗常被视为《楚辞》的首次英译,影响很大。单从其题名的翻译来看,庄延龄对“离骚”一词内容的理解较为到位,恰与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离骚者,犹离忧也”一致。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庄延龄其实就是根据司马迁的解释来翻译“离骚”一词。
但细阅正文,可以发现,庄延龄的这首译诗存在着不少缺憾。比如,屈原好用典故,其诗句中有不少富含文化内涵的词语,而庄延龄却忽略了这些文化专有项的迻译,当然也就无法真正传达原诗的丰富内容。试看《离骚》首节的中文原诗与庄延龄的英译:
中文原诗: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庄延龄译文:Born of the stock of our ancient Princes,
(My father Peh Yung by name),
The Spring-star twinkled with cheery omen
On the lucky day I came.[14](P309)
很明显,庄延龄并未将原诗中的“高阳”、“摄提”、 “孟陬”与“庚寅”等文化专有项的内涵移植到其译文中来。这既可能是因为他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无法正确理解这些词汇并恰当地加以重新表达,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这些词汇过于深奥,一成不变地将其译入英文反而会不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欣赏,所以有意识地加以删略。但不管怎么说,庄延龄的译文在文化移植方面确实做得还不够好,仍有改进提高的空间。
五、拉夫卡迪奥·赫恩与《离骚》的片断英译
1887 年,美国波士顿的罗伯茨兄弟出版公司推出了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1850-1904)的《中国鬼怪故事》(Some Chinese Ghosts,书名页印有“龙图公案”四个汉字)一书。
赫恩出生在希腊,后于1896 年入籍日本,并改名为“小泉八云”。他以法国汉学家的法文译文为基础,再加上自己对中国的理解与想像,编译了《中国鬼怪故事》。该书内收《颜真卿宾天》(“The Return of Yen-Tchin-King”)一文,正文之前附有《离骚》中“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一句的英文译文: “Before me ran,as a herald runneth,the Leader of the Moon;And the Spirit of the Wind followed after me,quickening his flight. Li-Sao”[15](P87)。
此外,赫恩在卷末的“词汇表”(“Glossary”)中解释了“Li-Sao”(《离骚》)的所指,称“离骚”即为“满怀忧伤的别离”(“The Dissipation of Grief”)之意。他还简要介绍了屈原其人,并指出德理文的法译《离骚章句》已于1870 年出版。[15](P179)
六、理雅各与《离骚》的英文全译
1895 年,《皇家亚洲文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第27 卷第1、3、4 期(即1、7、10 月号)分三部分连载了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撰写的《<离骚>及其作者》(“The L?Sao Poem and Its Author”)一文。
该文第一部分“The Author”详细地介绍了屈原的生平活动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其中包括对《史记》中与屈原相关的文字翻译,最后还翻译了屈原投江自尽前所念的《怀沙》 (“The Stone Clasped to the Breast”)一诗。第二部分“The Poem”主要是对《离骚》全诗的评介与赏析。理雅各把《离骚》分成14 部分,并对各个部分的主要内容进行评析。第三部分“The Chinese Text and Its Translations”则是《离骚》的中文原文与英文译文。跟庄延龄与翟理斯的译文相比,理雅各的译文显得较为忠实于屈原的原诗。比如,遇到“高阳”、“伯庸”、“摄提”、“庚寅”等专有名词时,他采用的是“音译(注释)”的翻译方法,既能在最大程度了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助于英语世界读者更好地理解《离骚》的内涵。不过,跟很多西方汉学家一样,理雅各也会出现对中国语言与文化的误读与误译,如将“摄提” (《离骚》中的“摄提”指纪年当中的寅年)误译为“木星”(“the Planet Jupiter”)等。[16](P77-91,571-599,839-864)
1870 年,因为德理文法译本的出版与传播,《离骚》开始为英语世界读者所知。但直到1874年,英语世界读者才得以在道格思的书评中第一次阅读到《楚辞》英译片断。此后直到1895 年,萨缪尔·约翰逊、庄延龄、拉夫卡迪奥·赫恩、理雅各等人也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向英语世界读者译介了《离骚》。详见下表:

表1 19 世纪《离骚》英译情况简表
由上表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四大要点:
1. 从国籍来看,5 位译者当中,有3 位英国人、1 位美国人与1 位希腊人。英国译者是《离骚》的英译主力。但若从他们译介《离骚》时生活与工作的地方来看,情况则有所变化。道格思与理雅各当时都生活在英国本土;萨缪尔·约翰逊与拉夫卡迪奥·赫恩均在美国生活与工作;庄延龄则身在中国。但不管怎么说,英国与美国可谓是当时《离骚》英译的中心,这恰恰跟两国在英语世界的领导地位相符。
2. 五位译者译介《离骚》时的身份无一相同,但对于当代读者来说,他们其实都可以被冠以“汉学家”的荣誉。道格思后来陆续出版了多种重要汉学论著,还担任过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的汉学教授[17]。萨缪尔·约翰逊所著《东方宗教及其与普世宗教的关系:中国卷》正文多达975 页,是早期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宗教的一本重要文献。庄延龄著有《鞑靼千年史》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1895)等汉学研究专著,在西方很有影响。拉夫卡迪奥·赫恩后来入籍日本,撰有多种向西方介绍日本的著作,但所译《中国鬼怪故事》则是译介中国传统鬼怪文化的重要文献。理雅各则是英国汉学界的三大星座之一,长期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
3. 在各种译介载体中,杂志最为重要,刊载了三种《离骚》英译版本;专著与译文集次之,各收录了一种《离骚》英译版本。杂志的辐射范围较广、读者群体更大,而专著与译文集面对的读者群体较小,这就使得杂志所载《离骚》英译版本产生的影响远大于专著与译文集中收录的《离骚》英译版本。其中,庄延龄所译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更是被视为《离骚》暨《楚辞》的第一种英译版本,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与探讨。
4. 虽然萨缪尔·约翰逊是在其宗教研究论著中介绍《离骚》并据之编译了四句诗,但相关内容所在的章节标题就是“诗歌” (“Poetry”),亦即他从一开始就是将《离骚》当作诗歌作品来进行译介的。而拉夫卡迪奥·赫恩虽将其《离骚》英译片断当作一种类似于引言的东西置于其译文集中,但他明确指出,《离骚》是“古典时期最为有名的中国诗歌作品之一” (“one of the most celebrated Chinese poems of the classic period”)[15](P179)。
至于其他四位译者,明显就是从其文学的角度出发而对《离骚》进行译介。简言之,《离骚》主要是因其较高的文学价值而被译介到英语世界中去,并且获得了较为广泛的传播。
[1] Hawkes,David. The Songs of the South[M]. 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
[2]马祖毅,任荣珍. 汉籍外译史[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3]何文静.“楚辞”在欧美世界的译介与传播[J]. 三峡论坛,2010,(5):42-49.
[4]张婷.《楚辞》英译本之描述研究[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146-146.
[5]洪涛. 从窈窕到苗条:汉学巨擘与诗经楚辞的变译[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6]严婧.“英国楚辞学”及其研究概述[J]. 语文学刊,2013,(4):54-55;75.
[7]魏家海.《楚辞》英译及其研究述评[J]. 民族翻译,2014,(1):89-91.
[8]郭晓春,曹顺庆. 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J].求是学刊,2014,(2):128-34.
[9]New Publications[J]. The Academy,1870,1(10):272.
[10]Short Notices of New Publications[J].The China Review,1872,1(1):60.
[11]Douglas,Robert K. Hervey de Saint-Denys'(Marquis d')Le Li-sao (Book Review)[J]. The Academy,1874,6(123)(New Series):285-286.
[12]Johnson,Samuel. Oriental Religions and Their Relation to Universal Religion[M].Boston:Houghton,Mifflin and Company,1877.
[13]V. W. X. 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or Li Sao[J].The China Review,1879,7(5):309-314.
[14]Knechtges,David R.& Chang,Taiping.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Vol.I)[Z]. Leiden & Boston :Brill,2010.
[15]Hearn,Lafcadio. Some Chinese Ghosts[M]. Boston:Roberts Brothers,1887.
[16]Legge,James. The L?Sao Poem and Its Author[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895,27(1,3,4).
[17]Brown,Yu-ying. 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and His Contemporaries[J].British Library Journal,1998,24(1):12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