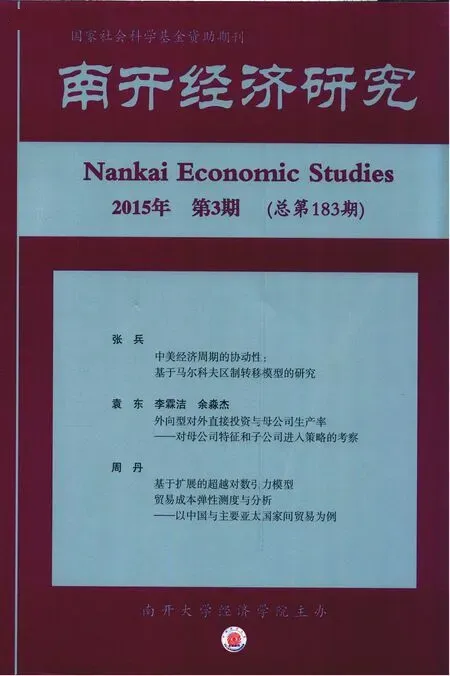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历史借鉴:近代中国地权分配研究述评
2015-01-02关永强
关永强
一、引 言
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要素,土地产权制度也是各项农村经济制度的基础,稳步推进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我国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在20 世纪以来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并因应具体社会经济需要而不断改革和发展的。因此,回顾近代中国地权分配状况,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进而为将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近代中国的地权分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广泛涉及到对很多政治和社会事件的评价,因此一直为政府和学界所重视。早在民国时期,一些政府行政机关和学者就已经对农村地权分配情况开展了统计和调查;进入1950 年代以后,随着土改运动的完成和地权分配官方结论的形成,国内学术界基本中止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但国外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经济史学者则根据一些民国时期的统计和调查资料,对近代中国地权分配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98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学术气氛日益活跃,加上一些近代农村经济资料的重新整理出版,使得学者们得以在新的高度上对近代土地分配问题重新展开了探讨。
这些调查和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部分观点甚至针锋相对。有的是由于抽样调查所选取的地点不同所致,有的体现了调查质量的高低差异,有的则是源于研究者政治立场的不同。本文下面就根据时间顺序,对以上三个阶段的主要调查和研究成果作一个总的回顾,并就其所使用的调查资料进行简要地分析和评论,其中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识者批评指正。
二、民国时期政府和学术界的主要调查
笔者所见最早对近代中国土地分配状况进行全面统计的是北洋政府农商部。从1917 年开始,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在每年的《农商统计表》中设立了一项关于“农家户数耕地多寡别”的统计科目,记载各省农户土地面积的差异情况,日本学者长野朗就曾引用过这项统计数据。如果我们采用历年《农商统计表》中涵盖省份最多(22 省)的1917 年数据,那么据此计算所得全国地权分配的基尼系数约为0.53。但是,《农商统计表》的数据主要是由地方填报而非实地调查所得,因此其统计质量也一直为学界所质疑。当时的经济学家何廉就曾发现,《农商统计表》中很多县可耕地的面积比该县的总面积还要大,而有的县已耕地面积又比可耕地面积还要大;陈翰笙(1930)也认为农商部报告的“简陋虚妄之点不胜枚举”;章有义(1988)还指出,《农商统计表》中并没有注明所统计的究竟是土地经营面积还是所有权面积,因此它并不是一项可以依赖的结论。
与之类似的还有国民政府内政部1932 年的一项报告,也提供了包括17 省800 多个县土地所有权的统计数据(赵冈,2006),据此计算所得的基尼系数为0.56,与1917年《农商统计表》比较接近。但这项资料也没有说明其统计调查的方法和过程,参考以往学者对内政部调查的观点来看,这很可能也是由地方政府逐级填报汇总而非经专业人员调查所得的。
在1927 年国民党农民部土地委员会发布的一份21 省农村报告中,还认为中国农村人口14.4%,的地主和富农占有了农村土地的81%,以上,据此计算,则地权分配基尼系数高达0.84。但这一报告并没有说明其资料来源和统计方法,农业经济学家吴文晖(1934)就直言这一数据是捏造的,万国鼎(1937)也称其为“闭门杜造之数字”,主要服务于当时政治活动的需要,并不足为学术研究所采信。
吴文晖(1934)另外根据十余项地区性调查资料估计占中国农村总户数10%,的地主和富农合计占有土地的53%,,贫雇农等占农村总户数的68%,和土地的22%,,据此,则全国农村地权分配的基尼系数约为0.56。周锡瑞(Joseph Esherick,1981)和刘克祥(2002)后来均指出,吴文晖在研究中遗漏了大量的不在地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地权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同时,陶直夫(1934)也根据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主持的江苏无锡和河北保定调查结果,加上河南辉县、广西38 县和广东等资料,估计占全国总户数10%,的地主和富农,合计占有了土地总数的68%,,而占总户数70%,的贫雇农则仅占有土地总量的17%,,由此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为0.67。然而,抛开这些个案调查是否具有全国代表性不论,乌廷玉等(1993)还指出陶文所采用的论据并不能支持其结论,即使按照这五个地区性案例计算,地主占有的土地也达不到陶文所说的比例。
在1933 年到1934 年间,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相继举行了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和云南六省农村调查,也由陈翰笙主持,调查结果分别以各省农村调查为题于1934 年和193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调查虽然只抽样了这六个省中的24 个县,但调查人员相当专业,态度也十分认真,质量相对较高。薛暮桥(1937)曾根据这些调查的结果,估计占户数9.9%,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的63.8%,,而占户数70.5%,的贫雇农占有土地的18.4%,,六省合计的基尼系数为0.65 左右。
1934 年8 月到1935 年7 月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也对十六省163 县农家的地权分配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以《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题于1937 年2 月出版。这一调查共动用三千余人,其中经过训练的专业调查员一千多人,其质量在同类调查中可能是最高的。该报告指出有25.8%,的农户没有土地;在有地户中超过1/3 的业主有地不到5 亩,50 亩以上者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拥有总亩数的1/3,据此计算所得的有地农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约为0.59。
但是,万国鼎(1947)曾对该报告提出过修正意见,指出该项调查合计户数为1,745,000 户,但是在计算百分比时只考察了其中的有地农家1,295,000 户,而忽略了450,000 户无地农户;他进一步根据农家实际经营总面积2401 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 万余亩,推断出差额的436 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如果假设其中一半是公田,一半属于不在地主,而不在地主户均有地200 亩,那么约计有一万余户不在地主,经此修正后的基尼系数约为0.72。
此外,近代较大规模的农地调查还有金陵大学农经系卜凯教授主持的1921—1925年七省调查、1929—1933 年22 省调查和中央农业试验所1934 年组织的22 省统计调查等,但这些调查都着眼于农业的生产能力而不是生产关系,主要考察的是经营面积而不是所有权面积,因此并不适用于土地产权分配的研究。以董时进(1948)为代表的一些农业经济专家,虽然没有对地权分配进行过大量定量调查,但基于自己的专业研究经验认为“中国土地分配情形还没有到使我们过分惊慌的程度”,“土地分配的不平均,并不一定就是工业化的大障碍,也不一定就是国家贫弱混乱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富贵阶级大都集中在城市…至于一般的乡下人,不论是地主还是自耕农或佃农,他们的财产和生活情形都还不够现代的标准,都应该提高,而决不是一部份人太高,另一部分人太低”。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和机构也以村或县为单位进行过大量的地权调查统计,总计有百项以上,有的以单行本刊行,有的发表在《益世报》、《中国农村》、《社会学界》等报刊上,但大都是零散的个案,本文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三、1950 年至1980 年代美国学者的研究
土改期间,全国各地的土改委员会都对地权分配状况进行了认真详尽地调查,其资料可靠程度也是非常高的。1952 年国家统计局成立时,曾根据土改资料计算出当时全国地权分配情况为:占户数6.87%,的地主和富农约占有土地总量的51.92%,,对应的基尼系数为0.61 左右。此后,鉴于1950 年6 月14 日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关于中国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土地这一官方论断的形成,国内学术界基本中止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而同一时期,国外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学者则对该领域进行了相当深入地研究。
马若孟(Ramon Myers,1969)以前述《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主要依据,并参考满铁调查的资料,计算出4/5 的乡村家庭拥有不到40%,的土地,而另外1/5 的家庭占有土地的60%,,全国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57。但周锡瑞(Esherick,1981)则指出这一研究忽视了前述土地委员会调查中的不足,只包括了有地的农户,而没有计算无地农户和不在地主以及官有、公有土地,因此严重低估了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对此,Esherick(1981)也做出了自己的估算,认为占中国家庭10%,的地主和富农合计占有土地的56%,,中农占家庭数的22%,和土地的30%,,而贫雇农及其他共占家庭数的68%,和土地的14%,,对应的基尼系数约为0.66。但是,在周锡瑞的估算中,由于缺乏租佃土地的准确数据,他只好假设各阶层平均土地数是相等的,从而通过佃农和半佃农的家庭数来推算租佃的土地数,而这一假设与现实间的差距也使得我们也很难评价周氏估计的准确性。
使用《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数据进行计算的还有查尔斯·罗尔(Charles Roll,1980),他注意到了该项调查中关于无地农户和不在地主的问题,因而根据调查报告中租入地和租出地的差额,估算出调查范围以外的土地面积约为440 万亩,这与前述万国鼎(1947)的估算基本一致。不同的是,罗尔并没有意识到其中含有大量的公田面积,因而直接将这些差额全部都当作了不在地主所拥有的田地面积。加拿大学者布兰特(Loren Brandt,1990)等的研究也引用了罗尔的结论,并补充了满铁等一些调查的资料,结论也与罗尔基本一致。
艾琳达(Linda Arrigo,1986)则以前述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关于土地经营面积的数据为基础,进行一系列修正,包括对人口与土地加权、对特殊年份产量的调整和去除复种指数影响等,认为中国华北、东南和西南三个地区的地主和富农分别占有土地的57.3%,、75%,和84.9%,,全国地主和富农占有69.8%,的土地,折算成基尼系数应在0.7以上。这与陶直夫的研究和刘少奇的论断较为接近,但在推算过程中,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比例是将她估算出的租佃土地比例和大规模经营的土地比例两者直接相加而得出的,而大规模经营的地块中本身就存在着一定比例的租佃地,因而很可能产生了重复计算,从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高估。
此外,旅美学者赵冈(Chao,1986)也结合我国古代的地权史料,指出自宋代以来农村土地分配就呈现长期逐渐分散化的趋势。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也对近代中国农村的土地和收入分配进行了探讨,但是在所采用的资料数据和研究方法上并没有超过上述研究,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四、1980 年代以来的新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学术研究气氛日益活跃,加上很多近代农村经济资料被发掘和整理出版,国内学者对近代土地分配问题的研究也因此而重新展开。章有义(1988)最先对1950 年代的官方论断提出了质疑,他对民国时期研究所采用的一些数据资料进行了分析评论,并通过中南与华东区的土改资料等数据来验证以往的研究,提出了地主和富农所占有的土地应在50%~60%,的新观点。
郭德宏(1989)也对民国时期的地权分配研究进行了回顾,并结合更多的社会调查和土改统计资料,认为占总户数10%,的地主和富农在抗战前、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占有的土地比例分别为53.7%,、48.84%,和48.93%,,因此,近代地权分配的总体趋势应该是分散的。朱玉湘(1997)也根据与郭文不同的调查资料,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认为20 世纪我国土地占有的总体趋势是趋向分散的。
乌廷玉(1998)则广泛使用了全国各地土地改革委员会的档案,指出到解放前夕,占全国农户6%~10%,的地主和富农,只占28%~50%,的土地,而且大多数地主和富农的土地都用于出租,土地使用非常零散,缺乏规模生产。其和以往研究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专门考察解放前后这一时期,其结论中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的比例也是所有研究中最低的。如果我们根据郭德宏和朱玉湘提出的分散化趋势来推断,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是长期以来地权分散化的结果。当然,尽管土改运动调查人员的态度认真可信,但是也可能有土改过程中地主逃离本地和隐瞒不报的情况,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土改资料低估地主和富农土地占有比例的可能性。
还有很多区域性的研究也涉及了近代中国的地权分配问题,主要包括:史建云(1994)关于华北平原的研究,秦晖和苏文(1996)关于关中地区的研究,史志宏(2002)、武力(2004)、凌鹏(2007)、隋福民和韩锋(2014)对河北保定的研究,黄道炫(2005)对江西和福建的研究,王广义(2011)对东北地区的研究,李金铮(2012)对河北定县的研究,董佳(2014)对晋绥边区的研究,胡英泽(2013)对晋冀鲁三省的研究。他们大都认为各自研究区域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十分严重,或者认为其存在着地权分散化的趋势。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另一派观点以刘克祥(2000、2001、2002)为代表。作者认为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等的影响下,1930 年代初的中国出现了全国性的地价剧跌和土地恶性集中,主要购地者是身在城市的军阀、官僚、高利贷者和华侨等不在地主,占全国人口11.8%,的地主和富农垄断了61.7%,的土地,而占总人口66%,的贫雇农仅占有土地的17.2%,。作者虽然提供了很多土地集中的案例,但也给出了不少土地分散的情况,总体而言很难说集中化是全国性的趋势。刘克祥先生自己也指出,这一时期地价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卖地者多而置地者寡,因此地价下降和抛售土地可能会导致荒地增加,而并不必然伴随着地权的集中化。因为根据农商部的统计,1940 年的荒地面积较1914 年增加了两倍多,而1934 年土地委员会的调查也表明荒地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正在不断增加。
刘克祥(2000、2001、2002)的观点得到了徐畅(2005)的支持,后者在对1930 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研究中发现,农村经济的萧条导致了农民负债状况的恶化,由此造成了土地因抵债而流入城居地主、官僚、商人和高利贷者之手;凌鹏(2007)则发现,同一时期的河北清苑虽然也出现了大量的土地转手交易,但购地者主要是贫雇农、中农而不是地主。因此,这一时期土地集中是否为全国性趋势尚难以确认,即使存在着这一趋势,集中的程度可能也比较有限。
此外,国内外学术界的大量研究还表明,导致近代中国农村生产力增长缓慢的原因与其说是地权分配不均,不如说是农业经营规模过于狭小。珀金斯(1984)和吴承明(1989)等研究就发现,与1930 年代相比,1950 年代土改完成后的人均粮食产量和主要农作物亩产量均没有出现明显的增加,而新中国的农业增长更多是源自于水利建设、农机应用、化肥、改良种子等技术因素和政治环境的长期稳定。关永强(2012)认为土地革命的经济意义主要并不在于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是保障了更多底层农户的生存和利用由此形成的经济剩余来建立乡村新秩序,进而巩固新政权和国民经济体系。张晓玲(2014)也发现土改完成后的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虽然又出现过增大的趋势,但增幅并不大;而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并不是为了抑制地权分配差距,而主要是要配合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五、小 结
总体而言,近百年来关于近代中国地权分配状况的国内外各项研究中,除少数几项外,大部分估算结果折成基尼系数后,都介于0.5 到0.7 之间。从变动趋势来看,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近代中国农村的地权分配呈现逐渐分散化的趋势,只有很少数学者认为近代地权分配的差距是趋于恶化的。
在这些研究中,北洋政府农商部、国民政府内政部和吴文晖估计的结果折算基尼系数都在0.60 以下;1952 年国家统计局根据土改资料的估算值约为0.61;陶直夫、薛暮桥、周锡瑞和艾琳达的估算都在0.65 以上;同样是基于土地委员会调查的结果,马若孟的估算值为0.57,而万国鼎的修正值则约为0.72;1927 年的国民党农民部调查的估计值最高(0.84),但其可信程度可能也是最低的。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是源自于调查和统计区域的不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自然禀赋和经济发展程度都有着很大差异,而上述调查和统计中,即使是涉及区域最广的土地委员会调查,也只包括了一百多万户农家,而当时全国农户总数约在七千万户以上。不同地区的调查结果自然也会有所差异,从笔者所见的百余项个案调查资料来看,近代东北地区的地权集中程度相对较高,而华北尤其是山西和陕西关中地区的地权分配则相当分散。因此,要获得对近代中国地权分配状况更为可靠的整体性结论,我们可能需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差异,先从一些地区性研究入手,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加权汇总出全国性的认识。
虽然已有的研究还不足以得出关于近代地权分配状况的全国性准确结论,但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也可以发现,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近代中国存在着全国性地权集中化的趋势,相对于土地耕作规模和现代农业技术而言,地权分配对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力也并不是第一位的;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可以忽视地权制度的重要性,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地权制度在农村经济制度中具有着核心和基础的地位,因而才被近代以来的众多学者和政府机构所关注,而土地革命本身也已经表明,通过对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变革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剩余,支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经济秩序的重建。
[1] 陈翰笙.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J]. 北新半月刊,1930(15):107-117.
[2] 董 佳. 抗战时期边区农村的地权转移与乡村土地关系——以晋绥边区黑峪口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2):31-39.
[3] 董时进. 土地分配问题[J]. 经济评论,1948(10):3-7;1948(11):3-6.
[4] 杜润生. 中国的土地改革[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5] 关永强. 近代中国的收入分配:一个定量的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郭德宏. 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J] 中国社会科学,1989(4):199-212.
[7] 胡英泽. 近代华北乡村地权分配再研究——基于晋冀鲁三省的分析[J]. 历史研究,2013(4):117-136.
[8] 黄道炫. 1920—1940 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J]. 历史研究,2005(1):34-53.
[9] 李金铮. 相对分散与较为集中:从冀中定县看近代华北平原乡村土地分配关系的本相[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3):16-28.
[10] 凌 鹏. 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商品化与地权分散——以河北保定清苑农村为例[J]. 社会学研究,2007(5):46-83.
[11] 刘克祥. 1927—1937 年的地价变动与土地买卖[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1):21-36.
[12] 刘克祥. 20 世纪30 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1):19-35
[13] 刘克祥. 20 世纪30 年代地权集中趋势及其特点[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3):33-48. .
[14] 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 中华民国九年第九次农商统计表·民国六年二十二省农家户数耕地多寡[R]. 1924.
[15] 珀金斯. 中国农业的发展[M]. 宋海文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6] 秦 晖,苏 文.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17] 隋福民,韩 锋. 20 世纪30-40 年代保定11 个村地权分配的再探讨[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3):150-166.
[18] 史建云. 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初探[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1):90-102.
[19] 史志宏.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以河北省清苑县4 村为例[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3-20.
[20] 陶直夫. 中国现阶段底土地问题[J].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4(2):613-632.
[21] 万国鼎. 介绍《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J]. 地政月刊,1937(1):107-109.
[22] 万国鼎. 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J]. 学原,1947(8):38-48.
[23] 王广义. 近代中国东北地区地权的流变[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18-125.
[24] 吴承明.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2):63-77.
[25] 吴文晖. 现代中国土地问题探究[J]. 新社会科学季刊,1934(4):99-174.
[26] 武 力. 20 世纪30-40 年代保定土地分散趋势及其原因[J]. 古今农业,2004(3):42-55.
[27] 乌廷玉. 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J]. 史学集刊,1998(1):59-64.
[28] 乌廷玉,张占斌,陈玉峰. 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演变[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29] 徐 畅. 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以20 世纪30 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J].近代史研究,2005(2):78-122.
[30] 薛暮桥. 中国农村经济常识[M]. 上海:新知书店,1937.
[31] 章有义.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2):3-10.
[32] 张晓玲. 从基尼系数看土地改革后农村地权分配[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1):134-141.
[33] 赵 冈. 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34] 朱玉湘. 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J]. 文史哲,1997(2):43-52.
[35] Arrigo L. Land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in China:The Buck Survey Revisited [J]. Modern China,1986(3):259-360.
[36] Brandt L,Sands B. Beyond Malthus and Ricardo:Economic Growth,Land Concentration,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Rural China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90(4):807-27.
[37] Chao K.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An Economic Analysis [M].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38] Esherick J. Number Games: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J]. Modern China. 1981(4):387-411.
[39] Myers R. Land Distribution in Revolutionary China:1890-1937[J]. The Chung Chi Journal,1969(8):62-77.
[40] Roll C.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Incomes in China:A Comparison of the 1930,s and the 1950,s[M]. New York:Garland Pub.,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