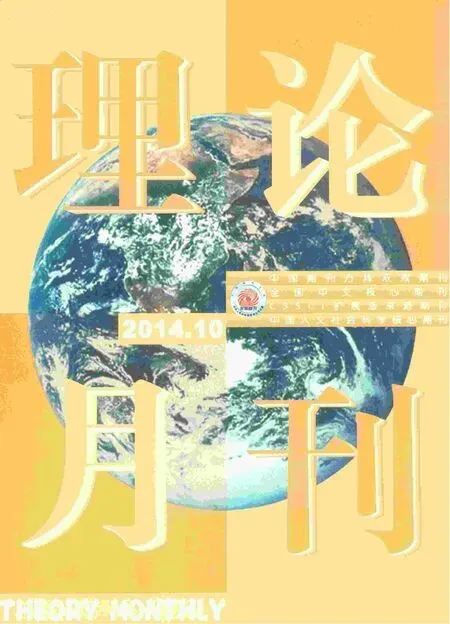章学诚笔下的戴震形象
2014-12-04王萌
王 萌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
清代朴学是继宋明理学以来,我国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戴震作为清代朴学的领军人物,不仅精通考据之学,对于形上思辨的义理之学也多有发挥,并对后世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各派学者或出于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或出于实现自身政治主张的需要,或出于对新的学术术语的解读,对戴震的评价和描述往往不同。其中有一个人对戴震的描述不能不提,那就是章学诚。在崇经好古、贵博贱约、以饾饤考据为风气的乾嘉年间,这位崇尚理论研究的思想家,自许“知戴最深”。[1](P553)观察章学诚笔下的戴震之学问与心术,或许隐约可以透视出此后百余年间学术发展的趋势,以及特定时代风气下理解戴震的特点。
一、章学诚对戴震义理之学的看法
在当时的考据学风下,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诸篇的理论意义并不为人所重。如章学诚所说:
近三四十年,学者风气,浅者勤学而谙于识,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深痼之病,不可救药者也。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者,而乾隆年间,未尝有其学识。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视以为光怪陆离,而莫能名其为何等学。[1](P556)又在《答邵二云书》中提到:
当时中朝荐绅负重望者,大兴朱氏,嘉定钱氏……其推重戴氏,亦但云训诂名物,六书九数,用功深细而已,及见《原善》诸篇,则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1](P553)
戴震的好友朱筠就以为“戴氏可传者不在此”。[2](P139)其弟子洪榜是当时少数将义理之学作为戴震真正学术旨归的学者,谓其“早岁稽古综核,博闻强识,而尤长于论述。晚益窥于性与天道之传,于老庄、释氏之说,入人心最深者,辞而辟之,使与六经孔孟之书,截然不可以相乱。盖其学之本末次第,大略如此。 ”[3](P254)并极力争取将代表戴震理论宗旨的《答彭进士书》载入《行状》。另一弟子段玉裁亦称戴震治经“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即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4](P452)在此之外,可以说戴震少有解人。
真正与戴震同道,为其知音的还是章学诚。据章学诚记载,乾隆丙戌(1766),他与戴震第一次见面,遂以为在一时通人之中,“能深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的惟有戴震。[1](P553)在章学诚眼中,戴震与“一时通人”的区别在哪里呢?章曾将“学”分为功力与学问,认为二者“实相似而不同”。所谓功力,只是“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而学问乃是“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也就是说,当时饾饤考据仅是功力,不得谓之学问,只有能“得其所以然”的才是学问。以此为标准,他认为今日言学问者,当以戴东原为最,因为其能识古人大体,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者可比。[1](P679)此后他亦多次称道戴震的学术,称其说理之文,如《原善》诸篇,“多精深谨严,发前人所未发”。[1](P654)其在《书〈朱陆〉篇后》记载戴震的话颇可注意,戴氏自称:“余于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舆之隶也;于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1](P76)这在考据学者对戴震的描述中是绝看不到的。这也说明与考据学者不同的是,章学诚认为戴震的学识,不是因为其考据之功,而是“精微醇邃”,能“学以求心得”的“说理之文”。[1](P581)
与章学诚不同,当时有人褒扬戴震的义理之文,目的是突出其教化意义。如不满汉学家琐碎考据及理学家空谈义理的经世之士陆燿,在读过戴氏论宋儒理欲之文后言道:“来教举近儒理欲之说,而谓其以有蔽之心,发为意见……可谓切中俗儒之病”。[2](P138)洪榜认为,《孟子字义疏证》“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戴震去世,洪榜挽其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2](P140-141)段玉裁也认为戴震“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是能“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的。[4](P485)而章学诚所亟亟表彰戴震之处,却是其文“精微醇邃”的理论意义。至于戴震是否能“明察于人伦庶物”、“垂世立教”,章学诚的看法却正与之相左,认为其“心术不正”。
二、章学诚对戴震“心术”的批判
1777年戴震过世不久,章学诚便作《朱陆篇》批驳戴震,其文曰:
今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然究其承学,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1](P73)
十年后,章氏又作《书〈朱陆〉篇后》,明确贬斥戴震不通史学,其论史是“自欺而至于欺人”,然而这些姑且不论,因为尚未“得罪于名教也”。真正让章学诚不能容忍的是戴氏“心术未醇”,主要是指其学承袭程朱却又非议程朱。所谓:“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而戴氏“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侥幸为世所宗以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章学诚就此论道:“此则谬妄甚矣。”戴震之文已与朱子有所异同,“而口谈之谬,乃至此极,害义伤教,岂浅显哉!”且给徽歙两地的学风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使当时徽歙两地“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风流大可惧也!”以至于“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从矣。”章学诚由此斥责戴震“不知其口舌遗厉,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惼衷而害于道也”。[1](P76-78)在章学诚笔下,戴震非但不如钱大昕所说,“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5](P672)更成了“害义伤教”的名教罪人了。在以宋明理学为官方指导思想的清代,这样的指责不可谓不严厉。
其实“心术不正”在章学诚笔下,当指“诽君谤主”的“名教罪人”之流。例如章氏在《史德》篇中有言:“夫以一身坎坷,怨诽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1](P184)章氏多次在给友人的信中,批驳了戴震“心术不正”。如在1788年给邵晋涵的信中称:“戴氏笔之于书,惟僻宋儒践履之言谬尔,……至腾之于口,则丑詈程、朱,诋侮董、韩,自许孟子后之一人,可谓无忌惮矣”。[1](P553)在《与史余村书》中亦称:“戴氏学识虽未通方,而成家实出诸人之上,所可惜者,心术不正,学者要须慎别择尔”。史余村不满章学诚对戴震的非议,写信为其辨诬。章学诚又回信申诉委曲,以表明自己并“无私心盛气”,因为“世道人心所系,名教大义所关”,不得不辨。章学诚承认戴震批判宋学,是因为宋学理论中杂糅了释、老两家的学说。但是“戴氏力辟宋人,而自度践履万不能及,乃并诋其躬行实践,以为释老所同,是宋儒流弊,尚恐有伪君子,而戴亦反,直甘为真小人矣”。[1](P556-557)章学诚批判戴震,原因即戴氏其学源自宋儒而诋毁宋儒,正所谓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之学,本是朱子格物致知之法。戴震之误,“误在诋宋儒之躬行实践,而置己身于功过之外”,后人可以校正宋儒之讹误,但不可一切抹杀,肆意诋毁。戴震之学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使休、歙之间,少年英俊,无人不骂程、朱,而戴震实为始作俑者。[1](P654-655)由是,当时学者对戴震学问与心术的赞美,章学诚颇不以为然,认为戴东原去世十余年,“同时有横肆骂詈者,故不足为戴君累;而尊奉太过,至今有称谓孟子后之一人,则亦不免为戴所愚”。后学“至今未能定戴为何如人,而信之过者,遂有超汉、唐、宋儒为孟子后一人之说,则皆不知戴者也。 ”[1](P76-78)
不惟心术,章学诚对戴震人品的记述也与考据学家大相径庭。据戴震的好友汪梧凤记载,汪有一族父为巡抚书吏,为人清廉不阿,“人有纷难,每竭己之财以拯其急”,最后家财散尽,“以穷困殴”。戴震闻之,“慷慨激昂,反复不已”。[6](P165)其子汪灼也有一段对戴震性格的生动描写:
有村人暨他族以事白,或持文就正先严者,先生即拂衣起,归室据一席高歌无所顾,如冰炭然。而稚川先生(汪肇龙,1722-1780)来,则又如冰之投水,炭之在炉,冷热各相得。京师多达官长者,闻先生处之亦若是,以故多不理人口,然尤未至世皆欲杀者,以素未肯与俗争是非也。[2](P42)
其弟子任兆麟、段玉裁亦分别称其立身不苟,不为矫激之行,[2](p37)虽学高天下,而不好为人师。[4](P460)且“接物待人以诚,谋人之事,如恐其不遂,扬人之善,如恐其不闻。其教诲人,终日矻矻,不以为倦也。”[3](P259)总之,在考据学者尤其是戴震学生笔下,戴震分明是爱憎分明而不恃权贵,严以律己又诚以待人的形象。
在章学诚笔下,戴震不惟是“心术不正”的名教罪人,其平日里流露出的品行亦不当为人所重。章氏《书〈朱陆〉篇后》记载,有人向戴氏询问如何作古文辞,戴震则曰:“古文可以无学而能,余生平不解为古文辞,后忽欲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复思之,忘寝食者数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为文者,振笔而书,不假思索而成,其文远出《左》、《国》、《史》、《汉》之上”。[1](P77)然而关于戴震对学习古文的看法,段玉裁所记却与章氏相反,戴氏自认为“做文章极难”,“吾如大炉然,金银铜锡入吾炉一铸,而皆精良矣”。因此段氏称戴震文字“皆厚积薄发,纯朴高古,如造化之生物,官骸毕具,枝叶并茂”。[4](P486)细观之下,章学诚所谓“取古人之文反复思之,……一夕有所悟,……振笔而书,不假思索而成”,实在与段玉裁所记“熔炉”之说于本质上是相同的,但二人表述却全然不同,所展现的戴震形象因此也截然相反。但是在章学诚看来,戴氏言语故为玄妙,狂狷而妄作。更为严重的是,其不惟狂妄,言行亦表里不一:“其人于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及笔之于书,仅有微辞隐见耳,未敢居然斥之也”,而“习文口舌之间,肆然排诋而无忌惮”。又称戴氏“生平口舌求胜,或致愤争伤雅”,其生平口谈,约有三种:
与中朝显官负重望者,则多依违其说,间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见锋颖,不肯竟其辞也。与及门之士,则授业解惑,实有资益;与钦风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则多为慌惚无据,玄之又玄,使人无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终莫能定。……及门之士,其英绝者,往往或过乎戴。戴君于其逼近己也,转不甚许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也。后学向慕,而闻其恍惚玄渺之言,则疑不敢决,至今未能定戴为何如人,而信之过者,遂有超汉、唐、宋儒为孟子后一人之说,则皆不知戴者也。 ”[1](P78)
然而据洪榜的记载,戴震平日与学生讲学却“平正通达,近而易知,博极群书,而不少驰骋。有所请,各如其量以答之。 见先生者,未尝不有所得也。 ”[3](P259)对此,章学诚却认为“今之尊戴过者,亦以其法求戴遗言,不知其笔金玉而言多粪土,学者宜知所抉择也”。[1](P553)在他的笔下,戴震竟成了见风使舵,教分亲疏,嫉妒后学,搪塞虚伪的小人。
三、从章、戴交恶看清代中期学风的嬗变
戴震过世已二百余年,章学诚的记录与其行径有几分相符我们不可得知,也无意为其辩诬。但需要指出的是,章学诚斥责戴震对敬慕者虚与委蛇,故为玄妙,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却证明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据章氏的记载,他与戴震首次相见的时,戴氏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仆重愧其言!”章学诚继而深思,“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1](P672)又据《答邵二云书》所载,当年他因仰慕戴震学问,往见戴氏休宁馆舍,“讯其所学,戴为粗言崖略”,于是“疑郑太史之言不足以尽戴君”,认为“一时通人”中惟戴氏“求能深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章学诚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学,在首次相见的情况下,戴震即“振臂而呼”,明确为其指出实学的重要性,并“粗言所学之崖略”,就使这位聪颖的晚辈看出在众多学者之中,只有戴震的学问不仅限于考据,且有能“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的义理之学。这是不是也可以称得上是对章学诚“实有资益”呢?余英时亦指出此次见面对章氏的影响是极大的,因为在此之前,他所接触的北京学术界人士,多少都具有反义理的倾向,以使他对自己以往的治学方向有所疑惑,而戴震对义理的推崇,才使他有勇气坚持自己的选择。(P16-17)那么是否可以说章学诚称戴震对慕名而来者讲话恍惚玄妙、虚伪搪塞,是有意发泄对戴的不满呢?至于称戴震对超过自己的学生“转不甚许可之”,更是与其弟子洪榜、段玉裁等人笔下的戴震形象截然相反了。
如果说章学诚对戴震心术的指责,是出于卫道的立场而尚可为人理解的话,那么他对其人品的攻击与污蔑就不免使人费解。这或许就需要从二人因史学争论而起的个人恩怨中寻找答案。
1766年第一次与戴震见面时,章学诚还怀有求教的谦虚态度,但七年后当他对学问尤其是史学已经有了成熟的见解之时,第二次见到戴氏,便一改昔日钦佩之状,对其批评道:“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继而记叙了二人关于方志是“古国史”还是“地理专门”的争论。[1](P747)当章学诚询其班、马二史优劣时,戴震则“全袭郑樵讥班之言,以谓己之创建”,[1](P77)结果二人不欢而散。第二天两人再次见面,章学诚记载了一段戴氏对史学的见解,戴震认为僧侣和古寺当归入古迹类,而不可归入人物类,否则即是庸史的作法。章学诚对此嘲笑道:“无其识而强作解事,故不如庸俗之犹免于怪妄也”。[1](P749)同年又在杭州第三次与戴震会面,亦记其“痛诋郑君《通志》”,章听“其言绝可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1](P169)后来又特地作《申郑》篇,讥戴震不懂史家之“别识心裁”,谓其“溺文词而泥考据者,相与锱铢而校,尺寸以绳,不知更作如何掊击也? 今之讥郑樵者,何以异是! ”[1](P167)由此称戴氏“其于史学义例、古文法度,实无所解,而久游江湖,耻其有所不知,往往强为解事,应人之求,又不安于习故,妄矜独断。 ”[1](P77)认为其所考订之所见尚可,而纪传文字,非其所长,编纂方志,更不能晓其大意,又“强作解事,动成窒戾,此则不善趋避而昧于交相为功之业者也”。[1](P584)指出戴氏之训诂,朱筠之文章,皆无今古于胸中,“其病则戴氏好胜而强所不知,朱氏贪多而不守统要”。[1](P668)且将戴震与程瑶田相比,程氏《通艺录》中收录的“不今不古”的传志状述,犹如“村俚供招”,而戴东原比程氏还不如,其文集中“应酬传志,亦自以为文也而存之,且以惹人笑柄之《汾州府志》,津津自道得意,然则人之真自知者寡矣!自己尚不知,如何能知古今人之是非? 良可慨也! ”[1](P584)在这位史学家的笔下,戴震从“学通天人”的“一代儒宗”,转而竟成为“无其识而强作解事”的不解史学精要之人。
在章学诚这位不满于饾饤考据之功力,而追求义理的史学理论家眼中,将考据比作“肩舆之隶”,将义理比作“乘舆之大人”的戴震,实在是他在考据学旗帜高张之下的唯一知己。然而可悲的是章氏能知戴震,而戴震却不能知他。二人虽然均以义理为自己学术之大要,却都在当时难得解人。归根结底就在于,戴震的义理在经学,而章学诚的义理在史学,二者实不相同。尽管百余年后,“六经皆史”是学术发展的大势,但是在乾嘉年间经学考据方兴未艾的情况下,章学诚高倡史学之义理的境遇仍然十分艰难,戴震这位学界领袖的傲慢更使他心怀不满,以至于他在戴震过世之后,仍多次对其恶意攻击甚至丑化。戴震对章学诚的轻视与章氏的过度反应,也正反映了在学风嬗变之际,经学和史学两种学风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的现象。且不同以往的是,戴震从经学考据出发,证实“程朱”理学的义理是从佛老理论中所得,由此触动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根基,并用“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来取代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也就是动摇了中国社会早已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而章学诚正是以宋学“纲常名教”为安身立命之旨的卫道士,因此他因戴震非议宋儒而心怀不满,斥其为“名教罪人”也就不难理解了。章学诚笔下对戴震义理的褒扬、对其不通史学的斥责,以及对其心术与品行的抨击,正反映出在当时社会价值观的悄然变化,以及乾嘉考据之风所即将遭遇的挑战。
[1]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戴震.戴震全书(七)[M].安徽:黄山书社,1994.
[3]戴震.戴震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戴震.戴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钱大昕.钱大昕全集[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6]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 28册[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7]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