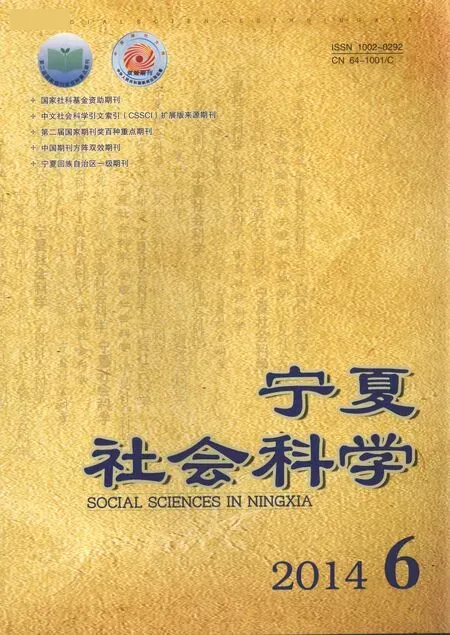书法艺术“创新”之我见
2014-12-04李兴科
李兴科
(中卫市文化馆,宁夏中卫 755000)
近年来,书法界谈论比较多的话题莫过于“创新”二字了。毫无疑问,任何一种艺术都应该不断以新的面貌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这样,才会引起人们的审美愉悦。
然而,什么是书法艺术的“创新”?或者说,现代书法风貌究竟应该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认识和思考。任何一种艺术在其审美形态方面的革新和创造,都是在吸收了传统的精华之后自成体系。书法这门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模式和审美理想的艺术尤其如此。众所周知,凡学书法者都必须学习古人,从临帖入手。没有一个人能说,他的书法能不通过临帖而登堂入室的。因此,“继承传统”是创新的不可跨越的必经之路。近年来,“创新”似乎变成了一句时髦话,不独在书法界,其他艺术领域也有类似情况,很多人认为只要是“前所未有”,便是“创新”,因而张冠李戴、不伦不类。事实上,“创新”远非那么简单。
“创新”顾名思义,为开创新的境界,必须有所建树。
一个三岁的孩子,拿起笔来往纸上一涂,说他“新”,的确是前所未有,这能不能冠之以“创新”?显然不能。因为他无法构成新的境界,无法得到社会的承认。一位书法家,即使他想出了一种特别别致的写法,同样不能说是创新。因为他也同样面临一个被社会承认的问题。即使他名噪一时,还不能贸然称为“创新”,因为他还将渡过“历史鉴定”这一关。“身谢道衰”(孙过庭《书谱》),自古有之。“创新”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是代表整个时代的动向问题。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当时作者并不感到是“创新”,只是感到“应该如此”,但是到了后代,在后人的眼里,才确认这是真正的“创新”。例如,东晋王羲之首创行书新体,在当时,他只是用他深厚的功力,去大胆融入民间俗书——稿草而已。而对稿草的采用,当时连他仅十六七岁的小儿子王献之也感到:“古之章草,未能宏肆,不如今之稿草。大人宜改体。”由此而知,已是势所必然的了。所以,“创新”的确立,必须有两大前提:形成于一个时代,代表着一个时代;同时又必须经历史的鉴定。
在书法界中,人们以自己的书法面貌而自豪。确实,书法需要有个性,这种个性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必定是作者的性格、经历,特别是书者多方面的素养,其中包括文化素养、审美观以及气质悟性的程度的浓缩和流露。那么,这种有自己的面貌,是不是就能称之为“创新”呢?尽管历史上凡创新的书法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强烈的面貌,但如果把个性和创新画成等号,还是不对。其一,如果某人某作很有特点,但其形貌乖劣,不堪为人师表,能不能称之为“创新”?显然不能。例如宋代曾出现过一种“唯墨书”,点画粗厚,形同“墨猪”;此书虽然前所未有,但很快被社会淘汰。其二,古人云,“书如其人”,任何人都有个性,差别只是个性的强烈与否,因而,书貌也人人有之,其差别只是醒目与否。那么强烈到何种程度才算是创新,又何等程度不能算创新?这个概念无法划清。
简而言之,个性是创新的起点,但个性不能代替创新。即创新必须来自于个性(独特性),而个性又必须溶解在浓厚的传统功力中(继承)。不但如此,创新又必须迎合时代的发展,代表整个社会的审美追求(社会性)。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加以肯定。
纵观历史,被公认为创新的大书法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处在文字、书法的重大变革时期,能因势而动,大胆采用民间“俗书”,使之正规化,从而创立一种新的字体。这类书法家,数量很少,但成就高、影响大,每每被列为千古书圣,或各体世祖。例如,秦代李斯,首创小篆;汉代蔡邕,首创八分体,并将汉隶推向成熟化;汉末张芝,转化章草为今草,被誉为草圣;晋王羲之,首创行书新体,被尊为千古书圣。另一类,主要是在宋以前,这类书家还是以继承为主体,但能迎合整个时代的风尚,用自己独特的风貌,开创出一种影响广大流派书风,这类书家的历史地位虽然远不如前者,但与学书者来说,常被尊为宗派的首领,从而师之,故影响极大,这类书家虽以前多不记名,如:汉碑中的《张迁碑》、《礼器碑》、《曹全碑》、《石门颂》,等等;北碑中的《张猛龙》、《张黑女》、《郑文公》、《始平公》,等等;隋碑中的《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等等;唐代的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等等;宋代的苏东坡、黄山谷、米芾,等等。
在书法界,普遍有一种说法:学书者必须以继承为手段,以创新为目的,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从理论上来说,这一说法无可非议。作为一个书法家,应该要有这样一个高远的目标。但是,纵观历史,自古以来能够称得上创新的书家屈指可数,也就是说,能走完继承到创新这条道路者寥寥无几,创新书法家和以继承传统的书家相比,后者远远多于前者。如唐代薛稷不离褚河南车辙,陆柬之极力效仿王右军、虞永兴,特别是明清以后,书法大都以尊古为主。正因为有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单纯地说继承是手段,创新是目的,就不大合宜。
首先,从社会因素上看。其一,历史事实证明,书法艺术的重大创新变革,每每处在书法艺术十分繁荣的时期,而书法艺术的兴旺与否,又往往与上层社会的重视和提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我国历史上书法繁盛的三大时期,东汉末年、东晋和唐代,都与皇帝的雅好有密切关联。东汉末年,桓帝、灵帝十分喜爱书法,其实,书家优者能直接入仕,并曾举办过历史上第一次书法大赛——鸿都门试书,结果师宜官以大字径丈、小字方寸千言,列于榜首。就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蔡邕、钟繇、张芝等大书家。唐代,唐太宗本人就是位书家,自然十分提倡书法,崇虞世南为师。后又在魏徵的谏议下,以书取仕,提拔褚遂良,并于“国学”中立“书学”科,形成我国历史上的书法第三高潮。其二,上层社会的提倡,必定导致民间书法的普及,从而为书家的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东晋时代,民间对书法爱好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到唐代民间书法更是繁盛,新疆出土的卜天寿《论语》抄本,出自十二岁的孩子之手。颜真卿书风的形成,早期便是采用民间的“经生书”为范本。而这些唐人写经,至今尚有大量遗存。其三,创新除了民间的土壤外,还要有一大批书家的努力。历史上创新书家的形成时期,往往也是书家辈出的时期。例如,东汉末年除了蔡邕、张芝外,知名的尚有师宜官、曹喜、杜度等。东晋时代,士大夫几乎没有不爱好书法的,正如孙过庭《书谱》所述:“东晋人士,互相陶然。”唐代更是书家辈出的时代,除欧、褚、柳、颜等之外,尚有欧阳通、张怀谨、王知敬等。唐代许多诗人文人都兼为书家。
其次,从书家个人因素来讲。其一,创新书家必须具备深厚的继承传统的功力。前面已经论及,这里不再赘述。其二,如果细鉴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历来卓有成就的创新书家,大都不是政治家便是文学家,都有极其丰富的阅历和十分鲜明的个性。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在与殷浩争北伐事宜中,甚有政治见地,同时,他又是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兰亭序》文,至今被用作古文教材。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几乎满门追杀,而后官至鲁国郡公,他为人正直不阿,最后不容于奸相卢杞,秉节被害。由于有独特的个性和见解,才使他们有不同凡响的书貌,这大概就是陆放翁所说的“功夫在诗外”吧!其三,创新必须具备清晰的头脑,能顺应时代而动,绝不是逆时代而行。
这是创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人认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是位创新书家,其实,郑板桥的“六分半体”是在八分体的基础上与楷书再打八折,八八六十四,因而得名。试想,楷书已成熟了一千余年,再和近二千年的隶书打折扣,当为复古可知。故郑板桥不能成为人们效法的一大流派,其书只能因板桥的为人、艺术见解所赋予的特殊韵味,而成为一件观赏作品。鉴古必为今用,目前的书法创新,可否以创造新的汉字来体现,如过去从篆刻到隶到楷那样?其实没有这种必要。因为创造一种新汉字,属于文字改革范畴,不是书法艺术的本职任务,由于书法是从汉字的实用书写中发展起来的艺术,它与实用写字关系极为密切,因而使人们把历次的文字改革误认为书法的创新。时至今日,书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已为公众所认识,所以对文字改革这一类大事,今后我们不必也不应再去越俎代庖了。总之,搞书法创新,不可急躁从事,任何为创新而创新的做法,都是不会取得好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