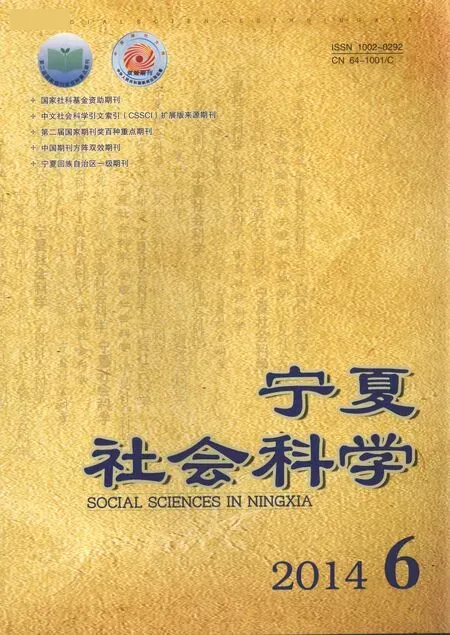消逝族群的历史建构与文化想象——基于对西夏佛塔的历史民族志解读
2014-12-04李柏杉
李柏杉,周 毅
(1.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宁夏银川 750021,2.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
在中国封建王朝政权更迭的历史舞台上,少数民族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并且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对外交流和对话。然而,与这些少数民族的灿烂文化相比,正史中关于党项族及其所建立的西夏王朝的记载过于简略,从而使我们只能借助少数文献和更多的想象去理解那个神秘的王朝及其文化。而唯一能使我们摆脱这种想象而去直观的感知那个时代的就是那些与朔风相伴的西夏古塔。
一、宁夏境内现存西夏古塔概述
西夏古塔研究,主要基于考古学的角度和对塔内出土文物的研究。牛达生先生在《宁夏境内的西夏古塔建筑》一文中对宁夏境内现存西夏古塔建筑的现状作了介绍,但他的研究是“仅就数处古塔的发现情况、建筑特点等略加陈述”[1]58,而并没有比较全面和细致地对现存的西夏古塔进行介绍说明。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在直观感知的基础上从具体问题意识出发来作出相应的思考。
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通晓佛学。立国之初,元昊就大兴土木,建立佛教寺院和佛舍利塔。《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中记载了当时建造舍利塔的盛况。在前列佛塔中,只有银川的承天寺塔(谷称西塔)是现存的唯一有文献记载的西夏佛塔,“据《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和《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记载,元昊卒,谅祚幼登宸极,太后承天受命,于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敕建承天寺,元明之际,寺塌塔存”[2]。而其他的塔之所以断定为西夏佛塔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其所出土的文物。比如在拜寺口双塔周围有大面积的西夏遗址,并且在对双塔进行维修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在西塔的9层发现了与西夏王陵出土的绿色玻璃套兽一样的套兽;在康济寺塔顶刹座下的佛龛内发现了带有西夏文题记的方砖。不管是基于文字记载还是借助文物推测,这些佛塔结束了那种没有现存西夏建筑的观念,使得关于西夏宗教艺术和西夏建筑的研究有了一定的也是唯一的类型参考。
总体上看,西夏佛塔的类型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这可能与党项族的历史迁徙和西夏国的地理区位有关。在这些佛塔中,8角13层密檐式砖塔和8角楼阁式砖塔似乎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著名考古学者宿白先生在关于西夏佛塔的类型学研究中,将类似于承天寺塔的8角楼阁式砖塔归类为Ⅰ型,认为这类塔的塔身一般为多层楼阁式,如宁夏中卫的鸣沙洲塔、甘肃武威的护国寺感通塔等都属此类。除了这些“主流”佛塔以外,也有一些国内十分罕见的佛塔类型,如宏佛塔,“它既非常见的楼阁式塔,也非密檐式塔,更不是喇嘛塔,而是一座类似花塔的复合式塔”[3]。至于像双塔和塔阵这样的类型在国内就更为罕见了。
通过文献资料我们看到,学术上对于西夏佛塔的研究是十分平淡的,而是把重点都放在了塔身及其底部出土的文物上面。比如宏佛塔之所以为人们所知是因为在1990年和1991年对该塔进行保护维修时从刹座天宫内发现了大量带有西夏文字的佛经、唐卡等国家级文物。这次发现被列入了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填补了很多西夏文物的空白。之后学术界便将重点放在了这些出土的文物上面。在我们考察过程中发现,如今的宏佛塔被遗弃在一片麦地里,虽然经过修复,但后续的保护工作并不是很乐观,同样的命运在韦州康济寺塔等佛塔身上都有所体现。
我们还考察了银川海宝塔、灵武镇河塔、中卫鸣沙洲塔、恩和华严寺塔等,但是由于考古发掘和文史资料的缺乏,还不能断定这些塔到底是否属于西夏时期。但是,在对地方长者和民间学者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了两个信息:一是灵武镇河塔是韦州康济寺塔的传说中的一个姐妹;二是鸣沙洲塔是和韦州康济寺塔同一时间建造的,而且所用材料均来自甘肃麦积山。这些信息都带有一定的传说色彩,但不能就此质疑它们的真实性。传说也不过是对社会现实的另一种反映,我们也不妨把这些从民间收集到的故事称为口述史。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讲,口述史是做历史研究不能或缺的一个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官方正史的一个补充,既然帝国的统治阶级没有把西夏写进官方史书,那么从民间的口述史中去寻找和建构西夏历史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尝试。既然人们将研究焦点放在佛塔出土文物而忽视佛塔本身,那么依靠这些口述资料去解读和解释这些佛塔就会显得必要而且重要。
二、佛塔的空间表征与党项的历史建构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发生都具有一定的场景性,都需要一定的场域,需要一定的空间。虽然宗教文化具有超验和抽象的特征,但宗教实践者却通过将抽象具象化为某种可感知的空间形态(诸如塔)来表征它的意义,以此启迪人的精神,震撼人的灵魂。在我们看来,佛塔跟雕塑一样是一种纯粹的空间艺术形式,而相比主题繁多的雕塑,佛塔可以定义为一种纯宗教艺术表达的空间形式,它在实质层面是三维的和静止的,但它的象征语义传达却是历史的和流动的。
西夏佛塔的结构多样性和组合形式多变性,反映了西夏国的主体民族党项族信仰边界的不断飘逸和流动。党项族属于羌人的一系,早期分布在今青海省东南部、四川省西北部的广大草原和山地间,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最初奉行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的信仰。唐朝时开始陆续东迁至今甘肃、宁夏和陕西北部一带。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游牧生活开始向定居农业转变,加之由于接触到汉族、女真及契丹政权及其文化,在长期的文化涵化过程中,党项人的宗教信仰也开始转向中国文化“大传统”主流所信仰的汉传佛教。到了后期,在西夏国不断西征的过程中,党项人跟吐蕃人天然的文化亲缘关系使得藏传佛教在党项人中一度盛行,因而藏传佛教文化因素又渗透到西夏后期的宗教艺术创作当中。从大量出土的西夏经幡、唐卡、擦擦等文物资料中可证明这点。
可以看到,西夏佛塔表征的空间是一种社会历史空间,它的合成象征意义是巨大的。它以有限对抗无限,以相对固定的场所来补偿变动不居的历史文化,以确定的边界象征了自我与他者的不同,从而将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浓缩在一个意义空间内,最终实现人与神灵、现实与历史的互动。西夏佛塔表征的空间是一个允许我们发挥想象力的空间。在集国史之大成的《二十四史》中,唯独没有西夏史,这使得西夏文化具有一层神秘的色彩,在可供我们直观感知的西夏文化遗留中,除了具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外,便是那些矗立于残垣断壁上的佛塔。西夏文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党项人的宗教生活和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在西夏文已成为一种死文字之后,我们只能凭借想象去解答自己的疑惑。
这些或孤立或相伴而立的佛塔,也营造出一种关于消逝民族历史记忆的“场”。西夏国先后经历200多年,在主流史书中所对应的是北宋时期。党项族自从唐僖宗中和元年平夏部落首领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起义而被唐朝皇室赐姓李开始,到蒙古铁骑屠城后的消亡,他们留给后人的只有神秘。如果稍对历史有点兴趣,我们都会本能地去寻找有关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党项族是真的灭亡了,还是融入了其他民族中,我们无法断定。但作为跨越历史维度的“他者”,我们无法去记忆,只能凭借想象去建构。西夏佛塔象征的族群历史记忆场是一个理想型的“场”,一个历史的“场”。要建构这个已经消逝族群的历史,佛塔和宗教史是最容易去把握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一部西夏国的宗教史便是一部党项民族建国立业的兴衰史,党项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建构必须依赖于这些古塔以及古塔出土文物。
三、文化交流与多元融合的文化景观
如果将宁夏境内所有的古塔看作一个个孤立的坐标点的话,那么将各点之间用一条条线相互连接起来,从而形成的网络所覆盖下的就是繁盛的西夏宗教文化圈。党项人的信仰不是孤立和静止的,而是在不断的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这种宗教文化是历史性的和动态的。这给我们一种启示,似乎文明的交流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纵观世界文明史,很多文化现象正是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的。
由于西夏主要所在地的河西地区是中国佛教传播和信仰比较早的地区之一,党项族东迁至此之时,当地的汉、吐蕃、回鹘等民族已信仰佛教。由于常年的迁徙加上中原和吐蕃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人们感到痛苦,他们向往美好的生活,“佛教因果报应的理论,以及经过信佛行善可以解脱轮回、往生极乐世界的说教,为现实生活中饱受煎熬的劳动人民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4]。党项民族也因此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佛教。西夏建国之前,夏州节度使李德明于宋景德四年(1007年)要求到五台山修供佛寺,献供物,他还派使臣到宋朝求取大藏经一藏。元昊继位后继续向宋请取佛经,并到五台山供佛。西夏第二代皇帝毅宗母后没藏氏一度出家为尼,她于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命令兴建承天寺及佛塔,用以供佛所求经书和舍利。到了惠宗时,曾经第六次向宋朝求经。
由此可见,西夏早期所信仰的佛教受内地显宗的影响较大,六次向中原求经反映了西夏在国家层面上对佛教文化的需求与重视。但是西夏晚期的时候,由于受吐蕃的影响而接受了密宗的思想。因此,佛教在中国的两大主要宗派通过党项族而在西夏交汇,汉传佛教往西到西夏境内便止步不前,而藏传佛教往东到西夏也戛然止步,两大佛教宗派在此相互碰撞,彼此借鉴,并通过党项民族的发挥而形成了一种融合显密两宗的宗教文化景观,而留存至今的西夏佛塔便是这种文化景观的代表。
如前所述,西夏国境内并非单一的党项民族,同时还有汉、回鹘、吐蕃等民族。因此,西夏国内的民族文化结构也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格局,以党项族为文化创造主体,其他各民族参与到创造过程中。在党项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互动过程中,这个民族无意中担当了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这种中介作用也可通过这些佛塔来体现。
西夏佛塔是一种多元宗教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景观。一是对唐宋中原佛塔文化的吸收。唐朝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佛教寺院和译经规模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僧人数量更是达到历史的巅峰,而当时的佛塔建筑多呈现为楼阁式和密檐式砖塔,多数是正方形的平面形式,代表作有西安大雁塔等。宋代的佛塔多呈正八边形,塔身外用砖堆砌,中空而成塔室,承天寺塔和康济寺塔等都借鉴了唐宋佛塔的艺术形式。二是对辽金佛塔的借鉴。辽金流行一种上覆钵、下楼阁式的佛塔,现有具体年代可考的辽道宗清宁四年(1058年)所立的天津蓟县观音寺舍利塔即属此类。三是对藏传佛教宗教建筑形式的借鉴吸收。西夏后期盛行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佛塔形式多样,如球形塔、覆钟塔、扁圆塔等,并饰以不同的颜色,如桑耶寺的白塔、绿塔等,而位于青铜峡水库斜坡的一百零八塔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风格。同时,覆钵式塔在西夏中后期出现,这一定程度上是西夏跟吐蕃加强交流的反映。自11世纪以后,西夏不断占领属于吐蕃的夏州、甘州等地,至12世纪,西夏乾顺帝更与青唐联姻,这一切打通了西夏跟吐蕃的关系,使得两种文明的交流成为可能。
由此可见,西夏佛塔不仅表征出建构历史和文化想象的宗教文化空间,它更是记录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展现多种宗教文化元素融为一体的文化景观。文化的交流有时候是潜意识的,但它的功能却关系到一种文化形态的生命力。
[1]牛达生.宁夏境内的西夏古塔建筑[J].寻根,2010(6):58-65.
[2]转引自承天寺塔简介碑文.
[3]史金波.西夏的佛教(上)[J].法音,2005(8):34.
[4]史金波.西夏的佛教(下)[J].法音,2005(9):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