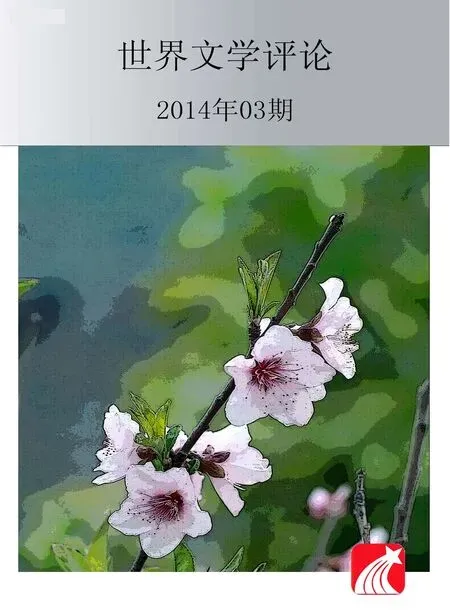问汝平生相思,空忆赤阑桥西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姜夔“合肥情词”解读
2014-11-14王平
王 平
问汝平生相思,空忆赤阑桥西——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姜夔“合肥情词”解读
王 平
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其产生的特定文化基因,特定的地理环境是决定文化基因的关键,自然山水环境与作家的成长及作品的产生存在必然的联系。大抵之于读书人总有一个地理环境是特别的存在,比如,苏东坡的“黄州惠州儋州”,柳子厚八书以记的“永州”,刘梦得二游的“玄都观”等等。而对于姜白石来说,这个特别的地理环境就是“合肥”。30岁之前,白石寓居合肥赤阑边西风门巷时,结识了赤阑桥边两位琵琶艺妓——莺莺、燕燕,一往情深。在以后的时间里,他写了20多首词来怀念这两位情人或歌咏合肥风物。白石几次往返合肥,其行藏痕迹与词章的创作关系十分密切。
一、合肥与姜夔词的创作
白石一生风流自任,却专情于合肥的红粉知己。他在合肥的这一段情事,铭心而刻骨,常于其文字中透露出只鳞片爪,却又总是语焉不详。半个世纪前,经过夏承焘先生仔细地寻绎勾勒,终于使这段情缘为人所知,我们将词人缅怀“合肥情事”的词作称为“合肥情词”。据夏承焘先生的《合肥情事考》与《姜白石词编年校注》,在白石现存的作品中,与“合肥情事”有关的词作有20多首,约占其全部词作的1/4,而他对发妻萧氏,却无一语提及,足见其对这段恋情的萦心不忘。
(一)合肥渊源
姜夔原籍饶州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市),自幼随父亲宦游于湖北汉阳。自青年时期起,他就与当时宿儒名士广为交游,往返羁滞于江淮湖杭之间。后来,萧德藻因赏识姜夔的才华,将侄女嫁与他,姜夔遂移居吴兴(今浙江湖州)。由于他经常往来于江淮之间,而合肥(又作“合淝”,顾名思义就是肥水汇合之地)处在长江水系和淮河水系的衔接处,是当时水陆交通的枢纽,这就为他与合肥结下不解之缘带来了契机。
(二)合肥情结
30岁之前,白石寓居合肥赤阑边西风门巷时,结识了赤阑桥边两位琵琶艺妓——莺莺、燕燕,一往情深。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姜白石32岁时,路过合肥,却不能停伫。客居长沙,追怀合肥恋人,写有《一萼红》、《霓裳中序第一》、《小重山令》。同年秋,客居汉阳,写有《浣溪沙·著酒行行满袂风》。岁暮从武昌沿水路东下,宋淳熙十四年丁末元日抵达金陵。遥望淮南群峰,他又想起了与燕燕、莺莺的朝夕相处的时光以及离别时的难舍难分,江上感梦,写下了著名的《踏莎行》一词。第二天,又写下了《杏花天影》。
自此三年后,于宋淳熙十六年(1189),白石客居吴兴,载酒春游再次想念远在合肥的恋人,作《琵琶仙》抒写离情。
白石第二次客居合肥是在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初,写有《淡黄柳》吟咏合肥风物。初夏,流寓金陵,始离开合肥时,写有《浣溪沙·钗燕笼云晚不归》,此时,感时怀人写有《醉吟商小品》、《长亭怨慢》。秋,由金陵重返合肥途中,夜不能寐,写有《秋宵吟》。词人终于又回到了伊人身边,心情愉悦,词集对此有明确的记载。例如,《摸鱼儿》序云:“辛亥秋期,予居合肥。小雨初霁,偃卧窗下,心事悠然。起与赵君猷露坐月饮,戏饮此曲。盖欲一洗钿合金钗之尘。”(夏承焘 104)这次欢聚不久,词人乘舟东下,再次离开合肥。这次离别倍感伤情,白石写有《点绛唇·金谷人归》、《解连环》。白石在石湖,与范成大盘桓一月有余,写下《暗香》、《疏影》等著名的词章。夏承焘先生依据词中“叹寄与路遥”、“红萼无言耿相忆”、“早与安排金屋”等语,认为这与“合肥情事”有关,仍是对燕燕、莺莺的怀念。(夏承焘 49)
自此以后,白石再未与恋人相会。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白石客居绍兴,在鉴湖写了一阕《水龙吟》,深情回忆相识之时的场景,叹息道:“我已情多,十年幽梦,略曾如此。”(陈书良 141)
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冬,词人在无锡,打算再去合肥,却因事未果,又形之于梦,醒后作《江梅引》以寄相思。元宵之夜,又在梦中与二姬相会,写下《鹧鸪天·元夕有所梦》。同年,写有《月下笛》追怀合肥恋人。
“不同区域的地理特征绝非纯客观的自然存在,受作家环境感知与地理价值判断的支配,它们被赋予强烈的主观色彩,通常用以指示个体生命历程的延伸与坎坷,承载创作主体的喜怒哀乐等种种体验。”(周晓琳、刘玉平15)在白石客居合肥赤阑桥边西风门巷期间,此处的地理空间的架构深深影响了其词的创作。比如,《淡黄柳》中曾提到“小桥宅”,桥公(玄)曾住在临近赤阑桥的回龙桥桥畔。桥公有二女,长女大乔,次女小乔,皆一代国色,姜白石在“合肥情词”中常提到二乔。如“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强携酒,小乔宅”(《淡黄柳》)(陈书良 92),“为大乔能拨春风,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解连环》)(陈书良 119)。因为白石在此与一对姐妹歌妓相爱,赤阑桥与回龙桥又相距不远,所以常以“二乔”喻他所爱的姐妹歌妓。
二、独具匠心的地理影像
凡是地理空间上的万物之象,只要写进文学作品里,都可以称之为文学作品中国的地理影像。“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从根本上规范着古代作家审视地理环境的文化视域,密切了创作主体与自然景观的心物联系” (周晓琳、刘玉平 15)在“合肥情词”里,频繁出现了几个独特的地理影像,透彻明晰地向我们传达了白石词作的情感意蕴。
(一)莺、燕
地理环境会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影响,进而对文学家的创作造成影响。(曾大兴24)在合肥这个地理环境的影响下,白石“合肥情词”的地理影像别具特色。与黄河流域诗歌众多粗犷的地理影像不同,“莺、燕”十分符合长江流域诗歌地理影像“纤细柔美”的特点。正值青春年少的白石遇到了风华绝代的莺莺和燕燕,在此后的生命里,他唯有文字以慰相思。在20多首“合肥情词”里,“莺”出现了3次,“燕”出现了7次。莺莺、燕燕既是两位女子的名字,同时也是古典诗词中经常出现的地理影像,在白石的“合肥情词”里可谓有双关之意,具有丰富的情感内涵。
1.借助“莺、燕”传达思念情人之切
江淮春季,黄莺通常双宿双飞, 燕子则素以雌雄颉颃,飞则相随,引发了有情人寄情于燕、莺,渴望比翼双飞的情怀。曾在此寓居的白石则借助地理影像“莺、燕”传达思念情人之切。试看《踏莎行》,词曰:
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陈书良 47)
这首词以“莺莺”、“燕燕”开篇,既是借“莺莺”、“燕燕”称呼昔时的恋人,流露出缠绵情意,亦含双关之义,即以燕、莺各自的鸟类特性比喻伊人体态“轻盈”如燕,声音“娇软”若莺,“燕、莺”句乃是词人梦中所见的情境。日有所思,夜才形诸梦,这就向我们传达了词人日夜相思的情态。笔触一转,是“莺莺”、“燕燕”的自述,表达恋人对自己的相思之情。下片写自己与情人别后睹物思人,旧情难忘 。紧接着承接上片的梦境,进一步写伊人之情。诉说伊人离魂以追随所爱,无奈却是“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末二句写词人梦醒后,想象恋人魂魄无奈归去的情景:在一片清冷的月光下,淮南千山愈发清寒孤冷,她就这样独自归去。一种怜惜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
王国维说:“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彭玉平 128)可见评价之高。这首词可以说是以“莺莺”、“燕燕”贯串全词的,词人想念“莺莺”、“燕燕”,而又不单写自己的相思寂寞之苦,亦写到“莺莺”、“燕燕”思念自己,可见白石之至情至性。
2.借助“莺、燕”幽诉离情之苦
古人认为燕能传书,白石则借助地理影像“莺、燕”传达离情之苦。试看《月下笛》,词曰:
与客携壶,梅花过了,夜来风雨。幽禽自语。啄香心,度墙去。春衣都是柔荑剪,尚沾惹、残茸半缕。怅玉钿似扫,朱门深闭,再见无路。凝伫,曾游处。但系马垂杨,认郎鹦鹉。扬州梦觉,彩云飞过何许?多情须倩梁间燕,问吟袖弓腰在否?怎知道、误了人,年少自恁虚度!
(陈书良 203)
这首词是白石追怀昔日冶游,思念昔时恋人之作。光阴已逝,情事已非,词人依旧不能忘怀,于是“与客携壶”,借酒浇愁写下了这首《月下笛》。这首词开篇即已点出仲春的时令,接下来描写“幽禽”,称黄莺为幽禽,暗示词人心情的孤寂、幽独。“自语”二字,实写黄莺,却暗示了词人清苦寂寞的情怀。下面以细腻的笔触写到身上穿的春衣是伊人素手亲绣,词人睹物怀人,却把无限深情凝聚在不易觉察的“残茸半缕”之上,从中可知词人对这件春衣凝视之久,观察之细,进而表现出对这件春衣的珍视以及对裁衣之人的惦念。下片用“凝伫”作引领,追忆昔日冶游,一个“但”字,使时空由过去转到现在,从而把人去楼空、事过境迁的感慨传达了出来,有风景不殊而情事已非的深深慨叹。大梦既觉,却还是难以忘怀“吟袖弓腰”,忍不住托付“梁间燕子”去代为探问,写出了词人无限惆怅难解之情。
这首词开篇以地理影像“莺”暗示词人的心绪,中间情感几经起伏,词人甚至宽慰自己,斩断情丝,最后还是难以自制情感,以“燕”传书,表达自己的一往情深,地理影像——莺、燕,各据首尾,使词人的情深意切似在一个无限循环的圆之中,别具韵味。
白石用地理影像“莺、燕”传达感情的词句还很多,如“金陵路、莺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陈书良 50)(《杏花天影》),“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陈书良 117)(《点绛唇》),“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 (陈书良 92)(《淡黄柳》),“流光过隙, 叹杏梁、双燕如客” (陈书良10)(《霓裳中序第一》)等等。由此可知,“莺、燕”这两个极具江淮地区特色的地理影像,对白石创作的文化心理结构(包括生活经验、文化积累、生命意识、价值观念、个人气质、思维方式、审美追求等)影响很大。
(二)柳
在20多首“合肥情词”里,地理影像“柳”出现了10次之多。“柳”自“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程俊英、蒋见元 462)(《诗经·小雅·采薇》)起,又因为“柳”字谐音“留”,发展至后世多表现离情。
白石“合肥情遇与柳有关”(夏承焘 28),白石当年曾住在杨柳夹道的赤阑桥西的小巷内,此处的地理空间的架构深深影响了其词的创作。赤阑桥的景象在白石的词章创作中时有出现,有诗为证:“我家曾住赤阑桥,邻里相过不寂寥。君若到时秋已半,西风门巷柳萧萧。” (陈书良 93)(《送范仲纳往合肥》)他还专门用“淡黄柳”为词牌,自制了一首咏合肥的词,在词前的小序中,提到自己曾在合肥居住,并强调柳树很多,这也是他将词牌称为《淡黄柳》的原因:“居合肥南城赤阑桥之西,巷陌凄凉,与江左异。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因度此片,以纾客怀” (陈书良 92)。桥边柳色浓郁,此处别浦萦回,在这种地理环境之下,游子多折柳相送,佳人常倚桥相思,留下众多的文坛佳话,美诗妙词。
《杏花天影》词曰:
丙午之冬,发沔口。丁未正月二日,道金陵。北望淮楚,风日清淑,小舟挂席,容与波上。
绿丝低拂鸳鸯浦。想桃叶、当时唤渡。又将愁眼与春风,待去;倚兰桡,更少驻。金陵路、莺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满汀芳草不成归,日暮;更移舟,向甚处?
(夏承焘 50)
从词序中可知此时为正月初,远不是柳丝低垂的时节,唯青青柳芽,依约可见。故首句是虚写,词人因初萌的柳芽而想到垂垂柳丝,继而念及巷陌多种柳的合肥,引起怀人之思。渡口青青杨柳,词人追念前朝桃叶典故,再“北望淮楚”,益动怀人之思。下句又写柳芽,与开篇“绿丝”相呼应。王国维曰:“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彭玉平188),在移情的作用下,愁人见欲绽还闭的柳芽,自然也恍似含愁。词人此处之愁,大概是柳可再见而人难重觅,景物犹在情事已非之恨,故着一“愁”字。接下来写与合肥渐行渐远,词人心系伊人,眼前的一切遂幻化为合肥杨柳依依的巷陌,眼前的“莺吟燕舞”也幻化为他魂牵梦萦的往日恋人。结尾几句,不知人该归何处,更不知情何以堪,言极其“苦”。
由地理影像“柳”引起诸般想象与无限痛楚,均注于词意转折之中,其心之痴,其情之深,其思之切,其念之苦,虽未明言,已然“尽在不言中”了。
又《琵琶仙》词曰:
《吴都赋》云:“户藏烟浦,家具画船。”唯吴兴为然,春游之盛,西湖未能过也。己酉岁,予与萧时父,载酒南郭,感遇成歌。
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桃根桃叶。歌扇轻约飞花,娥眉正奇绝。春渐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几声啼鴂。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又还是、宫烛分烟,奈愁里匆匆换时节。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榆荚。千万缕、藏鸦细柳,为玉尊、起舞回雪。想见西出阳关,故人初别。
(陈书良 71)
此词的主旨并不在春游,而在感发对昔时恋人的一往情深。上片写暮春时节看到与情人相似的面孔,心情由惊喜到失落再到沉痛,只能安慰自己“前事休说”,蕴含了词人无限心伤的情态。下片又漾开笔触写景,“又还是、宫烛分烟,奈愁里匆匆换时节”,此处化用韩翃《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顾青318)下句“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榆荚”,化用了韩愈《晚春》:“杨花榆荚无才思 ,唯解漫天作雪飞。”(彭定求 1746)上两句所化用的诗,皆含有杨柳之描写,从而引出下一句“千万缕、藏鸦细柳,为玉尊、起舞回雪”。此句从眼前的青青杨柳,幻化出别时依依难舍的情境。眼前渐可藏鸦的杨柳,不由让人想起初别之时,柔柳轻舞,漫天飞絮,依依留人。词人从化用二韩之诗引出杨柳之实写,从现境之杨柳引发忆别之幻境,以“柳”为媒介,转换自然而意境空灵清远。
白石寓居合肥时,因其生活环境中多柳树,进而影响了他的文化心理结构,故而,词作中的地理影像——柳,在“合肥情词”里别有一番韵味,体现了“合肥情词”极具地域性的特色。此外,在白石“合肥情词”中,“草、风、雨”等地理影像出现频率也较高,多是寄托或衬喻词人的离愁别绪。
三、别具特色的地理时空
各具特色的地理时空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地理时空各有千秋。纵观“合肥情词”所呈现的地理时空,时间上,多为冷色系,隐含着情感意蕴的悲剧性;空间上,则多与“水”有关。
(一)时间的冷色调与悲剧性
地理时空对于一个作家生命意识的影响是显著的,地理时空的变化使得作家展开关于生命状态、价值与意义的深层次思考,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古人多伤春悲秋。纵观“合肥情词”,其描写,在季节上,多为春天(大部分为暮春)和秋天;在时间上,多为黄昏以及夜晚。“黄昏意象”出现了7次,明确点明时间是“夜”的有9次,可以从词意中领会出是夜晚的有4次。这些时间在感情色彩上都是冷色调的,且都有一种生命意识在其中:暮春时节,百花凋零,极易引发词人的伤春怀人之情;清秋已至,秋风惨淡,情怀难免寥落。许瑶光在《雪门诗草》(卷一《再读〈诗经〉四十二首》)里说:“最难消遣是昏黄。”(傅道彬 60)长夜历来漫漫,最是让人伤神多思。这些特定的时间都与词人一生不得所爱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相符合。
试看《解连环》,词曰:
玉鞍重倚,却沉吟未上,又萦离思。为大乔能拨春风,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柳怯云松,更何必、十分梳洗。道郎携羽扇,那日隔帘,半面曾记。
西窗夜凉雨霁,叹幽欢未足,何事轻弃。问后约、空指蔷薇,算如此溪山,甚时重至。水驿灯昏,又见在、曲屏近底。念唯有夜来皓月,照伊自睡。
(陈书良 119)
上片言及时间为秋季,写到彼此即将分离却百般不舍,接下来赞美伊人技艺超拔,并追忆他们初见时的情景,可见其情之深挚缠绵。下片用一系列冷色调意象,调动想象、幻觉来描写惨别。深夜秋雨,孤馆不寐,回忆最后一次分别时的情景,“问后约、空指蔷薇”与“算如此溪山,甚时重至”似是矛盾,约定蔷薇花开时见,为何又问“甚时重至”?从此处可知词人心中亦不知何时再见,但为给安慰伊人,只能空指蔷薇,掩饰不住的凄惶尽现于表。此三句曲折尽致地刻画出了伊人的一片痴情,也写出了词人内心的失落。追忆至此,接下来写的是幻觉之境。“水驿灯昏,又见在、曲屏近底。”昏暗的灯光下,曲屏近处又见伊人倩影。此一霎幻觉之描写,写出此时词人相思入骨以致神志恍惚。一个“又”字,可见精神恍惚已是常事,极言相思之切。结句“念唯有夜来皓月,照伊自睡。”凄凉无尽。
词中深夜秋雨,孤馆不寐,孤灯昏黄,烘托出的是幽沉哀怨的气氛,使表达的相思之情深婉摇荡,更为动人。此外,《长亭怨慢》(陈书良 97)写的是暮春时节,黄昏时分的离情,凄怆至极。《醉吟商小品》(陈书良 102)、《摸鱼儿》(陈书良 104)、《秋宵吟》(陈书良114)等词作都是运用冷色调的时间加剧了词作的悲剧性,成为词人表达悲戚伤感、幽怨多苦等情感的载体。
(二)地理空间的特点、成因及转换
在白石的所有“合肥情词”中,地理时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几乎每一首都和“水”有关,不是“水边送别”就是“见水怀人”。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与合肥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合肥处在长江水系和淮河水系的衔接处,是当时水陆交通的枢纽。古人的交通方式比较单一,词人南北穿行,大多行水路。那么,在水边发生的这一段铭心镂骨的情事,自然容易引发词人触景生情的感怀。
1.水边送别与见水怀人
“合肥情词”中的这些与水相关的地点多为“鸳鸯浦”、“池塘”、“远浦”、“江上”、“西湖”等。词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水边送别”和“见水怀人”。
从《浣溪沙·钗燕笼云晚不忺》(陈书良85)中提到的“系船”、《长亭怨慢·渐吹尽、枝头香絮》(陈书良 97)中的“远浦”,读者可以知道情景的发生地理空间是“水边”,这些词作都是词人抒写与伊人在水边依依相别的情景。
从《踏莎行》的词序:“自沔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 (陈书良 47)可知,其地理空间是“江上”。《浣溪沙·著酒行行满袂风》是怀念合肥恋人最早的作品之一,词序曰:“予女须家沔之山阳,左白湖,右云梦,春水方生,浸数千里 ,冬寒沙露,衰草入云。丙午之秋,予与安甥或荡舟采菱,或举火罝兔,或观鱼下;山行野吟,自适其适;凭虚怅望,因赋是阕。” (陈书良 85)其地理空间也是与水有关。《杏花天影》词序:“丙午之冬,发沔口。丁未正月二日,道金陵。北望淮楚,风日清淑,小舟挂席,容与波上。” (陈书良 50)点明地点是“波上”。《摸鱼儿》、《凄凉犯·绿杨巷陌秋风起》等词作所呈现的地理空间也皆是“水边”,是“合肥情词”中“见水怀人”的典范。
2.地理空间的转换
文学地理学研究让我们领略了地理影像与文学情趣融合的审美效果,地理空间的转换对于文学作品的结构、思想意蕴亦有非凡的影响。这种地理空间的转换在“合肥情词”里是通过“梦”或是“回忆”为纽带的。试看《江梅引》,词曰:
丙辰之冬,予留梁溪,将诣淮而不得,因梦思以述志。
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枝,忽相思。几度小窗,幽梦手同携。今夜梦中无觅处,漫徘徊。寒侵被、尚未知。
湿红恨墨浅封题。宝筝空、无雁飞。俊游巷陌,算空有、古木斜晖。旧约扁舟,心事已成非。歌罢淮南春草赋,又萋萋。漂零客、泪满衣。
(陈书良 176)
词人见梅枝而思念远在淮南的恋人,因作此词,小序指出:“予留梁溪,将诣淮南不得,因梦思以述志。”说明这是借记梦而抒相思之作。上片以悲欢两种截然不同梦境来反映相思之情。“人间”三句写时光飞逝,相会仍是遥遥无期。忽见梅枝,相思之情,悄然而生,大有“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之意,然思而不见,就只能在梦中寻觅。“几度”句,写两人相会于梦中。淮南雅居的小窗之下,伊人几度进入词人的梦境与词人执手相望。“今夜”四句,写另一种梦境,今夜却是佳人难入梦,词人在梦中独自徘徊,心中悲苦难耐,甚至感觉不到寒气侵入衾被。两种梦境,前者暂时的温情,与后者凄苦的现实形成对比,更是带来无限的伤感。下片主要通过回忆写梦已醒,人却未能归的刻骨相思。和泪写成了香笺,无限伤心往事尽在其中——即便旧景从昨,然情事已非;空忆佳人素手调音,如今已是音讯难通,通过回忆透露内心的惆怅和伤感。
从词序中可知,词人身在梁溪,却通过梦境与佳人重逢于淮南,通过回忆“看到”淮南旧景,完成了地理空间的转换。纵观“合肥情词”,《鹧鸪天·肥水东流无尽期》、《霓裳中序第一·亭皋正望极》、《踏莎行·燕燕轻盈》等词作亦是通过梦境与回忆来连接不同的地理空间来怀念自己的情人。这种通过梦境与回忆完成空间转换,使读者更能体会到词人蕴藉深挚,低回不尽的情意。
王国维曾如是评价白石:“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彭玉平 121)唐圭璋先生认为这种评价有失偏颇,“余谓王氏之论列白石,实无一语道着”(彭玉平 124)。虽然两人关于白石的评价是宗尚不同所致,但通过文学地理学的分析可知,白石的词别具幽韵冷香,用情至深。在文学地理学的视域下,仔细品读白石的词作,尤其是“合肥情词”,探讨“自然环境对作家的影响,作品中所存在的地理空间,地理大发现对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邹建军、周亚芬),从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合肥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姜夔词创作的影响之大,以及“合肥情词”极具地域性的特点,同时有助于我们多层次多侧面地理解白石词的艺术魅力与情感意蕴。
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陈书良:《姜白石词笺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周晓琳、刘玉平:《空间与审美》,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中华书局2011年版。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
顾青:《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2009年版。
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傅道彬.《晚唐钟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的十个关键词》,载《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作品【Works Cited】
王平,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