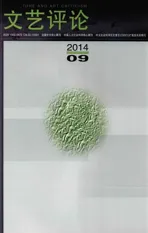对中国新世纪文学的观察和考量——关于朱小如《对话: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的解读
2014-09-29孔明玉
○冯 源 孔明玉
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里,对于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梳理以及中国文学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借鉴中国经验,无疑是许多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文学评论家甚为关注的,因而他们便以各自的学术见识、专业能力和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予以了多种向度、多个层级和深入肌理的智性分析。作为文学报刊的资深编辑兼著名文学评论家的朱小如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新近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对话: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一书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态势作为探寻问题的基点,通过对话的形式展开对中国新世纪文学自发生以来所形成的经验和所富于的范式意义的深入考察,目的在于对民族文学书写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中国经验进行智性的梳理,藉以在文学批评的学理层面上达成对中国新世纪文学书写的现有经验及其意义赋予理论总结的引领,进一步深入探寻在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走向中,我们应当如何发掘这种经验的意义和怎样鉴取这样的经验。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在其漫长的历时性的演进中,总会一步步地催生、形成乃至固化某些有着经验意义和范式功能的创作意识、艺术观念、表达技巧、建构方式、美学思想、审美精神、文学传统……这些都无疑是很值得我们去加以深入探寻和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总结的。因为只有建基于这样的起点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事业才能够沿着正确而康健的道路持续前行、愈发繁荣,最终在本质上铸造出这个国家或民族的一座座辉煌的文学圣殿,从而为整个世界所瞩目。中国文学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但以什么样的探寻方式来展开对文学书写的中国经验的分析和总结,又当以怎样的认知能力、学术水平、评判标准、价值认同对之进行深入、系统的考量,以及最终呈表出何种富有重要鉴取价值和意义的理论形态,这却是不尽相同、各有其意的。朱小如先生的探寻方式便是通过对话来展开。作为一直在当下各种文学研究学术场域里自由穿行,并竭尽所能对中国当代文学予以深沉注视和理性考察的朱小如先生,深知在学术研究中的这种对话形式自有其独特的优势所在:一是可以通过与不同的专家学者的对话、交流而引发彼此间的学术争论和思想激荡,不断拓展问题意识的视野和提升分析问题的能力,抵达对某些学术问题的多角度、深层级的理性判断和本质认同,切实有效地消解因研究者个体的学术自识限制所导致的在认知、评价、定论上的偏失;二是借助某些卓有成效的研究者们独特的问题意识或新颖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学术视野出发,以不同的研究方法探寻、厘清存在问题的复杂内部构成以及影响问题的诸多因素,最终实现对那些一直在学术界存有争议的复杂问题的深入梳理和现实解决。因而在此书中,我们看到参与同朱小如先生对话的,不仅有在学术研究领域声名显赫的著名专家学者费振钟、李敬泽、黄发有、洪治纲等,也有一直在评论界极为活跃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汪政、何言宏、张丽军等,更有在文学书写方阵或文学期刊编辑界叱咤风云的刘醒龙、何顿、贾梦玮、秦万里、杨斌华、王手、金宇澄等。同这些富于建树的行家里手们针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文学问题进行这般有着玄虚色彩、蹈空意味的对话,实则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因为对于首先发起对话的对话者而言,“除了思想和才华,还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问和长期的社会体验和人生感悟”。①对于朱小如先生而言,这似乎并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因为在他数十年的文学研究生涯和繁复多样的批评实践活动中,已然富有了这样的“社会体验和人生感悟”,具备了这样的“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问”、“思想和才华”,所以他得以在同这些行家里手们的一次次对话中表现出几许的从容和应对裕如,尽显一个著名文学批评家的独特见识和才能。
从文学研究的肌理层面上予以考察,即便是这种富有浓厚学术意味的对话,也不过是一种探寻问题的外在形式而已,只有真正达成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理论认同,并表征为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的理论形态,这样的对话才会是具有某种引领功能和实际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小如先生的这部著述《对话: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便有着对这种功能和意义的揭示。细致深入地翻阅朱小如先生的这部遑遑著述,著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谈起,从容自如地进入到中国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內腹,纵横捭阖地论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女权主义文学、先锋文学、都市文学、上世纪60年代作家的文学创作等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直入肌理地分析新时期文学以来众多小说名家们在各自的小说文本实践中所进行的审美建构和所显扬出的精神内涵、美学特质、文学意义以及存在的不足,像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古船》、莫言的《檀香刑》、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阿来的《尘埃落定》、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王安忆的《长恨歌》、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何顿的《湖南骡子》等,既有学理层面的深刻分析,又富于学术意义的公允评判,从而凸显出一个文学评论家所特有的伦理操守和职业素养。譬如在《何以“朦胧”,审美的退化——关于中国经验叙事的对话之一》中关于朦胧诗现象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分析,看似颇为另类和偏执,实则揭示了问题的本质所在:“所谓‘朦胧’是个低级问题,叶嘉莹说‘通感’这个词是钱钟书著作里早就谈论过的,让人们读钱的书,引导我们去读朦胧诗,然后才兴起钱钟书热和古典诗欣赏热。其实这是中文系的一种常识课。中国诗歌从来就非常强调瞬间的审美感受。我认为没有所谓的‘朦胧’诗,它也并不真是什么‘新的审美崛起’,只是反映了我们诗歌审美的退化而已。”②进而直揭我们曾经的文学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和那个时代所具有的病症,认为文学教育的简单化、文艺形式的单一性、长期的文化封闭和文化禁锢等,都是造成我们民族审美感觉退化的重要原因;又如在《寻根文学:走向悠久文化与亘古大地的文学——关于中国经验叙事的对话之二》里对于知青文学现象的分析以及对于某些知青文学作品的尖锐批评,认为知青文学产生的文学起点很低,同思想解放的大历史背景不相匹配,因而它也仅仅是“保持了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单纯幼稚却不失真实的自我成长的叙事而已”,“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和叶辛的《蹉跎岁月》只是抓住了这样一种‘苦难’的时代表象,但宣扬的却是‘青春无悔’的高调。我对唱这种‘青春无悔’高调的作品一直很反感,因为它们显然降低了一代人精神的‘苦难’深度,只是把自己城市人下乡(完全无视农民本身的)‘苦难’当作自己的风流成长史来写”;③再如在《女性还是女权?——关于中国经验叙事的对话之四》中对于女权主义文学既不失诙谐、幽默的调侃又富有理性睿智的坦诚评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学批评一开始就是用‘女权主义’名称,也就是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来解读新时期文学一大批女性作家的作品。但似乎是女作家们一般都不太愿意被评论家戴上‘女权主义’的硬帽子。于是‘女权主义’就改称为‘女性书写’、‘女性文学’这样的软帽子。软帽子虽然比硬帽子戴得舒服,但缺少了性别政治的尖锐性,同时也矮化了女性解放应有的精神追求高度。这里面的问题恰恰不在于男性对‘女权主义’的不认同,相反的是女性对‘女权主义’的不认同。”④朱小如先生在这部著述中所发出的诸如此类的学术批评声音,不仅领悟深彻、见解独特,而且一语中的、洞穿本质,都给读者以非常强烈深刻的印象以及深度的认知启迪。
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对于中外文学发展史的基本常识的具备,以及对于文学史发展的清晰脉络和主要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的了解、认知、把握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任何文学现象、文学思潮都只能是一种史态框架中的存在,任何文学史也必然是在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两者之间的高度关联性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一旦缺失了这样一种最为基本性的知识具备,而孤立地看待发生于当下的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我们就势必会对之做出偏失性甚至错误性的评判和论定。朱小如先生在《对话: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这部著述中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以来发生的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分析和评价,便是从这样的最为基本性的知识具备出发的。关于“民族文化叙事资源”或“中国经验叙事”等论题的讨论,无疑是近些年来在学术界和文学批评界较为热议的重要话题之一,有学者认为中国经验叙事的发生和生成是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叙事,也有专家认为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文学经验叙事的有效借鉴,朱小如先生则认为它主要在于对中国古典叙事经验的传承,同时也是对西方文学叙事经验的汲取,是两者之间形成了高度而有效的融合体,对任何一方的肯定或否认都是一种偏失性的理解或误读性的判断,并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纵深层面对之进行了一番富有实证意味的论说:“中国式的经验,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缺乏,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人、鬼、神、魔俱成叙事,笔记体、章回体也都独具特色。鲁迅的小说实践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先河,虽然从某种角度上说,是接受了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及医学、心理学的影响,将原本拖沓的、松散的小说自然长度浓缩在一个现在进行和现在完成的时态里,但从他的代表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和《铸剑》来看,走的也仍然是疯、狂、痴、癫的叙事偏锋,在他‘清醒的’现实主义中往往不惜采用‘曲笔’,其实多多少少暗合着中国传统小说中人、鬼、神、魔的叙事艺术气息。”⑤由此出发,朱小如先生又对存在于当下的那些偏失性理解、误读性判断予以了批评,并揭示了它们产生的根由所在——在于我们的文艺理论和外国文艺理论的滞后。勃然兴盛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叙事,无疑是对已然定型化的中国乡土叙事的一种突破,同时也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审美表述,但这样的城市叙事却一直失意于中国的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面对此种现象,不少文学研究者、文学评论家都表示出了难以理解的疑问,是因为乡土叙事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苦难意识、文化沉疴、伦理观念的审美表达更容易引发国人的情感共鸣,还是由于乡土叙事自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性以来就是一种在中国文学史上中占据主导、优势显著的叙事方式,拟或是我们的城市叙事本身存在着诸多缺陷与不足的缘故?因而对于城市叙事的深入分析便在所难免。在朱小如先生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城市叙事,无论是《子夜》还是《上海的早晨》,城市的美感几乎就是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同,处于被否定之列。这或许可以被理解成受当时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所局限。而现在这种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没有了,但城市的美感却没有提升多少,这似乎是因为审美的惰性,或者说城市的美感还缺少文化积淀。只要说到城市,我们所见的词不是‘酒吧’就是‘发廊’,再不就是‘小资’或者‘新天地’之类的做旧”,并以波德莱尔的作品《恶之花》为例证,说明西方文学在这方面的情况也大致相似。⑥显而易见,朱小如先生是把城市叙事本身的欠缺与不足看作是它不能登上中国文学奖的根本原因之一,虽然这样的观点未免有些偏颇,但却能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我们的城市叙事进行分析,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问题意识和探讨问题的方式。
对于自中国新时期文学以来不断涌现出的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小说名作和这些小说在审美建构中所表达出的多元而复杂的思想蕴意,以及这些小说的创作者在自身的文本实践中所显露出或隐蓄着的文学思想、审美观念、文化心理、人文意识、精神向度、美学追求等的探寻,无疑也是朱小如先生这部著述里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任何具体的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又同创作主体所具有的童年记忆、生命历练、现实处境、心灵意向、情感状态以及审美心理结构紧密相关,因而从作家创作与文本建造的内在关联性角度进行深入考量,我们便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最为基本的事实:一个作家的具体的文学活动实践和所建造出的富于个性内涵的文学文本,必然是其所富有的文学思想、审美观念、文化心理、人文意向、精神向度、美学追求等的综合体现。尽管这样的体现有可能是显性形态的,也有可能一直处于隐性状态之中,都无一例外地在确证着创作主体与文本建造之间的多种复杂关联性,从而为那些富有卓越研究能力的分析者的理性进入提供了或明或暗的甬道,分析者也总能在这个甬道的深处寻觅到小说文本生产的根由以及创作主体所要表达的思想蕴意和精神指向,进而深入展开对创作主体及整个文学文本生产的内在要因的全面分析。朱小如先生正是这样一个分析者,对于任何一位进入他对话视野的作家作品,他都能够从学术研究的学理深度进行分析,或直言不讳地进行尖锐的批评,或是含蓄地揭橥小说文本的意义,拟或从历时性的纵向角度来探究文学文本的史态价值,给读者在作品解读上的深入、分析问题视野的拓展和在认知层面上的打通以十分有益的启迪。贾平凹先生的长篇小说《废都》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反响,尽管文学评论界一直对它褒贬不一,但在有一点上却是共认的——《废都》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庄之蝶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通过对这个中国当代文学人物形象谱系中的“知名人士”的新颖塑造,写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沉沦”。朱小如先生对庄之蝶的知识分子身份却持十分怀疑的态度,“我更愿意把庄之蝶看做一个‘旧文人’,因为在他身上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太缺乏了。这并不是仅仅从他对女性的态度和意识来看,而在于他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在于透过他的视角我们看到的‘帝都’,骨子里还是中国式的土财主气息,而非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气息……以庄之蝶来表征‘知识分子’形象,是否说明了在人们的心中对‘知识分子’的想象出了问题”。⑦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无疑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能够荣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便是最好的明证。但关于这部小说所弥漫出的浓郁的“怀旧”色彩或“悼亡感”,以及创作主体产生这种情感的根源是什么,则是各执一词、几多争议。朱小如先生认为,这同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商品社会转型有关,是商品社会的突然降临彻底打乱或拆解了人们的情感认知序列与情感认同方式,在不忍其扰、不堪负重的情况之下便纷纷开始各自的情感意向的转变,而怀念、眷顾农业文明时人的情感生存状态,这恰恰从另一角度确证了人们的思想所存在着的某些缺陷,他指出:“作家们虽然生活在城市里,却并没有真正进入商品社会,于是作家们所习惯的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没有了太大的区别。作家们喜欢城市生活,只是对‘商品’不仅有抵触,甚至习惯了对‘商品’的批判思维,同时作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商品’的诱惑极大,大到足以颠覆作家们的思想,但作家们就是没发现自己的思想原本就有缺陷,原本就不健全。于是作家们只能凭‘想象’而不是用‘体验’来处理‘商品’现实。”⑧当然,朱小如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如此论道,也仅仅是他的一家之言,正确与否是值得商榷的,但至少从某一个方面揭示了那个时代作家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感的内在原因。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以词典的方式进行小说叙事结构和文本组织,一举成为我们汉语长篇叙事解放的成功标志之一,但也同时给习惯了编年体式、章回体式小说叙事的中国读者的文学接受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从而在优秀长篇小说排行榜上总是位列靠后。对此现象,朱小如先生也颇为不解,认为不仅仅是因为这部长篇小说在叙事结构方面的创新阻遏了文学接受大众的阅读兴趣,更在于它所要表达的内容构成了对“公共化语言”的压迫和障碍,进而具有归纳意味地这样指出:“《马桥词典》‘解放’的成功意义,首先就是这个语言的‘去中心化’,其次才是反小说叙事的‘线性故事情节结构’的审美习惯……这样的好处在于打开了小说惯常的整体‘封闭性’,但坏处却在于不能将作者的主观意图、思想躲避在‘虚构性’的客观叙述的故事情节之中。”⑨由是可见,朱小如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分析所显示出的深度和专业性。
著名文学评论家颜敏先生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症候分析》一文中指出: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由于受到“文学批评脱离社会现实、批评主体深受文学体制束缚、批评文体遭受世俗社会庸俗病菌的侵蚀等三个方面”⑩的因素影响,从而导致了文学批评“缺乏思想激情与社会责任感,不愿直面思考复杂的现实,更不用说触碰社会的敏感神经了;越来越注重专业的规范性和技术的操作性,充满学究气息……”⑪等乱象、病象的频发,并以米兰·昆德拉的“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的深刻之言告诫我们要对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进行强烈的全面反思。论者以为,朱小如先生在他的这部著述中表现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批评精神不仅不在颜敏先生所指的乱象、病象之列,相反则更体现出了批评思想的深刻与睿智、批评态度的郑重与真诚、批评思维的科学与严谨、批评方法的多样与灵活,这正如朱中元先生在《对话: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前言》中指出的这样:“总体而言,朱小如的批评可以视作声音、行为、发问的多声部合唱。其中他所著的正式批评文章,是其深思熟虑的郑重发声,学理层面的东西比较多,类似大提琴,声音沉着而厚重,幽深而坚实;其行为批评包括编选、推荐、研讨会发言等如鼓,虽不时时发出声响,但适时发声,掌控着节奏,击中要害;其发问有着发问者的睿智,尖利而急促,往往能启发被问者的思绪,点重文学现象和文坛的要穴,虽是问题,也有观点,类似打击乐的金属乐器,轻轻一点,却能发出悠长而尖锐的声音,引人深思,扭转讨论的进路。朱小如先生游走于这三者之间,娴熟地掌握各种乐器及其特性,在形成各自特色的同时演奏了多声部的交响。”⑫论者以为然,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就应该像朱小如先生这样,恪守文学批评的伦理道德底线,坚持文学批评的公允思想和严谨作风,在文学批评的思维、方法上做到既有“整体性”的思维又不失方法的灵活多样,从而完成对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深度梳理,建构出具有公信力的“中国经验”理论形态,为民族的文学事业奉献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