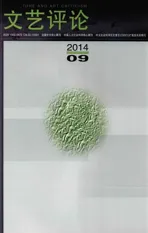晚清金石著述刊刻观念异同分析——以潘祖荫、陈介祺及其金石交游群体为例
2014-09-29程仲霖
○程仲霖 王 绘
潘祖荫(1830-1890)字东镛,号伯寅,较早步入翰林,一生高官厚禄,有搜罗古籍文献、金石文字之好,是晚清金石家与藏书家。陈介祺(1813-1884)与潘祖荫因父辈同官中枢而为世交,不惑之年返归山东潍县后,专心金石研究,是晚清鉴别最精、传拓最佳、多有创见的金石学家。二人同好金石,因而函札往来,颇多交流,为晚清金石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潘祖荫还搜访古籍,藏有百部以上宋元秘本、明清旧椠、域外孤本,并且择其善者刊刻出版几近百种,其中包括大量前人及时人的金石著述,保存了大量文献。其时,与潘、陈交游密切者还有吴大澂、王懿荣、吴云、鲍康、李佐贤等,他们收藏金石,同时出版金石著述,由于治学态度、收藏状况、刷印条件的不同,各家表现出不同的刊刻观念,本文就此作一粗浅分析。
一、金石著述刊刻的重要性
同治三年(1864)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书成,沈均初作跋文云:“物之寿无过金石,然惟藏也,历久不敝故。千载前物,日出而不穷,及出之,则天时人事得而成败之转,不能自存。其能存者,在著录家宋以前著录之碑。近数十年所出之碑,或皆不可见。其名可道也,著录存之故也。世不及见宋以来著录之碑,今时所出,宋以前人亦有不克见者,有宋后若元若明皆不克见,今复见者,曷以知之,著录存之故也。”①沈氏强调了刊刻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著录,碑石毁弃,拓本无寻,即永远消失。而著录之后,虽时代远隔,不必得见原石,可永存于世。罗振玉《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也说:“古器不能久存,设馆陈列,宇内学者不能人人就观,故宜遴简通人,撰成图籍付剞劂,以永古器之寿年,使薄海异域之士亦得手一编,而窥古器之图像,宜编名物图考一书,分别部居,以传世宝物为根据,合以先儒之经注,绘图勒成一书。”②对金石著录及刊刻的重要性,各家皆有共识。
潘祖荫入仕较早,一直官居高位,朝中政策的变化对潘祖荫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他的大量藏书毁于庚申之难,③但之后他继续大量收集古旧椠本,其中包含很多金石著述,对金石著述的刊刻尤其重视,光绪二年(1876)曾序赵绍祖《金石文钞》曰:“金石之坚,不如楮墨之久,金石有时而泐,而楮墨存焉。若洪文惠《隶释》中所录,今存者有几?反藉《隶释》以传,则金石之录可容已乎?”④可以说,潘氏于此用力与收藏彝器不相上下,其他金石同好对金石著述也颇为用心。
晚清以前的金石著述,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序讲述比较清楚,⑤此不赘述,这些著述当时盛行于世,对于晚清的金石学家来说非常熟悉,但当时金石学家的著述,则不一定能及时刊行,这些著述,按照著录体例分,大致分为存目、录文、考释、图象、尺牍等,内容十分丰富,今天我们得以获观,全得力于当时金石学家对著述的保护以及刊刻出版。
二、刊刻方法的探讨
一部好的金石著述,除了内容要精审之外,刊刻是最关键的,尤其是图像类的著述,刻图水平至关重要。一般来讲,刊刻的程序是先勾字写样,然后选版、磨版,无误后即行刊刻,刊刻完再校,最后刷印。这个过程中,刻工的刊刻水平至关重要。然而,时代条件的改变,往往直接影响到文化事业。咸同年间,各地学校、书院、藏书楼等文化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经过长时期积累起来的图书典籍包括四库全书在内,或散佚,或焚毁,许多典籍的刻版也被毁掉。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政府为重兴文化,相继在各省设立官书局,刊刻书籍,好多水平稍高的刻工,皆为官方罗致而去。实际上,即使是好的刻工,水平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吴云在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十六日致书陈介祺,就认为江浙一带自兵燹以后,刻工低劣,以及纸张刷印,无一可以入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过高,非精益求精不可,便会因噎废食,影响金石著述的刊刻出版。
与书法、绘画一样,刊刻同样有法。陈介祺与潘祖荫书札中认为:“第一必求其似,必讲求钩法刻法,与原拓既不爽毫发,又能得其古劲有力之神,而不流于俗软,乃可上传古而下垂久,方为不虚此刻,必须有学问、知篆法、肯耐心者相助,乃克有成。”⑥陈介祺强调刊刻要有“力”。这种力度感是通过线条的质感反映出来的,把握好线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当时潘祖荫、陈介祺的藏拓大多由吴大澂刊刻,吴氏曾并就钩摹之法、版式等问题函商陈介祺,陈氏告诉他:“若钩字则须用力,再责手民也。钩字易似己书,运腕难于指不动,指不动笔锋方能中正,中正而又能曲折分明,则虽古人之法万变,而能与之合,不似一手书,不弱不失矣。直落直下直行直往而曲折与力具在其中,所谓一线单微,所谓独来独往,皆在其中,如此则可以知古可以传古,而凡用笔用手莫不可通矣。”⑦陈氏以为,钩摹金文如同写字一样,尤在中锋用力,切不可如女红描样,形存而神失,他始终坚持考释可待而摹刻不可不精严。吴氏根据自身经验,认为陈介祺的观点过于严格了:“摹古文字求似易,求精亦易,求有力则甚难。手临不经意有神似处,影摹经意多形似处,而神采终逊,力亦逊。大澄自摹本较《积古》、《筠清》皆胜,恐刻工不良,则大失真。《积古》刻手佳,《筠清》稍次,失之肥重,然已不易得。”⑧真是言易行难,不亲身实践终不得要领。
双钩碑石文字同样面临很多问题,潘祖荫为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序中谈到古碑钩摹全文之难,他认为洪文惠作《隶韵》时还字字访求,而到了刘氏《隶韵》、娄氏《字源》以及顾氏《隶辨》都采取缩摹的办法,使字大小一律,结果形模尽失,再往后不管翟氏《隶篇》、牛运震《金石图》还是万廉山《百汉研》,只要是归于缩本,就失其真,不是此道中人是不会明白的。吴云以为这是钩刻问题,就拓本与陈介祺讨论过:“石刻住笔处似力稍弱,秀韵多而严正意略少,疑钩刻或未尽善,具见法眼。弟于初蒇工时亦曾与奏刀之钱君言之,渠云由于捶拓另易绵联纸精拓,一经装裱,顿觉笔力增劲,与原本竟无差异。”⑨可见,不仅仅是钩刻,还有装裱、刷印等问题,是各个环节的综合反映。
从钩摹、镌刻到刷印,刊刻工艺比较复杂,需要能工巧匠,陈氏所想最终没有完全实现。其卒后不久,照相石印、珂罗版印刷便风行于世。如今,现代印刷技术更是日新月异,陈氏之法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不过,他们对于文化遗迹的用心以及治学的严谨,都是需要今人好好思考的。
三、诸家对刊刻的不同要求
晚清同光时期金石诸家对著录的刊刻观念又各不相同,对刊刻要求最为精严的当属陈介祺。吴云较早和陈氏讨论刊刻出版事宜,二人自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恢复通函后,书札往来频频,陈介祺致吴云书中阐述了他对于金文刊刻的观点,前文已作引述,关键在要传真,丝毫不爽,且有力有神,不作玩物之好。对于古碑,陈氏以为以录文为要,不要像刘燕庭的《海东金石苑》一样,虽然内容多而精,但因为没有刊刻,已经不知所在,所以他极力劝告金石同好重视刊刻出版。
陈介祺认为,道咸以来只有阮元的著述刊刻最为精善,而之后的刻工水平在不断下降,如女工描样,虽不失形而神失,甚至说:“有图有拓无器何害,图拓之刻不似,何以流传嘉惠后之学者,是以考释可待而摹刻不可不精严也。”⑩对此,陈氏看得还是非常到位的。他还致书潘祖荫曰:“今人动讥阮书,蒙则谓虽未尽善,尚未有能及之者,非校审不知也,选工延友乃为先务之急,未可似如他书发刻即可无事。”(11)陈介祺意在刻工问题,然而时代纷乱,刻工之心或许亦不安于此,当不难理解。
凡事言易而行难,陈氏的要求也引起了金石同好的不同看法。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十四日,陈介祺致鲍康,提出:“好古家刻书,每患己见之陋且沮,愚谓刻摹精审,则天下后世,皆得借吾刻以考证,又何必因噎而使错过失时,惜乎,燕翁不明此理,而徒以玩物毕一生之精力而一无所传也。”(12)陈氏认为刊刻与传拓、藏器的地位是一样的,如果文字不精,即使考证再好也不足论。但友朋对陈介祺的做法大都不以为然,认为他太过讲究。
同治三年(1864)李佐贤刊成《古泉汇》一书,此书六十四卷,编撰始于咸丰九年,历时六载。陈介祺看到此书,认为“虽过前人,然体例尚未尽善,版本亦属简率,摹刻唐以上泉,甚为不精”。(13)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怂恿鲍康再著一古泉力作。其实,李氏作此书最为洒脱,没有拘束,曾致书鲍康曰:“笑骂由他笑骂,拙稿我自刻之。”(14)鲍康认为这个办法可以效法,对潘祖荫说:“青园、燕庭诸公皆过于慎重,转留余憾无穷。蕝斋集金文至九百种,康每促其早日刊定,但恐奢愿难偿。吾辈成一书,则是器即足以传,并聚散亦可听之。有动平泉一草一木之语,真千古痴人耳。”(15)
陈氏还同吴云讨论《古泉汇》一书,吴云认为此书“搜集之富,实古今所未有,自顾氏以来此书洵为大观”,并同意陈氏的观点,认为该书刊刻不佳,但转而劝曰:“剞劂一事,因不可草率,然必精益求精,转至因噎废食,前书劝兄降心相从,将应刻之书早早付梓,实有所为而言也。”(16)这件事情,吴云同样向潘祖荫表达了他的看法:“蕝斋为当代传人,惟其天性好胜,所作务要出人头地,刻意求工,转致因噎废食,即如汇刻先秦文字一端,若照薛、阮二书之例,选择器之字多而精确者,得好手影摹刻之,再得我二人相助为理,此书一出亦足继往开来,决为必传之作,乃必欲依许氏说文部目创例成书,条件既繁,诠证匪易,穷年累月,不知何日得成,来谕谓其刻古金文一事竟不能成,想亦指此也。”(17)吴云担心陈介祺刻意求工,反而因噎废食,不知何日成书。而陈氏认为石器出世,即有终毁之期,不可不早传其文字,反复以著述出版一事劝说吴云。
陈介祺还曾对李佐贤《续泉汇》表示出刻手不佳的评价,鲍氏大不以为然,致王懿荣函札中说其乃局外之言,因为懂篆隶者不去亲自钩摹,而厂肆中人工书通篆隶者少,如果屡易其人,费时费力费财,况且原拓有绿锈、有墨痕,笔画大率微茫,刻手不知书势,不能时时监刻,动辄舛误挖改,则版无完肤,只存形似。其实,功用不同,标准也要更易。
潘祖荫不同陈氏,他身居中枢,事务繁杂,作金石研究的精力有限,因此他善于发挥金石同好的作用。先后刊行的几部著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他先就自藏彝器五十件,请吴大澂绘图摹款,王懿荣写版,赵之谦篆名,集周悦让、张之洞、王懿荣、吴大澂、胡义赞和潘氏自己的考证分列器后,刊行专著《攀古楼彝器款识》,该书成为晚清金石学领域的重要著作。《双钩沙南侯获刻石》也是集体考释的成果,集中了张之洞、吴大澂、王懿荣和潘祖荫考证,还有赵之谦等人的考证没有列入。而《古埙考释》,更是集中十五人的考证与跋语,潘氏甚至未具一笔,却集中展示了这个金石研究群体的智慧。
潘祖荫还多为金石同好刊刻著述,以广其传。而同治十三年(1874)潘祖荫准备刊刻陈介祺论金石书札,订为《蕝斋丈笔记附手札》,由王懿荣汇集陈氏与潘、王手札中的精华部分,陈介祺得悉,分别致书潘祖荫、王懿荣,嘱咐前后所寄书札当令人写出,将来修饰删节,尚可付刊,以存二人往来之雅,王懿荣还专门为刻版设计了蕝斋小印,最终在当年刻入潘祖荫的《滂喜斋丛书》,该丛书中还刻入了鲍康的《鲍臆园手札》。潘祖荫甚至想把陈介祺和吴云的手札合刻成《陈吴尺牍》,王懿荣和吴大澂的手札合刻成《王吴尺牍》,专刻论古内容。后来,先成《蕝斋尺牍》寄与陈介祺。潘氏又改变计划,酝酿把陈、鲍、吴、王等人的手札集中编刻,拟成《秦前文字之语》。陈介祺因此数次友朋,认为务必“以识古字论古文为语,不涉入赏玩色泽语也”。(18)可见陈氏的不安。潘祖荫先刻成一册寄与陈介祺校删,此时王懿荣忙于科场,很多事情滞后,陈氏致王懿荣书曰:“伯寅欲不改恶札即刻,悚愧之甚,是令不敢作札矣。”(19)陈介祺一直非常谨慎,担心缺少斟酌,留下笑柄。光绪元年(1875)三月三日,陈介祺又致潘祖荫:“吾人之忧戚唯自有得者能解之,否则求养而更有以求自扰者矣。”(20)后陈氏一直恳乞《秦前文字之语》录存勿刊,结果可能正应了吴云的话:因噎废食。光绪二年(1876)后,潘、陈书札渐稀,刊刻《秦前文字之语》一事再未提及。
光绪三年(1877)潘祖荫要刻《捃古录》,致吴重憙书云:“金文与同志名流再酌,若廉生之类是也。寿卿讲究太精,不可商也。”(21)陈介祺乃吴重憙岳父,潘氏仍直言不讳,两位同光时期最重要的金石同好最后因为各自的坚守而分道扬镳。罗振玉说过:“潍县陈寿卿先生收藏吉金石刻为海内之冠,顾平生撰述矜慎,至老无成书,惟歙鲍氏、吴潘氏刻其手札数十通而已。”(22)罗氏所言极是。
四、基于传古的刊刻态度
金石著述刊刻依托的是彝器碑石拓片,拓片意趣在古,这也是金石的重要审美趣味之一,表现为坚实厚重,古拙苍浑,一旦拓制下来,那种自然风化的斑驳,使得文字线条变得粗拙古朴,形成了独特的美学特征,有很强的表现力。梁启超以为“好古”为中国人特性之一,什么事都觉得今人不及古人,因此出口动笔,都喜欢借古人以自重。(23)他提出这个观点原本是针对伪书而言的,却也恰恰可以说明陈介祺等一类文人对于“古”情有独钟的原因。
陈介祺的谨慎矜严,诸家多有所言,陈氏所为基于传古的思想。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陈介祺收到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一书,该书由吴大澂绘图、刻版,王懿荣写样。陈介祺复函,认为潘祖荫的序清真雅正,是心知其意者,该函并未评价刊刻如何,但云:“拓与刻之功与藏器并大。刻精则至极,惟工匠得古意不易耳。过精则刷印易损,先干后湿,均易损板。”(24)在陈介祺看来,刻版要求极高,要精而有古意,但过精,容易丧失所谓“古意”,在刷印的过程中又会变形,很不易把握。在陈氏看来,吴大澂的刻版存在过精的问题,在十月十一日又致潘氏曰:“清卿至精,只欠一古,图成,再拓原象形文,求神似则备矣。”(25)他以为,可以先刻图,至于文字可以拓成,这样才能神似。
陈介祺对古人作字之法作过深入思考,认为楷书取法于隶书,隶书取法于篆书,大篆胜于小篆,越古越好。他还从辨伪的角度说:“汉刻能如汉碑,而篆则不如秦,秦不如周末,周末不如周初,再古即商即夏。真者今人必不能伪,伪者必有不如古处。”(26)陈氏根据自己丰富的收藏鉴定经验,认为“古人之法,真是力大于身而不丝毫乱用,眼高于顶明于日而不丝毫乱下,乃作得此等字,所以遒敛之至而出精神,疏散之极而更浑沦”。(27)反映在对于彝器真伪的判定上,认为笔力遒劲者多非伪刻,字体圆熟而少力者,极可能即伪。所以,他对王懿荣说:“古文字义理第一,文法第二,书法第三。书能毫发不失而有力即是佳刻,方足传古,非易易也。”(28)
吴云《两袦轩彝器图释》刻成寄与陈介祺,陈氏认为超过前人,为必传之作,同时也提出:“我辈所述,乃为传古人非为传一己,古人传则己亦必传,是不可不公其心求古人之是者,而我先为传之,正不必器之在我,惟专以拓为贵,以图为备,只标我所及见者,其文与制,可传则传之。”(29)陈氏是以传古的标准提出要求的,所以就谨慎了许多,他的著述也迟迟不能开刻。当然,不仅陈氏,在晚清从事金石研究的群体中,崇古成为一种共识,只是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以古为尚的观念也促进了晚清金石文化的发展。
总体上看,同光时期金石研究群体中,陈介祺谨慎,王懿荣粗略,潘祖荫广博,吴云、吴大澂细致,李竹朋洒脱,但他们就出版刊刻问题积极发表意见、大胆实践、不断总结经验,虽然时代条件在变化,个人观念不同,刊刻要求也有高低之别,但每一次实践都是对金石文化的丰富与发展。
[本文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2014年院级科研项目“书画艺术在当代职工文化建设中发挥高效作用的探索性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4YY013]
①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国家图书馆藏同治三年刻本。
②罗振玉《云窗漫稿》,民国间贻安堂刊本。
③潘祖荫《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跋》,见《郑盦诗文存》,吴县潘承弼陟冈楼丛刊甲集之九,1944年。
④潘祖荫《金石文钞·序》,见《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版,第279页。
⑤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序》,见《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版,第263页。
⑥(11)陈介祺《致潘祖荫手札》,国家图书馆藏稿本,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函。
⑦(26)陈介祺《秦前文字之语(致吴大澂)》,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300页,第286页。
⑧吴大澂《吴愙斋尺牍》,国立北平图书馆金石丛编,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⑨(16)(17)吴云《两袦轩尺牍(致陈介祺)》,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七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687页,第645页,第561页。
⑩(29)陈介祺《秦前文字之语(致吴云)》,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217页,第236页。
(12)(13)陈介祺《秦前文字之语(致鲍康)》,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45页,第146页。
(14)鲍康《续泉汇·序》,见《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版,第909页。
(15)鲍康《鲍臆园丈手札(致潘祖荫)》,潘氏滂喜斋同治光绪间刻本。
(18)(19)(28)陈介祺《秦前文字之语(致王懿荣)》,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88-89页,第93页,第106页。
(20)陈介祺《致潘祖荫手札》,国家图书馆藏稿本,光绪元年三月三日函。
(21)潘祖荫《潘文勤公书札(致吴重憙)》,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第22通。
(22)罗振玉《蕝斋金石文考释跋》,见陆明君《蕝斋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2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版,第299页。
(24)陈介祺《致潘祖荫手札》,国家图书馆藏稿本,同治十二年七月十日函。
(25)陈介祺《致潘祖荫手札》,国家图书馆藏稿本,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函。
(27)陈介祺《致潘祖荫手札》,国家图书馆藏稿本,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