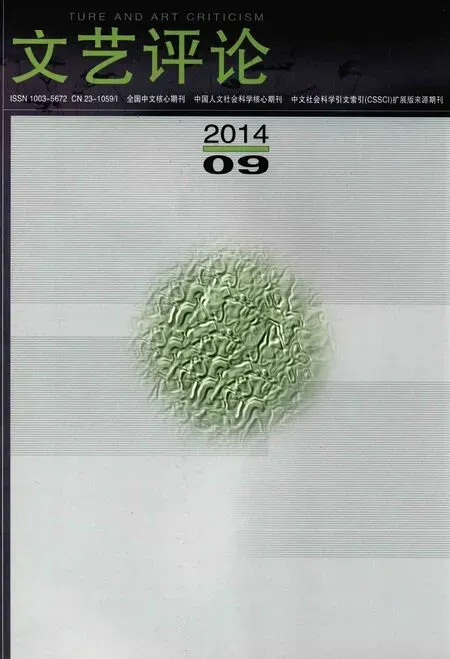舒斯特曼的反本质主义哲学实在论
2014-09-29周丽明
○周丽明
实用主义美学的复兴是20世纪末美学的热点问题,美国当代哲学家、美学家舒斯特曼是实用主义美学复兴的焦点人物之一。在号称哲学与艺术已经终结、美已经被废黜的今天,舒斯特曼直面哲学、美学、艺术的生存困境,企图以恢复哲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实践论立场,复兴以杜威为代表的正统实用主义以力挽狂澜。但是,舒斯特曼的实践论并非是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完全照搬、彻底复制,恰好相反,舒斯特曼的实践论是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美学的改造和发展,这首先体现在舒斯特曼反哲学实在论本质主义立场上。
一、“反本质主义”哲学实在论的思想渊源
“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是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提出的重要范畴,它主要针对分析哲学的本质主义,是对分析哲学所推崇的本质主义的反动;同时它攻击的范围又远远超出了分析哲学,它“作为一种从现代贯穿到后现代的思潮,不仅指对分析哲学的本质主义的颠覆,还泛指上承尼采的对亚里士多德、培根到笛卡尔以理性为中心的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①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始于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他否定了“认为事物均有其本质,可以通过现象的认识加以揭示的理论。……本质是完全的理想形式,是不容怀疑的,真实的,确切的;事物是理想形式的不完全摹本,是可争议的,不真实的,不确切的”本质主义。②这种本质主义以片面的、静止的、决定论的观点来认识世界,认为事物有唯一的、固有的、确定的本质,而且这个本质是永恒不变、不容置疑的。从本体论上说,本质主义“主张每一类事物都有惟一不变的普遍本质”,③这个绝对的本质构成世界的本源;从认识论上看,这个绝对的本质构成知识和真理;从方法论上看,本质主义认为“只有一类方法具有揭示事物普遍本质的奇效”。④毫无疑问,这种本质主义是在西方近代经典科学的机械决定论影响下产生的,它们都造成了理论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立和疏离。
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西方经典科学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基本信念,“即相信在某个层次上世界是简单的,且为一些时间可逆的基本定律所支配”。⑤这种自然观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古希腊原子论者的时代起,在西方思想中便出现了一种冲动,想把自然界的多样性归结为由一个幻象结成的蛛网”,⑥这种冲动在牛顿那里达到了顶峰,这个幻象在牛顿力学体系中幻化为永恒静止的自然图景,其特点是时间可逆,被约化为一个参数,过去与未来等价,确定而永恒。这是一个与随机性、偶然性和历史无关的“神明空间”,一个与人类的经验相背离的世界:在人类的经验中,世界是混乱复杂的,时间一去不复返(不可逆),世事无常,千变万化,充满了随机、偶然与不确定。科学的进步成功地“开创了与自然的对话”,但是其“首要成果就是发现了一个沉默的世界”,于是形成“经典科学的佯谬”,即牛顿力学理论所描绘的自然图景与人类经验世界的悖谬。⑦
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戈金分析了经典科学佯谬产生的原因,认为其根源在于,牛顿试图从机械的运动理论出发沟通人与自然,将亚里士多德的恒星世界与人类的月下世界统一起来,认为恒星世界与月下世界都遵循引力定律与运动定律,于是造成了科学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离。在经典科学佯谬的影响下,形成了对自然发展的三个核心问题的争论,即是否存在时间之矢,时间是否可逆问题;假如存在时间之矢,自然界的演化是否有序问题;自然界的发展是否具确定性,是否服从决定论问题。⑧牛顿力学体系坚称时间可逆,否认时间之矢的存在,认为自然界的演化服从决定论,从而彻底否认了任何经验性、直觉性、偶然性和随机性的作用。从科学史上看,经典科学为科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它确实表明“科学开创了与自然的一次成功的对话”,但另一方面,它的弊端也非常明显,“这次对话的首要成果就是发现了一个沉默的世界”,这个沉默的世界是“一个僵死的、被动的自然,其行为就像是一台自动机,一旦给它编好程序,它就按照程序中描述的规则不停地运行下去。在这种意义上,与自然的对话把人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而不是使人和自然更加密切”。⑨这是一个失去了人性的世界,一个拒绝想象力和诗意的世界,一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完全崩裂的世界。这个世界中孤立的不仅是人自身,自然也被孤立并被祛魅了。自然的祛魅“意味着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亦即“否认自然具有任何特质”。⑩而没有了经验的自然,是不会产生任何内在价值的。自然的祛魅最终使“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规范”,⑪由此人类的生命自主了,但同时也异化了。人与自然分别被孤立,自然被祛魅、人被异化,导致知识、理论的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互为参商,不相一致,知识、理论世界成为一个自律的系统,但无法回应、解答现实生活世界中产生的问题。
后现代科学的发展则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本质”,它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随机性和偶然性的世界中,“不确定性总是伴随我们,它绝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无论是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整体)中完全消除。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测总是模模糊糊”。⑫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我们生活的世界,“小变化能够产生大影响”,⑬“偶然性和随机性不仅大量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中,而且其作用在系统的进化中越来越大,有时甚至起支配作用”。⑭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随机性和偶然性的世界中,如果还要盲目地追求“现象间的单纯性、一样性和统一性”,⑮去发掘那个支配一切的永恒不变的本质,必然会越发远离现实生活。实用主义的哲学改造,就是要剔除墨守成规、无视生活现状的旧哲学,重建能够面对当下生活实践、解决当下生活实践所遇到的问题的新哲学。
二、杜威的反本质主义哲学实在论
舒斯特曼反本质主义的哲学立场,与“反本质主义”概念的提出者与罗蒂并不相同,是对杜威的哲学实在论继承并发展的结果。罗蒂是一位彻底的反本质主义者,他的反本质主义是对哲学本质的彻底否定,他说:“对我们实用主义者来说,不存在任何像X的非关系特征这样的东西,就好像不存在像X的内在本性、本质这样的东西一样。”⑯罗蒂不仅用“反本质主义”来称呼“我们实用主义者”,而且还总结说,杜威是一位“反本质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⑰他认为“这个当代哲学的舞台就是以反本质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多元主义的汇合”。⑱但事实上,杜威与罗蒂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并不一致,“杜威不像罗蒂那样反对关于本质的理论,更不像他那样反对事物的本质存在”。⑲杜威仍旧信仰普遍本质的存在,“科学地探索事物的本质是他哲学的基本出发点”,⑳对实在本性的合理改造是杜威哲学改造的重要内涵;而舒斯特曼则继承了杜威改造哲学实在的建构立场,并进一步将实在转化、发展为关系实在,关注哲学实在的生发性、变化性和偶然性。
在探讨哲学改造的合理性时,杜威分析了科学因素对哲学的影响,他认为近代科学革命同经济、政治和宗教的变革并起,使自然世界、物理世界和人的信仰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带来了“一个开放的世界,它的内部构成变化无定,不容加以限制,它的外部伸展超出任何假设的境界,没有涯际”。㉑开放、变化、没有边际、无法限定是这个新世界的特质,面对这样的新世界,传统宇宙观和实在论无法发挥效用。杜威认为,传统的宇宙观和实在论是固定不变、静止长存、整齐划一的,同时也是封闭、僵化的,它们认为,“如同我们品第动植物一样,宇宙间一切物亦各有等级。一切物各因其性质而所属部类不同,这些部类便形成一个品级的系统。自然界亦各有等级存在。宇宙按贵族制构成,认真地讲,是按封建制构成。种族和部类是不会混淆或重复的,只有偶然陷于混沌而已。此外一切都已预定属于一定的部类。各部类均在‘实在’的品级中各有一定的位置。宇宙确是一个整洁的处所”。㉒很明显,这是一个理想世界,它整洁有序,除了“偶然陷于混沌”,几乎完美无瑕。而后现代科学却证实,这个完美有序的世界与人类的现实生活世界完全相悖,人类真实的生活世界既有有序、确定、简单、整洁的一面,又有混沌、不确定、复杂、混乱的一面,自然世界、物理世界和人的信仰世界,都是混沌和有序、不确定与确定、复杂和简单、混乱和整洁的统一。正如杜威所说:“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中,它既有充沛、完整、条理、使得预见和控制成为可能的反复规律性,又有独特、模糊、不确定以及后果尚未决定的种种进程,而这两个方面(在这个世界中)乃是深刻地和不可抗拒地掺杂在一起。它们并不是机械地,而是有机地混合在一起,好像比喻中的小麦和稗子一样。我们可以区别它们,但我们不能把它们分开来。”㉓传统的理想的世界观和实在论的宏大叙事却只青睐于这个世界的确定性与规律性的一面,“盼望这个真实存在的世界具有完全的、已完成了的和确切的特性”,㉔因此不能够真正地观照真实的生活世界。它得意于有序、确定、简单和整洁,但同时也带来了静止、僵化和死寂,造成了灵动、生机、美和诗意的魅力的丧失:“当自然被看作一套机械的交互作用时,它的意义和目的就完全丧失了。它的荣光也被剥夺了。性质的差别既已泯灭,它的美跟着消逝。对于自然否定了向往理想的一切内心的憧憬和愿望,就是隔离了自然和自然科学与诗、与宗教和神圣事物的接触。所剩下的只有严厉的、残忍的、无生气的、机械力的展览。”㉕杜威认为,哲学家的任务,绝对不是“展览”这个毫无生气、失去了人生的诗意性的冷冰冰的世界。他指出,古代人是因为没有正确认识自然的能力,才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贵族制、封建制运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支配和命令的作用,命令就等于法则,普遍支配万物万象;近代科学不缺乏正确认识自然的能力,却偏执于用同一法则一统自然世界与人的生活世界,它废弃了“天上高贵的理想的势力与地下的卑贱的物质的势力的区别……天上地下的物质和势力的差异性被否定了,所肯定了的却是处处运行着的同一法则,自然界处处的物质和变化过程都有同质性”。㉖此时,杜威忽视了近代科学,尤其是牛顿力学同样对同一性的追求、对差异性、多元性的摒弃,只是赞美近代科学废除自然界与实在的封建等级制度的进步性。杜威关注的是“变化”。
杜威批判了旧宇宙观和实在论,强调随着近代科学对于自然界认识能力的提高,旧实在论失去了效应,应该用新的实在论加以取代,这个新实在论的本质就是“变化”。杜威指出,“现在科学已代这个密闭的宇宙而付与我们一个于时间和空间均无定限,既无边际也无终竟,而于内部构造则无限复杂的宇宙了。从此它也就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在古代的意义就不能叫做宇宙的世界。这样的复杂,这样的广阔,既不能撮其大要,也就不能括入一个公式里面。现在成为‘实在性’或存在的功能(energy of being)的标准的已不是‘固定’,而是‘变化’了。变化无处不在”。㉗“变化已不会被人家看作美德的衰落,实在的缺损,或‘实有’的不完的表征”,㉘“变化”代替“固定”成为实在的新的性质,成为新的秩序观念的标准。
为何传统的宇宙观和实在论如此推崇“固定”而贬抑“变化”?杜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通过阐释人与环境的间性关系,对此问题进行了解答。杜威认为,对“固定”,即对确定性的追求源于人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现实经验。人生存的世界是“动荡的和不安宁的”,㉙环境的动荡和不稳定使人的存在也是动荡的、不稳定的,由此人产生了威胁感、恐惧感。“逃避危险”的本能迫使人寻求安全感,人们在“确定性”与“安全性”、“不确定性”与“危险性”之间划上了等号。人们发现,人的实践活动是不确定的,而思维似乎与之相反:“实践活动有一个内在而不能排除的显著特征,那就是与它俱在的不确定性……关于所作行动的判断和信仰都不能超过不确定的概率,然而,通过思维人们却似乎可以逃避不确定性的危险。”㉚凡是变化的、不稳定的、“化成”、“生灭”、“有限”、不完整的东西,包括人的行动,都被认为不具有理性的安全的保证,是危险的、不能信任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具有安定性的东西就被假定构成最后的存在”。㉛既然只有固定、永恒不变的精神世界才能够给人以安全感,人们于是认为,常住性的精神世界才是真正的、最后的实在。推崇“固定”而贬抑“变化”,乃是由人的现实需求决定的;传统哲学的实在观,便从人类对安全性、确定性的本能需求中衍生而出。
不过,杜威自己也感觉到用“变化”代替“秩序”,似乎也只是一种“代替”,“变化”作为最后的秩序标准,本质上还是有形而上学的嫌疑,于是他为这种观点辩护,强调新的秩序标准与传统的秩序标准之间的差异。他认为,与传统实在论相比,这种新的秩序观念不是追求“物理的”、“形相的”、“形而上的”东西的永远存在,而是强调“事物的作用和机能的永久不变”、“互相联系的变化的叙述或推算的一个公式”。㉜也就是说,杜威对实在论的哲学改造是从“物质实体实在论”,转变为一种“关系实在论”。
“关系实在论”是学者罗嘉昌提出的命题,这种实在论不再将事物的基础、本质、原因看作是某种先于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用关系来代替。“关系实在论”强调,“关系即实在,关系先于关系者,关系者和关系可随透视方式而转化”。㉝具体地说,关系实在论包含五个方面的论题:“1.关系是实在的;2.实在是关系的;3.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先于关系者;4.关系者是关系谓词的名词化;5.关系者和关系可随关系算子的限定而相互转换。”㉞关系实在论认为,事物的本质不是由绝对的、独立不变的、不证自明的实体所规定,而是存在于相对的、变化的、内在的、不可还原的、先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生成性的性质与关系相互转化的关系网络之中,或者说存在于“多种间性之中,并且是在间性中相互规定、影响、甚至造就他者的”。㊱杜威对何谓关系也提出过解释,他说,无论是在自然、生活还是艺术中,“关系是相互作用的方式”,关系“将注意力固定在事物的相互影响,它们的冲突与联合、实现与挫折、推动与被阻碍、相互刺激与抑制的方式之上”。在此基础上,杜威进一步强调实在也存在于“事物的作用和机能”之中,即存在于事物与事物、事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之中。实在是事物与事物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时产生的变化性质,这种“属性与关系相互转化的过程”,是变化性质的“生成和退化过程,也是现象如何成为实在,实在又如何在一定条件下消解的过程”。㊲总之,杜威用关系来解释实在的理论,就是一种“关系实在论”。对实在的生成性与变化性的强调,表现出杜威的建构立场。
三、舒斯特曼的反本质主义哲学实在论
舒斯特曼继承了杜威对实在变化性本质的认识,并将杜威的实在“变化”性质进一步地界定为实在的本性,他认为,“实在的本性是变动的、开放的和偶然的”。㊳
舒斯特曼首先限定了实在所在的范畴,指出它指的是经验的生活世界的实在,而非先验的生活世界的实在。舒斯特曼说,“我们通过人的经验所了解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绝对固定或永久不变的世界。不仅我们的个人经验,而且外在的世界都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其规律性和稳定性都存在于一种变动的框架之中,且其大多数的变动并不为人注意。甚至我们所看到的永久形象,譬如山脉,都是变动的产物,并且还由于侵蚀或者其他自然和人力的作用而在持续地变动”。㊴在此,舒斯特曼强调,实在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实在,这个日常生活世界既包括人的经验世界的内在世界,又包括自然世界的外在世界。总之,是真实的现实世界,而不是先验的本真生活世界,前者关注活生生的、人类经验到的现实生活,而后者则继承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将世界看作是抽象的、经验所不能把握的世界。这个日常生活世界的实在的本性是变化性,所有的秩序、规律、稳定等性质都处于“变动的框架之中”。这可以说是对杜威的“事物的作用和机能的永久不变”、“互相联系的变化的叙述或推算的一个公式”的观点的准确解读。更重要的是,实在的变动不是外在地产生的,因为实在来自于事物与事物、事物与环境、人与事物乃至人与人、人与环境等等诸多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甚至相互转化,是生成性的,因此变动性是实在内在的、固有的、与生俱来的性质,它存在于多种间性之中。
舒斯特曼并没有停留在对实在的变化性的认知上,他进一步提出,实在是开放的。杜威虽然认识到近代科学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开放的世界,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地赋予实在以开放性质。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杜威对世界的开放性的认识,对摒弃旧的传统观念所推崇的秩序的热衷,就已经包含了对实在的开放性的肯定。杜威曾强调:“非至关于固定不变的类型和种,高低阶级的安排,暂时的个体对于普遍或种类的从属等信条,在人生科学上的权威受到摇撼,新观念和新方法应用在社会、道德生活里面是不可能的。”㊵只有封闭的、僵化的传统观念真正地被破除,以开放的、变化的立场和观点解决现实生活中不断产生的新问题,“科学的发达可以完成,哲学的改造可以实现”。㊶舒斯特曼将杜威的潜台词明确化,认为“实用主义者”,包括杜威,其宇宙观是“开放的、变动的”,这种宇宙观、实在论,为个人、世界和哲学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他指出,“世界开放的、易变的本性促进积极行动的自由理念,这一积极行动自由理念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实用主义宇宙观所带来的进一步结果是,就像介入这个变动世界的人的活动一样,哲学也可以有助于改变这个世界”。㊷舒斯特曼在此勾勒了一个运动的、进化的脉络,一条由人与世界、人的哲学与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运动、变化并进化的线索:世界、实在的开放性、变化性促使人产生积极活动的观念——人的积极活动的具体实施改变世界——世界发生变化——人的观念发生变化——哲学观念发生变化——哲学帮助世界进一步改变、开放……如此良性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是一幅美好乐观的个人观念、世界与哲学(知识)的积极进化图景。舒斯特曼始终坚信,通过个人的自我关怀和修养,不仅可以改造哲学,更可以“内圣开外王”,进一步改变世界,改善生活,改造社会。
实在还具有偶然性。舒斯特曼对实在的偶然性的认识仍旧承自于杜威。杜威发现,虽然表面上看哲学史中各种派别林立,甚至有的似乎“达到绝对对立的极端”,㊸但实际上,这些对立与分歧都被纳入了同一个思维框架之中,是同一目标之下的对立与分歧,那就是对确定性、普遍性的推崇,对变化性、偶然性的贬抑,否定偶然性是不同哲学流派的默契与合谋,只不过否定的手段各不相同:“一切不同的哲学派别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而它们之间的分歧是由于接受了这个共同的前提。不同的哲学派别可以被视为提供一些如何否认宇宙具有偶然性的秘诀的不同的方式,而宇宙是不可分离地具有这种偶然性的,于是对于偶然性的否认就使得从事于思维的心灵找不到一个线索,而使得后来的哲学思考惟有听命于个人的气质、兴趣和局部的环境条件了。”㊹杜威认为偶然性是自然、人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实在也具有偶然性。他辩证地分析了偶然与必然的关系,指出二者互益互补,相互对立而存在,他说,“必然性就意味着动荡和偶然性,一切都是具有必然性的世界就不会是一个必然世界,它就只会是存在而已”;㊺“必然并不是为了必然而必然,它是为某些别的东西所必需的,它是为偶然所制约的,虽然它本身是充分决定偶然的一个条件”。㊻也就是说,偶然性是必然性存在的前提。一个没有偶然性的世界是没有缺陷的、完善的世界,它本身就是极致的“存在”了,再没有任何需要、满足产生的可能,因此也再没有变化,因为已经得到了终极的满足和结果,于是一切活动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这个世界,既是一个圆满的世界,是“存在”,同时也是一个死寂的世界,“热寂”后的世界。舒斯特曼承继了杜威的这一观念,在此意义上他指出偶然性对于人的生活的重要性:“偶然性意味着机会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即人的行为过程和社会过程甚至自然法则都是偶然的事情,而不是绝对必然的事情,绝对必然是不容许有惊奇、例外或偏差的。”㊼舒斯特曼完全赞同杜威对实在的偶然性的认知,强调偶然性为生活提供了活动的需要,提供了活动的前提和机会。没有“惊奇、例外或偏差”的绝对必然的生活和世界,只有结果,没有过程,人的行为和社会便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同时舒斯特曼指出,对实在偶然性的肯定是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结果,它为实用主义的改良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即可谬论存在的合理性。实在的偶然性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存在的前提,正因为生活中存在缺陷,人才有欲望和需要、有了以行动改变生活的机会和动力;同样,正因为思维中存在缺陷,人类当前的知识和信念不完善,人才有了以行动去完善的机会和动力,这就是舒斯特曼所说的:“我们当前正当的信念或创立的知识总是有待于依据未来的经验来改善和修正。”㊽这是合理的可谬论,而不是怀疑主义。
舒斯特曼继承杜威的衣钵,以开放的、多元的间性建构立场确认实在的变化性、生成性、偶然性,反对静止、固定、一成不变的本质主义实在论,这是实用主义批判旧的传统实在论、建构新实在论的历史进步性的体现与证明,也是舒斯特曼实用主义复兴理论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