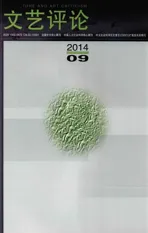时间观和叙事结构 ——以两部英国荒岛小说为例
2014-09-29杨建国
○杨建国
1.引言
法国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提出: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构的。(戈德曼1988:182)遵循戈德曼的指引,本文提出:叙事作品所体现出的时间观和叙事结构之间存在着呼应关系。①时间观是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叙事结构是叙事文本的组织方式,二者的呼应将叙事的虚构与社会的现实“缝合”起来,产生出浑然一体的“意蕴”,弥散于文学的想象空间和世界的现实空间。本文将首先从理论上探究时间观和叙事结构的呼应关系,继而借助于两部英国荒岛小说,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威廉·戈丁的《蝇王》,在文学实践中对这种呼应关系加以验证。
2.时间观和叙事结构的理论探究
2.1 两种时间观:循环往复和矢量直线
时间是生命的载体,无论是物质存在,还是精神意识,无不在时间中发育、成熟、衰老、更新。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人们对时间形成种种不同的观念,可划分为两大类:循环往复式时间观和矢量直线式时间观。
古代社会中,耕种和游牧的生产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逐水草而居,择四时以游的生存韵律,为山川、河流、深峡、牧场所割裂的生活空间,以及与日月星辰、河水涨落、草枯草荣等自然现象的亲密关系,令各民族不约而同形成循环往复式时间观。尤西林教授在他的文章《现代性与时间》中对古代时间观作如下总结:
(1)以占据生产——生活方式基础地位的自然变化为时间坐标系;
(2)时间过程非匀质性与参照系的具体性;
(3)时间度量非标准化;
(4)以天体旋转为中心的诸自然参照系提供自然节律时间,促成古代时间观最为重要的特征:永恒不变的循环重复。
(5)血亲关系和祖先崇拜令古代时间观中“过去”一维隆重。(尤西林 2003:21-22)
于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指出,由“启蒙”所标示出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同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出现于对时间的体验上,“现代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古代,一个重要事实就是,现代社会向未来开放,每一刻都产生出崭新的下一刻,时代由是不断更新,源源不绝”。(Habermas 1987:5)现代时间观以矢量直线为特征,时间的未来向度吞没了当下和过去,呈现为向着未来的矢量直线运动,生存成为向着未来单向展开的永恒将来时。英国学者罗纳德·施莱弗尔(Ronald Schleifer)在《现代主义和时间》(Modernism and Time)一书中对现代矢量直线时间观作了一番总结,它包含以下一系列假定:
(1)时间永恒不变,无地域之别,是没有内容的流动;
(2)时间对发生于时间“之内”的事件不施加影响;
(3)时间的永恒直线运动带来无限进步的观念,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就是其典型代表;
(4)知识、经验的主体性与事实、事件的客体性超出时间之外;
(5)主体与客体均超出时间之外,故而观察者亦可超出时间之外,对时间中发生的一切做出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观察。(Schleifer 2000:2-3)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文化矛盾的加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时间观经历了一次转向,至少在哲学、文学、艺术等表意话语领域,呈现出由矢量直线向循环往复回归的趋势。时间的周始循环抹去了过去、当下、未来之间的差异,无数时间之环相重叠,环上每一点均压缩着过去、当下、未来的体验,矢量直线模式下过去、当下、未来之间截然分明的区划在循环往复模式下“短路”。这正是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命名为“星从”(constellation)的时间/历史观。本雅明的星丛时间观视时间为无数当下的集合,是非连续的断点勾勒出的轨迹,每个断点都是一簇“星丛”,当下与过去在其中相遇、碰撞、聚合、变异。在《拱廊规划》中一段意味深长的注释中,本雅明写道:“当下的每个形象皆决定于与之同时存在的所有形象:每个当下都独一无二……并非过去把光辉投射于当下之上,亦非当下把光辉投射于过去之上。许多事物与当下同时涌现,如电光火石,所谓形象就是它们同当下形成的星丛。”(Benjamin 1999:1)
在星丛时间观的观照下,历史犹如一幅巨大的拼贴画,可辨识的图案之下是一个个非连续的断点和色块。越走近历史,看到越多的是一个个当下时间的坚硬外壳,而非抽象逻辑的流动。历史失去其单向度性,从一个当下时间走向另一个当下时间,从一簇“星丛”步入另一簇“星丛”,不仅在“前进”,同时也在“后退”。未来不仅是未知的疆域,也是曾经的回归。②
2.2 两种叙事结构:线性和非线性
叙事,视情节在逻辑关联上的不同类型,呈现出线性和非线性两种组织结构。一种叙事在情节的逻辑关联上呈现出线性特征,情节的各个部分矢量发展,步步推进,最后形成完整的故事;另一种叙事在情节的逻辑关联上呈现出非线性特征,情节的各个部分与主题直接相关,情节在时间上的递延令主题所包含的冲突不断复现和增强,并常常借助于某个具有强烈象征色彩的场景,将原本看似离散的各个部分整合入完整的情节图示中。③
较早提出叙事结构的线性与非线性之别的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在《现代文学的空间形式》(Spatial Form in Modern Literature)中,弗兰克指出:“所谓小说形式的空间化,就是至少在一个场景内,叙事的时间之流被打断,在这时钟停摆的空间内,焦点集中于各种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上。所有这些关系被并置到一起,不受叙事发展的控制,也通过反思各个意义单位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握场景的全部意义。”(Frank 1991:17)对于叙事情节逻辑关联的线性与非线性之别做出详备理论阐述的是伟大的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发表于1956年的论文《语言的两个方面和失语症的两种类型》中,雅各布森提出,语言包括两种基本行为:组合(combination)和选择(selection),二者构成两条轴线,“组合轴”(axis of combination)和“选择轴”(axis of selection)。组合轴上,各单元之间的关系体现出“邻接性”(contiguity);选择轴上,各单元之间的关系体现出“相似性”(similarity)。紧接着,雅各布森又指出,邻接性和相似性分别是两种传统修辞方式的组织原则,隐喻建立于相似性之上,而换喻则建立于邻接性之上。凭借其惯有的超广角视域和游走于不同系统之间的一贯作风,雅各布森敏锐地领会到,隐喻和换喻,或者说相似性和邻接性在言语行为中的表现并不平衡,“个人同时在两个方面(位置和语义)操纵这两种关联方式(相似性和邻接性),他既选择,又组合,并将二者排出孰先孰后,从而显现出个人的风格,自己在语言上的倾向和偏好”。(Jacobson 1971:255)这种不平衡性为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类型划分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文章结尾处两段极其精练、浓缩的文字中,雅各布森写道,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以隐喻为主要的话语组织方式,而现实主义则更偏重换喻。(Jacobson 1971:255)雅各布森的这篇文章看似同叙事结构关系不大,实则厘清了叙事结构分析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话语(包括叙事话语)在逻辑关联上既可以以邻接性为主导,呈现出线性特征,也可以以相似性为主导,呈现出非线性特征,这种线性——非线性之别可成为判断不同叙事结构,以至于不同文体和文化现象的重要依据。戴维·洛奇(David Lodge)正是由这一理论出发提出“钟摆论”,指出,英国20世纪的文学发展,尤其是小说发展,在隐喻和换喻的两极间摆动,或者说在线性和非线性叙事结构间摆动。(Lodge 1977:52)
2.3 时间观和叙事结构的呼应
法国著名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构的。时间观念属于超出文本之外的宏观文化结构,叙事结构则是体现于文本之中的微观结构,遵循戈德曼的指引,本文提出:叙事作品所体现出的时间观和叙事结构之间存在着呼应关系,作为意义生产的活动,叙事不仅在结果上反映现实,更在意义生产的具体过程中重复和强化现实的结构,产生出詹姆逊所说的“形式的意义”。叙事作品中,时间观和叙事结构的呼应关系在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得到体现。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两种时间观和两种叙事结构都是历史现象,分别对应着西方现代文明发展史上的不同阶段,二者在历史分期上存在着呼应。矢量直线式时间观兴起于文艺复兴,直到19世纪中叶都是西方世界的主导时间观,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线性叙事结构发生、发展,进而主导西方文学话语。19世纪中叶以后,循环往复式时间观开始对矢量直线式时间观发起冲击,在哲学、文学、艺术等表意话语领域尤为显著,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非线性叙事结构开始为文学所接纳,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话语组织方式。
更重要的是,从共时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本视为存在同一维度中的观察对象,可以发现,叙事作品所体现出的时间观和叙事结构在组织方式上存在着一系列呼应之处。时间观是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叙事结构是叙事文本的组织方式,二者的呼应将叙事的虚构与社会的现实“缝合”起来,产生出浑然一体的“意蕴”,弥散于文学的想象空间和世界的现实空间。可以从过程的透明与混浊、意义的外在与内在、主体的出场与缺席三个方面来讨论叙事作品中时间观与叙事结构的呼应。
(1)过程的透明与混浊。矢量直线式时间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过程对结果不施加影响,时间被视为空洞的形式,透明的容器;线性叙事结构中,语言被视为“中性”介质,透明的载体,由此产生出文学的“窗户”之喻。循环往复式时间观认为时间与具体生命历程密不可分,过程与结果密不可分,时间不是透明的容器,而是生命流动留下的印记;非线性叙事结构中,语言也不再被视为“中性”介质和“透明”载体,过程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结果,意义很大程度上保存于话语的组织形式之中。于是,文学不再是明净的“窗户”,而是离析出斑斓五彩,投射下离奇幻影的“透镜”。
(2)意义的外在与内在。对于矢量直线时间观来说,意义生产的过程在时间之内,而其结果(至少是理想中的结果)超出过程之外,或者说凌驾于过程之上,不受时间的限制。线性叙事结构中,相较于叙事之过程,其结果,即意义,处于高一级的层次上,拥有相对超然的地位。这意味着叙事的意义“先于”其表达过程而存在,构成叙事过程的“焦点”,从外部控制着叙事中单元的选择和各单元间的结合方式,确保由此而产生出的符号链的统一性和连贯性。循环往复式时间观形成一种周始历史观,历史被视为永恒的循环,意义内在于这一循环之中,保存于无数当下时间中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共存与对位之中,借用本雅明的话,保存于当下时间的“星丛”之中。非线性叙事结构中,相邻单元在逻辑关联上发生断裂,意义内在于叙事结构之中,保存于各叙事单元的共存和对位之中。
(3)主体的出场与缺席。矢量直线式时间观以及由其衍生出的进步历史观必须依赖于主体的出场,而主体本身又必须超然于时间和历史进程之外。无论是犹太—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还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惟有主体的出场才能确保观察的客观性、知识的有效性,也惟有在主体的引导之下,历史才能向着确定目标进发,最终终止于与主体的融合之中。线性叙事结构中,这种主体意识表现为超越于时间和语言之外,或者说悬浮于二者之上的叙事者。如迈克尔·莱文森(Michael Levenson)所描述,“叙事者不是故事中一个人物,而是非实体的存在,在一幕幕场景之上自由翱翔,其视野绝非肉眼凡胎所能比拟”。(Levenson 1984:8)犹如漂浮于叙事之上的一股意识,这位叙事者凝视情节的发展,洞悉人物最隐晦的想法和最细腻的情感,却绝不卷入到情节中去,维护着自己独立超然的地位,也惟因如此,确保着叙事的连贯与“透明”。叙事之外,主体意识体现为“通情达理”的公共读者,普通读者只有参与到这位公共读者之中,成为其一部分,才能体会到故事中的辛酸苦辣、喜怒哀乐,享受到恐惧和同情所带来的快感。线性叙事结构中,尤其在其开端部分,不乏诉诸于“人同此心、情同此理”的表达。无论是《理智和情感》中的“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还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都是对于这位公共读者的直接诉求。
循环往复式时间观以及由其衍生出的周始历史观即便没有取消历史的主体,至少也严重质疑其出场的能力。历史的循环本身构成了阐释的一切,没有什么能超出这一过程之外,凌驾于这一过程之上,历史主体或许存在,却决不能出场。④同样,在非线性叙事结构中,叙事的主体也悄然缺席,从超然独立的“天国”跌落三千红尘之中,堕入词语与词语之间、时点与时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在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阅读和交换之中被消耗、蚕食、分解、颠覆。
3.两部英国荒岛小说中的时间观和叙事结构
3.1 《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时间观和叙事结构
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叙述了一个由“蛮荒”走向“文明”的故事,故事主人公鲁滨逊以其近乎天真的乐观,孜孜不倦的实干精神,以及强烈的白人优越感引来无数评论,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细读小说,可以发现,鲁滨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对时间,更准确地说,是对矢量直线式时间观的极度坚持。
无论作为叙事之内的主人公,还是作为叙事之外的叙事者,鲁滨逊都竭力维护着矢量直线式时间观的完整,即便在身陷荒岛,远离西方文明的27个春秋之中,也不敢有丝毫松懈。一方面,鲁滨逊把自己在荒岛上的每一天小心翼翼地串接成时间链条,不留下丝毫的脱节和空白。翻看他在荒岛上写的日记,看到在如此蛮荒的自然环境中,主人公对矢量直线式时间观依旧如此执著,不禁令人惊叹。另一方面,鲁滨逊不断把自己生存中的小时间链嵌入到以纪元标识的大时间链中,其精确度可具体到天。依据推算,鲁滨逊确定,自己于1659年9月30日登岛,1686年12月19日离岛,在荒岛上共度过了27年零19天。
对矢量直线式时间观的执著不仅是鲁滨逊这个人物性格的突出特征,也渗透到小说的叙事结构之中,令其呈现出明显的线性特征。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冒险经历被绑定在一条紧密连贯,有着精确的内部度量和外部参照的时间链之上,原本松散的故事要素被穿缀成一个整体,呈现出由“蛮荒”向“文明”的直线运动。最后,荒岛被改造成殖民地,鲁滨逊自己也成为殖民地之“主”,一部“荒岛进化史”随着故事的结局也完成自身的终结。与线性叙事结构相对应的是一个有着强烈控制欲的叙事者,他监视故事中人物的行为,转述人物的话语,裁定人物的判断,甚至预言人物的遭遇。鲁滨逊不单是自己叙事中的主角,实际上也是惟一的角色。读者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出由这位叙事者一人包办的独角戏,所有角色由他一人出演,所有声音由他一人发出,所有行为由他一人代理,所有意义由他一人阐释,一切含混和空白、断裂和冲突在这出戏中没有容身之地,必须毫不留情地放逐到无名的荒野。我们看到,叙事中也只有叙事者拥有全名——鲁滨逊·克罗伊茨内,其余所有人物就只剩下代号——父亲、母亲、船长、莫尔人、星期五……叙事者抛弃了他们的姓名,也把一段段人生中不可溶解的“沉积物”抛落汪洋大海,只剩下可为他所用的部分,搭乘着他的叙事之舟,驶向文明神话的终点。
3.2 《蝇王》中的时间观与叙事结构
威廉·戈丁的《蝇王》中,矢量直线式时间观为循环往复式时间观所替代。王卫新在其文章《论〈蝇王〉的时间变奏》中指出,《蝇王》的时间变奏处在一种未来—原始—现代的模式之中,而从时长角度看,原始时间最长。(王卫新,2005:36)同《鲁滨逊漂流记》中丰富的时间参照不同,《蝇王》中叙事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时间参照的匮乏。一方面,叙事中各单元之间的时间关系松散脱落,读者只能从一些环境描写中推测出一些时点信息,却无法将这些离散的时间缀合起来,形成衔接紧密的时间链。另一方面,叙事之内所发生的一切也缺乏外部时间参照,读者只能从某些人物的只言片语中推测,发生了核战,孩子们本应乘飞机飞往疏散地。与时间参照的匮乏形成鲜明对比,《蝇王》中空间信息异常丰富,极度简略的时间参照和异常丰富的空间信息令《蝇王》获得一种游离于现代时间之外,重返原始混沌的氛围。
与循环往复式时间观相呼应的是《蝇王》的非线性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在小说的前八章体现得尤为明显。“海螺之声”为故事划定一个模糊的开端,由此经过“山上之火”、“海滩上的茅屋”、“花脸和长发”、“兽从水中来”、“兽从空中来”、“暮色和高树”各章,直到“献给黑暗的祭品”,各章节间维持着松散的逻辑联系,却又通过各种叙事要素的对位和对立,不断加强日神和酒神之争这一主题。《蝇王》中,各叙事要素的对位和对立首先体现在拉尔夫和杰克这两个人物上,围绕着拉尔夫和杰克这两个核心人物,《蝇王》中的其他叙事要素聚拢成团,逐一对位,形成两大“星丛”,日神和酒神的冲突就寓存于这两大星丛的对立与碰撞之中。
非线性结构令《蝇王》中的叙事获得“共时并存”的效果,而这种效果的产生往往需要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叙事要素的介入,这就是美国文学符号学家迈克尔·里法泰尔所说的“双重符号”。里法泰尔对双重符号的定义是:双重符号是一个语义含混的词语,处在两条语义序列链或形式联想链的交汇点上。(Rifaterre 1978:86-89)当然,双重符号不仅可以是一个词语,也可以是一个意象,一段话语,或一个场景。随着双重符号的介入,原本逻辑关联松散的叙事各单元在象征和想象中瞬间整合,呈现出紧密完整的情节图示。《蝇王》中的双重符号出现在“西蒙之死”这一场景中:
一条条木棒揍下去,重新围成一个圈子的孩子们发出嘎吱嘎吱咬嚼的声音和尖叫声……“野兽”挣扎着朝前,冲破了包围圈,从笔直的岩石边缘摔倒在下面靠近海水的沙滩上。人群立刻跟着它蜂拥而下,他们从岩石上涌下去,跳到野兽身上,叫着,打着,咬着,撕着。没有话语,也没有动作,只有牙齿和爪子在撕扯。(戈丁2006:177)
这血腥的一幕令读者联想起希腊远古神话中另一场血腥悲剧:俄狄浦斯被狂热的酒神信徒撕成碎片。一旦读者察觉到这段描写中强烈的酒神仪式色彩,日神和酒神之争这一主题就从叙事中凸显出来,在这一瞬间,之前松散的各叙事单元聚拢成形,形成日神和酒神两大“星丛”,叙事呈现为这两大星丛的对立和碰撞。
非线性叙事结构令《蝇王》这部小说获得了语义的多重性和阐释的多层次性。一方面,可将故事解读为揭示西方现代性内在张力和困境的寓言,如一位评论者所说:“《蝇王》所展示的就不仅仅是野蛮战胜了文明、非理性战胜理性所导致的社会的混乱和灾难,更揭示了文明的本质中即深藏着野蛮,理性的内核中深藏着非理性。”(何德红2013:55)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故事解读为对西方现代文学历程的反思。尼采笔下的日神和酒神始终是艺术之神,二者持续不断的争斗勾勒出艺术的发展轨迹。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文学艺术始终是日神的艺术,仅以英国为例,《暴风雨》中的异域怪物在肌肤胜雪的魔法公主膝下俯首帖耳;鲁滨逊凭一己之力,战胜险恶的“自然”,在海外荒岛上生存27年之久,降伏、归化了一个食人生番,最后把荒岛建设成一片繁荣的殖民地;《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托马斯爵士悄然去了安提瓜,留下一个用南美种植园提供的大笔财富建立起来的英国乡绅小社会,让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年轻人们在其中探究爱情和道德的真谛。壮阔瑰丽的日神之梦中,西方现代文明根底的野蛮和残暴被忘却,一个个笑中带泪,感人肺腑的故事悄然编织起文明、进步、财富的宏大叙事。然而,幻象终将破灭,美丽的梦境终将褪去,个人终将惊愕于现实的丑恶与怪诞之前。《蝇王》中,拉尔夫最终惨败于杰克手下,日神之梦被迷醉的酒神信徒戳得千疮百孔,这不也是在说,西方现代文明的大梦已醒,造梦的日神艺术已行将就木。从今往后,文明的蜃景让位于原始力量的迷醉与癫狂,朗朗乾坤下的公共理性让位于内心的黑暗与迷雾,和谐、温润、明快、内敛,以人的形象为焦点的美的艺术让位于非人化的艺术,让位于比例失调,形象怪诞,内容晦涩的丑的艺术,以及如惊涛拍岸,烈焰腾空,巨石压顶,怒海扁舟般的崇高艺术。这是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艺术的反思,也是对其未来道路的预示。
4.结语
叙事作品中,时间观和叙事结构的呼应将具体作品和特定的历史境遇“缝合”起来,由此可以看到某个特定时代或特定社会集团的整体思维和情感结构特征。这正是文学作品意蕴之所在,也是文学之真实的终极依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现代性视域中的艺术体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760126)和广东省江门市201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立项号:JM2013C40)阶段性成果]
①本文所说的“时间观”不同于“叙事时间”,前者属于超出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结构,后者则是文本的内在要素。
②爱尔兰诗人叶芝也提出过类似的想法,叶芝称之为“伟大回忆”(Great Memory)。所谓“伟大回忆”,是由远古流传下来的“集体回忆”,它独立于个人回忆之外,又时常以形象和思想丰富着个人回忆。在“伟大回忆”中,既没有时间的矢量直线运动,亦没有历史的进步,不同时代的思想和形象凝结为一体,无分彼此。除叶芝外,其他一些现代主义者,如修姆,劳伦斯都有过类似的表述。限于篇幅,此处无法一一列举,可参阅Louise Blakeney Williams的专著Modernism and the Ideology of History的第五章“A Particularly Lively Wheel:Cyclic Views Emer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③这里讨论的是情节在逻辑上的关联,而非在时间中的关联,二者并非一回事。有些叙事,尽管情节在叙事时间上(相对于故事时间)表现出非线性特征,但其逻辑关联依旧是线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侦探小说,尽管作者可以使用省略、闪回等手法打乱叙事时间的线性发展,但整个故事情节在逻辑关联上依旧是线性的,也惟因读者对情节的线性逻辑关联有着强烈的预期,某些部分的隐匿和错置才能产生出强烈的效果。另一些叙事,尽管在叙事时间上表现出强烈的线性特征,其情节关联却是非线性的,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④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杰姆逊,都坚持认为,历史主体真实存在,却无法直接出场。个人无法直接接触历史,所能接触的只能是经过意识形态中介的文本表征。可参阅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 2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