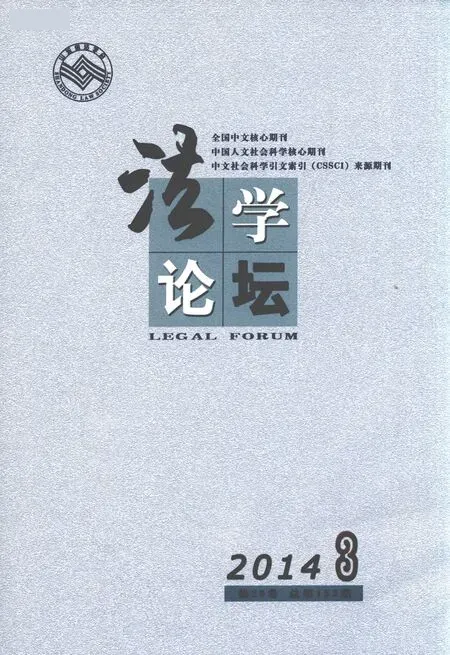政体选择与国情影响——基于中亚五国政体模式的分析
2014-09-20董和平
董和平
(青岛大学 法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
政体选择与国情影响——基于中亚五国政体模式的分析
董和平
(青岛大学 法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
中亚国家的宪法体制正处于一个持续转型时期,移植于西方国家的宪法制度呈现出强势总统、弱势议会、司法独立不足、选举与政党制度流于形式的特点。这既有历史遗存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政治需要。这些特点及其政治后果的存在说明,宪法制度的转型是一个复杂漫长的历史过程,制度借鉴与移植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宪法制度的建设要结合本国国情,创造特色设计,否则便难以产生民主实效。
政体;中亚五国;宪法特点、国情选择
政体是国家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政体模式的选择,既要考虑宪法民主要素,又需现实的政治考量;既要合理借鉴外来不同经验,也要顺应本国的历史和国情。这些要素充分结合,才能形成较为理想的政治体制“顶层设计”,才能取得国家稳定、民主进步的实际效果。而在这些诸多要素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国情因素是至为关键的。这一点在中亚国家宪法体制转型进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前苏联解体之前,中亚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政权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前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摒弃了前苏联时期的政体模式,颁布了新宪法,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起新型宪法体制。中亚国家的宪法体制整体上是以西方国家的宪法制度为模板而加以变通的产物,可以说是对西方宪法体制的移植;另一方面,由于前苏联集权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受国内外多种政治因素的制约,导致这种“移植”困难重重,充满变数。中亚国家的宪法体制正处在一个由旧到新的过渡阶段,从整体上看,中亚国家虽效仿西方国家政制建立起以分权制衡、议会制、多党制为基础的宪法体制,但在政权具体架构与实际运行中受国情影响体现出鲜明的自身特色,可以说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宪法模式。这种模式对本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以至于国际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值得关注和研究。分析中亚国家宪法体制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独特历程和现实政治后果,能够深化我们对政体选择之国情因素重要作用的认识,对我国的宪法制度建设也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强势总统与弱势议会
中亚五国独立后,需要应对国内外重重压力,诸如国内民族冲突不断,矛盾迭起;各种国外势力竞相影响其政治进程,从而造成中亚地区的动荡不安。五国针对这一现实,在政体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总统制,各国在宪法上也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在这种总统集权体制下,总统成为主导政治生活的核心角色。在20多年的转轨实践中,纳扎尔巴耶夫、尼亚佐夫、卡里莫夫等强势总统均以其个人色彩影响着各国宪法制度的变迁。美国作为典型的总统制国家,成为中亚五国效仿的对象。但是,中亚五国的总统制有别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出一种总统高度集权的趋势,总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都扮演着决定性角色,政府、议会则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美国政制中的总统可以说是世界各国权力非常大的总统,而中亚五国的总统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体现为:
第一,总统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不同。美国总统制充分体现了分权制衡原则,如总统在行使职权时受到国会的有力牵制。独立之初的中亚五国,虽然在政体上确立了总统制,但宪法也赋予议会、司法机关较大的权力,加之新宪法带有过渡性质,很多事项的权力归属和划分并不十分明确。这就使得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经常掣肘、争吵。各国的强势总统正是在这种权力斗争中,逐步通过修宪,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在哈萨克斯坦,总统利用宪法赋予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两次宣布议会自行解散,之后又通过修改宪法和几次议会改革,削弱议会权力,加强总统权力,基本上实现了西方式三权分立制向总统集权制的过渡。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利用自己领导的人民民主党和地方政权机关的党团代表控制了议会,并通过修改宪法,使得总统拥有了直接任命7名议员、委任宪法委员会主席和2名委员的权力,加强了总统对议会和司法机关的控制。2002年土库曼斯坦当局以总统车队遭反对派的攻击为由,对国内反动派进行了严厉打击,并于“2003年初更换了各强力部门的领导人”。*汪金国:《全球文化力量消长与中亚政局变化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通过修改宪法加强了对议会的控制,扩大了对政府组成和工作的决定权,扩大了对司法机关长官的任免权,从而使得总统处于国家权力的中心地位。”*杨丽、马彩英:《转型时期的中亚五国》,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通过议会选举、修改宪法和政府改组不断扩大自身权力。
第二,总统任期的随意性。实行总统制的西方国家一般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总统任期为四年或五年,且最多连任两届。而中亚五国经常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突破宪法的规定,以延长总统的任期,甚至设立终身总统。如1990年尼亚佐夫经全民选举当选土库曼斯坦总统,并于1992年6月21日再次当选总统,1994年1月15日该国举行全民公决,将其任期延长至2002年,1999年12月人民委员会又对宪法进行修改,规定尼亚佐夫作为首任总统,是无任期限制的总统。*参见吴宏伟:《中亚地区发展与国际合作机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乌兹别克斯坦也存在突破宪法规定,延长总统任期的做法。
第三,美国总统制下的总统可能在任职期间因叛国罪、贿赂或者其他重罪和轻罪而被弹劾,中亚五国议会居于弱势地位,根本无法做到对总统的监督与弹劾。如哈萨克斯坦在宪法中规定“议会因总统叛国罪,可罢免总统”,但又规定“在共和国总统审议关于提前终止共和国议会权限问题或者提前终止议会下院权限问题期间,不得提出关于弹劾共和国总统的问题”。依照此项规定,使得议会可以提出罢免总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苏东剧变后,一方面中亚各国试图通过借鉴西方的总统制和多党议会制,以稳定国家政局;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扩大总统权力,突破甚至无视宪法规定,从而降低了宪法和法律权威。虽然中亚五国在宪法中明确了总统、议会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为相互协作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在权力的实际操作与运行来看,总统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权力,甚至有的国家在独立初期的宪法中并未对总统列举较多权力,而是日后基于现实的需要和中亚其他国家的影响,利用全民公决或者修改宪法的方式赋予总统非常广泛的职权,并弱化议会权力,形成了民主框架下的总统集权。
在中亚五国作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时候,所奉行的亦是苏维埃代表制,以最高苏维埃为本国的立法机关,中亚五国独立后效仿西方国家建立了议会制。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议会为“一院制”,其余3个国家采用“两院制”。事实上,哈萨克斯坦议会制度变迁可谓是一波三折。哈萨克斯坦在1994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便选出176名议员代表。然而在1995年3月6日,哈萨克斯坦宪法法院裁定这次议会选举违宪,随后总统下令解散议会。*参见赵常庆:《列国志——哈萨克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因此,哈萨克斯坦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无议会时期。如今的哈萨克斯坦议会实行的是由参议院和下院(马日利斯)组成的两院制,两院皆为常设机构。

中亚五中议会构成变迁表*参考资料: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2007年版;杨雷:《中亚五国议会制度比较》,载《新疆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当今世界宪法的大趋势是由“议会主导”倾向至“行政主导”。在这个大背景下,中亚国家议会权力都出现了向行政机关转移的趋势。中亚国家的总统独揽行政大权,议员带有着浓厚的行政部门色彩,还得面对“解散议会”的压力,三权分立的原则未能落到实处。在西方议会制国家,议会对于政府不能信任时,得以投不信任票的方法促令去职。中亚五国的议会之不信任权的行使后果却大不相同。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总理并非议会权力所出,真正发号施令的总统躲在后面,不信任投票对总统无丝毫影响,总统不过换个总理,而议会又得面临重新选举。*参见齐光裕:《中亚五国政治发展》,台湾文笙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二、依附于总统的政府和渐趋独立的司法
中亚五国政府一般由总统组建,主要成员包括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国家委员会主席及其他国家机关领导人,政府总理、副总理及其内阁成员由总统提名经议会同意或批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设有总理这一职位,唯独土库曼斯坦不设总理职位,而是由总统兼任。*参见赵常庆:《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政府虽不设立总理职位,但仍保留着副总理的职位。副总理职位的数量曾达到13位之多,这在世界上极为罕见。
在前苏联的集权色彩的烙印下,政府需要定期向总统报告、提请总统批准国家的社会经济纲领和科技纲领、组织执行共和国总统的文件和实施对各部、国家委员会、其他中央机构以及地方执行机构执行总统文件情况的监督。在哈萨克斯坦,政府还须履行总统委托它向议会递交法律草案的事宜。政府还与共和国总统共同协商政府的法律工作计划,总统可以完全或者部分中止政府文件的效力。
中亚五国在独立之前,其国家机构的运行规则乃“议行合一”。独立后中亚各国普遍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确立了一系列司法原则。例如,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原则、保护被告权利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
在司法体系方面,中亚地区基本一致,分为共和国最高法院、地方各级法院、最高经济法院等,并禁止设立特别法院,这是中亚地区司法系统的显著特征。经过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主化”进程,独联体各国对苏联历史上曾经通过建立特别法庭秘密审判政治犯、大规模镇压持不同政者的做法持强烈批判态度。哈萨克斯坦宪法载明:“不得建立特别法院和非常法院”。土库曼斯坦亦不允许设立特别法庭以及其他同法院分庭抗礼的机构。另外,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都在宪法中明文禁止设立诸如特别法院的法院。
此外,中亚的有些国家还存在一类既不是审判机关,又不具有司法职能的机关——最高司法委员会和最高法官理事会。例如,哈萨克斯坦在独立后的首部宪法颁布不久,便成立了一个旨在强化总统职权的最高司法委员会,总统担任此委员会的主席。1997年2月,由总统主持召开的会议审议了最高法院一名法官辞职以及推荐其后备人选问题,同时还讨论了解除一批法官职务、任命一些新法官的问题。再如,有的总统利用过去自己领导的人民民主党和地方政权机关的党团代表控制议会大多数席位,掌握司法机关的任免权,以此操纵司法权。*参见赵常庆:《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篇》,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中亚五国普遍设立了宪法法院。宪法法院(土库曼斯坦称宪法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在总统和议员的选举、全民公决发生争议时,予以裁决;对议会通过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议;负责解释宪法;在总统因生病不能理事或因叛国被弹劾时,依法作出结论;对法院认定的违反宪法的法律和法令的结论是否正确予以审议。根据哈萨克斯坦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可以对宪法委员会决议的全文或部分内容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宪法委员会可以以其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推翻总统的反对意见,在未能获得上述法定票数的情况下,宪法委员会的决议被视为未通过。此外,宪法法院作为国家违宪审查机关可以就总统颁布的命令和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宣布其违宪,从而使其丧失自身的法律效力。
三、流于形式的多党制和问题重重的选举制度
中亚五国独立后,放弃了过去的一党执政体制,允许多个政党的存在,政党政治开始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各国政党法律对反对党苛刻的限制,加之总统享有绝对权威,致使反对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十分有限。乌兹别克斯坦1996年颁布的《政党法》规定,建立和登记政党须征集到8个州的5000名以上公民的签字支持。根据此项标准登记成立的公正社会民主党、民族复兴党和“自我牺牲者”民族民主党等5个政党都是属于拥护总统的政党。*参见吴宏伟:《中亚国家政党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4期。土库曼斯坦宪法虽然规定实行多党制, 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多党并存的格局,而一直由总统领导的民主党执政。哈萨克斯坦通过两次修改《政党法》,基本上形成了多党政治的格局。但在2007年修改宪法,废除了总统不得参与政党活动的限制,使得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得以出任在哈萨克斯坦拥有绝对优势的祖国党党主席。
由上述内容可知,虽然中亚的政党制度有宪法和法律的支持,但基于维护总统强权地位的需要,在现实中国家政权针对反对党的限制措施司空见惯。有的学者将中亚的多党制建设概括为“西方多党民主制的躯壳+本国的现实需要+前苏联一党集权制的特质”。*汪金国:《多种文化力量作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正是这样的政党结构决定了中亚各国“政党的作用,尤其是原共产党的作用和影响日益下降。各国总统均通过自己委派的行政长官来治理国家,政党作用十分有限”。*赵常庆:《中亚五国独立以来政治经济述评》,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第6期。
中亚五国独立后,逐步建立了各级选举制度。但在实践中,选举制度的实际运行与制度设计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
首先是差额选举流于形式。中亚地区有关总统、议员等国家高级公职人员选举虽采差额选举制,但在落实过程中却得不到充分实现,致使差额选举的结果与直接连任的结果并无较大差异。以哈萨克斯坦为例,现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自1991年起至2011年已经是第四次担任国家总统。1990年4月24日,哈萨克斯坦首次确立总统这一职务,纳扎尔巴耶夫当选国家独立后的首任总统;1991年12月1日,经全民公投,获得连任;1995年,经全民公决延长总统任职期限;1998年10月8日,议会决定于1999年1月10日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在本次选举中,纳扎尔巴耶夫再次连任;2011年1月14日,议会上下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会议,支持绝大多数选民动议,举行全民公决将纳扎尔巴耶夫的总统任期延长至2020年。*参见《哈萨克斯坦总统选举胜负无悬念》,http://www.people.com.cn,2011年4月3日。此后总统建议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最终在2011年2月4日决定于同年4月3日举行总统选举。毋庸置疑,总统凭借其在国内政治权威最终获得本次大选获得连任。中亚其他国家在选举工作中亦存在着这种形为差额选举,实为“等额选举”的现象,甚至有的国家还规定总统为不受任期限制的总统。例如,土库曼斯坦在2001年1月对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明确规定萨巴尔穆拉特·尼亚佐夫作为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其任职期限无时间限制。*参见施玉宇:《列国志——土库曼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直至2006年12月被誉为“土库曼之父”的尼亚佐夫逝世,才结束尼亚佐夫神话式的强权时代。
其次,全民公决成为强化总统职权的工具。全民公决起源于古希腊城邦雅典的公民大会,是一种直接民主形式。但是从中亚政治权力的实践效果来看,全民公决并非更为民主,而是加强集权的手段。中亚国家试图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延长总统任期,以达到强化总统职权的目的。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由于其最高会议任期到2000年,而总统任期却到1997年,为协调任期的不一致现象,乌兹别克斯坦于1995年2月经最高会议通过了关于就延长总统任期举行全民公决的决议,随后在3月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将总统任期从1997年延长至2000年,因而总统卡里莫夫的任职期间又延长至2000年。类似于这种总统集权的方式在中亚其他国家都普遍存在。
四、国情赋予了政体特色
上述关于中亚国家宪法体制特点的分析表明,中亚五国宪法虽然均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作了明确规定,但与实行三权分立原则最为典型的美国相比,其在国家权力的划分方面更突出总统的地位和作用。国家总统拥有相对于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更为广泛的权力,甚至有的国家总统还享有相当程度的立法权。这种以“总统权力的最大化,议会职权的最小弱化,司法权力的最小仲裁化”为特征的政权体制,是中亚地区三权分立宪法体制运行的新模式。
中亚五国独立后的首任总统都曾在前苏联时期担任国家要职,他们一方面深知前苏联时期高度集权政治模式的弊端,认为这种集权政治“忽视具体的历史、社会、经济、民族心理、人口、自然条件和地区差别,实行联盟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赵常庆:《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篇》,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希望在借鉴其他国家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综合本国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实际需要,选择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政治道路;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刻认识到国家独立后政权稳定和社会管理对权力集中的实际需要,建立带有集权色彩的总统制既体现了中亚各国历史、民族、文化特点,同时也反映出各国在社会变革时期需要国家权力强有力地推动社会发展的普遍愿望。*参见汪金国:《多种文化力量作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中亚宪法模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和现实政治根源,既是受前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历史影响,同时也是独立初期国家稳定的现实需要。可以这样说,中亚五国政体特色的形成是本国政治精英主观追求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说,五国政体选择受制于本国国情。前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尽管成为独立国家,但它们无法割断与前苏联历史遗产的联系,前苏联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或多或少地嵌入了这些国家新选择的政体制度。中亚五国独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经济独立和发展,在这些民生重于民主、优先于民主的国度里,民主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化”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超越了这些国家民主发展的历史阶段,“水土不服”造成了中亚五国在效仿西方制度的过程中“留其形、失其神”的政体局面。中亚五国这种带有集权色彩的总统制模式,在国家独立之初的优势是客观存在的。总统权力的相对集中,对于一个刚刚独立不久、内政外交尚不成熟、民众习惯集权体制且对民主存有渴望的国家来说,更有利于稳定政局以及对应急事件的有效控制。*参见汪金国:《多种文化力量作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但是随着国家政局的稳固和国家政治建设的持续发展,这种过于集权的总统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甚至成为对国家民主政治和人民民主权利的一种削弱和侵害。
这种宪法体制对于民主治理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腐败问题突出,集权制和裙带风、小集团利益横行不法。*参见高永久:《独立后的中亚五国政治体制》,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9期。有关统计表明,吉尔吉斯斯坦从农业部到司法部,从教育部到税收机关,腐败案子数量在几年里急剧增加,腐败程度进入世界前15位之列。*参见丁佩华:《西式民主成“鸡肋”——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更的警示》,载《决策信息》2010年第7期。政府腐败也是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颜色革命”的诱因之一。这样的现实激化了某些中亚国家的矛盾,导致不理性的战争的爆发。政府的权威遭遇到民众的质疑。二是,“司法独立”受到挑战。总统的集权式统治常常使得司法权受控于它,使得司法机关不能完整、有效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司法职能。因而,这不仅是对“司法的独立”公然挑战,更是对司法公正的亵渎。三是,政党实际作用有限。一些亲总统派政党的扩大与联合,为总统对政党间接地施加政策压力产生明显的效果。比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的女儿自己组建的阿萨尔党,它无疑是以拥护总统政策的一支新生力量,随之与祖国党的合并,不仅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更是为总统的变相干预提供了便利。四是,选举缺乏广泛性与民主性。中亚国家独立后选举制度最大的变化就是将有关国家的高级公职人员的间接选举方式转为直接选举,这种看似民主化的选举变革却又伴随着不民主的选举问题的产生,甚至全民公决也已经慢慢演变成为国家总统集权的有效途径。虽然当今中亚各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这种全民公决已成为了中亚选举制度的一大特色。
中亚宪法体制的特点及其运行实践,也为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宪法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就整体而言,中亚五国的宪法体制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旧传统的变革与新体制的确立都需要一个逐步磨合的过程。中亚国家的宪法体制虽已基本确立,但并不稳定。移植于西方国家的宪法制度还需要长时间的调适,国内外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会不断引发宪法体制的变化。从中亚五国宪法体制和政体模式的演变过程看:一方面,国情因素的作用是根深蒂固不能回避的,高度集权的历史遗存和现实政治需要引导着宪法政治发展的主流方向;另一方面,外来宪法因素在本国的认同过程也充满着本国国情的顽强抵抗和潜移默化地实际改造,其作用的范围和有效程度最终要受到本国国情的制约。
政体选择受国情影响,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规律。中亚五国的宪法实践表明,国家政体模式的选择和宪法制度的建设主要根植于本国政治发展的实际需要,简单的外来制度移植绝不可能解决本国的民主实践问题。外国先进的宪法制度和政治理念一定要经过科学的论证筛选才能确定其是否可以被纳入借鉴移植的范围。即使再优越的外国宪法机制,在进入本国宪法制度时都必须经由一个政治改造和文化改造的过程,否则便难以发挥预期的民主效果。简单片面的制度移植只能是流于形式,以民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甚至引发政治动荡。结合本国国情,走具有本国特色的制度建设之路,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也是中亚五国的政体制度变革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2014年4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强调:“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参见《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4/01/c-1110054309.htm毫无疑问,不脱离中国的历史,不脱离中国的文化,不脱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不脱离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不脱离现行宪法及其确立的国家制度,尤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脱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发展道路,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对国家政体制度的重大影响,这是完善国家政治制度的重大课题,也是推进中国宪法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吴岩]
Subject:On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Condition on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Selection——From the the Model of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uthor&unit:DONG Heping
(Law School of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071,China)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constitutional system is in a transition period, transplanted from western countries constitutional system,show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ing president, weaking parliament and judicial independence, unworkable elections and party system. They could be influed by the historical relics, to some extent, is the political reality.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mean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system is a complex and lengthy historical process, the system reference and transplantation is necessary, but more important is that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constitutional system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national conditions, to create the characteristic design, otherwise it is difficulty to produce the democratic effect.
political system;central asian countries; co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national conditions choice
2014-04-06
本文系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中亚地区宪法体制变迁研究》(11BFX093)的阶段性成果。
董和平(1963-),男,陕西大荔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在职法学博士生,青岛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
D911
:A
:1009-8003(2014)03-007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