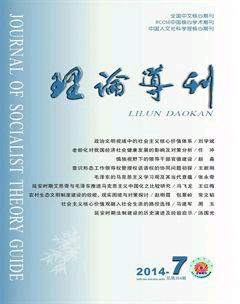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协同问题初探
2014-08-12王新刚
王新刚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河南 焦作 454000)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要求,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坚强保障。”[1]那么,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协调运行,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笔者认为,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具体工作,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了其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具有协同统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运行的过程中表现为“协同”关系。
一、协同的现实依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作为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间接性和能动性,但从根本上看,它大体上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能够协同一致,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尽管意识形态是伴随着阶级产生而产生的,但对其关注和研究却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特有的精神现象。1796年,德斯图·德·特拉西在法国国家研究院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意识形态”的概念来说明观念学说及人的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全部科学,并在《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中系统阐述了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依据人的理性原则建构起来的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形态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开启了西方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理性原则”的流派。与之相对的观点是“虚假建构”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不同阶级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虚构的虚假意识。比如拿破仑基于对19世纪法国意识形态理论家对宗教的批判和现实专制的否定,认为意识形态是荒谬的诡辩术,是人苦思冥想的理论形态,于是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全盘否定。
不管基于“理性原则”还是“虚假建构”,从根本上都没有找到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和依据,落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淖之中。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认为,任何意识形态都要依据并表现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存在,因为不仅人的理性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且阶级利益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意识是个人的精神存在方式,它必须依赖社会现实,“‘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533意识形态是“意识”在“共同体”层面的存在方式,是意识的特殊表现形式,它也不可能离开社会现实利益关系而单纯存在。马克思在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揭示出了意识形态自身的规律性,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2]550正是这种阶级关系的对立性制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基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获得其领导权和管理权,但从根本上看,却无法实现与话语权的统一。这个观点也被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所证明。
新时期我国的意识形态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而形成的现实社会关系,它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是基于中国道路而形成,同时又反作用于中国道路,具有协同一致的现实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先后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文化方面就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意识形态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表达了意识形态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彰显了意识形态在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协调统一关系。因此,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维度实现了完全统一。也正是这种从根本上的统一性,意识形态也反作用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旺盛的生命力,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
二、协同的理论特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利益表达的观念形式,它的主要功能是维护现存的阶级利益关系,具有把阶级利益说成全社会利益的“虚假性”,还具有掩饰现实利益关系矛盾的“遮蔽性”。只有真正地实现阶级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才能结束意识形态“三权”分裂和抵制状态,实现它们的协调统一。
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三权”处于分裂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分离,它的价值操纵性成为了被批判的根源。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第一部分的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经济学批判,就认识到了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性。政治经济学家发现了人的劳动是财富的来源,但基于私有制的理论前提,无法解决工人工资与劳动所得成反比的社会现象,于是,把他们的学说变成了维护资产阶级现实关系的理论,马克思认为这种与现实相悖的理论就是意识形态,并且体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身的虚假性。法兰克福学派多是基于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进行批判,认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是绝对对立的,它具有只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这种功能借助于大众文化和科学技术起到了很好的操纵作用,甚至把人都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以至于雷蒙·阿隆和丹尼尔·贝尔等都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等问题。卢卡奇和葛兰西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总体性的消解作用,而且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卢卡奇从“物化”范畴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物化的特征,而且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伦理、法律等社会意识也普遍性被物化,造就了物化意识,这种物化意识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直接导致人的总体性和批判能力的缺失。葛兰西则直接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要不断地提高人民中越来越广泛的阶层的智力水平,换言之,要赋予群众中无定向的分子以个性”,[3]22提升人民的启蒙意识和批判水平,其核心就是不仅要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还要获得管理权和话语权。可见,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身“价值性”和“真理性”的分离,“虚假”的意识形态必然终结,代之而起的则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利益的表达,它既具有解释世界的相对真理性,还具有维护统治的鲜明阶级性。一方面,任何真理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意识形态的真理性是在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存在的,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是相对的,即相对真理,它是通过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比而显示出先进意义。那种认为意识形态是依据于人的理性原则而存在的,是一门自然科学,具有“普遍适用”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另一方面,任何阶级社会的不同阶级都有自身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维护自身阶级关系进行辩护,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由此断定意识形态是虚构的虚假意识、不具备可证实的真理性,也是错误的。因为意识形态的价值性是建立在相对真理的基础之上的。只有体现社会多数人利益关系的意识形态,才能够实现真理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具有真理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为“三权”协同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从真理性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合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它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性质和方向,保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维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三者构成了社会客观精神中价值观念的完整系统、内在逻辑结构的完整性,也证明了其自身的科学性。从价值性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理想,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形成“利益认同共识、秩序认同共识、政治认同共识和共同理想目标认同共识”,[4]270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凝聚力量。因此,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的高度统一,才使得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三权”具有了协同的理论特质。
三、协同的实践条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协同一致,从实践条件上看,它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性。理性意识形态论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基于人的理性形成的“普世价值”,任何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工作,都要遵循或推广这种普世价值观念;虚假意识形态论者认为意识形态是虚构的理论,意识形态工作是“意识形态控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意识”和“人民利益”的分离。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因此,具有了“三权”协同的实践条件。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双重标准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在意识形态领域惊人地统一起来。一方面,吹嘘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意识形态控制的自由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一种“洗脑”活动。另一方面,却把西方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模式标榜为全体国民的意识形态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规范,向全世界推广。比如“美国制造”是国际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它通过制造教义、制造媒体、制造产业、制造敌人,实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系统性和结构化。这种制造已经被模式化,成为了美国开展文化帝国主义运动、谋求文化霸权的核心技术。[5]因此,西方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曼海姆所提出的超越阶级性和党派之争的“总体的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态的特殊观念”,即某一阶级或利益群体拥有了与自身利益相一致的某些价值观念,是真实的、具体的利益表达,它“是一个时代或者具有一个时代的历史——社会全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当我们涉及这个时代或者这个群体所具有的总体性精神结构的构成和各种特征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6]65不管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再隐藏,也总不可能具有超越具体利益的理论形态,利益仍然是决定意识形态的直接原因。西方社会已经改变了试图把意识形态变成充满激情的信念系统的策略,基于此才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指责。但它从未改变用潜在的隐形的意识形态对人民的控制,从未放弃过他们的文化帝国主义扩张活动。因此,西方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建立在自身双重标准和自相矛盾的基础上的,这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工作的强制性和虚假性。
事实上,国家和意识形态是任何阶级须臾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国家是政治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制度化的载体;意识形态是思想上层建筑,是国家统治思想化的表现。国家需要意识形态论证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意识形态需要国家强制才能保证实施。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不过是维护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全体国民的共同意志。只不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把意识形态隐藏于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工作之中。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意识形态是人民的意志表现,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都是人民利益的体现。因此,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是要在保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协同一致的基础上,探索积极有效的方式方法,促进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也正是基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性,才使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具有了协调统一工作的可能性。
四、协同的实现机制: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运行结构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协同过程就是要保证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积极有效的运行。只有探索三者在具体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才能避免相互抵制和消解的尴尬状况。各在其位,又各谋其事;权责明确,又相互关联,才能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确保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安全。
领导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协同运行的核心。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也称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是社会统治集团通过非暴力的形式,把统治集团的价值观变成被统治集团的价值观,使主导价值观转变为主流价值观,从而形成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领导权体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性和引领性,是意识形态工作具体实施的向导。一是社会思想领域,确保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围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核心问题,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纷纷踏上历史舞台,试图引导和影响我国改革的进程。保证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核心地位,就是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各种思潮的引领。二是中西方思想交锋中,保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我们要在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既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成果,又批判其糟粕。“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7]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保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三是社会生产领域,体现意识形态对中心工作的保证作用。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经济工作是我们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核心作用还体现在为经济工作的开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政治保障。四是社会管理领域,发挥意识形态工作的国家治理作用。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也就是制度执行力。意识形态工作是国家治理能力中文化实力的体现,其领导权就是要保证它发挥出引领社会、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社会治理作用。
管理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协同运行的保障。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是运用国家组织和机构对意识形态的一种管理活动权力,是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具体实施,它可以有效保障意识形态工作协调有序运行。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辅助执政力量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实施意识形态管理实践中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的主体以党政权力部门的管理者、事业单位及媒体行业的管理者为主,它的客体涵盖社会生活每个领域的成员,对象是有关意识形态工作活动的各个宣传文化活动。因此,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就是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管好各级各类宣传媒体;探索网络的新技术新应用,管好网络虚拟社会;弘扬主旋律,加强对各级各类文化市场和社会文化活动的管理。
话语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协同运行的基础。话语权不仅是“说什么话”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为谁说话”和“怎么说话”的问题,是一个话语权力、话语立场和话语艺术的综合性问题。话语权由领导权所决定,是管理权的具体表现,同时它又对领导权和管理权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因此,掌握话语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是保证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处理和分析当前社会领域中的各种思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文化生态建设,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协调的话语格局。二是坚持人民性的话语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说话,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和立场。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就是探索积极有效的方式方法,促进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践行。三是体现积极有效的话语艺术。话语艺术是一个“怎么说话”的问题,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就是要针对社会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贴近人民的具体生活,用鲜活的、易被接受的语言来说话。
总之,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协同,就是要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促进人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它们之间不仅具有协同的可能性,而且具有现实必要性。只要弄明白“三权”之间的现实依据、理论特性、实践条件和实现机制,才能促进其有效顺畅地运行。
[1]王伟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13-10-08.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葛兰西.实践哲学[M].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4]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姜安.美国制造:意识形态控制走向结构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5-25.
[6]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M].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7.
[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EB/OL].人民网,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