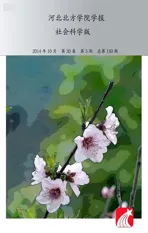晋语入声研究的新角度
2014-08-04王芳
王 芳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学部汉语进修学院,北京 100083)
中国内地方言学“晋语”一说的提出最早见于李荣[1]。他认为,晋语指的是“山西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从微观角度来看,入声是晋语区别于其他北方方言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晋语得以从北方方言中独立出来的一个重要标准。从宏观上来看,这一标准也很有效。侯精一曾指出:“用这条标准划出来的晋语,从地理分布上来看也是非常合适的。这一大片相连的地区,东边到太行山,西边和南边(中间有一个过渡区)临黄河,北边一直延伸到古老的阴山山脉。这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地理环境。巍峨的太行山和古老的黄河以及山西南部的太岳山脉、中条山脉作为天然屏障抵挡处于强势的北京官话方言的西进与中原官话的北上。”[2]1-2
入声是晋语的最主要特点,也是语音特征、地理分布这两条最重要的晋语划分标准之一。晋语入声特征的演变与消失直接关系着该方言的归属问题,同时也反映了晋语今后的发展方向。由于入声特殊的重要意义,入声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晋语语音研究所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及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不断深入,晋语入声的语音特征出现了非常迅速而且显著的分化,而这种分化与方言使用者的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使用场合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因此,传统的方言研究方法已不能满足晋语入声研究的实际需求,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结合语言变异的变项规则分析法对晋语入声进行语言变异的研究更符合晋语入声发展现状的实际需要。
一、晋语入声的研究现状
在《汉语史稿》中,王力先生认为近代汉语具有3个特点:(1)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的消失;(2)-m韵尾在北方话里的消失;(3)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其中前两个特点在北方话中已经完成,只有入声的消失是在有入声的各方言中正在进行的音变,并且在不同的方言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刘淑学指出:“它(入声)既涉及声调系统的变化,又涉及韵母系统的变化,而且入声在官话中的演变速度、演变方向各不相同。”[3]1-3由此可见,入声演变的研究不仅是晋语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对于汉语语音的发展史也具有重要意义。
从传统音韵学的角度来看,“入声”既是一个“韵”的概念,又是一个“调”的概念。从韵母的角度来看,音韵学上依据韵尾的不同,把韵母分为3大类,即,阴声韵:无韵尾的韵和以元音收尾的韵;阳声韵:以鼻音-n,-,-m收尾的韵;入声韵:以塞音-p,-t,-k收尾的韵。这3大类韵尾保存得比较完整的是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方言。其中入声韵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和许多北方方言中都已消失,而以上海、苏州为代表的吴方言,-p,-t,-k韵尾也都消失,它的入声韵尾都变成喉塞音[]。北方方言里保留了入声的情况也类似吴方言,如山西大部分方言和陕北方言(即李荣先生称作晋语的地区)就是如此[4]。
在传统音韵学方面,入声还是与平、上、去相应的一个调类,而声调还有一个“舒促”的概念。促指入声,舒声指平上去3声。实际上,舒促的不同也就是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的不同,因为阴声韵和阳声韵都只有平上去3个调类,入声调只与入声韵相对应(入声调可能也有舒促的区别,如广州话,詹伯慧[5]63-69)。所以,所谓入声,其韵尾特征和调类特征二者紧密结合、不可分割。
入声舒化是中古入声字在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总的趋势。入声舒化指的是中古入声字失去入声韵的韵类特征和声调特征而变成舒声韵的现象[6]42-43。韵类特征主要指塞音韵尾的有无,入声舒化时会失去塞音韵尾,变成相应的阴声韵;声调特征指声调的舒促,入声舒化时音节的时长延长,并和其他的调类合并。入声舒化既是一个共时的音变现象,同时也是一个漫长的历时演变过程。在现代汉语各方言中,入声的具体表现各不相同,如粤方言的入声系统保留了-p,-t,-k 3个塞音韵尾,而吴方言和晋语中则只存留了一个喉塞音[]。从塞音-p,-t,-k发展到喉塞音[]本身就已经是舒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阶段。
晋语各方言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入声舒化的现象,并且入声的韵母系统趋向简化,在舒化的同时韵类也在发生合并。从入声韵、入声调两方面来考察,结论是调由促变舒,韵由繁变简。
温端正[7]对晋语的入声韵进行了分类:(1)一组韵母型。由主要元音(/,)配以4呼,组成4个入声韵:,i,u,y。内蒙古晋语和陕西晋语多属这种类型。(2)两组韵母型。一般由主要元音a()和(/,)配以4呼,组成8个入声韵。山西晋语大部分属于这种情况,内蒙古晋语的准格尔旗、东胜、伊金霍洛旗等也属于这种类型。(3)三组韵母型。由主要元音a(),和(/,),()配上4呼组成。山西晋语有忻州、原平、定襄、河曲,陕西晋语有横山、榆林、靖边、米脂,河南晋语获嘉都属于这种类型。
入声舒化的程度与入声韵母类型紧密相关。一般而言,舒化程度较高的方言韵母类型较为单一,而入声字保留较多的方言其韵母类型往往则较为丰富。
二、传统方言研究的局限
对于入声的研究一直是方言学界关注的问题,入声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也基本都是传统的方言研究方法,即找到某方言点较为标准的该方言的发音人记录其入声字的发音情况,并与中古音系相对照,从而得出该方言入声系统与中古入声系统的差异,并从音韵学角度找出其分化的规律。李明[8]、范慧琴[9]等的研究都属于这一类型。
在单个方言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扩展研究是对地区性的入声特点进行跨方言的比较,对有入声地区的各个方言点进行逐一考察,总结各自的演变规律。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刘叔学的《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在这篇博士论文中,她调查了河北省具有入声的49个县市中的106个县市方言点,对河北晋语的入声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及演化模式的分析。
传统研究的意义在于发现入声舒化后声调、韵母的演变规律,是对中古入声演变过程、特别是在北方话中演变过程的有益补充。然而,这种研究反映的只是语言演变过程中语言系统内部的因素所起的作用。随着语言学的不断发展,语言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系统之外的社会因素也是语言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语言调查的结果经常显示,对不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的发音人的调查结果往往会大相径庭。因此,单纯依靠传统的研究方法无法反映在一个方言点内部不同发音人之间的共时语言差别,可以说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共时描写。
三、晋语入声研究的新角度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正在以强大的优势扩展,不同的方言也都不同程度地在向普通话靠拢。晋语入声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普通话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使得晋语的入声特征随着发音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语言态度等因素的不同而产生了明显变异。因此,晋语入声研究不应再停留在传统方言研究的阶段,而应该结合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考察。正如游汝杰所指出的:“社会语言学应该成为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10]346-367
(一)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理论
语言变异(variation)是社会语言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它与以往的结构主义学派和生成主义学派把语言作为一个同质体进行研究不同的是,社会语言学家更关注语言使用中存在的差异,希望从语言的实际变化中找到语言作为一个社会交际工具的发展变化规律,对语言的社会属性给予更多的关注。
语言作为人类共有的交际工具,必然以顺利完成其交际功能为首要的任务,与之相应地,语言系统的规律性和系统性也随之成为传统语言研究所关注、研究的焦点问题。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语言在完成其交际使命的同时,其被使用的实际状况往往大相径庭,它会因语言使用者本身、使用场合、交际目的等的不同而产生很大的变化。因此,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同质体”来进行研究并不符合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与此相反,文莱奇(Uriel Weinreich)认为,语言系统是一个“有序异质体”[11]75-77,从而开始把语言变异作为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语言变异的实质是不同的语言使用群体在实际语言使用中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差异。
晋语方言入声字所涉及的语音、词汇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变异。老年、中年、青年3代发音人之间入声舒化比例的显著差异、文白异读的语音变化、入声变化地区分布的不平衡等,都是这种变异在不同方面的显现。
语言最根本的特性就是它的社会性,语言呈现出各种纷繁复杂变异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语言本身必然存在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组织之上。因此,语言变异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社会性的变异”进行研究。社会性变异研究一方面包括言语社区内部各种由社会条件限制的集体性变异,另一方面也包括由特殊社会身份所造成的个人变异[12]62-65。
语言态度是个人对某种语言的价值判断及其行为倾向。语言本身并不存在高低优劣的区别,但是语言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赋予了一种身份、地位、文明程度的象征,所以也就形成了人们对语言的不同态度。人们对一种语言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人们对这种语言的使用,进而也会对这种语言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
(二)使用变项规则分析法对晋语入声进行研究
语言变项(variable)和语言变式(variant)是社会语言学在进行变异研究时常用的概念。如果某一个语言形式在不同的语言使用环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那么这个抽象的语言形式就是一个语言变项,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是组成该变项的不同变式[11]75-77。也就是说,语言变项是对某一种具有相同分布的语言形式的抽象概括,而语言变式则是这种抽象的形式在不同实际使用状况中的具体表现。实际语言中并不存在语言变项,语言变式是语言变项在语言中的存在方式。
对于晋语方言入声的研究,可以把“入声/非入声”这一抽象的语言变项作为研究的着眼点。这个抽象的语言形式在实际方言中并不存在,而是由于语言条件、社会因素等的制约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中或表现入声,或表现为舒声。从实际语音角度来说,即喉塞音[]的保留与否。所以,这个语言变项存在两个变式:一个是有“-”的入声形式,一个是没有“-”的零形式,记作“-”。
变项规则分析法(Variable Rule Analysis)是社会语言学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一般用来分析语言变异现象。这种分析方法适用于多种环境因素同时影响、交替出现的不同语言形式的选择情况。不同的语言形式可以是不同的语音形式,也可以是不同的词汇或者语法结构[13]。
变项规则分析法是在拉波夫“变项规则”(Variable Rule)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所得出的统计结果是一些概率性的参数,也就是在某种条件下某个变式产生的概率。由于变异是在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语言环境中发生的,那么变式出现概率的变化就需要综合这些因素来考虑。也就是说,在多种因素构成的特定语境中,每一个因素都有其影响变项X的概率。变项规则分析法正是把同一个因素在不同环境中的影响力综合起来进行分析的。所以,如果知道某变式的出现环境受哪些因素影响、各因素的出现概率是多少,就可以预测相应的变式出现的概率。
例如,如果已知一个变项出现与否有a、b、c、d 4个影响因素,它们的概率分别为Pa、Pb、Pc、Pd,那么该变项在a、b、c、d 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环境中出现的概率Px就可以表示为:Px=Pa×Pb×Pc×Pd。同样道理,任何一个变式的出现概率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计算,用一个一般的公式来表示就是:P0=P1×P2×P3×P4……×Pn。
根据变项规则分析法的理论,对晋语入声音变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可以参考以下解释模型,见表1:

表1 晋语入声变异调查表
综上所述,在统计结果的基础之上,变项规则分析法能够对多因素共同影响下的语言变异做出一种概率性的预测,能够使得社会语言学对各种社会因素对语言变异的影响的研究更加科学化、量化。因此,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语言变异研究的多因素解释模型。
晋语方言的入声变异属于微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也可以运用变项规则分析法进行分析、考察。根据表1晋语入声变异的变项规则分析法解释模型,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进行入声变异的社会语言学调查。首先,对于发音人的确定:突破了传统方言研究只请一两位典型发音人朗读《方言调查字表》并记录其发音的局限,而是在老、中、青3代方言使用者中都选择发音人;其次,对于可能影响发音人发音的相关社会因素的考察:传统的方言研究方法很少考察语言以外的社会因素,因此得到的结果往往是静态的,很难体现在普通话大力推广的社会语言环境下方言的生存状态。因此,从性别、受教育程度、地区对方言使用者的入声使用情况进行考察,具有实际的价值,并能对晋语入声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最后,对使用语体进行考察:使用语体是影响和制约方言使用的又一重要因素,而传统方言调查的方法很少涉及。方言的使用者会根据实际语言使用场合的不同,对自己的入声使用情况进行调整和改变。因此,针对入声使用语体进行考察对了解和记录入声的文白异读具有重要的意义。
变项规则分析法的应用有赖于大样本的实际语料,否则就失去了其统计分析的价值。现在,虽然在晋语入声的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基于大样本的统计分析还鲜有运用,但这种方法可以作为今后进一步进行更加科学、严密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也为入声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J].方言,1985,(1):2-5.
[2] 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 刘淑学.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4] 唐作藩.音韵学教程(第3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詹伯慧.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6] 陈鹏飞.豫北晋语语音演变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7] 温端正.晋语区的形成和晋语入声的特点[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93-101.
[8] 李明.晋东南晋语入声调的演变[J].语文研究,2005,(4):52-62.
[9] 范慧琴.从山西定襄方言看晋语入声的演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4):430-435.
[10] 游汝杰.社会语言学与汉语方言学的新阶段[A].刘丹青.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11] 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当代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2] 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3] 徐大明.新加坡华社双语调查[J].当代语言学,1999,(3):2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