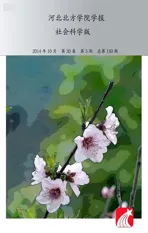论黄帝涿鹿之战真实性考古学依据
——从张家口新石器时代考古角度切入
2014-08-04陶宗冶
陶 宗 冶
(原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河北 张家口 075000)
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历史巨著《史记·五帝本记》里开宗明义记载了黄帝与炎帝、蚩尤大战于涿鹿的历史。从此,人们追寻中国史前文明的目光就一直关注着涿鹿,而涿鹿的黄帝城、黄帝泉、蚩尤寨、桥山这些与黄帝有关的地名也让人萌发出无限的遐想,体现出涿鹿历史的久远与厚重。
在中国人心中,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是中华民族的源和根。正因为黄帝在国人心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位置,所以,千百年来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民间人士,人们一直在探索、求证有关黄帝的史迹,对黄帝所在地域、黄帝陵的位置也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常见的就有“陕西黄陵说”、“河南灵宝说”、“甘肃正宁说”、“山东曲阜说”和“河北涿鹿说”[1]。上述考证究竟哪个更可信?司马迁记载的黄帝战于涿鹿的涿鹿是张家口的涿鹿吗?
从考古学的角度观察,今天涿鹿所在的冀西北地区早在7 000年前,就曾有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北上来到这里。之后,6 000年前陕晋豫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2]24-33以及约5 000-4 500年的辽宁西部的小河沿文化[3]12-27、晋中盆地的龙山文化也先后来到这里[4]181-183。这些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文化的到来,既为冀西北地区洋河、桑干河流域史前文明的发展注入了多元的文化血液,也为这里带来了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曙光。
纵观冀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明显感到这里史前文化的独特。
考古证实,冀西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曾有几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先后在这里存在,它们相互交替或相互交融,中间很少出现直接承袭的文化关系,这在其它地区是及其少见的。冀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的这一独特性应该源于这里特殊的文化与地理环境。文化上,这里处在中原、辽西和内蒙、山西几大文化区的交界地带。地理上,冀西北地区境内既有与山西汾河河谷相通,并通过汾河将陕晋豫地区联系起来的桑干河,也有可以把内蒙和辽西链接起来的洋河与永定河,可谓纵接南北、横贯东西。特殊的文化交界区域和具有文化互通作用的河谷地理环境,使冀西北从远古时期起,就是沟通黄河流域与北方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之间交往的孔道和枢纽。而孔道和枢纽地位,又使这里在中华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发挥着向不同地区输送文化血液的作用,也奠定了这里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多次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交往的舞台。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就是古史中的黄帝文化。对此,红山文化的主要发掘者和研究者郭大顺先生曾有详尽的论述[5]72-76。视红山文化为黄帝文化的主要依据是:红山文化在北方地区分布广,时间早,农业生产发达,有祭坛、宗庙和神像崇拜(宗教崇拜),文明程度高,尤其是有高度精致、自身特征明显,且数量众多的玉器和时间最早、造型独特的龙形图腾。众所周知,龙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从红山文化开始,龙的形象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角,从古至今在中国人心中从未消失。红山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里出现龙图腾最早的文化,加之《史记·天官书》有“轩辕,黄龙体”的记载,所以,起码自西汉以来,人们一直是把龙与黄帝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源于上述原因,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里指出:“红山文化的突出文明特征是龙纹图案。《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6]130据此,将红山文化看做是黄帝文化是有历史和文化依据的。小河沿文化也叫后红山文化,顾名思义,它是继红山文化之后与红山文化有继承关系的一种文化,如红山文化是黄帝文化,与红山文化有继承关系的小河沿文化自然也是黄帝文化。冀西北地区蔚县壶流河沿岸发现过红山文化;宣化、崇礼、涿鹿、阳原县所在的洋河和桑干河流域又发现过小河沿文化,而且阳原小河沿文化墓地还出土过红山文化典型的玉器——玉雕龙[7]1-17,说明新石器时代黄帝文化曾抵达冀西北。
小河沿文化之后,以龙为代表的黄帝文化历经5 000多年的沧桑巨变,在中华大地上一直延绵不绝生生不息。早到商周时期精雕细琢的玉龙,再到今天依然随处可见的各种形态的龙,甚至辽、金、元、清几个由中原地区以外的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同样是以龙作为皇权的象征。所以,新石器时代之后,随着中华文明的融合、发展、统一和走向成熟,龙已不再是某一个区域文化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了,它已经演变为整个中华文化的象征(图1),这应当是后人把龙和黄帝联系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1.红山文化(赤峰翁牛特旗) 2.红山文化(辽宁牛可梁) 3.小河沿文化(阳原姜家梁) 4.商代(安阳花园庄) 5.商代(安阳妇好墓) 6.商代(安阳妇好墓) 7.战国(台北故宫) 8.汉代(台北故宫)
图1各个历史时期玉雕龙
关于黄帝在历史上的年代,学界普遍认为是距今5 000年到距今4 500年前之间,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这个时间点为基础,冀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小河沿文化、龙山文化和学界认知的黄帝年代相符。考古证实: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发源地和中心区在今天的辽西地区,冀西北地区之所以也发现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是这两种文化发展强大后从辽西南下西进的结果。与辽西地区不同,涿鹿既有小河沿文化,也有与之时间稍晚的龙山文化。通过分析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分布范围、迁徙路线以及冀西北地区龙山文化在这里传播发展的变化过程,笔者认为黄帝涿鹿之战说在论点、论据方面是有考古学依据的。
一、考古证实冀西北地区是黄帝文化的分布区
目前,冀西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存只在蔚县壶流河流域有零星的发现,其它区县没有见到。就是在壶流河流域,现存的红山文化遗存数量也很少,遗址文化堆积同样很薄,可见壶流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所在时间不长,也不是十分发达。与红山文化情况相反,冀西北地区的小河沿文化遗存发现的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大大多于红山文化,除蔚县外,目前已公布的就有涿鹿、宣化、崇礼、阳原,赤城也有,但还未公开报道,这不会是一种偶然(图2)。这一现象说明,冀西北地区出现黄帝文化的时间始于距今6 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但黄帝文化真正在冀西北地区一带扎下根来,并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冀西北地区的主体文化,是在距今5 000年以后的小河沿文化时期,这既在时间上与学界普遍认为的黄帝存在时间相符,而且,正是由于小河沿文化已发展成为冀西北地区的文化主流,才有能力与外来的文化相争。换言之,因为冀西北地区小河沿文化的强盛,才具备黄帝文化与其它文化在涿鹿发生征战的历史基础。

1.崇礼石嘴子遗址采集 2.赤峰大南沟墓池M27.7 3.宣化贾家营H3.2 4.赤峰大南沟墓地M52.4 5.涿鹿煤沟梁出土 6.赤峰大南沟墓地采集 7.蔚县三关遗址出土 8.赤峰大南沟墓地M27.1
二、考古所见的黄帝文化在冀西北地区的融合过程
根据学者对小河沿文化的分期来看[8]32-43,冀西北地区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小河沿文化,可分早晚两段。其中,早段遗存多分布在洋河流域,晚段在桑干河流域。早晚两段文化的主体都是小河沿文化(图3),基本不见其它文化的因素。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上述情况发生了显著改变。首先,这时期遗存,虽然小河沿文化的折腹盆、筒形罐还有保留(图3,1.2.4.),但同时大量出现了以罐形三足鬲、釜形斝等三足器为代表的晋中地区龙山文化因素(图3,5.6.9.),还出现了以小领横耳罐为代表的部分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9](图3,3.)。
冀西北地区从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文化结构的变化,与晋中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晋中地区一度受到周邻地区东、西和南、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遗存成分异常复杂”[10]的状况极其相近,说明仰韶文化之后在中国北方地区曾出现过一次大的人类文化迁徙活动,其波及区域十分广泛。迁徙中,来自辽西、晋中盆地和山东地区不同方向、不同谱系的文化在洋河和桑干河流域形成了交汇,不同谱系文化间交汇碰撞的结果必然是不同文化的融合。冀西北地区龙山文化时期表现出的复杂文化现象正是这种多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对冀西北地区这一时期复杂的文化现象,张忠培先生有一段精辟的概括:“总之,这里是多种不同谱系的诸种考古文化的拉锯地区,情况显然相当复杂。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谱系的诸考古文化之间相互吸收、融合和斗争。可以说,这里是不同谱系的诸种考古文化登台演出她们的壮丽史诗的舞台。”[4]据此可以推测:在几个强大的不同谱系文化碰撞的初期,相互之间极可能发生的情况之一就是出现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处于文化交汇点之处的冀西北地区自然责无旁贷地成了这种文化迁徙、人类征战的最佳舞台。
小河沿文化的下限和冀西北地区龙山文化的上限在时间上间隔很短,虽然从考古年代上讲小河沿文化早于冀西北地区龙山文化,但考古年代上的早晚之差是指两大文化的相对年代,不是绝对年代,在绝对年代上小河沿文化晚期与冀西北地区龙山文化早期应该是相接的。例如,赤峰大南沟小河沿文化墓地有3组14C数据,其中两组人骨数据显然偏晚。剩余1组树皮测试结果,1个是距今(4 345±180)年,另一个距今(4 830±180)年[11]。属于冀西北地区龙山文化的蔚县筛子綾罗遗址木炭14C测得的数据为距今(4 260±120)年[2],年代与大南沟的年代十分接近。另外,考虑到仰韶文化晚期冀西北地区已有发达的小河沿文化,因此很难想象从仰韶文化晚期到晋中地区龙山文化到来之前冀西北地区没有人类居住,而已知的考古发现又明确告诉人们,在这两者之间没有其它文化在这里存在。所以,当时在冀西北地区应当存在一段短暂的小河沿文化和东进的晋中地区龙山文化共存的时间。大量的田野考古证实,当时冀西北地区的小河沿文化、晋中的龙山文化都很发达。因此有理由推测:距今5 000年至4 500年前,晋中地区龙山文化沿洋河由西向东推进,与已在冀西北地区的小河沿文化在涿鹿(这里所说的涿鹿泛指大涿鹿,即整个冀西北地区)相遇,于是两种不同谱系的文化在洋河和桑干河流域先后发生了几次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乎逻辑的。战争的结果导致了晋中龙山文化和冀西北地区小河沿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冀西北地区龙山时期独特的遗存。因为这几次征战的规模与残酷给人们留下的记忆过于深刻,在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期,人们通过口口相传,代代演绎,到司马迁写《史记》时还能听到以“黄帝”之名在涿鹿征战的故事而记录下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另外,司马迁所在的西汉时期,龙已经成为君王和正统文化的象征,所以,以龙为代表的“黄帝”大败诸敌而君临天下,自然也就作为正史而被载入史册,这既不违常理,也符合历史传统观念。

1.折腹盆(崇礼石嘴子) 2.折腹盆(宣化贾家营) 3.罐(崇礼石嘴子) 4.罐(宣化贾家营) 5.斝(蔚县筛子绫罗) 6.斝(蔚县筛子绫罗) 7.折腹盆(宣化贾家营) 8.罐(宣化贾家营) 9.鬲(蔚县筛子绫罗) 10.豆(阳原姜家梁) 11.折腹盆(阳原姜家梁) 12.折腹盆(阳原姜家梁) 13.高领罐(蔚县三关) 14.盆式豆(阳原姜家梁) 15.敛口钵(宣化贾家营) 16.豆(涿鹿煤沟梁) 17.折腹盆(宣化贾家营) 18.折腹盆(涿鹿煤沟梁) 19.罐(宣化贾家营) 20.高领罐(涿鹿煤沟梁) 21.高领罐(崇礼石嘴子)
图3冀西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陶器比较
三、陕西和河南出土红山文化玉雕龙并不代表那里就是黄帝文化发祥地
研究黄帝文化不能不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从黄帝涿鹿之战到司马迁动笔记载这段史实,中间已间隔3 000年左右的时间了,3 000年后司马迁记载这段历史时只能是追记。不管司马迁追记的依据是凭口传还是当时还能看到一些后世补记的史料,但司马迁记载中既然还提及涿鹿,可见涿鹿之说必然出之有据。否则,作为一位历史公认、学识渊博、记史严谨的史学大家不会在没有掌握某些证据的情况下,随意去写出一个自己没有考证的地名。目前考古证实,冀西北地区是小河沿文化的分布区,再往西小河沿文化没有进入到陕西和甘肃,往南也没有传播到河南。反之,从考古学分析,涿鹿既有小河沿文化,又是晋中龙山文化东进的前沿,它从地域和文化迁徙两个方面验证了司马迁“黄帝涿鹿”之说出之有据,也让人相信黄帝之战发生在涿鹿不是无稽之谈。
这里不能不提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考古学者虽然没有在陕西和河南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发现过红山或小河沿文化的遗存,但却在河南三门峡西周墓、陕西韩城春秋墓、韩城战国墓、凤翔春秋墓这些远远晚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随葬品中发现过红山文化的玉雕龙和勾云玉器[12]69-73,其中陕西韩城梁带村春秋早期墓出土的玉雕龙不仅和红山文化玉雕龙形态完全相同,而且形体硕大引人注目。
考古中,晚期的墓里出土早期的遗物并不鲜见。比如,西周时期的墓里就常常可以见到商代的青铜器,湖北明代梁庄王墓里也曾出土过多件金、元时期的玉器和帽顶。红山文化距春秋早期有2 000多年时间了,春秋早期墓里居然还出土红山文化玉雕龙,可见红山文化的玉器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被人们,尤其是古代贵族所喜爱和珍藏。但是,红山文化玉雕龙在河南和陕西的出现,并不代表这两地就是黄帝文化的分布区,因为,考古学确认一种古文化是不是分布到这里的主要标准,是这里有没有属于这种文化的遗址或墓葬,其中有没有这种文化的典型陶器更是判断这种文化分布的重要标志。因为玉器、石器、青铜器便于携带又便于保存,可以传播很远保存很久,但陶器不具备这些优势,所以陶器往往只存在于本地,且保存时间也不长。由于上述地区至今没有发现红山或小河沿文化的陶器、遗址和墓葬,所以,上述地区黄帝之说存疑。
虽然考古工作者没有在河南、陕西发现红山和小河沿文化,但河南、陕西西周到战国以来墓葬中玉雕龙的存在,也让人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当时河南、陕西贵族喜好玉龙,把玉雕龙视为珍品收藏,除了出于对玉的喜爱外,在当时崇尚礼制的社会风尚下,保存玉龙也是权贵、身份和正统的象征。而正是河南、陕西在青铜时代延续了龙文化,所以古代的人们才有了“龙”(黄帝)源自河南和陕西,从而慢慢引申为这两地就是黄帝故土的观念。
四、冀西北地区是史前几大文化碰撞的必然通道
任何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各个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与融合,是一个强大古代文明得以形成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因为只有文化传播才有不同文化的交融,有交融才会使不同区域先进的科学技术相互吸纳,文化发展才有动力。多种文化间不断地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融汇是使文明从弱到强,从多元走向统一,从而最终形成强大文明体系的必然过程。冀西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处在中原、辽西和内蒙、山西几大文化区的交界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必然成为沟通、链接上述几大文化区古代文化交往的枢纽。因此,冀西北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的文化沟通作用,对促进中国远古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和不可或缺的意义。正因如此,苏秉琦先生才把以张家口为代表的冀西北地区称之为“中国古文化的三岔口”。地理上的“三岔口”,多是军事要冲和征战咽喉,文化上的“三岔口”,又多是文化碰撞交融之地,现代如此,古代也同样。冀西北地区是中华史前文化的“三岔口”,是红山文化西进的必然通道,自然也是多种文化的碰撞之地。从这个角度看,史前的冀西北地区就是多种文化征战、交往、融汇的前沿,而涿鹿就是这个前沿中一个重要的节点。
五、关于涿鹿的黄帝遗迹问题
涿鹿有黄帝城、蚩尤寨、桥山等和黄帝有关的地名。虽然这些具体的地点人们至今还不能确定它们一定和黄帝有关,但不能就此就将这些地名的出现看作是后来人们对历史的杜撰,其实地名的由来更大的可能是当地人对远古时期发生在家乡那场战争的历史记忆。众所周知,古史传说的背后往往有真实历史的影子,如同传说时代里的故事并不一定全是传说一样。这些地名有的可能是古代那里曾经修建过与黄帝有关的建筑,有的可能是人们看到一座战国古城,因为很古老又不知道它的确切修建年代就把它和记忆中的黄帝联系起来了。这种张冠李戴的事例在中国历史遗迹里并不鲜见。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曾说:“历史传说是我们古史的组成部分,不但我们这样,世界文明古国都是如此,追溯到一定时期以前都是传说,均有神话色彩因素。炎帝、黄帝的传说,是我们祖先通过他们的认识、记忆、语言记录传递下来,其中有真实的素地。”[13]109由此笔者认为,对一个大的历史事件的研究,不必拘泥于一个具体地点的年代符与不符,从而放大到推翻黄帝涿鹿之战说,因为采用以点带面的方法考证历史并不一定科学,反之,人们倒应该将探索的眼界放到史前文化在涿鹿迁徙、碰撞、交融的角度来思考黄帝与涿鹿的关系才对,因为对史前史的研究,从一个时空广阔的、文化交叉的历史层面得出的结论,往往比一个点得出的结论更接近历史的实际。所以,探讨黄帝与涿鹿关系,需要从时间、地点与文化迁徙等综合因素考证才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史记·五帝本记》在记载黄帝涿鹿之战时,也记载了与黄帝征战的对方炎帝和蚩尤。对黄帝和炎帝的关系《国语·晋语》有“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的记载,如若果真如此的话,黄帝、炎帝可能是同宗,也就是说很可能是同一种或关系密切的考古学文化。从民族学的角度看,黄帝、炎帝、蚩尤应该代表的是两个或多个不同的人类族群或部落,黄帝、炎帝和蚩尤只是酋长或各代表一个族群或部落的名称而已。而从考古学角度看,不同的考古文化肯定属于不同的部族群体,但不同的部族群体不一定就属于不同的考古文化。由此推论,要确认某一处地点可能是黄帝、炎帝和蚩尤曾经征战之地,首要的条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地方起码有两种以上不同的人类文化族群或多个部落群体存在才可以,而且其中首要的是要有小河沿文化,否则没有黄帝文化的地点,黄帝之说从何谈起?所以,只要涿鹿有代表黄帝文化的小河沿文化,同时也存在时间上与黄帝文化并不矛盾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就不影响对黄帝涿鹿之战观点的确认。至于炎帝和蚩尤目前是否也能归于已知的某一个考古学文化,笔者认为现在的研究尚属探索阶段,有些观点在时间和源流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故该文并未涉及。
历史上,人们很久以来一直认为中原是中华文明正统的发祥之地,中原之外的地区为蛮夷之所,既落后又不开化,当然不会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念的出现应当源自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长城修建之后。当时,位居中原腹地的人们一直把居住于北方或南方的胡、狄、匈奴和各种少数民族看做异族,认为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生产落后,物资匮乏,不讲礼制,不尊儒教,所以非正统,更不可能是中华文明起源之地。这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带有偏见的错误历史观一直影响了学界近2 000年。20世纪初,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之后,大量的田野工作使一些新的史前文明不断破土而出,新的发现让人认识到,中华史前文明的形成不仅在中原,而且在其它以前认为不是史前文化发达的地区同样有非常发达的古代文化。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距今约7 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约8 000到6 000年前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约5 000多年前的杭州良渚文化,包括青铜时代以来的四川巴蜀文化、广西百越文化等,其文明程度都出乎所有发现人的想象。这些发现渐渐改变了学术界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更让人们想象不到的是,这些所谓的非正统地区发现的文化,有的恰恰就是后来中华文明的主体之一。例如,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就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器上人面纹;商周青铜礼器中的鼎和鬲,也可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地区的文化里找到同类器;良渚文化、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刻画符号又使人联想到了汉字的起源;特别是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玉龙和以玉龙为代表的玉器文化,更让人感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上述事例说明,中华史前文化是多元的,中华文明是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类群体共同创造,并历经长时间的历史交往融汇最终形成的,这是形成中华文明的文化之源,更是形成今天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其中以龙为代表的黄帝文化,就是这些众多远古文化里最具代表的,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古文化之一。
20世纪初叶,由于甲骨文的研究导致学界发现了商代的殷墟,之后,学界由商文化推导确认出了夏文化。从20世纪中叶到现在,学界又从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确认了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文化,这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学研究进展,让人们看到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史实不虚,司马迁黄帝涿鹿之战的记载不虚。学界今天依然锲而不舍越过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追寻黄帝的足迹,实际是在寻找中华民族的源,中华民族的根,更是对中华文化的祭拜、崇敬和继承。笔者相信,随着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面纱一定会不断地被揭示出来,中华文明的历史极有可能比人们现在认识的更早,对此人们充满期待。
参考文献:
[1] 黄帝陵基金会.黄帝文化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2] 张家口考古队.1979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A].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口考古文集[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3] 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口古陶瓷集萃[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4] 张忠培.张家口地区考古的重要收获[A].张忠培. 中国北方考古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5] 郭大顺.追寻五帝[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
[6] 苏秉琦.论西辽河古文化[A].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C].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A].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口考古文集[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8] 索秀芬,李少兵.小河沿文化分期初论[J].考古与文物,2006,(1):32-43.
[9] 陶宗冶.关于张家口及邻近地区龙山时期遗存的几个问题[J].张家口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66-73.
[10] 许伟.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J].文物,1989,(4):40-50.
[1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12] 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3] 李学勤.深入探讨远古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A].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