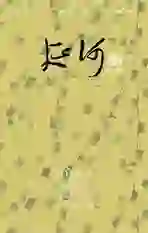小小说三题
2014-07-24青霉素
青霉素
朱三和他的老盆
朱三死了。
邾镇的人都说朱三活着的时侯亏,死了以后更亏。
朱三的脑子有点毛病,大事犯糊涂小事不清醒。小时候发烧烧断了他脑子里的一根筋。他两个哥这样说,但这并不妨碍朱三拾破烂换钱。
朱三的工作很辛苦,每天天不明就起来,围着邾镇大街小巷转。别人不要的东西,只要能换钱他都拾起来,分门别类的放好,积攒到一定数量送去废品回收站换钱。朱三在邾镇拾破烂为生,准确地说是以拾破烂换钱为目的。他吃饭从不用他换来的钱,邾镇的大小饭店都是他吃饭的地方,别人吃剩下的东西就是他的,饭店老板都认识也不为难他。
有闲人故意问朱三:老三,银行里存了多少钱了?
嘿嘿,不多。朱三一脸真诚地笑。
闲人又问:你存钱有什么用啊,既不用钱吃饭又不用钱买东西。
嘿嘿,等俺媳妇回来。朱三又是一脸真诚地笑。
这时众人才想起朱三是有过媳妇的,只是媳妇早没了踪影。早年,朱三的老娘还在的时候,把一个讨饭的女人领进家,劝她说,你赶百家门讨吃的也不易,不如留下给俺儿一起过日子吧,保你吃喝不愁!女人竟同意了。新婚之夜,朱三给新媳妇揭下红盖头就乐了,乐了一脸鼻涕泡。乐着乐着,朱三脑子里的哪根筋就搭错了,找了一把菜刀就砍新媳妇,新媳妇哭着喊着跑到邾镇外的黑夜里再也没回来。
媳妇没有了,朱三就找了一条狗做伴,淘来吃的人一半狗一半,一家两口不离不弃的样子。朱三傻也有傻心眼,他还知道去找会卜卦的伤兵求卦,看看媳妇啥时候回来。伤兵看着朱三,笑得两眼冒水,说,你使劲拾破烂攒钱吧,攒够十万元媳妇就回来了。伤兵是说着玩的,他知道朱三那媳妇不可能回来,要回早回了。十万元对朱三来说,那就是天上的星星,看得到摸不着。
朱三领着他的狗追着日子围着邾镇街巷拾破烂,几十年就过去了,狗也换了好几个。本来这样的日子还可以继续下去的,偏偏朱三丢了一百元钱。朱三见人就问,拾到他的钱了吗?问谁谁摇头。
朱三上吊死了。众人都说他是丢了一百元钱心疼死的,朱三死时的样子很特别,一只手紧紧抓着一张印着100元字样的冥币,另一手紧紧握着一个红盖头。他两个哥把红盖头取下来,发现里面包着一个存款折,打开一看都傻了,存款折上的数字是99900元。
朱三的大哥张罗着朱三的丧事,并对别人说,自己的小儿子早年已过继给老三当儿子,现在要给老三摔老盆引路。大伙都知道,这是想要朱三的钱。老规矩讲,谁给死去的人摔老盆谁就得遗产。朱三的二哥自然不愿意,瞪起眼跟老大吵,你说你儿子过继给老三了,谁作证?我儿子还过继给老三了呢!最后经族人调解,想出了一个两家都能接受的法子。发丧的当天,烧纸钱的死人老盆放在棺材上,两家的儿子百米外跑着去抢,谁先抢到算谁的。
发丧这天邾镇大街上挤满了人,都是看热闹的。朱三的棺材停在大街上,装着纸钱灰的老盆放在棺头,两家儿子百米外蓄势待发。
执事的老总高声喊:时辰到,亡人上路!
两家儿子疯了一样冲向棺头的老盆,同时一条黑影也箭一样飞去。
砰的一声,黑影抢先把老盆顶上半空又摔到地上,老盆摔得粉碎,盆中的纸钱灰在空中飘着如同一片片灰蝴蝶。
馆前躺着朱三的那条黑狗,黑狗的嘴里鼻子里都有血流出来,黑狗一动也不动。
蝉鸣
邾镇后街的拐角处就是伤兵的家。破败的院落就像伤兵一个人过的日子,歪歪扭扭没着没落的样子。院里对着堂屋门堆着一座坟,没有人无事来他家串门,除了找他卜卦的人,绕过坟进他的堂屋。
伤兵会卜卦,据说很灵验,很远的地方都有人来找他。
这天伤兵去镇子西的棒子地里拔草,一场连阴雨让地里的草长得比棒子苗还高。日头偏西才提着盛满青草的篮子回家,路过西门外那棵大梧桐树时伤兵住了脚。树冠若伞,茂密的树叶子营造的凉荫,诱惑着过往的人。
伤兵靠着梧桐树坐下,努力地伸直腿。在地里拔了一上午的草,这个姿势让他很舒服很解乏。他的举动惊动树上的一只蝉,从一处飞到另一处。伤兵的目光在树上扫了一遍没看到蝉,目光就从树叶上滑到旁边的草垛上,他起身走过去,一只手轻车熟路地插进草垛掏出一个酒瓶。回到树下,从草蓝子里掏出一把酸枣,酸枣是地边摘的,小酒就着酸枣,让伤兵的惬意在树荫下慢慢扩散。
酒瓶见底的时候,伤兵看到远处一个人向镇子走过来。六月的太阳把路面烤的摇摇晃晃的,沿着摇摇晃晃的路面望过去,伤兵就看到来人手里提着的酒瓶。
来人走到树下停住,看着眯着眼打盹的伤兵。
“大叔,给您打听个人。”来人小心地问,“邾镇会卜卦的伤兵家怎么走?”
伤兵眯着眼,“什么事?”说着话一个酒隔犯上来,“我就是。”
“真巧,老天爷安排的呢!”来人说着把酒瓶举到伤兵面前,“有件事求您点拨点拨。”
伤兵闻到酒味,睁眼看到酒瓶心里一乐,但他使劲地抿了一下嘴,把心里的乐又咽了下去。“什么事?说吧。”
“我女人跟人走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来人说话的语气和他的头一起低下来,“想请您给卜一卦看看。”
伤兵的心一沉没说话,抬起头找树上的蝉,蝉鸣声很聒噪。没找到蝉他只感觉到每片叶子上都有蝉鸣的回声。
“凡事都有规矩,就像我给人卜卦。”伤兵说话的时候,眼睛还在树上找。“我的规矩是和女人有关的卦不接!”说完,伤兵直直地看着年轻人的脸,心里一动,一个酒隔犯上来堵在嗓子眼里。
“你走吧,我帮不了你。”伤兵不再搭理年轻人,又背靠树闭眼养神,眉头拧成一个疙瘩。
伤兵一闭上眼,就能清晰地看见他的女人,一看到女人就看到女人幽幽的两只眼。女人留给伤兵最后印象就是幽幽的两只眼。那天伤兵和陈皮一起走出村子时,女人就是这样看着他。
伤兵是真不想去贩私盐的,舍不得新娶的女人。陈皮劝他:“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女人跟你受屈?这些年我已经跑出路来了,你跟着我保准有钱赚!”
伤兵就去了。回来的路上和陈皮走散了,回到家也没见到陈皮,自己的女人也不见了。
“就是回来我咋办呢?”年轻人不甘心地又问。
被惊醒的伤兵站起身,提起草篮子就往镇里走,他不想看年轻人的脸。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还是转身看了一眼,没说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自从女人走了之后,伤兵就和酒瓶一起过日子。伤兵的酒瓶散布在镇里镇外任何一个隐秘的地方,一个墙缝里一个石堆里或一个草垛里。
日子就在酒瓶里不紧不慢地飘走了。他一直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走,而且走的无声无息。看着女人留下的东西,拿酒瓶的手就把握不住了,他把女人东西埋在院里堆成一座坟。
三天后,那个年轻人又来了,不是一个人来的,独轮车上推着一个老女人。伤兵看到独轮车上的老女人的时候,觉得几十年的日子一下子都没了。他看到了那老女人幽幽的两只眼,那眼里虽然填满了岁月和病痛,但幽幽的气息还是让伤兵喘不过气来。
“这些年俺娘过得不好,梦里经常念叨着您的名字。”年轻人说,“现在她病了,大夫说没多少日子了,俺娘想来看看您。”
年轻人扶着女人进了大门,再扶着女人进堂屋的时候,伤兵伸手挡住了。“这个屋是我的,那个屋是你的。”伤兵指指院里那座坟。
年轻人一愣,老女人却笑了,有泪慢慢流下来。
“我这辈子是对不起你了,下辈子还你。”老女人说话有些费力,每个字都揪着伤兵的心。老女人看看院里的坟说,“求你让我回家住吧!活着不能填你的屋,死了填你的屋,下辈子好在你跟前赎罪。”
伤兵抬起头,太阳光哗哗地流下来,他耳朵里全是蝉鸣的声音。
雪花飘满天
接到爹的电话有些意外,爹很少给我打电话,上班时间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
“爹,你在哪儿?怎么了?”
“我在家呢,没事,就想给你打个电话。”爹轻松地说,可我一点也不轻松。家里的小事爹从不给我说,怕我分心,爹说没什么事恐怕有事。
“爹,家里都好吗?我明天一早就坐车回家。”
爹意识到我的紧张,声音很重地,劝我:“我和你娘都挺好,没事不要回来了。”
爹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就挂了电话,我的心一直悬着。
第二天,我匆匆忙忙赶到家时,爹正蹲在大门口。嘴里含着一支自制的烟卷,缭绕的烟雾笼罩着他花白的头发。爹看见我忙站起身,一截长长的烟灰落在衣襟上。
爹脸色枯黄,仅仅两个月没回家,爹怎么老得这么厉害呢?爹站起身来差点摔倒,我急忙上前扶住。
“真是老了,蹲了一会竟蹲麻腿了。”爹靠着我自嘲地说。
“我娘又出去了?”
“她还有什么事,蹲在村头等人是她的活。”爹说着叹了一口气。
爹的叹气声堵得我心里满满的。
在屋里坐下,爹又点上一支烟,一阵咳嗽憋得他不停地捶胸脯。
“得少吸烟了,你的脸色不好。”我给爹捶着背问,“你觉着身子哪里不舒服吗?”
“也没啥,就是心口窝有点堵。上个月村东头你五爷老了,出殡那天我帮着抬棺,回来吃饭吃急了,吃下的东西又都吐了出来。从那时起就落下根,一吃饭就想吐。”
“你怎么不早给我说呢!咱去医院看看吧。”我一边埋怨一边收拾东西。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过一阵就好了。”
“咱现在就去!”我坚持着。
“你娘自己不做饭,我把饭给她做好再走吧。”爹说完就忙着做饭。我说,“我去把娘找回来。”爹说,“不用去,不到天黑她不会回来的。”爹把做好的饭盛了一小碗慢慢吃了。我拿起爹放在桌上的碗去洗,爹制止了我,说,“别洗碗,你妈看到我吃过了她才会吃。唉,她总怀疑我饭里放毒药似了。”
在医院里,我拿着大夫开出的一把化验单,扶着爹楼上楼下地检查,累得他气虚喘喘。
化验单都出来了,每张单子都写着同一个让我绝望的结果。我握着那些单子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栗,像受了极大的委屈,无助地靠在墙上,泪水在脸上纵横。
从洗手间出来,我擦干脸上的水迹去找爹。
“没大病,只是有点胃炎。”我故作轻松地对爹说。
“傻儿子,别瞒我了,我的身子我有数。”爹一脸坦然,“你五爷就是这种病走的,今天来就是想知道还能活多久。”
在我竭力劝说下,爹勉强在医院住了下来,却总是挂念着娘。“你不用担心,我都安排好了。”我说。
这天,爹拉着我的手说,“儿子,你娘一辈子不容易,以后好好替我照顾她。”
我噙着泪点头。
“我狠狠打你那次,还记得吗?”爹歉疚地看着我。
我又点头。长这么大爹就打过我一次。那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娘又坐在村口,一群小孩围着娘喊:“疯子,疯子。”我低着头去拉娘的手,娘恶狠狠地推开我,骂我:“谁家的野孩子?”我又羞又怒,哭着大喊:“疯子,疯子!”回到家,爹狠狠地打了我,
“你娘年轻的时候,是咱这片数一数二标致的人,又漂亮又有文化。那个下乡的知青因为这个娶了你娘,后来你娘有了孩子,孩子有病死了。那个知青回到城里又找了女人,逼着你娘离了婚。多好的一个人啊!被刺激得疯癫了。”爹怔怔地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又说,“那个知青又结婚的时候,你娘还傻傻地去帮他们烧火做饭。”
这些我听别人说过,但从爹的嘴里说出来,让我的心一阵阵地痛。
娘虽然嫁给了爹,但她的心永远留在另一个家里。娘的世界里有家有丈夫有儿子,但不是这个家不是爹不是我,娘总是在村头等他的丈夫回来。爹心里满满地装着娘,娘心里装着一个年轻时的梦,那梦和爹无缘。
爹在冬天来的时候走了。我坐在铺满麦草的堂屋地上为爹守灵。爹坐在棺前的像框里,看着我,也看着一会儿挨着我坐在地上,一会儿又站起来摸摸棺木的娘。这些天,娘一直不说话也没出家门。
出殡的那天,雪花飘满大街小巷。我抱着爹的遗像走在前头,族人抬着棺木走出大门。
啊呀!一声尖叫,满天的雪花静止在空中。所有的人都停住脚步,惊恐地看着站在大门口的娘。
娘的怀里紧紧抱着爹生前用的枕头,那声尖叫,耗去了她所有的力气。
“乙哥,你不要我了吗?”娘无力地梦呓着,像怕惊醒棺里的爹。爹的名字叫乙。
“乙哥,你不回来了吗?”娘又梦呓着,她的眼里是满天的雪花。娘抱着爹的枕头,靠着墙角慢慢地蹲下来,很冷很委屈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