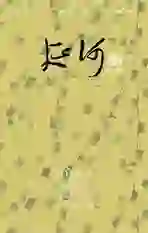谭五昌:海子的精神知音
2014-07-24王琪
王琪
谭五昌是近年来迅速崛起诗坛的一名青年批评家,以他多年来研究著名诗人海子诗歌为例,就能发现,他独到的诗歌见解、大胆的评判意识与独特的审美标准,令国内诸多诗人和诗评家为之赞叹。
一直以为,搞文学评论是一个“有风险的职业”,在新传媒迅猛发展,社会巨变、转型的新时期,诗歌遭受的冷遇是前所未有的,而诗歌批评家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诗歌正名,替诗人说话,无疑值得推崇,令人尊重。无论是研究海子及某个诗人,还是关注整个诗坛现状,作为诗坛批评新锐人物,使谭五昌评论本身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诗歌批评家的价值在哪里
王 琪:你好谭兄!难得通过这次访谈,和你聊一些关于诗歌方面的话题。你在诗歌批评方面已经很有建树了,至今已出版诗歌类编著及诗学著作20余种,可谓成果丰富,影响广泛。你是当代著名诗歌评论家,多年前就有“新锐批评家”之称了,那你认为批评家在诗歌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谭五昌:首先谢谢你对我进行采访!说起来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在诗歌方面的交往已有十多年时间,因此你才会对我的诗歌批评与研究工作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你提及的诗歌批评家在诗歌中的位置问题非常有意思,既道出了一般诗歌读者心中普遍存在的疑问,也道出了诗人们心中普遍的关切,还提醒着诗歌评论家对自己进行价值定位的必要性,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从一般意义而言,诗歌评论家在普通的诗歌读者(非专业读者)与诗人之间起着桥梁般的沟通作用,一个诗人的具体作品及该诗人的创作特色、艺术风格、文学史地位,只有经过那些够格的与优秀的诗歌评论家的到位解读与阐释工作,才能为广大的普通诗歌读者所理解、所认可。假如缺少诗歌评论家,普通读者对具体诗人作品的阅读过程与定位评价工作将变得比较困难。简言之,好的诗歌评论家对普通读者的诗歌阅读行为,会产生一种理想化的思想引导与艺术启蒙功能。另外,好的诗歌评论家还具备一种前瞻性的文学史眼光。他能对一些有天赋的或有开拓性贡献的诗人进行及时敏锐的发现与大力扶持,提前预言其在当代文学史(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
但必须客观指出的是,当代诗歌批评家与当代诗人及当代诗歌读者之间的关系存在某种具悖论意味的尴尬情形。一方面,某一位或某一批诗人的作品通常须经过诗歌批评家们的大力评介与宣传,方可达到为大众读者普遍知晓且广泛认可的境地,另一方面,诗歌批评家在当代诗歌场域却又常常处于某种边缘化的尴尬角色与境遇。具体说来,大众读者对当代诗歌批评家总体上并不怎么重视,也无认知与了解诗歌批评家的内在热情。举个例子,我经常参加各种大型诗歌活动,当主持人介绍某位具有明星效应的著名诗人(如舒婷或余光中)时,现场总是会响起非常热烈的掌声乃至尖叫惊呼声,而介绍到某位著名诗歌评论家(如谢冕或吴思敬)时,现场响起的掌声则明显不那么热烈,至少不会有人发出尖叫惊呼声。这说明在大众心目中,诗人的价值要远远高于诗歌评论家的价值,哪怕这位诗歌评论家的批评才华再怎么出色,在大众那里似乎也是不可能得到多大认可度的。可见,优秀的与杰出的诗人在大众眼中光芒四射,而优秀的与杰出的诗评家则相对光芒黯淡,几乎湮没无闻。这种情形对诗评家而言当然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对一些一辈子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某位著名诗人的追踪性研究或对某个诗群流派予以长期研究的诗评家,更是一种价值低估。更值得指出的是,不少当代诗人对当代诗评家一方面似乎也受到大众舆论的影响,对诗评家重视程度不够,甚至对他们的批评文本常常颇有微词,但另一方面,诗人们又很看重批评家的作用,内心里还是非常希望诗评家们能多为自己写到位的评论文章,并对自己的诗歌创作进行高层级的文学史定位。这就是许多诗人对待诗评家的矛盾态度,由此也凸显了当今诗人与诗评家之间的某种微妙关系。从这一点来看,诗评家的位置的确有其尴尬性。当然,真正优秀的有内涵的诗人对优秀的诗评家还是很尊重的,他深深懂得诗评家的价值。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诗人与诗评家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欣赏,良性互动,在张扬优秀诗人价值的同时,也应彰显诗评家的价值,二者之间价值平等,各有千秋。
王 琪:十多年前,我就曾读过你写下的《百年新诗的光荣与梦想》,这篇论文对“新体诗”的流变与发展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与回顾,很多观点颇有新意,现代手法的合理运用,与对古典诗歌的传承,这之间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谭五昌:《百年新诗的光荣与梦想》这篇论文实际上是我为自己十多年前所编选的《中国新诗300首》所写的序言,对百年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与美学潮流变迁做了宏观性的描述与梳理。如你所言,这篇文章得到了谢冕、牛汉、罗门、洛夫等不少诗坛前辈及国内一批知名诗人与诗评家的普遍肯定与好评,首先要谢谢大家对本人的青睐与抬爱,现在自己回头看这篇文章,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年轻人特有的批评激情与敏锐认知,那时自己的确非常年轻,正值风华正茂,写起文章来思维活跃,观念解放,见解独到,敢言人未尝言,甚少顾忌。说实话,我对这篇诗歌评论还是颇为满意的,它是我早期诗歌批评文章的代表作之一(但愿不要被读者朋友们解读为这是我的自恋态度,呵呵)。举个例子,这几年我每次见到台湾著名诗人罗门先生,罗门都会提及我的《百年新诗的光荣与梦想》一文并大大表扬一番,夸奖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棒”,主要理由是我在该文中评论台湾三位资深诗人余光中、洛夫与罗门本人时,对他们三位诗人不同的创作风格、艺术成就与文学史地位进行了细致的阐释与评价。我的大致观点是,余光中对古典诗学传统的继承最为充分,古典性有余而现代性不足;洛夫在古典诗学传统与现代性审美趣味上达成了一种大致平衡;而罗门则是相对忽视古典传统、最具现代性经验特质的一位诗人,他们均赢得了自己应有的文学史地位。罗门深深认同我的观点,这应是他激赏拙文《百年新诗的光荣与梦想》的主要原因。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你的意思是说,当代诗人创作诗歌作品肯定要合理的应用现代手法,如何来实现对古典诗歌的传承呢?这之间最大的难度在哪里?我认为,当下中国诗人的写作处于全球化语境之中,他要呈现的首先肯定是当下经验,但是他在处理与呈现这一经验时,肯定有意无意的会关注表达的独特性与有效性。假如他的表达与一位外国诗人的表达毫无区别,他的作品本身肯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这时候中国诗人的文化身份就显得颇为重要了。作为一名当代中国诗人,他肯定对中国文化有一种认同,他也不可能彻底隔断与中国诗歌传统的联系,无论出于自觉还是自发,绝大多数当代中国诗人都会或多或少从中国传统诗歌中寻找可以继承的审美元素。不少当代中国诗人在民族意象、诗歌韵律、传统表现技巧、东方哲学理念、古典审美情调与趣味的传承方面做得颇为成功,像刚才提到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大陆诗人舒婷也称得上是一个典型例证。但是,更多的当代诗人在艺术创新与对古典诗歌的传承之间常常处于一种纠结状态,因为他要表现的是当代生活与当下经验,很难用古典的传统的那套语言、意象与手法来加以有效呈现,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你所说的最大的难度就在这里。这个问题恐怕也只能在具体诗人的写作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当今许多诗人在创作中有意使用一些中国本土词语、意象来呈现中国本土经验,这实际就是对古典诗歌传统的很好继承了,比如洛夫在21世纪初用《漂木》来命名他的一首长诗,意图表达他的漂泊经验,东方色彩与韵味很足,中国读者很有感触,试想如果他用《漂流瓶》来命名之,那就没有什么中国的味道了。
王 琪:波澜壮阔的新文学运动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一时期出现的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徐志摩、戴望舒等一批杰出诗人成为新诗的主力,他们留下的大量诗歌充分显示了各自独特的艺术追求和精神特质,称得上是对中国新诗的“集体贡献”。已经跨入新世纪十多年了,为什么他们依然在文坛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谭五昌:新文学运动对中国新诗的影响的确非常深远,事实上,是胡适的新诗创作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大幕,由此可见新诗在新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你所提到的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称得上是新诗史上的优秀诗人乃至杰出诗人,具体说来,郭沫若诗歌中个性张扬的五四精神与自由形式的创造,闻一多诗歌中强烈的爱国精神与自觉的形式规范,臧克家诗歌中的底层关怀与草根意识,徐志摩诗歌中的浪漫情调与唯美形式、戴望舒诗歌中的传统情调与现代手法的有机融合,大概就是你所指称的这批现代诗人的独特艺术追求和精神特质,是他们对中国新诗的“集体贡献”。这批诗人在20世纪上半叶的诗坛上可谓叱咤风云,在21世纪的当下依然有其不容低估的影响力,但是否称得上具有无穷魅力恐怕还有待考证。至少在我个人看来,那些优秀与杰出的当代诗人在今天比前述那批现代诗人更具影响力,因为当代诗人笔下所呈现的当下经验对今天的读者而言比前辈诗人更具吸引力。我在北师大的课堂上曾长期给本科生与研究生们讲授新诗,也到过国内数十所大学做过新诗方面的专题演讲,我发现学生们普遍倾向于更喜欢听我讲解当代诗人的优秀作品。比如学生们更有兴趣听我来讲解食指、顾城、芒克、北岛、舒婷、梁小斌、王小妮、任洪渊、吉狄马加、翟永明、于坚、欧阳江河、王家新、李亚伟、西川、海子等当代诗人的诗歌及相关诗人故事。因为年轻人在这些优秀与杰出的当代诗人的作品中能够找到更多引起他们共鸣的人生经验与审美趣味。
倾心研究海子和海子诗歌
王 琪:研究海子的人很多,但我知道,你是较早系统研究海子的青年批评家。当年你从北京大学读完硕士的毕业论文就是一篇《海子论》,这篇论文正式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有些人不同意你的某些观点,能谈谈当时的状况和你对此所持的态度吗?
谭五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海子论》,如你所说,这篇论文后来在诗歌圈内逐渐广为人知,并有幸获得诗歌界诸多同行的认可与好评,从而为自己的研究生求学生涯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在此说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当初我的导师、著名学者与作家、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先生大力支持我的选题,并在我的答辩会上对我的这篇论文流露欣赏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曾在一张报纸上读到一位有才华、有个性的青年诗人的文章,他认为20世纪九十年代末只有两篇诗学论文他看得上,一篇是诗人批评家臧棣的论文《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还有一篇就是我的《海子论》。当然,也有极个别诗人不大同意我对海子诗歌及海子本人的研究与评价,并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一些比较情绪化的贬低海子本人的意见,我对此的态度是不必较真,一笑置之,因为一些诗人尤其是年轻诗人在看待与评价优秀与杰出的同行时内心总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心态,宽容与智性的来看,这其实不是件坏事,它至少能够大大激发该诗人的艺术创造欲望与能力。
王 琪:一直不太明白,你为什么如此关注海子?他对你学术之路影响很大?
谭五昌:简单说来,我最早看到海子的诗歌时,我从其中看到了自己心灵的影子,海子的纯粹、孤独、善良、对理想的赤诚、对爱情的热望等精神品质深深触动了我,我感觉自己是海子的精神知音,在很多瞬间,我甚至感觉海子的很多诗歌作品是我写下的(据说不少热爱海子诗歌的年轻诗人都有这种错觉),当然我心中有这种感受,但笔下写不出来,因为我还是没有写诗的天赋。从读到海子的诗歌那一天起,我就开始关注海子了,等我进入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后,我就花费不少时间与精力进行海子诗歌的解读与研究工作,毕业时写出了长篇论文《海子论》,被不少人视为很有前途的青年诗评家,从此我正式走上了诗歌批评的道路。
王 琪:前不久,也就是2014年清明之前,我无意中在一个朋友的微博上,看到你亲自带着海子的母亲去北京的二炮医院检查身体,当时微博声称海子的母亲身体健康,心情愉悦。看到这条消息,我非常感动,真有此事啊?
谭五昌:你看到的这个消息是真实的。今年4月3日,海子母亲和海子二弟查曙明应我要求来到北京,我想与他们商量海子诗歌奖的有关事宜。他们来到北京后,我发现海子母亲的一只手臂在老家摔伤了,至今还未痊愈,于是我在4月4日上午带着海子母亲去二炮医院专门做了检查,拍了片子,当时海子二弟和秦皇岛女诗人赵永红一起陪着老太太检查身体,见老人家手臂无大碍,大家都很高兴,老太太自己也心情大好。海子母亲对我很好,把我当儿子一样看待,我为她做这么一件事情合情合理,可以说不值一提。我觉得真正让人感动的倒是女诗人梅尔,她听说海子母亲到北京了便专门过来看望她,先是塞给老人家一个装钱的信封,听说海子母亲手臂受伤了又立刻打电话让她的一个理疗师朋友赶过来,让他特意为海子母亲受伤的手臂做了整整一个下午的理疗。我认为这是真正让人感动的爱心行为。
王 琪:2013年夏,在你的多方筹备和奔波下,征得海子家人同意后,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星星》诗刊等单位联合发起设立了“海子诗歌奖”,并于2014年3月在京揭晓。这个奖项的设立,是为了纪念“再也回不去的诗歌年代”,还是纯粹是为了推出致力于诗歌创作的优秀诗人?就目前来看,效果怎么样?
谭五昌:你知道,海子诗歌及海子本人这些年一直呈现升温状态,形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海子现象,许多诗界人士与普通读者都自觉的在为海子做事,其中比较有诗学价值的活动,一个是秦皇岛诗人赵永红、张鹤云等人筹办的海子诗歌艺术节,另一个是由诗人斯琴夫、卧夫等策划并筹办的青海德令哈海子青年诗歌节,以及由青海省宣传部、青海海西州政府、海西州旅游局等单位发起建立的海子纪念馆,就差设立一个“海子诗歌奖”了。于是我在去年上半年就萌生了设立“海子诗歌奖”的想法,这个想法首先得到了海子家人的一致支持,随后又得到了我的同事张柠教授、张清华教授等人的首肯与支持。再随后陆续得到了谢冕、梁平、燎原、树才、耿占春、唐晓渡、李少君、阎安、周庆荣、潇潇、安琪、洪烛、南鸥、韩庆成等一大批诗人与诗评家的大力支持。
简单说来,“海子诗歌奖”的设立,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海内外青年诗人的创作,弘扬纯粹性、原创性、理想性的海子诗歌精神。目前有寒烟等五位优秀诗人获奖,在诗歌界反响良好,大家普遍认为这个结果非常理想。一句话,青年诗人的创作热情被普遍调动起来了。
王 琪:对于海子诗歌的研究,你还有哪些新的打算?
谭五昌:目前为止,我出版了两本海子诗歌编著,一本是《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海子诗歌精品》,是我对海子五十六首短诗的鉴赏导读本;另一本是刚刚出版的《活在珍贵的人间——海子纪念集》,其中汇集了对海子的怀念文章、作品解读和诗学评论,这两本书都是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而且责任编辑都是于奎潮先生,即诗人马铃薯兄弟。由于马铃薯兄弟有很高的审美品位,做书又精益求精,这两本海子编著的印刷设计均堪称品质一流,大大提升了我这两本海子编著的传播幅度。
关于海子研究,我打算在这两年抽出时间来对海子全部作品进行深入研读,然后撰写出一部有水准的海子诗歌研究专著,海子家人也有这个意思,所以一方面我感到很荣幸,另一方面也很有压力,不能让海子家人感到失望。在此顺便说一下,燎原、西川、陈超、朱大可、罗振亚、张清华、熊继宁、西渡、荣光启等诗评家、学者与诗人已写出过很有分量的海子诗歌论著,我得向同行们学习,以提升自己的海子研究水平。最后还要强调一下,海子研究工作只是我整个当代诗歌研究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全部。
无法抗拒的前行动力
王 琪:据我所知,你当初是在江西读了中师,又通过读自考,进入北京大学攻读文学硕士的,毕业分配至北京联大后,于2001年9月再次返回北京大学攻读中国当代文学方向博士学位,最后落脚北京师范大学。无论作为老兄还是老师,你都值得我们敬重和学习。
谭五昌:我的奋斗历程就是一个寒门书生幸跃龙门的当代版故事。很多朋友已知道我的经历了,在此我就不再赘述以作炫耀了。谢谢你对我的表扬。
王 琪:多少年过去了,你走出了家乡小村,来到北京著名高校搞学问,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但这一路非常不容易。对你的人生经历,有何感慨?
谭五昌:我出生于井冈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一个典型的农家子弟。通过自己的奋斗,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愿望与梦想,来到北京生存与发展了。有人可能会羡慕我眼前的所谓风光,其实一路走来,经历过多少艰难、辛酸、挫折,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正所谓长夜漫漫无人伴,人间知己最难求。我深切体会到,自己的每一份收获是建立在自己加倍付出的汗水的基础之上,伟大的事业要用一生的心血与痛苦去追求之。当然,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我也收获了许多珍贵的情谊,它们给了我心灵的温暖与继续前行的动力。
王 琪:记得2006年夏天,北京还在轰轰烈烈大搞建设,迎接2008奥运会举办之时,我们在京师园附近有个小型聚会,傍晚我要回宾馆时打不到出租,你站在马路上大声地吼叫,结果吼来了一辆三轮车,把我顺利送至车站,那情景真是令人动容,可以看出,谭兄的性格很开朗,平时和学生相处也这么随和?
谭五昌:我都有些淡忘了,你现在这么一提醒,我在路边大喊大叫着为朋友拦车又可以当做一个诗坛趣事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小区还没建设好,路上很少出租车,只有三轮车,噪音很大,我只能吼叫了,否则师傅听不到就会耽误你的事情。另外交代一下,我是江西井冈山人,我们那里的人说话普遍嗓门比较高,我遗传了井冈山人的性格,性格比较热情,说话声音比较响亮。学生们普遍说我性格开朗、随和,许多学生还说我是最有亲和力的老师之一,我和他们相处融洽。
王 琪:不止一次听你讲过,你的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平时挺重,是不是很累?搞诗歌评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吗?
谭五昌:我的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平时确实挺重,非常累,这是我许多同事的共同境况与感受。诗歌评论是我科研任务的一部分,由于我主要致力于诗歌批评与研究,所占比重就会大一些。
王 琪:工作之余,是不是也去打打球、跑跑步?做点与诗歌无关的事?
谭五昌:是的,我兴趣比较广泛,一个从事诗歌研究的人不能全部淹没在诗歌当中,应该有自己丰富的日常生活。
王 琪:和你相处过的人都知道,你生活其实很简单,那么你认为诗性的东西和生活有什么相互依附关系?
谭五昌:我的确是个简单的人,崇尚简单、透明、诗意的生活。日常生活其实也充满了诗意,如果我们能长久保持一种好心情,能以超功利的审美心态打量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再普通的生活也透出或浓或淡的美好诗性氛围。
保持友好的诗歌批评态度
王 琪:对自己目前搞诗歌评论还满意吗?作为“学院派”诗歌评论家,你眼里的真诗和真诗人是什么?
谭五昌:我目前对自己的诗歌评论工作还比较满意,主要是我喜欢这项工作,有不少朋友说我热爱诗歌生活,我觉得是知音之论。作为一个诗评家,我眼里的真诗是它能以语言的天籁性与生动性、意象的妥帖性、情感的纯粹性、哲思的深邃性深刻地感染我,而我理解的真诗人应该是对诗歌抱有虔诚、纯粹、敬畏的态度,常怀一颗赤子之心,且对语言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与想象力,这两个问题内涵很丰富,我在这里简单作答了。
王 琪:你为什么如此热衷诗歌评论?是面对诗坛,经常觉得有话要说,对吗?
谭五昌:我前面说过,我热衷诗歌评论主要是因为我喜欢为诗歌做工作,更具体一点说是我想努力在诗人与普通读者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同时对于诗歌与诗坛也是有话要说,前者是我借助诗人的作品抒发自己的感受,后者则是我通过评论的方式对诗坛明确宣传自己的诗学主张。
王 琪:对于当前大学校园的诗歌现状,你满意吗?比如首都的高校,你更有发言权,有什么建设性意见或建议?
谭五昌:我对当前大学校园的诗歌现状总体上还不是特别满意,以首都高校为例,现在基本上每所高校的校园诗歌氛围不是那么浓郁,写诗的大学生人数偏少,热情也不是非常高涨,娱乐主义与实用主义思潮在青年群体中占据着优势地位。我建议每个高校的文学社平时组织固定的读诗会,形成诗歌创作与交流的内部小气候,同时,可以请一些对当代诗歌充满热情与价值认同的诗评家与诗人进行专题讲座,充分调动学子们学习新诗与创作新诗的人文热情。
王 琪:每个正在成长期、上升期的青年诗人,都希望听到评论界的声音,指责也好,鼓励也好,总之要真实、客观,你作为一名诗歌评论家,如何才能助推他们走得更远一些呢?
谭五昌:对处于成长期的青年诗人而言,最好的方法是让他能够及时听到诗评家对他中肯的评论意见,不一定都要听到溢美之词,批评意见也应虚心接受。不过对一个负责任的诗评家来说,他对青年诗人应抱有真诚的友好的批评态度,同时在此基础上须对该青年诗人的创作优势与发展方向发表明确的指导性意见,这对青年诗人的帮助将是最具实质性的。
王 琪:我知道这些年来你一直忙忙碌碌,为中国新诗做了不少事情,今年是马年,请问你有什么诗歌计划吗?
谭五昌:呵呵,你最后一个问题还真的问得很及时。我现在向你简单说说我马年的一个大的诗歌计划吧:就在年初,我联合中国诗歌流派网执行主编韩庆成先生发起一个21世纪中国现代诗群流派大展活动,意图让诗人们以集体亮相的方式呈现自己各自不同的群体流派艺术风貌与诗学主张,因为随着21世纪多元化文化环境与格局的形成,诗歌写作的多元化样态与圈子化倾向日趋鲜明。本次现代诗群流派大展得到了国内外数以千计的广大诗人与诗评家的热情支持,大家认为这个大展将极大活跃当代诗歌创作与发展态势,看来大家对这次诗群流派展示的意义达成了比较广泛的共识。否则,我也不会浪费时间与精力去做一件无意义无价值的事情。当然,肯定会有一些诗人与诗评家对这次大规模的现代诗群流派大展有自己的不同看法,这是属于合理的学术争鸣,我们对此持有完全心平气和的心态。
在拟定谭五昌为本期采访对象之前,我就在暗自思量,如果他不是很忙,就一定会爽然应约本期访谈,而事实确实如此。他是一名优秀的青年批评家,但其实更是位诗人。如果当初他没有先接触到诗歌,也不一定会有评论诗歌的想法。
时间证实一切。谭五昌在诗歌评论之路上不断前行的探索精神,也必将证实一切。
责任编辑:阎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