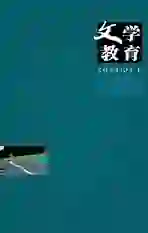谈诗歌鉴赏的两个概念:悖论与反讽
2014-05-26李小宁
内容摘要:悖论就是违背常理的思维表达,在诗则是一种无理性追求,即贺裳所谓“无理而妙”的诗歌创作原理。反讽是指一种正话反说,抑或所言非所指的语言现象;反讽会造成表层语义和深层语义之间的差异,从而形成诗歌自身很强的表现力。
关键词:批判思维 诗歌个性 悖论 反讽
一.悖论
“诗的语言就是悖论的语言”(布鲁克斯《精制的翁》)。所谓悖论就是违背常理(常情)的思维表达,在诗则是一种无理性追求,即贺裳所谓“无理而妙”(《皱水轩词筌》)的诗歌创作原理。“诗之情味每与敷藻立喻之合乎事理成反比例”(钱钟书《管锥编》),诗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表情达意往往采取无理、反常的委婉形式。
诗的语言忌直忌白。诗的语言必须直接楔至于鲜活的、生动的、跳跃的思想深处,然后熔解,抑或爆炸。“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如同人的生命最活跃部分的潜意识,只有语言的探头透过意识的老茧,才能触及生命的内涵,直指本质。
诗的无理性,并不是说写诗是不讲道理的胡乱拼凑与生搬硬套,而是强调诗要区别于世俗意义上的平铺直叙与陈词滥调。诗必须重视和审视诗人自我的存在状况,因为只要是诗,就别无选择。李小宁诗《马》:
没有蝴蝶幻化的草原
一匹马陷入一株树的芳年
远去的歌谣,这匹不会游泳的马
它要冻结自己的孤独与爱恋
“一匹马陷入一株树的芳年”,且在“游泳”,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事件。现实中没有的,意识中有,意识中没有的,潜意识中有。现实中有“马”有“树”,这就足够了,但“游泳”行为一旦发生,所能隐喻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生命关联的意义就会明朗化,形象化,乃至“合理化”了。
悖论在诗中运用的基本特征是因果链条被强行切断, 语言与语言之间的联系不再是语序上简单的语法关系;诗的句式往往不合乎所谓正常的逻辑性推理,而是以反常的方式将一些表面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物与感觉嫁接在一起;当然这种嫁接必须是以心理真实为依据的,否则,表达即使如何新颖精巧,也与诗无缘。
荒诞也是一种悖论,它不同于语序颠倒、变形夸张、反常搭配、省略跳接的无理性的语言组合。在诗中,荒诞是一种整体的表现方式,抑或言语方式;它是以人的存在方式表现出来的人的荒诞意识和荒谬处境为前提,是一种必须以心理真实为基础条件的生存体验。人之所以在生活中有荒诞感,是由于人常常处于理性的强行规范之中,总要严肃地选择所谓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然而,现实的遭遇却很难满足人这样的需求,于是人就会质疑自身存在的意义,怀疑自己的理性;可是人所固有的意识,以及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中的惰性理念,又无法使自己摒弃对既有意义的理性追求,这就构成了人生于世的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
诗人笔下的荒诞之所以具有特别的意义,就在于它突破了实用的理想主义与肤浅的乐观主义的单向思维的樊篱,对客观世界与自身生存现状的质疑所具有的批判意识,使其将理性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加以多维度的审视。清醒的痛苦总比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甚至简单的快乐更有价值与意义。诗人在自己的诗作中所表现的荒诞性存在,往往是在他最清醒时候的真实思想状况。
开愚诗《往昔》:“早晨,父亲拉着儿子的小手/走进故宫/黄昏,只剩下满脸皱纹的儿子/蹒跚地踱出宫门。”为什么父子两人早上进了故宫,黄昏出来,一天之内,儿子却成了满脸皱纹的老人?——这是人对时间感知上的荒诞。儿子老了,父亲去了哪里?不言而喻,诗人把人的一生浓缩于一天之中,用一个特定的事件去描述,突出表现的是人在绵亘的时间长河中真实与虚无的时间知觉。这就不能不让读者反思自身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然,诗中还隐含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对孩子心灵的戕害是如此的触目惊心,这与鲁迅先生当年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声音一样,振聋发聩。
诗,正因为有悖论的语言,才使得诗人的表达趋向真实。诗人之言语,犹如潜意识黑暗之河流中的鱼所吐出的气泡,虽不华美,但却透明。
二.反讽
反讽是指一种正话反说,抑或所言非所指的语言现象。反讽会造成表层语义和深层语义之间的差异,从而形成诗歌自身很强的表现力。诗的语言从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是单一的、生硬的、机械的符号系统;任何一首诗,不论作者的主观意图是什么,都会由于语境的作用而发生意义的转变,造成诗的语言的含混性,以及诗意表达的混沌性。
反讽会造成强烈的批判效果,皮日休《咏螃蟹》“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可谓入木三分地讽刺了社会上一些横行霸道之人等,形象、幽默、传神。如此反讽风格,在民歌中也用得很多,《诗经·国风》里反讽意味很浓的诗也不少,如《魏风·硕鼠》《唐风·鸨羽》等。
反讽这种手法不但在漫画式的讽刺诗中常常用到,就是在一般的抒情诗中也很常见。反讽不单指反语的意义,还应包括幽默、揶揄、机敏的智慧内涵。传说乾隆皇帝“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千万片”地吟咏雪花,突然灵感顿失,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他身边的纪晓岚接着吟出“飞入芦花皆不见”的诗句,使得整首诗的境界得以拓宽,趣味得以提升。
作为现代诗技巧之一的反讽,应是“自反的嘲讽,即嘲讽反过来指向自身,并成为对于自身及自身所置身的世界的反思维性认识”(沈天鸿《现代诗歌技巧十二讲》)。顾城的《远和近》、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都是将嘲讽指向“自身”,以及“自身所置身的世界”的很好的反讽范例。李小宁诗《狼》:
这些东西追来,赶去
彻底失去自由,笼子
若干年之前,之后
还狗以绝对,自由
其实,狗就是若干之前狼类的叛徒,对人的忠诚就是对同类的背叛。失去自由的“笼子”是在执行人的命令:让狼也同时失去自由。“若干年之前”(“之后”)的狗是绝对自由的,那时的狗还是(还原)真正的狼。难道这首诗是单单说狗吗?显然不是,是讽刺那些“狗性”十足之人的;同时也是对现代人渴望“狼性”回归的一种反讽。齐秦的“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的狼啸,曾经使多少人共鸣过,以及共鸣着。endprint
诗中的反讽首先是一种语言技巧,从语言技巧运用的角度来看,反讽的类型可分为夸大叙述、言此意彼、正话反说等。在诗的文本解读中,还有主题层面形成的反讽,即文本复杂的主题意义出现相反相成的两重或多重表现,从而形成强烈的反讽意味。
一般说来,径情直遂,并局限于表白某种单一情感的诗,根本就不能算是好诗。用委婉曲达、兼容并蓄、相反相成、虚实相生的反讽手法来组织创作语言的诗才是好诗。布鲁克斯在《作为一种结构原则的反讽》中说:“在这一深层的意义上,反讽就不仅是承认语境的压力。不怕反讽的攻击也就是语境具有稳定性,内部的压力得到平衡并且互相支持。这种稳定性就像弓形结构的稳定性,那些用来把石块拉向地面的力量,实际上却提供了支持的原则……在这种原则下,推力和反推力成为获得稳定性的手段。”反讽运用得好的诗往往回避明显的价值取向,以种种巧譬妙喻的手法,婉转曲达地表现诗人的复杂情感。林海《无奈》“乞丐在垃圾桶边站了半天/地球继续旋转”,诗人借用两个矛盾的对象,造成强烈的反讽效果,进一步强化了诗作意味。
闻一多先生的《死水》最为突出的艺术手法莫过于反讽。作者通过视觉描写死水的丑,通过嗅觉描写死水的臭,通过听觉描写死水的死寂。为了使死水的特点更为突出,诗人把死水里的种种肮脏成分譬喻以极其美好的事物,加以赞扬,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反讽效果。把人们扔进沟中的破铜烂铁上的锈迹比作“翡翠”和“桃花”,把死水中的油腻比作“罗绮”,把死水表面的一层霉菌比作“云霞”,把恶臭的死水比作“绿酒”,把死水里的气泡比成“大珠”“小珠”。读者可以调动各种感觉器官充分地展开联想:翡翠的晶莹碧绿,桃花的艳丽鲜红,罗绮的柔滑光亮,云霞的流丽飘逸,这些意象叠加在一起本身就是一幅美妙无比的图画。但是,当确知这些所谓美好的事物来自于作者笔下的臭水沟时,不但不能唤起审美的愉悦,反而会产生极其强烈的厌恶情绪。这就是反讽的力量。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说“看似单纯的问题其实最富有意义”,她的诗反讽的功力是出类拔萃的,且看她的《三个最奇怪的词》(林洪亮译):“当我说出‘未来一词,/第一个音节已成过去。//当我说出‘寂静一词,/我就立刻打破了这种寂静。//当我说出‘乌有一词,/我就在创造一种无中生有。”这是一首纯粹的诗,纯粹到几乎不存在技巧;但反讽的意味读者一定是能够感觉出来的,可以说除过反讽别无技巧。诗人冷峻、严肃、深刻地探究了三个名词的终极本质,探究了作为话语名词的意义。她不用意象,她用最朴素纯粹的语言,似在喃喃自语,“当我说出”之后,一切都是全新的,一切都改变了——这不仅仅是对“未来”“寂静”“乌有”本身的破坏,她在告诫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们,甚至人类:一切所谓的“创造”,都是“无中生有”,甚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由悖论到反讽,这之间没有天然的鸿沟,正因为悖论思维,才会造成语言上的反讽效果;反讽运用的恰切,则又反映了诗人批判思维的深刻。
(作者介绍:甘肃省白银市第一中学教师,甘肃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发表教学论文、文学作品400多篇。已出版《石头与花朵》《流觞》《流亡的翅膀》等教学、文学专著6部。撰写校本教材《诗歌鉴赏基础》1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