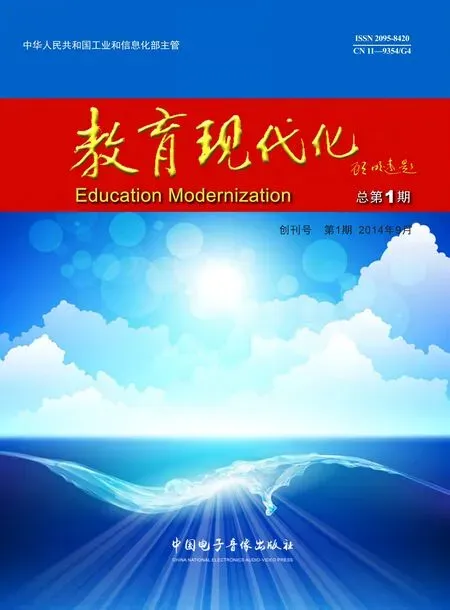“自爱”到“道德”
——卢梭道德情感的线索及启示
2014-04-17李文娴傅建明
李文娴,傅建明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卢梭在其教育著作《爱弥儿》对他所假设的教育对象爱弥儿进行一系列的自然教育。在第四卷中他集中谈论了自己关于道德教育的设想,试图回归到人自身去寻求道德的情感基础。“自爱”就是这样一个熠熠闪光的概念,弥散于卢梭道德教育所构建的情感空间。因而,本文立足于卢梭道德情感的线索去诘问当今德育的困境,试着探索一种有益的启示。
一 道德情感的独特价值及失落
哲学家休谟在描述道德情感时曾指出:“道德概念本身要求一种人类情感,这种情感使各个角落、最遥古的人的行为也成为道德上赞许或反对的对象”[1]。人是一种情感动物。有如俗语所述“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程度上是以情感维系的,而个体的判断、行为选择等也始终带有情感的色彩。与一般性的、动物性的情感不同,道德情感是人所特有的高级社会性情感,是人在一定的道德认识基础上对现实生活中道德现象、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等表现出的一种爱憎或好恶的情绪态度。它从更深层次上表征着个体的道德面貌。
在当今的语义环境中,我们衡量一种行为道德与否很多程度上是从社会关系角度切入,以行为的动机和社会后果加以衡量。归根究底,“道德”处理的是“他人与我”的问题。从本质上说,道德是以人为主体的,是人合目的性的现实表现和价值形态[2]。而真实的道德行为必须基于人的需要并直接与人的情感一致,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的确立,进而衍生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所做出的选择。毋庸置疑,在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选择的过程中,道德情感不可能“缺席”,相反,它是沟通道德桥梁最为直白的一种联系,它提供最为强劲的力量和动力。道德情感作为一种内在的心理机制和重要的精神力量,对完善自我、提升人格具有重要作用[3]。个体对其行为的选择、发生与塑造都注入了强烈的“非理性”因素——情感,而在道德行为的选择和生发过程中道德情感无疑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诚如布拉梅尔德所述:“人类决不完全是理性的动物,他们总是无意识地深受感情和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的”[4]。只有经由主体情感体验,外在的道德要求和规范才能真正为个体所认可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信念,并具化为现实的道德行为。不仅如此,个体在对道德行为或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往往采用“对”与“错”、“应该”与“不应该”等价值关系进行表达,而这种个人倾向性的表达都是基于个体的情感体验所做出的判断。有别于自然科学命题的严密逻辑和精准答案,道德价值判断的内容和对象总是掺杂着个体的道德情感倾向,为这种“非理性”因素所渲染和渗透。不同于一般性的情感,道德情感不单纯是个人意义上的“恣意妄为”,而更多的是社会道德规范与要求的理性要素与个人非理性要素的统一,实质上蕴含了道德理性的内控机制。在个体的道德价值判断的过程中,道德情感与道德认知相互协调,立足于社会道德规范的一般性原则和要求,对行为的动机、效果等做出理性而不失人情味的判断。
反观现实,道德教育的真实场景中却不乏各种难题。面对这样或那样的道德困境,我们抨击社会大环境下人情冷漠、道德沦丧的种种现象与惨剧,指责学校德育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冷漠、表里不一的“道德知识容器”。但当我们开始试着发掘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根源并将矛头指向唯经济主义与唯工具理性对人和教育的宰割时,我们似乎将自身置于这种物质与精神“分裂症”的“被害者”席位。而事实上,这一切绝不是毫无缘由,更不应是“无作为”的。我国“德育”在总体上偏重道德说教、社会-政治说教,人们对此不乏共识[4]。也有国外学者指出,认知性道德教育理论无法解释青少年中较常见的“故意失德”现象[5]。无论是“故意失德”的现象还是那些让人唏嘘不已而又无奈的道德冷漠事件,当事人并非对此类不道德行为的恶劣后果“一无所知”,更不是道德认知的匮乏或意志的缺陷,而是缺乏遵循道德规范的动力和情感支持。由此可见,将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定位于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依据上来看,确实有失偏颇。道德教育呼唤道德情感的参与,而道德情感的积极配合更是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前提和关键。因此,道德教育必须关注道德情感这一重要维度,去追问道德情感的重要线索,去寻求一种解答。
二 道德情感的线索及其解读
任何一个理论都有一个逻辑起点,同理,道德情感也有其特定的情感线索。道德教育对道德情感的关注必须立足于对这一线索的准确把握。而卢梭在《爱弥儿》中对道德情感及其道德教育详尽的论述无疑为此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如果说卢梭道德教育的理论起点是他对人性以及人性发展的认识,而他关于道德情感的线索则以“自爱”作为逻辑起点,进而衍生出其他社会性的情感,并最终指向道德。
(一)起点:“自爱”
卢梭这么说道:“我们的种种欲念的发源,所有一切欲念的本源,唯一同人一起产生而且终身不离的根本欲念,是自爱”[6]。在他看来,“自爱”是最为原初的情感,是其他情感衍生、发展的根基。在对“自爱”的重要性作了一番叙述之后,他这么说道:“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存,我们必须要爱自己,我们爱自己要胜过爱其他一切的东西;从这种情感中直接产生这样一种结果:我们也同时爱保持我们生存的人”[6]。显然,他所说的“自爱”究其本质是一种自我保存的情感,表现为个体为对自己生命的观照。“自爱”作为美德伦理学的一个基础性范畴,它表达的是一种最重要的基础美德[7]。一直以来,西方伦理学对“自爱”这一范畴始终保持着研究热情,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对无逻各斯的“坏人的自爱”和遵循逻各斯的“好人的自爱”的区分,还是伊壁鸠鲁、霍布斯、爱尔维修、休谟、沙夫茨伯等思想家对自爱的解读,他们或多或少支撑着自爱这一情感之于个体生命的重要意义,并肯定了自爱本身蕴含的道德特性。道德意义上的自爱是对自我人格、荣誉与价值的一种恰如其分所谓态度和要求,表现为珍视自己的生命,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8]。与自私截然不同,真正的自爱必定建立在自我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平衡点上。正如卢梭所言,“自爱始终是很好的”,它不等同于“自私”,“敦厚温和的性情是产生于自爱,而偏执妒忌的性情是产生于自私”[6]。诚然,“自爱”首先指向个体自己,但这并不否认自爱对他人的效用。正如亚里士多德曾说的“好人,必定是一个自爱者”[7]。自爱是爱己与爱人的立足点,是个体的存在是一切道德行为可能的前提。无论是自爱还是他爱乃至上升到对全人类道德理想的热爱,最终都是必须以“我”的存在,“我”的感受,“我”的需要,“我”的标准为前提,将“自爱”作为德性涵养的生长起点。
(二)延伸:“怜悯心”
在“自爱”这个情感起点之后,卢梭描述了这么一种情感:“我们之所以爱我们的同类,与其说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快乐,不如说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痛苦;因为在痛苦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看出我们天性的一致,看出他们对我们的爱的保证。如果我们的共同的需要能通过利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则我们共同的苦难可通过感情把我们联系在一起”[6]。在他的观点里,“怜悯心”是出于人类对“共同的苦难”的觉察。“怜悯心”或者说“同情”,作为一种社会性情感,它不同于原始的“自爱”情感,它开始转向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范畴。伦理学者何怀宏就曾说:“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怜悯之情作为人类最原始和最纯正的一种道德情感,对于使人们履行最起码和最基本的道德义务,使社会不致长久堕入野蛮的巨大意义。所以,不仅现代社会的底线伦理乃至我们整个生活都需要这种道德情感‘垫底’”[9]。而在卢梭的观点里,“怜悯心”是可以培育的,需要加以认识并引导。“为了使孩子变成一个有感情和有恻隐之心的人”[6],他指出要让他们知道有一些跟他相同的人也遭受到他曾经遭受过的痛苦,也感受到他曾经感受过的悲哀。从而使这种对同伴的同情与关怀“愈来愈扩充的力量用之于那些能扩大他的胸襟,能使他关心别人,能使他处处忘掉他自己的事物”[6]。不仅如此,卢梭认为人们单单从“怜悯心”就足以衍生扩展出人类的一切道德情感,诸如“慷慨”、“宽容”、“仁义”等等。怜悯心的情感使人们不会因为关注自己的生活状况而对他人的处境麻木不仁,不会为了个人私利而罔顾大众的利益和苦难,它将促使我们与他人的苦痛感同身受,这种“共情”不但是社会道德认同感的根源,也是评价人们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性的重要因素。霍夫曼在《移情与道德发展——关爱和公正的内涵》中就这么论证道:“移情的发展阶段与个体道德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移情是情绪社会化的基础,因而也是道德发展的基础”[10]。
(三)升华:“良心”
如果说“自爱”首先指向的是个体的生命,“怜悯心”扩充的是自己对他人的相对情感,那么“良心”规范的则是己与他人的关系。
在卢梭看来,良心为一种人之共有的道德情感,它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禀赋,是人类的一种先天的内在情感,而这也与良心的客观普遍性特征相互吻合[11]。《爱弥儿》中有这么一段论述:“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生来就有一种正义和道德的原则;尽管我们有自己的准则,但我们在判断我们和他人的行为是好或是坏的时候,都要以这个原则为依据,所以我把这个原则称为良心”[6]。简而言之,良心是一种辨别道德善恶的能力。它是基于道德认知、意志等因素统合而成的,表现为践行一定道德义务时的责任感及对现象与行为的评价能力。曾有学者对良心先验的观点加以批判。而实际上,卢梭所谓的良心是一种自然的潜能,就如同种子一般,它的生长需要阳光、土壤和雨露。他这么引证到“我就试想指出从心灵的最初的活动中是怎样产生良心的真正呼声的”,可见,良心的“产生”就如同他对自然教育的深刻理解,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如前所述,“自爱”和“怜悯心”是道德情感中即为关键的环节,那么,“良心”的作用又体现在何处呢?诚然,道德的社会属性必定将一些特定的要求与规范传递并附加给我们,而我们的道德情感在筛选和处理这些道德原则、要求的同时,也为这些外在赋予更为强大的内驱力。而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情感绝不仅仅是指向自我的“自爱”和针对他人苦难所产生的怜悯情感那么简单,对行为或现象的道德价值判断乃至道德行为的形成,始终需要一个指挥棒的角色,而这就是“良心”。可以说,良心是更为深层、理性化的道德情感,它所体现出对道德价值准则的自觉把握和责任感是人们道德发展由他律上升至自律的重要标志。可以说,道德良心对行为的控制是人的道德综合水平的显现[8]。
(四)终点:“道德”
“只要把自爱之心扩大到爱别人,我们就可以把自爱变为美德,这种美德,在任何一个人的心中都是可以找到它的根柢的”[6]。至此,卢梭将道德情感的故事主线呈现在我们面前。正如他所说的“人所应该研究的,是他同周围的关系”[6]。而道德,究其实质,就是一种关系范畴。
在呈现“自爱”、“怜悯心”、“良心”这一系列情感层次和次序之后,卢梭声称“我们终于进入了道德的境界”[6]。在他的道德体系中,“自爱”、“怜悯心”以及“良心”这一系列情感线索是原始情感的循序发展,指向的不是纯粹道德的概念,而是经由理智启发最终形成的关于“善”与“恶”的道德观念。他这么说道:“由自爱而产生的对他人的爱,是人类正义和本原。《福音书》中所包括的全部道德,归纳起来就是这一条法则”[6]。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从一定程度来讲,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它更多地被用于规范特定社会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的场合,道德行为更近似于个体所选择并采取的某些具有道德意义的亲社会行为,而这类行为恰恰是特定社会或族群所认可并推崇的。从卢梭个人所赞誉的“自爱”到普罗大众均推崇的“怜悯”和“良心”,这条道德情感线索的实质就在于“自爱”到“仁爱”的转换。从个人的自我保存情感到形塑社会形态与合理秩序的移情性情感,“自爱”开始借由“怜悯心”与“良心”这种相对的社会性情感,实行个体对他人“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体贴着想,进而完成亲社会行为。而这种内在的力量,究其实质,是个体主动建构的道德观念和判断,是内化了的道德动机,帮助个体诱发并生成真正的道德行为。
三 卢梭道德情感线索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许多道德理论研究与实践都说明,道德认知不一定导致道德行为,从道德认知到道德行为,其中介是以道德情感为核心的意向系统[12]。卢梭关于道德情感的内部机理和线索,无疑为我们把握这种动力系统提供了更为细节、详尽的参考,也为我们的德育实践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
(一)理清道德教育的根基,关注个体生命与道德情感
道德来源于生命,来源于人的自爱,关注生命是道德理想真正意义之所在。道德教育不是一种外在强加的规训,而是指导生命获得意义的过程。反观现今的德育实践,始终固着于“灌输式”、“知识授受”的形式,试图以抽象的道德说教向个体传递种种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显然,通过这种外烁的过程,学生固然学习到了系统的道德理论,却无法真正形成对道德价值的内在认同和情感共鸣。最终,他们学习到的只是脱离他们主体价值的“教条”,而不是那些能够震撼他们心灵的道德情感和真实体验,难以激发践行道德行为的意愿和动机。而这也正是现今道德教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低下的根源所在。而要厘清道德教育的根源问题,就要首先明确一个基本性前提,即道德教育的根基。
作为一种自然存在,个体生命的价值不言自明。道德所起到的框定社会秩序、规范行为的功能不可能脱离人的生命存在。无论特定的条件、对象等因素如何变迁,道德的本质属性依旧是为人类服务。而道德教育作为一种道德传递和授受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它所面向的主体依旧是人。因而,道德教育必须扎根于个体生命,首先立足于“自爱”这一原始情感,在关照个体生命价值的前提下予以展开。以往的道德教育常常在处理“他人与我”的关系问题上会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人我不对称的境地。一味地提倡抑制自我而将集体或他人的利益置于一个绝对优先的位置,倡导牺牲个人的自我价值以获取外在的“道德楷模”之类的赞许的称谓。在这种观念里,道德的最高境界是集体的,是忽视个体珍贵的生命价值的。而事实却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爱人与爱己,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更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排斥关系。更多的时候,只有个体生命被给予恰当的尊重,个人对道德才能真心实意地迸发出强烈的热情和积极践行的内驱力。尽管道德情感具备“非理性”、“激情”的成分一直以来备受理性主义的诟病,但它在道德价值判断和选择过程中却体现出内在动力的独特价值,为道德主体搭建情感共鸣的桥梁。
因而,真正的道德教育必须立足于这两大根基,关注道德主体自身的生命价值,激发个体积极的道德情感体验。一方面,要从观念上实现无主体、无生命的道德教育模式向主体性道德教育模式的转变,寓生命教育于道德教育,关注道德主体的价值,既要关注道德所要求的社会效益和集体利益,又要重视个体生命的深刻意义。另一方面,道德教育要重视道德情感在个体道德发展过程中的内驱作用,变革过去只重道德认知或道德规范的错误偏向。无论是何种教育场景,道德教育都不应忘却“人”的独特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让道德迸发出生命和情感的活力,也只有这样,道德教育才能实现从乌托邦式的空想向高效可行的德育范式的转变。
(二)创设“真”的道德情境,唤醒主体的道德情感
任何道德情感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与发展起来的。情感培育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情境而产生,情境是整个道德情感培育中的重要而有意义的组成部分。现今常被指责与诟病的“填鸭式”、“灌输式”的道德教育形态很大程度就源自于对道德情境的忽略。由教师、家长、社会舆论等外部因素所强加的条条框框由于缺乏相应的情境,往往难以引起道德主体积极的情绪体验。在不同的道德教育场域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么一种矛盾,那就是教育者精心安排的教育情境大部分是虚拟情境,而那些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生活情境却被排除在外。更多的时候,教育者更倾向于选择一些“高大全”的道德情境,以尽可能拔高道德水平。然而,在真正的实施过程中却发现,这一类虚拟情境却是脱离一般人的现实生活,而过高的道德要求也是难以企及的。可以说,这样的虚拟情境对道德情感的生成的效果非常有限。它们是不真实的。无论这种虚拟情境有多么逼真、生动形象,但对学习者来说,至多是一种“旁观者情境”,与他们的实际生活始终存在一定的距离,他们的道德情感实际是“不在场”的。因此,我们应尽可能地创设“真”的情境。所谓“真”的道德情境即贴近实际、真实、自然的情境,而不是“戏剧化”或“假想”的情境。因此,教育者在实施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重视道德情境的重要价值,寓情于景,以景育情,唤醒主体的道德情感。创设道德情境,必须把握它的基本属性,避免将一些过度理想化的“榜样”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可以从生活中常见且具体微小的一些生活场景入手,从涵养最基本的道德情感开始。“同情心的萎缩、义务感的匮乏与道德良知的遮蔽是造成德性发育不良和普遍性社会道德问题的直接原因”[13]。要想改变当前德育的面貌,必须重塑对他人处境和生命的关切。那么,道德情境的创设必须立足于现实的道德情境,把怜悯心及道德良知的培育作为重要的目标加以追求,把握道德情感的动态特征,通过教育过程的逐步深化和教育者的正向引导,激发学习者的道德情感,并鼓励将这类情感积极表达出来。只有这样,学习者才能实现由原本“旁观者”与“局外人”向“当事人”身份的转变,也只有这样,学习者才能真正融入并参与到情境互动中,沟通与其他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联系,达成道德情感的共鸣,并最终把“共情”投射到当前或者类似的道德情境中,做出符合社会期待且受个人主观情感认同的道德行为。
(三)提供道德实践的契机,实现道德品行的养成
荀子有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我们强调道德情感的动态生成过程的同时,必须关注由道德情感向道德品行的转换路径。而最行之有效的就是道德实践。现实的道德关系和问题,不是书本上、故事中那些至善至美的道德理想,诸多矛盾与冲突始终有待解决。而用脱离实践的眼光和理想化的标准去看待道德实践,无疑会面临满腔的热情与现实不匹配的困惑与无奈。作为个人道德行为中表现出的稳定的、一贯的特点和倾向,道德品行必须依靠持续不断的道德实践加以塑造,在解决真实的道德冲突的过程中实现道德水平的逐步提高。脱离道德实践侃侃而谈个人的道德情感如何丰沛、道德境界如何之高,是不现实的。诚如我们之前论证道德情感的重要性、层次及培育方式,但归根究底,道德品行的养成才是根本目的。道德情感的培育最终要为个体道德品行的养成服务,指向个体道德综合素质的提升。因此,道德教育要始终立足于实践,将实践作为贯穿道德教育的重要环节。一方面,要特别关注道德实践在德育各个阶段中的渗透。德育的各个阶段有不同的发展任务,任务的达成必须有相匹配的实践环节以满足道德发展的生成条件。因此,道德实践的开展必须结合德育的阶段性任务及道德情感发展的内在层次,在恰当的时机提供必要的道德实践的机会以强化主体的道德行为。另一方面,要开发道德实践的多样化形式。“1+1=2”是再简单不过的数学公式,而一个道德实践的形式加上另一个道德实践的形式却能焕发出“1+1>2”的夺目光彩。形式多样的道德实践不仅能够为主体带来丰富的情感表达,更能提供更多践行道德的场合和机会。因此,道德实践活动应基于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重点发掘慈善公益活动、社区服务、志愿者活动等社会实践活动的德育价值,让个体在参与中实现由道德情感转向对道德品行的执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