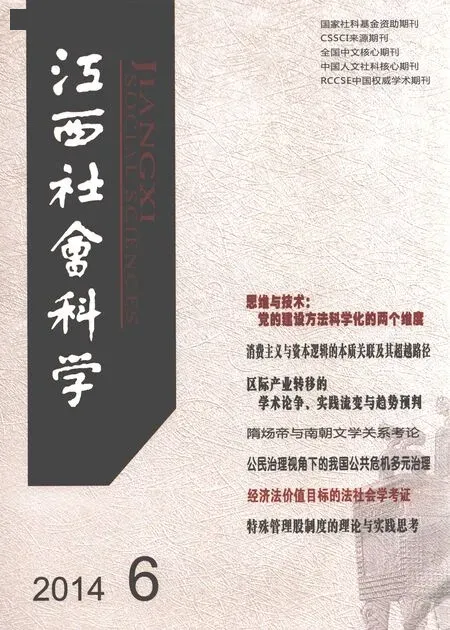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的抗争与纯情——兼论《上海沦陷区女作家服饰书写研究》
2014-04-15姜山秀
■姜山秀
一
据《上海通史》统计,上海开埠时外国人在上海登记的只有26人,到1942年,骤增至150000人[1](P2)。人口密集,经济繁荣,文学也随之走强。抗日战争前,社会名流云集上海,作家也从全国各地汇集于上海,上海成了新文化中心。这一时期,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浅草社”、“南国社”、“弥洒社”等文学社团凝聚了数百文学大家,如胡适、徐志摩、萧红、萧军、沙汀、艾芜、冯乃超、茅盾、郭沫若、巴金、叶圣陶、戴望舒、夏衍、柔石、冯雪峰等。这期间的文学创作,体裁丰富,形式多样,创作手法灵活。此时,文学期刊也大放异彩,为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曾在20世纪30年代做过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主持《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编撰工作的赵家璧曾经说过:“现代文学史就是通过现代文学期刊,展现了它最原始、最真实、最生动的面貌的。文学理论上的斗争场面,文艺流派的形成过程,作家由默默无闻而名扬四海,作品由最初在期刊上初露头角逐渐成为传世名作。”[2](P12)当时上海的出版业也非常繁荣,统计资料显示,“1927—1936年全国出版新书共42718种,其中规模较大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三家上海的出版机构就出了27864种,占总数的65.2%,在此,商务印书馆一家就独占48%”[3](P588)。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3个月后,上海成为“孤岛”,1941年,上海租界被日军进攻,上海全面沦陷。沦陷后,上海作家们异常艰难:一是作品大量被查被禁;二是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三是社团、出版机构大量被取缔;四是日伪加大了对被迫留沪作家的拉拢,作家们为了生存面临麻烦的抉择。郑振铎说:“把那些敌人们当作‘有理性’的‘人’看待,结果却发现他们原来是一群兽。”[4](P150)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作家被迫放弃了写作,如赵景深则抱定了“三不主义”,即“一不写稿,二不演讲,三不教书”[5](P365)。一些继续写作的作家,生存状况也不是很好,诚如谭正璧自己所说,为了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除了教书,就只有写文章”。[6](P1-6)苏青说:“投稿的目的纯粹为了需要钱。”[7](P86)沦陷区文学因为日伪的严格查禁不得不转向日常的生活叙事,张爱玲、苏青、施济美等女性作家异军突起,扛起了沦陷区文学的大旗,充分表现了女性的观察与思考。
这一时期,活跃于上海文坛的还有上百人[8](P91-96),可是在文学史留下姓名的却极其稀少,大部分背负了汉奸的罪名,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曾轰动过整个上海滩的知名作家张爱玲,也仅是近些年才在文学史上重新被提及。而事实上,上海沦陷区作家的斗争一直在持续。郑振铎在抗战胜利后追记道:“我们忍受着人类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我们吞声饮泣地睁眼看着狼虎的择肥而啮,狐兔的横行,群鬼的跳梁;我们被密密的网罗覆罩着;我们的朋友里,有的杀身成仁,为常山舌,为文氏头,以热血写了不朽的可泣可歌的故事;有的被捕受刑,历尽了非人道的酷暴的待遇,幸而未死,然已疮疾满身,永生不愈。”[4](P101)
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紧迫的情况下,这些女作家们写出的也不是“亲日”、“共荣”、“归顺”、“附逆”,相反,“笔下所写出的,都以‘博爱’、‘牺牲’等等为中心思想,然后由这个中心思想创造一个美丽、曲折、动人的,然而完全是超现实的理想的故事”。所作故事“不讲技巧,而自然平稳,故事不求夸张,而逼真切实,在平淡中见深刻,在朴素中寓美丽,没有刺激的力”。[6](P1-6)作品“切近现实俗态人生,但是又坚持自我理想追求和道德诉求”[9](P46)。即使是那些被日伪拉进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文人,创作内容也并没有明显“日化”或“伪化”,没有出现明显的政治化“迎合”,以至于日本代表骂他们:“真是坏透了!”[10](P221)
二
自“五四”以来,女性大胆挣脱旧时代束缚,在解放自己的道路上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与抗争。这些新时代的女性,扔掉缠足,摆脱女红,走进学堂,全力挣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进行“自由恋爱”,实现各种形式的逃婚,或直接同居。但据雷家琼的考察,女性逃婚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原谅与支持,也没有得到法律的实际支持,逃婚女性与其家人往往陷入了非常悲惨的境地,或者恋人遭到打击或判刑,或者父母被逼入自杀境地,或者自己的亲戚如妹子或表妹被强行抢去抵婚,或者自己走向艰难的人生绝境。[11](P101-107)女作家谢冰莹连续逃婚4次,前几次都没能成功,在第4次逃婚成功后,虽然登报得以解除婚约,但生活的窘迫到了极限,工作得而复失,没有了工作,饥寒交迫,境况极差。据谢冰莹的《女兵自传》讲述,她的一双布鞋居然穿到了“空前绝后”地步,“袜子虽有两双在换洗,也已补上加补,烂得简直不像话;遇着雨雪天,老是一双湿脚回来,等到第二天仍然是一双湿脚跑出去”,更为严重的是,膳食一减再减,最后有4天已无饭可吃了。[12](P177-178)
这些女性,有勇气走出旧生活的阴影,可无力对抗男权社会的经济封锁,许多在抗争中重新依附男性。婚姻生活、道德理念与人格体系在冲出旧生活时,又回到了新的生存抗争,生命被迫进行新的妥协与扭曲。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上海沦陷区的女作家们感知到了,她们的创作中明确揭示了这一可恶的现实,以引起对女性无法独立生存问题的急切思考。
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寻,对妇女解放思想进行反映,女性最多打出的口号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无疑是有勇气、有思想的宣言,但女性很少能够建立起女性自给自足的世界,社会没女性的立足资本,女性没有自己的“一间屋子”,真正身心的独立与女性的完全解放是很难完成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都市女性命运的沉浮与走向,女人的命运浓缩了那个时代都市中涌现出的一股对人性拥有强大的改造功能的力量,这就是物质利益与金钱,在其引诱、侵蚀下,现代女性的人性正在扭曲、异化。这也说明,妇女运动并没有使女性从根本意义上摆脱困境。[13](P138-148)
三
即使是生存状况不佳,但作家的纯情与作品世界的纯真却是不鲜见的。我们可以从张憬、周炼霞、曾文强、吴克勤等为代表的《万象》月刊女作家队伍,汪丽玲等为代表的《大众》女作家队伍,还有施济美、程育真、汤雪华、杨琇珍、俞昭明、邢禾丽为代表的“东吴系女作家”队伍,以及施济美、练元秀、张爱玲、苏青等人的作品中窥见一斑。张爱玲的《传奇》、《倾城之恋》、《半生缘》、《金锁记》,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歧途佳人》,施济美的《凤仪园》、《鬼月》、《小三的惆怅》、《十二金钗》,俞昭明的《小茉莉》、《落花流水》、《梅家酒店》、《黑芍药》,汤雪华的《郭老太爷的烦闷》、《烦恼丝》、《死灰》、《墙门里的一天》、《红烧猪头和小蹄膀》、《亚当的子孙》,郑家瑷的《逝去的晴天》、《她和她的学生们》、《霏微园的来宾》、《阴暗之窗》,练元秀的《紫》、《决斗》、《神秘的王先生——我的二舅》、《情盲》、《奇遇》,邢禾丽的《歧途》、《睡莲》、《空课》、《瞑目》、《上帝的信徒》,杨依芙的《蓝色的多瑙河》、《圣保罗教堂的晨钟》、《灯塔》和《庐山之雾》、《玫瑰念珠》、《西泠桥畔的黄昏》、《怀念曲》、《梦痕》等,在对于知识女性面对爱情、婚姻、事业和自我独立所面临的困境问题的看法,她们的创作都有了新发现,实现了一种似乎与战争无关的纯情。[13](P48-118)
以施济美为例。1937年,施济美与中学好友俞昭明和其弟弟俞允明同时考入东吴大学。在大学,她和俞允明相恋。可是不久,俞允明改入武汉大学,学校迁到四川乐山后,两人分隔两地。两年后,饱受异地恋相思之苦的施济美收到了俞允明不幸在日机轰炸中遇难的消息。这令施济美万分悲恸,在自己振作起来后,为了安慰俞允明家中年迈的父母,一直模仿恋人的笔迹写家信给两位老人,此后她终身未嫁。
这些作家自身如此纯情,在沦陷区的上海,这一特殊时期里面,在作家的作品中,也有许多纯真的故事。练元秀的《紫》中,小说写维德刚新婚满一年,一天,意外收到大学同学李可扬的消息,二人相约在一间旅社里见面。在旅社里,李可扬向维德讲述了自己这几年和一个神秘的“紫衣女郎”的情感纠葛。紫衣女郎叫杨海兰。李可扬和杨海兰偶遇在杭州公车上,杨海兰“窈窕的紫影”在李可扬的脑海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被这身“紫”所吸引。这里的紫色是女性美的化身,是男性眼中的“美”。于是他想尽办法接近杨海兰,可是,刚交往不久,她不辞而别。这让李可扬整天满怀着“紫色的惆怅”。他每天都在寻找着这个紫色,几经波折,他终于又找到这位神秘紫衣女郎。她也为他重新穿起紫色的衣裳,戴着紫色的花。但最后,她又一次选择离开,因为她早已经有了心上人,为了和心上人相聚,只能抛弃李可扬,留下了那朵惆怅的紫花。
施济美的《凤仪园》中,新婚燕尔的冯太太为了让丈夫去经受暴雨狂风的袭击,接受苦难对人生的磨炼,她坚持让丈夫远行到海上去。可是丈夫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这一次海浪太大,丈夫葬身在海底,一个美好的开始陡然落幕,一次人生的锻炼成了终生的悲剧。此后,冯太太带着两个遗腹子,孀居了十三年,在慢慢长夜中等待了十三年。终于她实在熬不住了,就为女儿们请了一位男教师,以前她总是为女儿请女教师而拒绝男性。男教师叫康平,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工科大学生。年轻的康平来到凤仪园,最吸引他的,是第一夜就听见窗外凄婉、哀怨的杜鹃声,周身感到一种冰冷的悲凉,于是他起身来到园中散步,此时发现冯太太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光。涉世不深的他迷恋上了凤仪园中的颓败神秘气息,更被凤仪园女主人的风华绝代的气质和美丽的外貌所征服,不顾年龄的差距和世俗的眼光而坚决向冯太太求爱。此时的冯太太也渴望有一个能爱自己的异性,对于康平的求爱,她欣喜。可是当康平把她变成另一个妇人时,她突然觉得这是对死去丈夫的背叛,对原来自我的背叛,所以,这一次过后,她断然拒绝了康平,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拒绝再背离旧我,背离以前。
小说《鬼月》中,生活在乡村的海棠是个普通的姑娘,她没有受过任何一种系统的新式教育,继母要将少女海棠嫁给比自己父亲年龄还要大的宋老头儿,但海棠与孤儿长林两情相悦。最后两人决定在约定的日子私奔,可是到了那天,长林却失约了。长林的软弱让海棠陷入绝望。在中元节的夜晚,她硬逼着长林和自己一起“举身赴清池”,希望两人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长相厮守,于是,她将长林推入河中,自己也跟着跳河自尽。
时代在经历炮火纷飞,人随时都有化成烟云的可能,在刺耳的枪炮声中,沦陷区的文学却在远离炮火的纯情世界中,没有硝烟,没有征服,没有人生的仇恨,没有刀光剑影,只有男女主人公的心灵在交会,这些爱,不夹杂世俗的尔虞我诈,也没有金钱地位权势的攻守交易,只有心灵的牵挂,只有情的真纯。难怪有学者认为:“1937年至1945年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现代文学是产生在沦陷区的作品。”[14](P519)
四
翟兴娥注意到了这一纯真的世界,《上海沦陷区女作家服饰书写研究》中有较大的篇幅对这一独特的心灵审美、心灵情结、服饰情感进行了较好的分析。
透过服饰分析作家作品,分析时代,分析人物,分析生存状态与作家心理,是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中国古代有此运用,特别是在创作中运用比较普遍,在理论上,也有零星的论述。数十年来,前贤的研究大都停留在简单的服饰图案、颜色、材质、结构、民族、风俗、符号等的比较上。翟兴娥结合现代美学、社会学、心理学、创作理论、文学进行系统研究一个断代文学碎片,实现跨学科断代边缘探讨,在这个方面走得比较深入。
翟兴娥以上海沦陷区女作家服饰为研究对象,探索这一时期女作家对服饰的独特书写,完成一系列人物服饰的研究,论述在不同的群体中,服饰在其文本中的蕴涵,揭示其文化心理动因。通过对“东吴系女作家”群和张爱玲、苏青等文学作品中的服饰进行研究,分析“东吴女作家”群通过服饰书写表现出的感伤叙事,揭示服饰隐喻中的上海女性,谋生亦谋爱、金钱异化、精神迷失以及还有一部分人对爱情、家园、理想的坚定守候。通过对张爱玲服饰书写表现出的唯美叙事,以及苏青服饰书写中表现日常叙事来探讨女性生存困境,寻找到在深厚的服饰情结背后隐藏的女性内心世界以及集体生存状态。这是对以前服饰研究成果的一次大胆突破与深入,也是一次透过表面直达心灵的学术研究。
[1]高福进.“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应国靖.现代文学期刊漫话[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3]陈伯海.上海文化通史(上卷)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4]郑振铎.西谛三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5]赵景深.抗战八年间的上海文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6]谭正璧.当代女作家小说选·叙言[M].上海:上海太平书局,1944.
[7]苏青.饮食男女——苏青散文[C].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
[8]翟兴娥.近代市民小说的价值取向问题探讨——兼论上海沦陷区文学主体创作[J].江西社会科学,2013,(4).
[9]张曦.古典的余韵:“东吴系”女作家[J].书屋,2002,(9).
[10](日)泽地久枝.日中友好的桥梁[J].文艺春秋,1981,(5).
[11]雷家琼.艰难的抗争:五四后十年间逃婚女性的存在困境[J].社会科学战线,2011,(12).
[12]谢冰莹.女兵自传[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13]翟兴娥.上海沦陷区女作家服饰书写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4]徐錣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