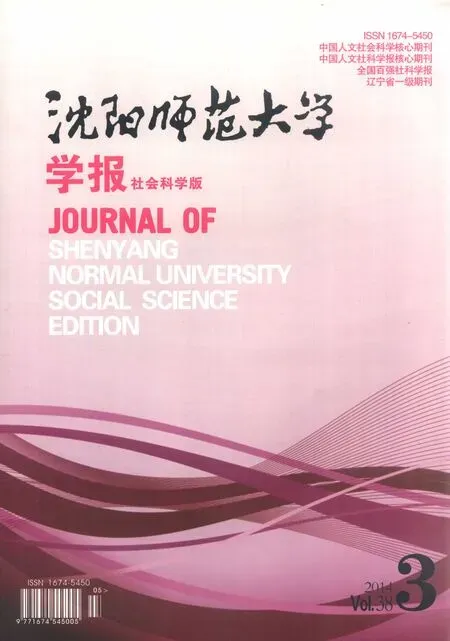明代科试经义文失范及其政治原因
2014-04-10刘建明
刘建明
(浙江省旅游发展研究中心 社科部,浙江 杭州 311231)
朱明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守住已有战果,十分注重对臣民的思想控制,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主要途径就是设科取士,制定经义文书写规范,要求士子作文须做到:理宗程朱、辞尚简洁。
一
到了天顺朝前后,士子作文偏离了朝廷设定的轨道,官方把文风上的这一转变称为“奇诡”之风,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考官出题割裂经旨
经义文割裂经旨的出题形式在天顺朝就已经出现了。天顺三年(1459),温州府永嘉县教谕雍懋上疏:“考官出题多摘裂牵缀,……浙江乡试春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题,头绪太多……且《春秋》为经,属词比事变例无穷,考官出题往往弃经任传,甚至参以己意。”[(1]卷七十一)对于这种出题方式导致的后果,明人丘 感言:
近年以来,典文者设心欲窘举子,以所不知,用显己能。其初场出经书题,往往深求隐僻,强裁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以此初场题目数倍于前,学者竭精神,穷日月有所不能给,故于策场所谓古今制度、前代治迹、当世要务,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前后、字书偏旁者,可叹也已!提学宪臣为小试,其所至出题,尤为琐碎,用是经书题目烦多,学者资禀有限,工夫不能偏及,此策学所以几废,而科举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2]。
偏题、怪题耗费了士子大量的精力,不仅严重背离了朝廷向士子灌输儒家义理的初衷,还极大限制了士子接受较多知识的可能。
(二)士子答题援用佛、道
至晚在嘉靖初期,士子的经义文出现了援用佛、道的创作倾向。嘉靖六年(1527),朝廷曾申斥过:“科场文字,务要平实典雅,不许浮华险怪,以坏文体”。[3]对于明代后期经义文援引佛、道之风,冯琦说:“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朱、程,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以实为空,以空为实……取佛书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窜入于圣言,取圣经有‘空’字、‘无’字者强同于禅教。”[4]一部《四书集注》考了数百年,考生对其中的内容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每科考试的题目基本相同,每个考生答题的内容又基本相似,答卷实在是没有什么新意,令人厌烦。考生将佛、道的义理言词掺用到其中,势必会给文章的内容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让考官耳目一新。
(三)士子试卷文辞繁冗
嘉靖中期之前,经义文虽也有超过书文200字以上、经文300以上的字限,如王守仁以“志士仁人”为题的作文就有651字之多[5],但类似这样的长篇巨制只是个别现象,而到了嘉靖中期之后,长篇巨制成为主流,杨廷枢就此说:“嘉靖初载,文格简练,亦间有长篇,中、晚则长篇多而简练者间出矣!”[6]
为此,朝廷不得不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从政策上对经义文字限做出调整。此一议案最早由耿定向提起,他在《申饬科场事宜以重选举以降圣化疏》中是这样说的:
国初科场所取,初场经义多不过三百余字,故士得有余力以及于二三场,当时不独人有实学、世有真才,而为主司者,亦有据凭得以悉观其蕴。即嘉靖初年,曾申限字之法,一时文体尚有可观。近日场中所取多至千余字者,即少亦不下七八百字, 窃支蔓,音义无当。士方毕一生之精力以从事于无用之虚文,又何暇博习古今,晓练世务,以待国家异日之用也哉!此其为弊义浅鲜矣。近奉该部题准通行,考官阅卷,必文理纯正简实方准中式,盖鉴于此。然窃谓须是严定限字之法,明示中外,使士人晓然知有章程而后可。臣又惟先年限字之制,经义止是二三百字,今积习已久,欲其卒改,一时难行,合无限定五百字,渐令复古,但过此一字,即为违式,不□誊红,如更能简洁者,尤当甑录。其论策亦量为程限,毋令浮冗,如此行之,逾时可使士习崇雅黜浮,不至虚费精力,而主司亦不至为浮靡之习所眩瞀矣[7]。
耿氏的提议很快得到了允准[8]。(1582)事实上,此后的士子并没有真正恪守朝廷调整后的500字限,否则当时的君臣就不会有这样的言说了:“明初科举,诏令举子经义无过三百字,不得浮词异说,……百余年后,文渐冗长,凡千百余言,庸陋支离,无恶不备。”[9]
二
导致科试经义文风气转变的因素很多,仅政治层面上的原因主要有四个:
(一)朝廷放松对佛、道的管制
就总体而言,明代朝廷对佛、道的管理采取的是两手政策,一手是抑制其发展,不使其发展失控;另一手是给予一定程度的扶植,积极利用其治世功能,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两手的力度不同罢了。相比较而言,洪武至宣德期间,朝廷限制的力度要明显大于扶植的力度,而到了明正统之后,情况正好颠倒了过来,朝廷扶植的力度要远远大于抑制的力度,以至佛、道规模的发展几乎失控,尤其是明英宗[10]5371、代宗、武宗、世宗[10]3516时期,朝廷每次度牒都在万人以上。大量的佛、道教徒“或居寺观,或寓人家,动以万计。”[11]6458-6459
佛、道教徒游居民间的行为,极大地促进了佛、道义理向士人阶层的渗透。此时,很多文人士大夫对佛、道义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谢肇 《五杂俎》载“: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夤舍,唪诵咒呗嚣于炫欢,上自王公贵人,下自妇人女子,每谈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者。”[12]1653
文人对佛、道义理的接受,直接促进了明代后期多元思想的融合,很多考官的思想中佛、道印迹十分明显,其中包括:担任万历五年(1577)和万历八年(1580)两科会试主考的申时行、万历八年(1580)和万历十一年(1583)会试主考的余有丁、担任万历十一年(1583)房考的冯梦祯、万历十一年(1583)和万历十七年(1589)会试主考的许国、万历十四年(1586)会试主考的王锡爵、万历三十一年(1603)应天乡试考官的陶望龄、万历三十二年(1604)会试主考的唐文献、以及万历四十一年(1613)会试主考的叶向高,等等。在这种多元思想杂糅的境况之下,士人已经很难对程朱与程朱之外的其它学说确切区分了。他们的思想往往兼蓄多个学派,已经难分彼此,这种思想状态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经义文写作。
(二)考官对经义文审美形式的提倡
明代后期的很多考官十分关注经义文的写作技巧。冯梦桢指导李君实作经义文时,让他研习名家程文格律[13],清楚地透露了文辞格律是这位考官选士的一个重要标准。事实上,在这些考官当中,很多人本身就是经义文理论家。担任过江西乡试考官的董其昌,作有《文诀九则》,总结出了经义文创作的九条原则。陶望龄为万历三十一年(1593)应天乡试的考官,同样十分注重经义文的创作技巧,他在《阳辛会稿序》中说:
今之为经义者有三病:有善绘眉目口鼻而不知位置者,加目于眉,进口于鼻,故虽善而不似人;有善绘知位置而未肖者,似人矣而非所貌;又有 眉口鼻修短美恶一如所貌,而形合神离、色符意槁者。此三者皆工文者之通患也。求之于今,眉与目争序、口与鼻竞长者多,况其它乎?[14]
陶氏的这段话涉及了经义文结构的安排、语言的运用、以及形神关系等三个层面,应该说对经义文的批评是比较系统的。似乎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考官对经义文章法技巧、艺术形式的重视,直接导致了明代经义文分股论说体式的形成。
科举考试的取士权掌握在考官手中,考官这种重视经义文写作技巧,对经义文审美文风的提倡,直接反映到他们的取士行为。史载,在景泰二年(1451)的会试中,考官专以文辞取士,“江北之人文词质实,江南之人文词浮赡,故中第者南人恒多,北人恒少”[8]。(1555)考官的这种行为会对士子作为产生直接引导,士子们为迎合考官需求,一味地追求经义文在形式上的创新,从而使得这一文体在形式上开始变得日趋繁冗了起来。
(三)考官好异说取士行为的引导
考生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了登科及第,往往是“躁于趋进,亦投时好,竞出新奇。”[15]江以达为嘉靖五年(1526)进士,作文喜欢“险语”,主试福建时,刘汝楠即“以险语迎合得置首解。”[16]嘉靖十八年(1539),礼部的一份奏疏首次言及过这样的风气:“今试录所刻之文,士子视以为向趋,彼见诡异不经之文尚在所录,必曰主师所崇尚如此,有不靡然仿效之乎?如是虽日谆谆然戒之无益也。”[1](卷七十)王锡爵也说:“士之字雕句缋,剽猎诸子二氏之唾余,见谓弗收,至主司自为辞,非诸子二氏无取也,籍具在此,可谓不欺否?”[17]朝廷政策规定是一回事,考官取士的标准又是一回事,可以说,考官的喜好对科试经义文之走向产生的导向作用是极为直接的。何良俊就此说:“朝廷求士之心,其切如此,而有司取士之术,其乖如彼,余恐由今之日以尽今之世,但用此辈布列有位,而欲致隆古之治,是犹以鸩毒愈疾,日就羸惫,必至于不可救药而后已耳。”[18]22
(四)朝廷政令无法执行
为有效扭转科试经义文偏离政策规定的风气,朝廷频繁发布政令,申明经义文写作规范,从天顺三年(1459)开始,一直到崇祯朝灭亡,申明的总次数至少有32次之多,时间密度也呈递增之势。此外,朝廷还制定了一些其他整治经义文风气的措施:
首先,以惩处的方式来儆示天下。科考士子是经义文的写作者,他们首当其冲会成为朝廷主要的惩治对象。有明一代,朝廷制定处治违反经义文规范的考生的政策始于嘉靖初期,处治方式最初只有两种:一种是取消考生当年科考的及第资格,另一种是由主司奏明朝廷另行处治,如杖责等。违禁士子最终会遭遇何种命运,要视他们的经义文违反朝廷规范的程度而定。嘉靖十一年(1532),世宗下旨:“近来士子经义诡异艰深,大坏文体,诚为害治,其出榜晓谕。今年会试文卷必纯正典雅、明白通鬯者方得中式,若有仍前钩棘诡僻,痛加黜落,甚则令主考官奏闻处治。”[1](卷六)嘉靖中期,朝廷加重了对违禁士子的惩治力度,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处治方式,即对于违禁情节严重的考生,朝廷将予以除名,永远不许再试。嘉靖十七年(1538),世宗诏令规定:考生作文“驾虚翼伪、钩棘轧茁”,一律黜落,而对于那些违规情形严重的考生,要“奏请除名,不许再试!”[1](卷二十三)此后,这三种方式并行使用,成为了明廷处治违禁士子的主要手段。考生做了违反规定的经义文要遭受惩处,考官命题违反规定、及选录了答卷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考生同样要遭受惩处。就惩治考官的具体形式而言,主要有下狱、罢官、降职和罚俸四种。
其次,实行提学负责制。明代后期,朝廷还制定了针对提学官的处治措施,提学官遭受惩处的原因在于他们没能扭转辖区士习,没能起到整治文风的作用,最早将提学官列入处治对象的时间是在万历十六年(1588)。在这一年,万历皇帝下旨:“若文体违式,系提学官造士不端,宜从重参治。”[1](卷四十九)提学官在考满后,是否能够得到升迁,要视他们个人的工作业绩而定。
再次,颁行程文令士子模范。为了使科考士子能够恪守经义文标准,在每次乡试、会试之后,朝廷都会让考官从中式的试卷中选出符合政策规定的试卷,结集刊刻,颁发到各地学校以示模范。有明一代,这一成式始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科的会试。[19]刊刻的内容要以士子的墨卷为准。然而,部分考官由于个人政绩的需要,往往弃士子的墨卷不用,亲自代作进呈,邀宠请赏。嘉靖四年(1525),邓显麟对考官的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说:“臣切(窃)惟乡试、会试有录本进呈上览,得信天下,近来往往假举子之名刊刻试官之作,吾谁欺、欺天乎?且使草茅之葵霍竟同鱼兔之筌蹄,名虽甄录而文已失其真矣。合无今后刊刻试录,止用举子本色文字,考官惟精白一心专事雠校,庶上无假借欺君之非,下无失实蹈伪之诮。”[20]卷下
从实际情况来看,明代后期朝廷颁发到学校的范文除了考生的墨卷外,还有考官亲自作的程文。万历十五年(1587),朝廷曾选刊历代程墨一百七十篇颁行天下学校。万历二十年(1592),还刊刻了十八房考官的程文集《钩玄录》。
值得注意的是,朝廷这种颁布程文的行为导致了两方面的不良后果:
第一,很多士子弃儒家典籍不读,通过记诵这些旧文来应付科举考试。万历二十三年(1595)会试,邹泗山的试卷为房师所赏,被“荐为榜首”,有人言其“前场七艺,尽录坊刻,自破承至结题,不易一字,坊间寻刻魁卷,亦不复改窜”[21]。万历四十四年(1616),吴道南和刘楚先主试会闱的时候,发现成绩第一名的沈同和与第六名的赵鸣阳有两篇作文内容雷同,且皆出自以往旧文[22]。
记诵旧文的风气兴起之后,士子对程、朱义理变得陌生起来。袁宏道在《陕西乡试录序》中说:“臣窃叹昔之士以学为文,而今之士以文为学也。以学为文者,言出于所解,而响传于所积,如云族而雨注,泉涌而川浩,故昔之立言难而知言易也。以文为学者,拾余唾于他人,架空言于纸上,如贫儿之贷衣,假姬之染黛,故今之立言易而知言难也。”[23]不读原典,势必不能做到贯通文义,往往还会因不通原典而误掺程、朱之外的其它学说。
由此可见,朝廷颁布程文导致士子记诵旧文风气的形成,不仅使经义文失去了衡量贤才的效用,还会因士子不通儒学、掺用异说,严重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
第二,明代后期的试录文很多并不符合朝廷标准规定,这类文章刊发后,会产生负面的导向作用,致使士子的经义文创作偏离了标准规定。夏言在《请变文体定程式简考官三事》中就此说:“近年……各处试录文理纰缪、体裁庞杂,殆不可观,以致初学之士不辨臧否,方且争效所为,至于平日善为文者亦不能守其故步,反迁就其非缪以市合一时,则文之弊也。”[24]
最后,禁止私人刊刻经义旧文。明代后期,出版业极其发达。士子记诵旧文的需求促成了书坊刊刻旧文的动机,出版业的飞速发展为书坊刊刻旧文提供了物质基础。明代后期时文的刊刻出版因此而变得极其繁墙上房翻瓦,攘夺中式姓名,人吏环视莫之敢禁,是以试录未及进呈上览,而京城家喻户晓矣!”[26]卷下
这些被刊刻售卖的旧文,大致有四类:一是程墨:“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钩玄录》即属此类;二是房稿:“十八房进士平日之作”,《艺海元珠》、《阅艺随录》皆属此类;三是行卷:“举人平日之作”;四是社稿:“诸生会课之作”。[26]
这些被刊刻的文章到底质量如何呢?沈鲤说:“照得近年以来,科场文字渐趋奇诡,而坊间所刻及各处士子之所肄习者,更益怪异不经,致误初学,转相视效”。[8]1595-1596让这类不规范的文章流布天下,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就可想而知了,正所谓文体坏导致士习坏,士习坏致使国运衰。
为了消除这种负面影响,朝廷颁布政令,禁止书坊私自刊刻印卖违制旧文。正德十年(1515)十二月,南京礼科给事中徐文溥首次上疏:“近时,时文流布四方,书肆资之以贾利,士子假此以侥幸,宜加痛革,凡场屋文字句语雷同,即系窃盗,不许誊录,其书坊刊刻,一应时文悉宜烧毁,不得鬻贩,各处提学官尤当禁革,如或私藏诵习不 者,即行黜退。”[10]2631这种规定最早是由嘉靖前期的提刑按察司副使魏校实施的:
书铺当禁之书,一曰时文,蠹坏学者心术;二曰曲本,诲人以淫;三曰佛经,四曰道经,扇惑人心。先已通行禁革,委官宜责取各铺、并地方总小甲邻佑结状,如再发卖前项书籍,重治以罪,再不许开书铺;仍大书告示,张挂关隘去处,不许从外省贩卖前项书籍私入广东境内,不时差官盘验,以诘奸弊[27]。
万历中期之后,转由中央机构正式颁布:万历二十四年(1596),礼部尚书范谦疏:“使知近习在所必禁,坊间新刻诡异主意时文,转相蹈袭,惑乱初学,有妨士习。提学官即行查核,将板劈毁,勿得传布,本部仍行吏部,凡提学官升转各以转移士习与否以为殿最,庶斯文之统纪不淆,祖宗之法纪愈肃,诸所得士必光明纯正,用以成人才、维世道,所 益不浅矣。”万历皇帝批复说:“近来文体险怪,屡经明旨申饬,全无改正,这所奏依拟着实举行。”[1]卷四十九崇祯皇帝继续推行此项政策:“房刻有文体怪诞的,各学臣即行毁板。夫房刻法非学臣所得问,尚严重如此,况似刻乎?今后尔士子不但妄刻窗稿,欺世自媒,概行禁绝!”[28]
事实上,朝廷制定的这些整治经义文文风的措施并没有被严格执行,马从聘就此说:“文体之醇漓关士风,士风之邪正关治化。迩来文体弊坏,屡廑宸纶,申斥厘正,不啻再三,而其敝乃益甚,良以禁令止属之空盛,对此,李诩不无调侃地说:“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25]在商业利益的刺激下,不仅时文刊刻的数量空前繁盛,而且传播的时效也快得惊人。邓显麟《梦虹奏议》云:“切(窃)见京闱填榜之夕,有等射利光棍公然持梃谈,革惩未见之行事,以故忽明旨而不信,玩禁例而不遵,法之不行,自上始耳。”[29]何良俊在南京时,曾经传令于督学赵方泉和福建巡按御史,让他们分别将上江和建宁等处书坊刻行的时义尽数烧除,但二人只是空言应付,并没有付诸实施[18]24。
概而言之,一项政策能否达成预期效果,关键在于执行力,而与之相关的其它抵制政策的推行,及当道官员的喜好、消极不作为等,都会成为消弭该项政策执行力的因素,致使目标与结果难以合拍。明代朝廷试图以经义文约束士人的思想,以实现朱明王朝的长安久治,然而朝廷大开度牒之门、考官随意取士及怠政行为,则销蚀着这一目的的达成。从维护朱明王朝稳定的角度来讲,是极其不利的;但从经义文的发展角度而论,则是有益的,这有利于此一文体思想的丰富和审美的多元。
[1]俞汝楫.礼部志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张翰.皇明疏议辑略[M].明嘉靖三十年大名府刻本:卷二十.
[3]申时行.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448.
[4]陈梦雷,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6:775.
[5]方苞.钦定四书文[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
[6]杨廷枢.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第十册)[M].明崇祯间书坊金阊叶氏刻本.
[7]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M].明万历二十六年刘元卿刻本:卷二.
[8]王世贞.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阮葵生.茶余客话[M].清光绪十四年铅印本:卷十六.
[10]明英宗实录[M].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1]徐学聚.国朝典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6458-6459.
[12]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3]冯梦祯.快雪堂集[M].万历四十四年黄汝亨、朱之蕃刻本:卷三十二.
[14]陶望龄.歇庵集[M].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433-434.
[15]田艺蘅.留青日札[M].明万历刻本:卷三十七.
[16]雷礼.皇明大政纪[M].明万历刻本:卷二十三.
[17]王锡爵.王文肃公全集[M].明万历刻本:卷一.
[18]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9]黄佐.翰林记[M].清同治道光间刻岭南遗书本:卷十四.
[20]邓显麟.梦虹奏议[M].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2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424.
[22]万历邸钞[M].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1982:2331.
[23]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530.
[24]夏言.桂洲先生奏议[M].明忠礼书院刻本:卷七.
[25]李诩.戒庵老人漫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2:334。
[26]梁章钜.制艺丛话[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24.
[27]魏校.庄渠遗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九.
[28]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M].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卷十七.
[29]马从聘.兰台奏疏[M].清光绪五年谦德堂刻《畿辅丛书》本:卷二.
【责任编辑 曹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