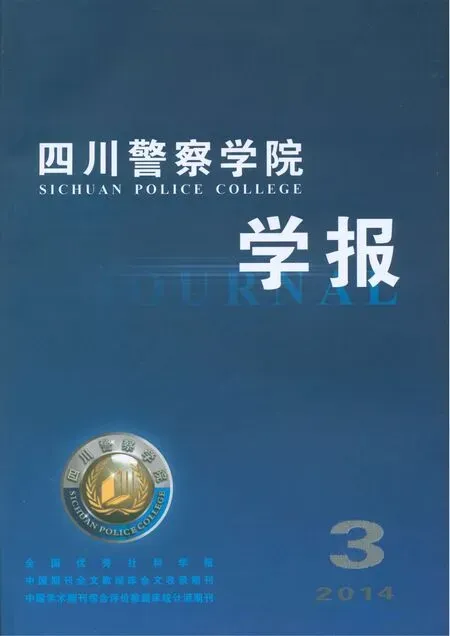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刑法防控
2014-04-09贾健,宣刚
贾 健,宣 刚
(1.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401120 2.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南京 210097)
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刑法防控
贾 健1,宣 刚2
(1.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401120 2.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南京 210097)
在当前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发生越来越频繁,涉案范围、资金和人数急剧膨胀,社会危害性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若干基础性问题应被学界所重视。但基于理想主义和克制主义的思想误区,刑法学界却并不重视对其防控的研究。刑法应该本着务实的态度,从规范认定和政策适用的角度,合理防范及化解涉众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
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认识误区;被害人认定;宽严相济政策
所谓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是指,由集资犯罪和传销犯罪所引起的,有众多人员参与并形成的,且有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的活动。应该说,在当前非法集资案发生越来越频繁,涉案范围、资金和人数急剧膨胀,社会危害性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若干基础性问题及其防控必须被认真对待。但遗憾的是,学界特别是刑法学界,却很少有人关注,这种理论与实践“冰火两重天”的研究现状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刑法又应该如何组织起对集资犯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防控?这些正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一、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特征与现状
(一)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特征。
第一,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是一种目标极为明确的私益型群体性事件。涉众型经济犯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绝大部分同时也是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被害人及其亲属,一般很少有旁观者参与,这一点不同于泄愤型的群体性事件,其参与者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具有无限制的扩散性,但是涉众型经济犯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挽回集资的本金和利息,这一点亦有别于无特定目标的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事实上,如果挽损问题难以满足,其他一些处理方式也是很难有所成效的,例如,有学者主张应该对涉众经济犯罪的被害人群体完善诉讼告知制度和沟通释法机制、建立审查起诉阶段的被害方诉讼代表人制度,但是这些做法对于化解集资犯罪群体性事件来说,只能作为挽损措施的辅助性手段。另外,就一些公法学者主张的扩展协商制度的适用范围,确立多元纠纷有效解决方式,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等等来谋求化解[1]。这些对于贵州瓮安事件、安徽池州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等发泄情绪型群体性事件或者一些目标型公益群体性事件,如厦门的PX项目事件等等,确实是一种很好的化解手段,但是,对于集资犯罪群体性事件这样一类以挽损为明确目标的私益型群体性事件,从根本上说,是无法通过如此单纯的澄清事实或改变决策予以化解的。
第二,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矛盾更易激化,更易由和平型向涉罪型群体性事件转变。如上所述,如果说对于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和某些具有特定目的的公益型群体性事件而言,合理的沟通和安抚对于平息事件具有很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由于更为关涉切身利益(实践中,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参与人往往来自各个阶层,特别是对于一些社会底层的被害人而言,被害影响更大),且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被害人往往相互认识,甚至在很多案件中,正是熟人之间的推荐才得以参与集资的,因此,该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参与人之间相互联系更为便捷,更具有组织性,生成为群体性事件也更为迅速,一旦挽损诉求被拒绝或没有充分满足,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就极易升级。如在吉首9·4事件中,“非法集资人员将涉嫌非法集资企业法人围堵涌进州人民政府,在一时得不到如愿答复后,便迅速朝吉首火车站聚集,演变成堵塞铁路,拦截火车,甚至打砸抢超市、商店等严重暴力性刑事犯罪事件”[2]。可见,相对于其他泄愤型群体性事件或涉及公益的目标性群体性事件,涉众型经济犯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潜在的危害性更大,提前防控的重要性和压力也更大。
第三,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更为困难,往往“案结事难了”。集资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主要也正是因为集资方的资金链断裂,无法正常维系到期本金和利息的偿还,因此,群体性事件参与人的挽损诉求实际上很难被满足,当前实践中的做法一般是公安机关先对所有参与集资人员进行登记,并由政府接管企业,对其进行破产清算,再根据每个参与人的涉案损失金额将公司剩余资产和追讨的公众存款,进行有比例的补偿,但往往受偿的比例很低。以2008年辽宁营口东华经贸(集团)公司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返款处理为例,根据辽宁省东华返款工作领导小组提供的数据,地级市东华集资群众总数为514人,集资总额3855万元,返还金额1549.25万元,尚欠2305.75万元,返还比例为40.19%。在该市514名集资群众中,返款人数为369人,其中有28人待核查后返款,零返款人数为145人[3]。因此,集资犯罪往往结案容易,但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却断续难了,某些地方政府对未被受偿或受偿不到位的集资被害人往往采取政府补偿的方式,或者是对一些有特殊生活困难的受害人群体建立 “生活困难补助机制”,以求事态平息,但这显然并非常态的做法。
(二)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现状。
第一,当前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日益呈现出向全国蔓延且在特定区域内有全民参与的趋向。仅2008年至今,大规模的涉众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就在各地不断上演。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统计,近三年来,该院接待的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的集体来访高达300余批次3万余人次,每次集体来访多则四、五百人,少则二、三十人[4]。2008年7月浙江省丽水银泰集团遂昌分公司因资金链断裂,不仅未能偿还到期的非法集资本金和利息,且单方面顺延还款期限,引起全县百姓骚动,7月11日晚,约500多人聚集在遂昌县政府门前讨要说法,随后波及整个丽水市区。2008年9月发生的湖南吉首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仅“9·4事件”和“9·24事件”聚集人员就多达3000人,围观群众上万人。另外,当前各地发生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还呈现出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均广泛参与的特征,以2008年湖南吉首事件为例,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中既有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也有个体工商户、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几乎涉及当地全部阶层和行业的人员。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看,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防控不但是一个法律问题,更关涉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大局。
第二,当前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身份认定较之以往更为复杂。参与人中虽不排除有单纯因为被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新型“外衣”所迷惑的真正被害人,但这类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当前更多参与集资的人是持一种投机的心理,即明知自己所参与的是非法集资,但基于“把握时机,在崩盘前退出”的侥幸心理而参与。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是,当前涉众型经济犯罪总体上呈现出金字塔形态,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中亦越来越多地出现如传销犯罪那样的金字塔结构,即一些被害人既是集资犯罪的行为人,同时也是其上一层吸资者的“被害人”,在2011年7月江苏泗洪非法集资崩盘事件中,这种上下线结构甚至多达四、五层之多(当地称为大爪头、小爪头),对于这样一些具有双重身份的群体性事件参与人,如何认定其身份,实际上关系到其卷入集资犯罪中的资产性质的界定,进而关涉所有参与群体性事件者的挽损返还比例的问题。另外,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拉人垫背”现象,即行为人明知集资者已经无力偿还本金和利息,整个集资“金字塔”即将崩盘,但在崩盘信息还未公开之际,采用隐瞒或强制的方式,拉入新的集资参与人,以新入伙者的资产作为自己的利息乃至本金,进而顺利抽身的现象,实践中,这样一部分人往往是消息灵通或有权势的公职人员,这种行为如何定性,也同样关系到集资犯罪被害人,特别是真正受害者的挽损诉求的实现及其程度。最后,在2008年5月,央行、银监会联合发文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之后,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额贷款公司参与非法集资的现象,今年9月,山西省金融办甚至因此向省政府申报关于停止各市县审批小额贷款公司的文件,这些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更促使了当前非法集资的金字塔结构的形成,同样,对于这些小额贷款公司在集资中的双重身份行为如何定性,也关系到集资犯罪群体性事件的化解。
二、刑法防控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认识误区
当前刑法学界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现状,可以概括为:重视对相关集资犯罪的研究,轻视对集资犯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研究;重视对涉罪型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轻视对非涉罪型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较之于公安学和社会学,群体性事件特别是集资犯罪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在刑法学界可谓无足轻重。本文认为,这一现状背后存在两点刑法观念上的误区,本文将其概括为刑法防控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理想主义与克制主义。具体而言:
(一)刑法防控的理想主义。
事实上,当前刑法学界非常重视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集资类犯罪的研究,涉及相关罪名的确定、构成要件的诠释,还包括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益有无及样态、集资犯罪治理的模式选择和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的认定等等各个方面。但是,其中却极少有着重探讨集资犯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之防控问题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只是被作为涉众型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一个部分,用以表明当前相关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严峻形势并强调对其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但群体性事件本身却并未被作为一个有着单独理论质料的问题来看待。这种理论热度的反差,本文认为,无法排除这样的思想认识,即只要控制了作为引发集资犯罪群体性事件之上游的相关集资犯罪,就可以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这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和理想主义的防控态度。
(二)刑法防控的克制主义。
笔者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查询,以“群体性事件”为关键词在“刑法”目录下进行搜索,从1990年至今只有不到20篇的公开成果,且没有一篇专门讨论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文章,而在公安学目录下搜索“群体性事件”则有多达2013篇的公开成果,从中可以窥见一个事实,即刑法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关注程度远没有公安学高。本文认为,这与刑法防控的克制主义思想有关,当前学界更多地将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宪法性的权利来对待,例如,有学者认为联合行动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和宪法权利,刑法在由联合行动权行使而引发的社会问题面前,应当保持基本的理性与宽容,包括立法的“犯罪化”、司法的“犯罪化”与“刑罚化”方面应当谨慎与宽容[5]。还有学者认为,刑法并不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完美方式,即便刑法可以达到较好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基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多原因性,刑法只具有最后的适用限度[6]。也即是说,基于刑法的保障法性质,刑法应该将目光限制在涉罪型的群体性事件上。就刑法作为二次保障法的性质来说,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不说,这导致了刑法在面对当前如此严重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态势时,推卸了本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或者说,造成了其能动性防控能力的不当缩减。
(三)对上述两种认识的不同意见。
1.对于刑法防控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理想主义而言,问题在于,当前集资犯罪的生成环境决定了其发生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必然,是当前宏观经济调控背景下无法避免或者说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正如上文所述,当前的非法集资正处于一种国家政策性导向的高发期,试图完全依赖规制非法集资犯罪来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不切实际的。现实的做法是,刑法应该将集资犯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本身的防控问题纳入研究的范围,用一句俗话表述就是,在无法用中医根治的情况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疗法应当受到重视。
2.对于刑法防控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克制主义而言,事实上,涉罪型群体性事件向来是我国刑法所重点关注的对象,刑法一般通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等等来予以规制,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刑法能否介入未达犯罪程度的和平型和违法型群体性事件?本文认为,就发挥刑罚对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惩罚机能而言,刑法的克制和宽容确实是应该的,但这并不等于刑法就应该退出对非罪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更不意味着刑法应该静候群体性事件发展到犯罪程度才出手规制,事实上,如上所述,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事件的矛盾极易激化,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极易升级,因此,刑法一开始就应该做出与公安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等联手消解群体性事件的努力。另外,惩罚机能仅是刑罚的多种机能之一,且刑法介入群体性事件的对象选择也并非仅限于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刑法完全可以多角度、全方位、积极能动地发挥各种机能,在群体性事件激化为涉罪类型前就予以消解。
三、刑法防控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具体措施
本文认为,在处理和化解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上,刑法应该持一种务实和能动姿态。即是说,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群体性事件的防控,刑法不能苛求一种完整的理论建构,而是应以一种颇具实践性的态度来对待,只要是能够起到预防和化解集资犯罪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举措,都应该受到刑法的关注。具体而言,至少有以下几方面措施值得关注和尝试。
(一)从规范角度,合理地认定集资犯罪的被害人。
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中出现的最为显著的动向就是集资犯罪中的参与人及被害人的情况日益复杂,如上所述,这关系到集资犯罪群体性事件参与人的挽损进而事件的化解。实际上,对其的身份认定首先是一个规范刑法的解释问题。以下将阐述这种新的犯罪动向以及本文的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知对方行为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仍投入资金的行为及其涉案资金的定性处理问题。首先,由于我国刑法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保护法益是金融秩序,而非可放弃的个人法益,因此,这里不涉及被害人承诺问题。那么投资者在明知的情况下仍投入资金,这种行为是否成立可罚的片面对合犯呢?就可罚的对合犯的成立条件而言,有学者认为,如果原本不处罚的片面对象行为超出了必要参与行为的“定型性”或者说“通常性”的射程范围,就变成可罚的对象行为,应该按照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处罚。团藤重光教授即认为在买卖淫秽物品的场合,如果购买者仅提出:“卖给我吧”,这种行为并不可罚,但在购买者积极地给卖方做工作,鼓动对方出售目的物的场合,则应认定教唆犯的成立[7]。同样,如果行为人只是单纯的基于“资产寻租”目的将集资款交给吸存者,这种行为虽然不合法,但也并不存在刑罚的处罚的必要,但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一些“信誉好”、利息高的“爪头”,会对“投资者”进行选择,不少“投资者”必须采取请客送礼的方式“恳求”“爪头”吸资,这时就可以参考总则中关于教唆犯与帮助犯的规定,对其共犯的身份进行认定,其就不是单纯的受害者,事后也不存在受偿挽损的问题,并且由这部分资金所得的利息收益应该作为犯罪所得,纳入真正被害人的受偿资金范围,这样就提高了真正被害人的挽损率,对于提前防范及平息“非吸”引发群体性事件无疑是有帮助的。
第二,明知对方行为是集资诈骗,仍投入资金的行为及其涉案资金的定性处理问题。首先,必须指出金融诈骗罪的法益不同于传统诈骗罪,一般认为,“经济犯罪是指在经济生活中完成的追求经济利益的犯罪,这种犯罪造成了经济生活中超个人法益的损害或者采取了滥用经济生活的工具”[8]。因此,这里也不存在当前在传统诈骗罪理论中发展起来的,从被害人与行为人互动视角审视以投资心态“被骗”的被害者权益保护必要性或者说是行骗者的行为是否成立传统诈骗罪的问题。实际上,这种情况不同于上述明知对方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仍投资的情况,后一种情况中的返回收益理论上是吸资者的经营活动,而此处的返回收益则只能是后加入的资金,即是说,前者的加入实际上是以自己的行动助益着骗局链的维系,因此,从一开始投入资金或者说只要投入资金,就可以认为是作为可罚的对向犯以片面共犯的形式(两者的竞合)介入到了对后来者的集资诈骗中,这样,对于这部分人同样不能作为被害人参与事后的损失分配,其已经收到的利息也应该作为犯罪所得,予以纳入受偿资金范围。
第三,对于集资犯罪中既是犯罪人又是“被害人”的,即俗称的“爪头”的处理。这要分情况对待,对于其作为集资犯罪人的一面,自不待言,而对于其作为集资“被害人”的,要具体分析。如果上线行为人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那么上述第一种情况,应该按照其行为是否超出了参与行为的“定型”予以认定其涉案资金的性质及是否参与事后的挽损补偿(因为这种情况往往是明知对方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如果其上线是集资诈骗,那么应该按照是否明知,来予以认定。
第四,对于上文中所言的“拉人垫背”行为的认定。这种行为本文认为应该视其参与的集资性质而定,如果其参与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那么应单独构成诈骗罪,非吸行为人视情况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如果其参与的是集资诈骗,则其行为并未超出集资诈骗的类型,这时应该视原集资诈骗的本犯是否知情,认定其究竟是单独构成新的集资诈骗还是原集资诈骗的共犯。
(二)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角度,合理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
在当前部分集资犯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其参与人的心理或者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触因有两类值得关注,一是在上文中提到的,为了抗拒司法机关的正当或不当介入,二是在实践中,非法集资往往出现公职人员参与的现象,群体性事件参与人会认为其被害正是在某些代表政府的公职人员的蛊惑下进行的,因此为了发泄对公职人员直接或间接为集资行为人“做宣传”的怒火,而参加群体性事件。对此,刑法要把握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体而言:
第一,从预防的角度看,应从严、尽早打击集资诈骗和没有挽救可能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而对于有挽救希望,特别是涉及面广、影响巨大的非吸企业或个人,要从帮助克服困难的角度,从宽处理。这一点对于稳定正处于“中小企业倒闭潮”和“中小企业主跑路潮”的部分地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刑法可以通过对有挽救余地且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企业主和个人,有倾向性地多判处缓刑,让其有机会继续参与企业的管理经营,甚至于司法机关在控制吸存局面后,有条件地不介入,让其通过合法经营,自行“瘦身”。另外,还应借鉴金融机构对银行坏账呆账的托管模式,聘请有专业资质的公司托管或帮助经营涉案公司业务。总之,在上述情况下,刑法应该恪守谦抑性原则。
第二,从处理涉罪型群体性事件来看,应从严处理涉罪群体性事件中的公职人员和金融掮客,从宽对待社会底层受害人和真实被骗者。事实上,当前公职人员参与非法集资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根据湘西自治州对公职人员参与非法集资做的调查,全州131名厅级干部(其中在职62人、离退休69人)中就有113人主动向调查组说明情况并进行登记[1]。基于其公职身份所具有的号召性和带动性,可以倾向于认定其首要分子或积极参加者的身份。而对于一些社会底层的参与者,其投入集资的往往是全部的养老金和生活费,因此对其所参与的涉罪性群体性事件,应本着避免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的考虑,对其从宽处理。另外,对于金融掮客的行为,从有过错的被害者学角度看,其被害并不具有可同情性,且在实践中由于其受损较一般集资参与者更大,且更希望政府介入处理,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往往起到更多的煽动作用,因此,更有理由对其从严处理,相反,对于真实被骗者,则更多地应从被害同情的角度,从宽处理。
另外,还应重视对刑罚的安抚机能的发挥,以稳定群体性事件参与人的情绪。当前学界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应该对非法集资改变规制路径,将其纳入证券法的监管范围,而非上升为犯罪,用刑罚来处罚,本文同意刑罚对于因制度性造成的民间集资行为是起不到威慑和预防效果的,但对于一些造成严重的群体性事件,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且事后无财产进行退赔的集资犯罪人,可以说,对其动用刑罚以安抚被害人,是平息群体性事件的唯一选择。
[1]杨海坤.群体性事件有效化解的法治途径[J].政治与法律,2011,(10).
[2]杨正国.关于处置湘西州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的做法和启示[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5).
[3]相庆梅,刘 东.涉众型经济犯罪对受害人补偿的政府角色——“以蚁力神事件”为例[J].理论探索,2011,(3).
[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矛盾化解机制研究[J].法学杂志,2011,(1).
[5]蔡道通.刑法的理性与宽容:面对联合行动权的行使[J].政法论坛,2006,(1).
[6]高永明.群体性事件刑法规制的限度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2011,(5).
[7][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M].东京:创文社,1990:433.
[8]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
PreventionandControlforEconomicGroupCrimeEventinCriminalLaw
JIA Jian,XUAN Gang
Due to the increasing occurrence of economic group crimes,the range,the funding and number of people involved in cases are in rapid expansion,causing the serious social problems.So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must be noticed by the academics.Bu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basing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idealism and restraint have been ignored in criminal law research.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e mus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ms and applicable policies,reasonably prevent and resolve the economic group crimes with pragmatic attitude.
Economic Groups Crime Event;Misunderstanding;Victim Identification;Punishment with Mercy Policy
DF6
A
1674-5612(2014)03-0047-06
(责任编辑:李宗侯)
2013年度司法部基金项目《行政法与刑法衔接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3SFB3012;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变迁与刑事政策》,项目编号:12FXB005。
2014-04-16
贾 健,(1983-),男,安徽芜湖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学、刑法哲学;宣 刚,(1980- ),男,安徽凤阳人,南京师范大学刑法博士生,安徽科技学院法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学、经济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