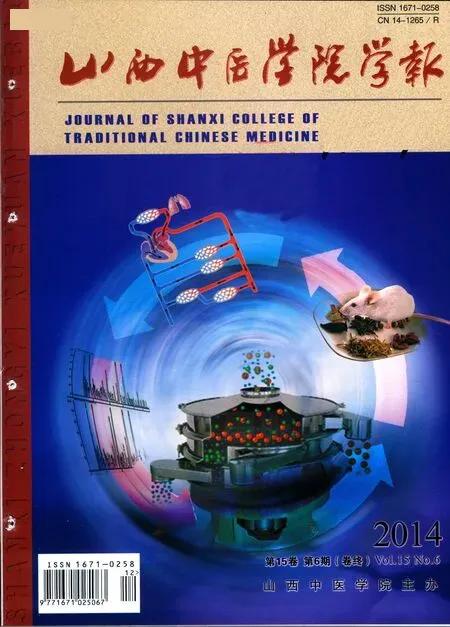大道至简
2014-04-05曲进
曲 进
在印象中,我很早就知道大道至简这一成语了,虽然平常也时不时地随生活或工作情景记起它来,并在面对那些复杂纠结的事情的时候借以鼓励自己的心灵,但对其进行深究,并与科学、艺术甚至是科学与艺术相融汇通的传统中医药学联系起来却是最近的事。
关于大道至简的出处,文献中说法不一,有人说源自老子的《道德经》,所谓“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但也有人说《道德经》里并没有提到大道至简,其只不过是后学者通过凝练老子的思想和智慧总结出来的。大道至简的语义及其要表达的思想就像大道至简本身一样至简、至深而纯朴,那就是决定和支配自然及人间万物万人变化之始的道法是极其简约的,虽然其变化的始终之间有纷繁复杂的万千衍化,但其繁杂之中却依然遵循并接受着至简之道的支配,普适性地利用着一种至简的机制。追朔历史,人们对这种至简之道的向往和探求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提出并讨论过至简的命题。除了“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老子还曾表达了“少则得,多则惑”的思想。由《孟子·离娄下》中的“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之句形成了“由博返约”的成语,教导学者学会应用由博然升华至简约的学习方法。据汉代刘向《说苑》的记载,孔子曾说,“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这形象地表现了孔子对简朴素雅的向往和喜爱,而这也充分地体现在他的“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的思想中。南宋诗人严羽在《历代诗话·诗法家数》中有“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的论述,由此衍生出的“删繁就简”从古至今都不只是一个用于修饰文章的成语,而更多的已经成为人们在处理复杂事物的时候加以应用或希望建立的思维认知方式及其分析和解决方法。其实要是更深一层地说起来,古汉语就是一门简约之至的语言,像《道德经》这样至今都需要解读并令人敬仰的文章,数来也不过只用了五千个汉字。
而在西方,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就在一直孜孜以求物质世界至简的本原,那时候的德谟克利特等就提出了许多大致与古中国哲学家相似的关于构成物质世界本原的思想,就如原子、水、土、火之类。到了二十世纪初,不知是受到中国老子的影响,还是源于独自的灵感爆发,欧洲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Mies Vander Rohe在建筑设计中提出了几乎与老子“少则得,多则惑”思想完全一致的“Less is more”的理念,这既成了西方建筑设计的核心风格,也是简约主义在西方的起源。至现在,简约主义的设计思想已经成为流行在艺术品和产品设计中的一种极具营销冲击力的时尚,成为被艺术家们时常提及的一种思维方法以及进行艺术创作和凝聚在艺术品中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就像计算机天才乔布斯把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作为苹果电脑的Logo,将Bite的读音和语义映射于计算机的Byte之中那样独具匠心的简约主义创意。
真的,细数起来,充满在哲学和艺术中的至简思想和方法比比皆是,或者更准确地说,哲学和艺术本身就是至简的学问。哲学之所以具有普适性的精准,就在于她是在发现和勾勒世间万物运动中那个具有共通边界的轮廓,而艺术之所以通美,就在于她从世间万象中能如“剥茧抽丝”一般地抽提出其中原本简约然却至美的线条。
由此说开,不仅仅只是哲学和艺术,而且科学的发展也同样在悄然步入大道至简的认识轨道,用以去揭示那些隐含于物理和化学运动乃至生命行为的深层,然却形成并决定着它们的运动规律的至简机制。例如,物理学家正在寻求支配自然界万物运动的那种统一的力,它就像存在于物质时空中的一个“幽灵”对物理学家们充满诱惑;构成难以计数的化学物质的基础是有限的化学元素,而那些绚丽多彩的化学反应无非来源于简约的原子结构及其量子力学规律;人的行为衍化出了变幻莫测的人间百态,然其也只不过都是生物学欲望的表达,如果理解了欲望产生的身心机制,我们也就能从人间百态的变幻莫测之中找到安顿自己心灵的方法;在传统的生物学视野中,生命系统无疑是异常复杂的,可分子生物学在DNA中发现的基因编码规则以及在分子水平普遍利用的能量耦联机制却又是异常简约的;生命科学在分子水平发现鉴定了众多的生物活性分子,但却发现分子的生物学作用的普遍规则是一个分子在共奏生命乐律中常常扮演多种“角色”,面对这一“景象”,生物学家不免也生出了像老子“多则惑”一样的感叹,于是一种被称为compendium的简约性研究方法以及系统和网络生物学被“催生”出来;数学之所以能“凌驾”于所有分科之学的顶上,就在于它能将几乎所有的物质运动规律用简洁的数或代数的公式、方程或函数表示出来;控制论仅通过输入输出认识“黑箱”,用混沌、模糊或灰色理论及方法认识、解析和控制复杂系统,都是于复杂中发现和应用简约的思想和方法;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基本原理就是并不难接受的简单事实,然而由此做出的推论却根本性地改变了自牛顿以来物理学的根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谈到物质运动本原的至简规律以及哲学、艺术和科学认识其的至简方法,就不能不论及医学,更不能不论及传统中医药学,因为我们只要潜心分析一下医学一路走来的历程,就不难发现它正清晰地显现出一条“删繁就简”的发展轨迹,也正是在这一发展轨迹上,我们发现现代医学与传统中医药学正在相互交叉。例如,目前医学家们已经认识和能够诊断并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系统中的疾病大约有近两万种之多,但病理学和分子病理学的研究却日益表明,那么多的疾病其实是由极为少数的病理生理学过程或分子病理学机制构成的,有许多疾病的发生常常在分子水平普遍地利用着同一类分子机制,这正是传统中医药学“异病同治”理论及方法的基础;许多疾病的发生和演变就如一个链条互为因果,如果能控制该链条关键节点上的某种疾病就可以控制由此继发的一系列疾病的发生,而传统中医药学发现的“未病”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由此使得传统中医药学“未病”理论及方法的光辉耀眼地反射出来;慢性身心性疾病的发生有许多原因,但细胞衰老却是它们发生的共同生物学基础,如果能够揭示细胞衰老的生物学机制并切实找到有效的延缓方法,那么,我们就可能取消这一类疾病发生的内在生物学基础,由此我们便能理解传统中医药学为什么是那样的重视延缓衰老的养生;当现代生物医学在生命的分子水平面对大量分子复杂的生理和病理行为而倍感“多而惑”的时候,我们却重新注意到传统中医药学把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概括聚类为精、气、血、津液四类基本物质形态,抽象出阴阳五行相互作用规则,把疾病综合成“证”并创立“辨证施治”的理论及方法,这与生命科学在分子水平正在应用的compendium方法以及系统和网络生物学虽不谋,却相合,虽殊途,却同归,由此研究开来,可生动地指示出生物医学认识生命和诊断疾病的一种全新,但却是非常简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如此看来,大道至简是深深地渗透在哲学、艺术和科学之中的,深谙其真谛,应用其思想,真的可以拨亮我们很容易迷惑的心扉,以使我们能从表象纷繁嘈杂,甚至令人迷乱的事物人情中透视出那幅本原却异常宁静集美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