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骥 物质形态给出的思考起点
2014-04-01
从陈文骥大量的工作中能够看到一个“提取”的过程,包括早期作品中出现的静物、风景,他们都是对现存的抽离和放置,现阶段的作品中突显抽象因素的同时具有着很强的物质性,陈文骥用“写实性”将物质的“质感”、“雕塑感”、“空间性”体现在画面中。“写实”是陈文骥在绘画中持续性的方式,在他用这一方式构建出带有抽象因素的画面时,也就与我们概念中的抽象表达区别开来。陈文骥并没有强调自己必须要进入一种所谓的抽象表达。他认为对艺术家来说应该用更适应、擅长的方式来完成自己所要表达的真切内容,这对艺术家来说是最重要的。而陈文骥的“写实”方式跟他所经历、掌握的一些因素有关,“针对我所掌握的一些资讯,所学到的一些知识和我对造型艺术理解的程度,我感觉我比较适应这种表达。我希望我的每一个表达都是有一定的依据,这种依据可能在我的内心会发生转换、提升、改变。但是我想我还是比较习惯于在一种客观因素上去认识事物再去反应事物。所以我认为我跟完全的抽象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在陈文骥的表述中,他提到了在创作中对于具体依据的转换、提升、改变,而这个过程便对应到“提取”的过程,那么陈文骥所提取的是什么?陈文骥虽然以写实方式来呈现,但是他并不是将物本身直接搬到画面上,他的物与直接的物象有所关联,但并不是物
象本身或本质的内容,而是更多的存在于其自身理解的一个结果,它不是具体指向性的,但是来源是有依据的。所以在陈文骥的转换、提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复杂的转变。在陈文骥的状态中,他认为他要建立自身对事物的限制和约束。
建立限制不仅仅是陈文骥面对事物时的意图,他还希望达到某种自己建立起来的理念来限制自己。陈文骥认为,“艺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艺术形式可以开拓出无限的结果,但是对艺术家来说,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家都是一个有限的成分,在无限当中做一个有限的工作。那么作为个人独立的态度,必须要强调个人的独立成分,这个独立成分就是必须用一种有限的因素来强迫它然后再来体现它。所以我认为在自己的艺术表达里面,有限因素或者是艺术态度对我目前是最重要的。这对我来说是个人的立场和行为,有了立场和行为之后才转换到对事物的认识以及进一步的表达。”
观看陈文骥的绘画,呈现的更像一种中立态度,并且具有克制的状态。陈文骥强迫自己在一个限定范围内来建立自己,建立他的表达和表达形式。但是他的表达不是在绝对理性层面上,“我还是承认感性的、人性的因素所存在的意义,我也更多的能理解人性成分下的克制态度,所以这里面会产生矛盾性,这种矛盾就很符合人性的本质,人本身在约定之下能反映出人本质的能量,我对这种东西很着迷。”
作品完成的过程中包含了艺术家的思考层面,在陈文骥注重人性的层面上,他在创作中并没有表象上的人性抛离,“你们看到的是我要给的一个结果,提供了产生思考的平台和参照,但是在建立平台之前,我所要建立的思考点首先在我内部就消化掉了。”
从早期作品中对生活对象的布局到对城市环境的自我反应再到近阶段抽象几何对象的构置,陈文骥一直在消解一种具体性,早期作品中的叙事成分和抒情成分还是明显的,而在现在的作品中陈文骥所抽离的就是这些内容。虽然早期作品中尽管有叙事,但它们并没有具体指向,它只是某种叙事范围,画面的不确定感很明显,所以后来,陈文骥就更强调这些因素,甚至将叙事抽离。陈文骥希望他的作品变成仅仅是一种对物态的体验过程,成为只是用感官来理解的对象。那么谈到这里,所谓的感官理解是否就是被普遍认为的对人的视觉和视觉心理的关注研究?陈文骥最初本意希望能带来体验,但不仅仅是视网膜的刺激,还是精神上的,通过视觉产生精神上的体验过程。陈文骥在表达过程中借用了基本的物质几何形态、色彩过渡变化的基本因素来表现,而这种面貌容易使观者进入视觉反应,陈文骥认为是其无意间进入了这个所谓人的视觉和视觉心理的语言系统,但这并不是他一开始所要追求的目标。
在陈文骥的作品中携带着一种工业意识。“我对工业时代有种特殊的迷恋,因为我当过两年的工人,而且我的父辈都是工人,所以我的基因里面有着对工业特有的感情,我对工业时代所产生的材料质感以及它的构件特别着迷,以及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工业性,这些东西都特别能影响我。可能在我的作品里面就自然的反应出了我本质上的倾向。”陈文骥希望画面里有工业时代的那种理性和坚定以及厚重、规则,但他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还是把所向往的工业文明的特性适当的人性化了,“我的作品里应该说没有彻底的工业因素,我是把工业时代已经生锈的形态经过我的打磨以后再呈现出来。”
陈文骥作品中的颜色虽然有过渡,但整个色彩属于一个阶度,这种刻意的控制是在消解色彩的指向性,“我其实不希望色彩在里面占过强的主导作用,尤其不希望他带有感情成分,我希望这些色彩是在物理层面的反应,使人更容易进入对物的形态理解,发生一种理性的感触过程。”色彩在光感下呈现着过渡性,这种过渡性引导着物质形态。陈文骥希望观看者能通过对物本身形态的过渡性来引发自己内心的变化,“我希望我们的眼睛有一种触摸能力,从而产生触摸式的理解过程,我想让大家在物体的起伏过程中能一点点随着色彩的深浅变化,产生很细微的、过渡的体验能力,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习惯是把物体置入具体的一个时态中来理解,即光对物的照射下的物理反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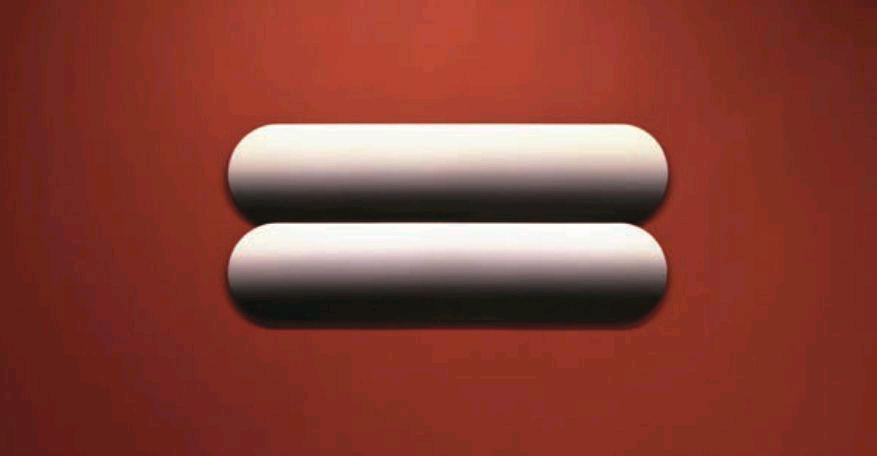
形式化在陈文骥的作品中有着一定的存在成分,他在设定某种形式,同时也在给自己做出限定。他认为这个设定过程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个执行过程,也是自我完善的理想过程。陈文骥选择的基本元素是圆形、柱体,虽然近阶段的作品在外形上存在变化,但是基本形态还是圆柱体、圆形这种基本几何形态。陈文骥认为对这种形态的表达很贴切,“我是希望我的作品在一个空间环境里面时他只是一个物象而不只是单纯的一件绘画作品,我建立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我会考虑空间关系,我希望作品在某个空间关系中能产生特有的视觉反应,所以我在物象的形态和处理表现上,甚至幅面的大小上,内心都会有一个具体的判断,所以我这种表现已经不是对一个独立单纯的画面来要求,而是设想他是空间里的视觉形态。”
陈文骥的绘画越来越趋于抽象状态,但是艺术家抽象思维的建立从绘画之初就建立了。“绘画把一个真实物象转换成平面的时候,这已经建立起抽象的思维态度,绘画不是简单地模拟过程。我们过去总认为画具象,甚至画写实都是直接搬照对象,实际上,我们在搬照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抽象的思维来转换我们对具体物象的一种认知结果,所以这里面包含了一些抽象因素,只是说我们还没有将提升的对象、具体的形象关系拉开更大的距离或者就是说还没有达到更纯粹化、更极端化的结论。”陈文骥认为其今天的表达,对自己所表现的事物存在更多的自我立场,他更强调观众在介入某种实际现象的时候在某一个具体的范围内使其变得更具纯粹性,“我希望单纯加上纯粹来突显我对事物认知的倾向性,所以可能在视觉上呈现出抽象化的反应,但其实是极端化的作用,因为这个极端化让我的思维表达更加单纯。”(采访/撰文:王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