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彦 建构中国抽象艺术的批评话语
2014-04-01
I ART:抽象艺术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不同阶段?各阶段有怎样的特点?
何桂彦:简单的分法,是将中国抽象艺术30多年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90年代、2003年至2013年是第三个时期。80年代抽象艺术主要的特点是,反叛既有的现实主义与写实体系,捍卫艺术本体的独立,并且向西方抽象艺术学习。但是,在80年代,抽象不仅仅涉及艺术形态和风格的问题,而是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几乎在每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抽象艺术都受到了批判。中国90年代的抽象艺术除了油画领域的丁乙、尚扬、王易罡、于振立等,主要还是发生在抽象水墨或者实验水墨领域。我曾在《抽象水墨的类型》一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我们可以将90年代的抽象水墨分为三类:表现型抽象、媒介型抽象、观念型抽象。譬如,和80年代那种追求形式反叛的抽象作品不同,水墨领域的抽象出现了新的变化。本土文化的因素:如张羽的“意象性表现”、阎秉会的“书写性表现”等;媒介性的因素:如胡又笨对宣纸的使用,刘子健的“拼贴”,杨诘苍对墨色的表现等;观念性因素:如邱志杰“书写一千遍兰亭序”、王川的“零度·墨点”等。第三个阶段之所以将2003年作为起点,是因为在这一年中,高名潞策划了“极多主义”展,栗宪庭策划了“念珠与笔触”展。这两个展览都与抽象有关,更准确的说,绝大部分作品是观念性的抽象。同时,这两个展览对新世纪以来的抽象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阶段抽象的特点,体现在艺术家普遍重视个人化的方法论,强调观念的转化。
I ART: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创作实践大致分为哪些类型?请结合实例进行一个简要分析。
何桂彦:主要还是表现性抽象、媒介性抽象、观念性抽象三个大的领域。不过,近年来出现了许多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和传统意义上的抽象、西方现代主义意义上的抽象都有了很大的区别。例如,王易罡近期的《浅绛系列》就将传统的图像与西方的抽象图式予以结合,作品既有波普因素、媒介性因素,又有传统的书写性因素。如张羽通过手指所形成的“指印”,李华生、路青那种反复出现的“格子性”抽象,孟禄丁《元速》系列的观念性,以及更为年轻的一批抽象艺术家,如王光乐、雷虹、杨黎明、刘文涛、张帆、徐鸿明等,他们的创作为当代抽象艺术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未来的抽象艺术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我现在无法给出明确的判断,但有几个创作趋势是值得注意的:一、大多数抽象艺术希望自己的作品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经验相结合。二、艺术家会更自觉地关注自身创作脉络的演进和艺术史的上下文关系。三、比较重视个人化的创作经验和风格特征。四、抽象形式的表达会注入越来越多的观念性因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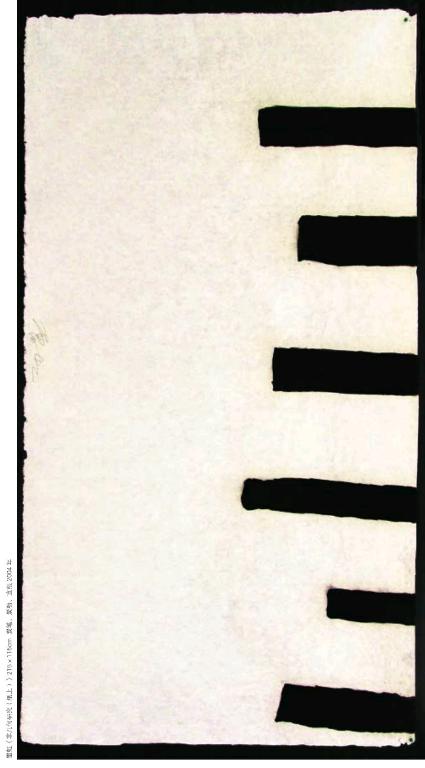
I ART:中国当代抽象艺术具有哪些自身或者说本土化特点?其生成条件是什么?
何桂彦:总体来说,中国抽象艺术的发端时期并不具有像西方现代抽象那样的历史与文化条件。因此,支持中国抽象艺术发展的并不是所谓的形式主义传统,相反,仍然是由社会学叙事支配的。之所以如此,这跟20世纪以来,整个文化与艺术机制的建立有关。譬如,尽管20世纪30年代,像“决澜社”的艺术家,或者更早的一些艺术家,如林风眠,他们曾将西方的现代风格引进中国,包括当时一些艺术家在抽象领域进行探索,但是,从40年代初“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再到50年代对艺术进行社会民族化的改造,特别是“文革”时期的“高大全、红光亮”创作体制的建立,在近半个世纪的时期里,早期的现代传统,或者说与抽象艺术仅有的一点知识,都完全被历史改造了,被遮蔽了,被遗忘了。
“文革”结束,紧接着是改革开放。这个时候,一些艺术家才发现,我们除了社会现实主义之外,其它的均一无所有。虽然1979年吴冠中提出的“形式美”在美术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但客观上讲,吴先生所讲的“形式美”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抽象。因此,在整个80年代,中国的抽象艺术家都需要向西方学习,必须借助西方抽象艺术的参照系来形成、发展个人的抽象风格。我们会发现,中国虽然在80年代缺乏像西方抽象艺术所具有的理性主义哲学与工业化的社会环境,但仍然出现了抽象艺术。这就是本土化特点的显现。从一开始,真正推动抽象的,仍然是社会学的叙事。为什么90年代的抽象会大量地出现在抽象水墨领域呢?其中,最为核心的原因就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艺术在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语境中,需要考虑自身的文化身份问题。而水墨正具有这种先天的优势。因此,全球化的语境与来自文化身份的焦虑,都会成为催化90年代抽象艺术生成的条件。
I ART: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创作是否也存在问题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何桂彦:我个人认为,当代抽象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出现了许多“伪抽象”的作品。所谓的“伪抽象”主要是指某些艺术家假借抽象艺术自身的边缘性和1980年代以来的那种“前卫性”来寻找进入艺术市场时的捷径。这也是当代抽象艺术最大的、也是潜伏在抽象艺术家内部的敌人,其隐蔽性和破坏性将自不待言。因为,“伪抽象”与抽象艺术都有同样的抽象外观,仅仅从表面的形式上看,好与坏、有意义和无意义很难用有效的方法进行区分与甄别。同时,从视觉心理上讲,只要作品中不出现任何具像的形体,摆脱作为符号性图像带来的直接阐释,那么都可以被看作是抽象艺术。
这样说可能反而会把问题复杂化,但可以肯定的说,抽象艺术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不比具象绘画少。在这里,我觉得还应把两个问题区分开。
作为艺术爱好和兴趣,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抽象艺术的创作。如果从这个层面讲,就不存在“真抽象”与“伪抽象”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学术的层面讨论,就必然会涉及“真”和“伪”的问题。因为艺术史仅仅只关注那些有突破价值的艺术家。所谓的“伪抽象”也就是仅仅只有抽象的外观和形式,缺乏自身的创作逻辑、问题情景和艺术史的上下文关系。绝大部分都属于高级的装饰画。
I ART:今天对中国抽象艺术的批评是否在以西方的体系作为参照?其适用性是怎样的?
何桂彦:西方抽象艺术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有非常完整的艺术谱系与内在脉络,这个系统到1960年代就十分完善了。这是我们无法与西方比较的地方。同样,西方抽象艺术的发展仍然得益于哲学、艺术批评、艺术理论的支撑。譬如康德的“形式的合目的性”与“审美的无功利性”、罗杰·弗莱的“有意味的形式”、格林伯格的“形式简化”、罗森伯格的“行动绘画”等等。从80年代以来,中国的批评家就开始学习西方的这些批评话语,这个过程在今天仍然没有完全结束。毫无疑问,西方的批评话语对中国的当代批评是有启示和推动作用的。但是,如果考虑到批评的有效性、适用性,那么,中国的批评家就需要结合本土的文化与艺术轨迹,以及艺术创作的实际情况,建构一套新的批评话语。很显然,面对今天多元而活跃的创作状况,简单地套用、模仿西方的批评话语肯定是不会产生学术价值的。
I ART:对中国当代抽象艺术批评话语的建构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
何桂彦:批评话语与艺术实践必须做到有机的统一。一方面,还得取决于艺术家能否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但另一方面,如果从国际化的视野出发,关键的症结还在于批评家是否能够建立一套有别于西方抽象艺术和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艺术史话语,将中国的抽象艺术与它身处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语境联系起来,将它放在传统与现实的历史维度下重新考量,从而在艺术史的梳理与书写中呈现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而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中,高名潞、栗宪庭、李旭、易英、朱青生等批评家对抽象的发展曾做了大量的推动工作。2008年,我曾在偏锋画廊策划了“走向后抽象”的展览,邀请了数十位艺术家参加。之所以强调“后抽象”主要是基于三个目的:一是希望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以抽象表现主义所形成的现代主义传统,以及与之相应的批评模式拉开距离;二是要找到一种不同于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0年左右评价中国抽象绘画的批评话语;三是想去讨论近十年来,中国抽象艺术出现了哪些变化,尤其在方法论与艺术本体方面所带来的可能性。对于未来抽象艺术的发展来说,原创的抽象理论与批评话语是十分关键的。(采访/编辑:王薇)
